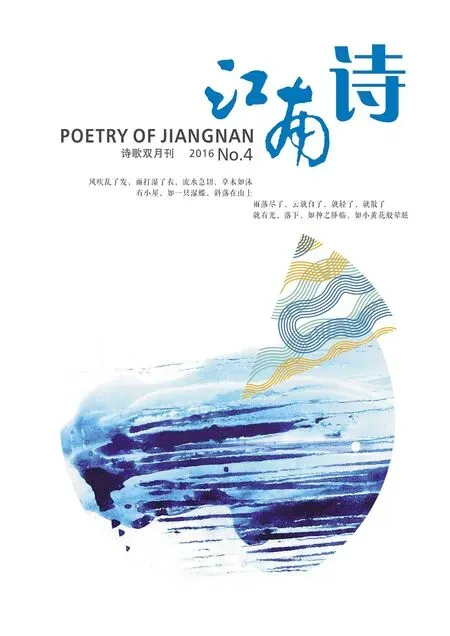流沙河的诗书生活
2012-04-29冉云飞
冉云飞
孟子曾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人生之至快!其实从学生这方面来看,更是切望得良师讲授,以期在析疑解惑、向善求真、为学做人诸方面日有所得。英才固不易得,然良师亦罕见,这是时代之病,无可如何。小子生于寒素之家,求学大不易,虽遇多数老师心地善良,为人勤谨,然良师终未得见。此与幼年失怙,均为我人生隐痛。未曾想,到得社会,复有求知问学之乐。人生有幸,幸而能得向沙河先生问学请益,未尝少间,于兹十数载矣。同住一院,过丛甚密,时得晤聚,以补腹俭之病。周日侧身二三师友间,品茗论学,奇文共赏,交通中外,纵横古今,聆听先生(为方便起见,下文直呼其名,非是不恭,为文求简)幽默风趣的谈吐,与众不同的识见,人生复夫何求!然思想见解,为学所得,终究人各有执,互相辩难,在所不免。惟真理是尚,和而不同,朋而未党,参差多态乃人类幸福之源,是我们这些师友乐而遵循的。
没有学生
诗人李钢为文诙谐有趣,大异重庆诸多为文者。几年前,我们曾于曾家岩餐聚,饭桌上用古诗逗趣,提及重庆大世界之桑拿池名“云梦泽”,为他所取。“冉匪,你是晓得的,云梦泽固是不小,但岳阳城更大啊”,“李老贼(读若脧),吾喜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啊”,听者无不绝倒,相与拊掌大笑。他曾在《我看诗人流沙河》一文里述及他与流沙河交往诸多趣事,令人莞尔,而“流沙河赠书”一节,可堪捧腹。首则“送给李钢同志”,次则“李钢同志雅正”,三则“李钢同志赐教”,四则“李钢垫枕”,五则“李钢我儿跪读尔父手谕”。李钢小流沙河二十岁,属晚辈后生。然李钢生性诙谐,殊无恶意,无论长幼,必与对方谐谑文骂而后快,故流沙河以“我儿”谑之,良有以也,可谓至当。
流沙河可谓有“儿”,且此“儿”大佳,但绝无一个学生。你可以师事之,他必不承认你是他的学生。一来,你师事之,以他的谦谨低调,必不接纳。当然你私心必师事之,他亦强阻不得,终是不复强阻。但不管你怎样师事他,他绝不以老师自居,了无其事,一如恒常。二来,你要自称是他学生,他虽不发表“破门声明”,必敛色辟谣,谦称自己尚是学生,何来学生?当今社会,好为人师者,正复不少。后辈与之交接,即以学生目之,于是学生几遍天下。异日必以师自居,后辈稍有怠慢,即斥之不尊宿学耆老,无端生出许多沟洫。流沙河则是人师尚不为,何况好为?再看当今所谓学生,未晤一面,未接一言,未闻其学,只要他是名人,轻者去信谀扬,溢诸纸墨,希冀套磁,以得提携。重则非泰山北斗、硕学大师,无以名之,远超古代拿死人钱财的谀墓高手。于是不学之学生蚁聚不入流之大师周围,师生互捧,几成潮流,淹没众议。至于学界之门派自铸,一些“养猪博导”(一年招十几乃至几十位博士之博导,吾乡农家勤快之养猪者尚不及此数也)近亲结婚,自产自销,形成拱卫之势,师生关系则与旧日江湖帮派无二。像流沙河这样特立独行、低调自洁的人,友必严择,必无多人,何况朋而党之?
犹忆当年初至流沙河家,他让小我两岁的儿子鲲鲲称我叔叔,使我惊悚离座。经我力争,改称冉哥。这种平视后辈,视晚生为友朋的老派风范,真是古风可仪,虽然把后生小子如我吓了一大跳。有此种风范,他岂肯随意视人为学生,你视其为师能得他认可,除非泛指,实属不可能。我虽向流沙河问学请益十几年,亦颇有自知之明,从不敢以他的学生自居。一旦有不明就里者,目我为他的学生,必戒惧而澄清之。一则他的为人及学问,我万不得一,辱没他风范及门墙(此处泛指。其实他应无门墙,因他无学生且从不以导师自居)的事,万不可行;二则,我虽不才,然尚知守拙,从未敢以谁的学生自矜。何况我从来认为,不必囿于名分上的师生之伦,问其学,得其实,乃求真之要诀。
流沙河虽没有一位真正的学生,但只要事关文化的讲座,大凡学校、文化团体有所请托,在身体健朗之时,写作暇余,他还是愿意去开个讲座的。此种讲座固与顾炎武先生所讥之“若徇众人之好,而自贬其学,以来天下之人,而广其名誉,则是枉道以从人”(《顾林亭文集》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大不相同。亦与明代御史倪文焕所诋周宗建的“聚不三不四之人,说不痛不痒之话,作不浅不深之揖”(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九)之讲伪学殊异。这些讲座我大多听过,举凡今年在成都市图书馆的《我说成都》、《语言与方言》,市政公用局“首期语言文字评估工作培训班”之《文字与文化漫谈》,西南交大的《陵墓设计之人文内容》等,大多能洞幽烛微,不唱高调,细明心曲。不特如此,他对晚生后辈的向学热情,历来勖勉有加。在西南交大讲学结尾,用下面这副对联,表达他对莘莘学子的深深祝福:“正当花朵年龄,君须有志;又见课堂灯火,我已无缘”。
对知识的纯然热爱
西哲罗素曾说他的人生有三个支撑点:一是对爱的渴求,二是对人类苦难有着不可忍受的同情心,三是对知识的纯然热爱。其余二点先按下不表,单是对知识的纯然热爱,不少人一生一世无一刻达此佳境。生活艰迫,谋生不易,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除了偶读利于考试晋职的实用书籍外,别无所观。这固不足厚非,然终究是人生的遗憾。至于把读书求真,当作人生绝大享受,且长期坚持不辍,真正算得上读书人的,以我有限的交往和观察,惟流沙河能当之。
流沙河一生坎壈,二十一岁时,父亲被“人民政权”在土改中枪毙。小子早岁失怙,深知其痛,何况他父亲是异常血腥的处斩,宁不痛心疾首,暗自饮泣?与先生交垂十五年,无一词及此,可见隐痛之深,不足与外人道。至于八一年在《自传》里说父亲被枪毙“是应该的”,这样悲痛难言的掩饰,正好表明强权者的残暴无比,杀了你的亲人,还要你白纸黑字说杀得好,以表忠心。一九五七年流沙河荣登钦点,贾得大祸,从此二十二年大好时光在苦厄郁闷、劳其筋骨、被人孤立中度过,偷活草间。为求一饭之饱,满足当政者的惩处,拉车、解锯等无一不做,至于挂牌游街,自取其辱更是不计其数。罹此大祸,义无再辱的耿介之士,弃世见捐,更多的人则消沉自毁,郁郁以终。
而流沙河的选择不同,他依旧利用一切能读书的机会——其中有两年在文联资料室当资料保管员——勤读不辍。例如他猛读文字学如《说文解字段注》等小学书籍,曾撰成十万字的《字汇漫游》,可惜此稿已佚,但人们在《书鱼知小》、《流沙河短文》等书里,不难看出他早年勤读所结下的慧果。他的求真好学,几乎到了无书不读的地步,彼时读了不仅无益,而且可能得祸,更不用说将读后所得发表以赚取薄酬。除了古人友他、不欺他,能安慰他孤寂抑郁的心灵外,没有不计眼前利害成败得失的超然态度,能有此种疯狂举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曾在地摊搜得《中国古代天学史简史》一残册,他马上问是否是陈遵妫的,真令我叹服他的博闻强识。
无书不读,固是书痴才能做到,然从善如流,服膺真理,便不是一般书痴所能企及。只有具备真正的求真态度,亦即对知识的纯然热爱者,方能做到。庄子早就告诫过,以有限的生命追寻无限的知识,完蛋了。但后继者并不放弃,还提高了调门: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世界浩瀚,未知之事,不知凡几?但为什么古人还要悬的过高如此?这是明知人类所知永远有限,而向无限的知识挑战的行为。在向无限的知识挑战里面,便有无数怀抱着“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读书人,一点一滴地剔爬、考订、辩难、正误的不懈努力,在求真之道上披荆斩棘,使真知犁然自现。常于求真道路上纠谬求知、析疑辩难,自然不免偶有错谬,也遭别人指陈,流沙河亦不免。十年前,何满子指陈流沙河有一联不合平仄对仗,流沙河不仅承认其误,后来还与何满子成为朋友。为掌握入声字的问题,特意从我处借得一册关于音韵学的线装书,编出入声口诀八大段。此后佳联频出,再无此种错误。
更难为得的是,不仅名家指谬纠错,他乐于承认。即便是后生晚辈指陈纠谬,他也从善如流。一位山东网友祁白水,因喜好流沙河的书,与我在网上相识。他在《书鱼知小》里读到《花椒古称椒花》一文,得知流沙河说花椒不开花,即以他们沂蒙山区花椒要开花来纠谬,让我将纠错的信转达给流沙河。收得此信的第二天,流沙河即回信如下:
祁白水先生:谢谢你的指正。我刚查了辞海,得知花椒真是要开花的。我未观察到庭院的花椒树开花,导致我的错误。世间万事皆学问,疏忽大意不得。在我,这是教训,以后将写文纠正之。流沙河04.10.20在成都。
日前,我读《旅游三香》一文,看到先生提及“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为宋人作品。我打电话说提醒他,说这是韩愈的作品《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中的一首。屈守元、常思春主编的《韩愈全集校注》、陈迩冬《韩愈诗选注》以及一般的合集选本都敬选不弃,就是他曾在《从蒲陶到葡萄》一文里指陈其错误的《唐诗选》(中社科院文学所编)下册里也有。他说大概是以前读《千家诗》,误记为宋人作品了,而且在电话中接连表示谢意。其服膺事实也如此,真可算一位对知识纯然热爱的“职业读书人”(流沙河有“愿做职业读书人”一文述其志)。
月旦人事
流沙河是个幽默的人,他第一次到我家,正值小女出世,我在医院照顾内人,家中只有彼时已年过七旬的母亲。他和师母送新毯子新衣服来庆贺小女诞生,家慈不认识他。他便告诉母亲说:我姓流,流汤滴水的流。至今犹能忆及母亲转述他的自我介绍时脸上的笑容,连连说他真是个异人。转眼间,母亲已弃不肖而去,小女业已读三年级也。
幽默自嘲,好文讥刺,历来是四川人的传统,流沙河的《Y先生语录》堪称此中经典。惹得仿作迭出,如冯川的《洋博士出丑记》等。一时间,寓讥刺于搞笑的作品,在四川大行其道。本来,褒贬贤愚,讥议时事,关心民瘼,以谑语出之,书生旧病,我等不免。但若说衡评论人之一语中的,还是流沙河老辣劲道。
台湾进入民主社会后,李敖这几年的表演,俗滥无比,议事论人,游谈无根。尤其是对他专制者的赞美,给中共飞媚眼、送秋波,让人如吞苍蝇,几欲呕吐。对此,朋友们各有自己的批评,不尽相同。但只有流沙河用《庄子·逍遥游》里的一段话来评价他,最惬我意:“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民主社会,言论自由,人人可批评政府,不独李敖所专有。勇气变得次要,关键是要说得在理,有见地,能洞悉他人所无。而李敖胡言乱语时可谓不少。这就像太阳出来仍点蜡烛、下雨了依旧提着水浇苗一样,可笑之至。用流沙河的原话来说便是:“台湾民主化之前,他是爝火照黑暗,大家崇敬他。民主化后,日月出矣,他就很失落,所以倒行逆施,站到我们这边来骂彼岸。”
金庸与李敖一样,同样也算大陆重视的一位“红色”文人,商业他当然是正确的,因为靠这个起家。事实上,他的政治正确,与他办报的商业才华一样惊人。他的武侠小说,我不像别人看得那么高,但总体上还是认可的。但他到处写对联、题词,以至于到大学当博导,便是有自露其丑的嫌疑。流沙河写《小挑金庸》、《又挑金庸》,将这些事予以指陈,只及知识错误,且行文客气严谨(传媒见此必用“炮轰”二字,强奸别人意志而不疲),不及政治评价,这是流沙河一贯的为文态度。他把对知识之求真,看得比一时的政治判断更重要,当然这并不表明他对金庸媚专制者的态度是认可的。因为一个曾经是商人的人,对眼前的厉害判断是非常明了的,有时明了到只顾利益而不及其他的地步。金庸目前到处说好话的做法,古人说是“圣之时者也”,今人则满口“与时俱进”,其实就是没有操守的实用主义,到处泛滥成灾。
由挑知识错误,流沙河继而在《最佳创作方法》里谈及金庸、琼瑶的创作方法。“当今文坛最会搞‘创作的,据鄙人看,男数金庸,女数琼瑶。江湖上明明白白无非鸡鸣狗盗之徒,他却写得出那么多英雄好汉。情场上清清楚楚尽是朝秦暮楚之辈,她却写得出那么多纯情男女。他与她都是聪明人,决不如实写真,犯‘资产阶级旧现实主义的错误。”金庸、琼瑶的作品固然只是和商业达成过分默契、粉饰歌舞升平的作品,将其比作完全跟官方亲密合作,刻意造假的《不能走那条路》(李准)和《在田野上前进》(秦兆阳),我认为这是不妥的。商业上选择固也有对政治迎合处,然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坛官方造假,还是有极大区别的。前者民众有更多意义上的自由,且明确是虚构的小说创作;而后者分明造假得厉害,却硬要说如实地反应了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误导你将其当作真正的现实来看待,洗人头脑,愚弄民众。
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金庸、琼瑶的小说创作虽然不够高明,但不足深责,因为另外的作品也有同等出笼的机会。目前的问题是,没有言论和出版自由,许多作品不能正常出版,客观上金庸、琼瑶的作品难免得了便宜。如果有同等出笼的机会,这些未能出版的作品在销路上或许依旧不是金庸、琼瑶的对手,但这没关系,自由竞争,参差多态,才是我们真正所期待的。正如流沙河指陈旧的牧民术,改作武侯祠赵藩的“攻心联” ——“能富民,则反侧自销,从古安邦须饱肚;不遵宪,即宽严皆误,后来治国要当心”——一样, 并非深责古人,不是说赵藩的对联不好,而是说沿用到现代不妥。
热爱乡梓
四九年后,任何人从小都被像瓜菜灌大粪一样,猛起灌输要爱国,却只从那些悬不着边的高调开始,而不从身边的琐细之事着眼。爱国思想中的“假、大、空”随处可见,爱国等于爱党、爱政府,培养了不少于身不亲,不说人话的人。一些浆糊脑袋,爱国愤青亦即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常打着爱国的招牌干着损及国家利益的事,已成当今中国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势力,其祸害社会正未有穷期。
在我看来,一个不爱自己亲人,不爱自己故乡的人,却奢谈爱国,实在是大言欺世,但这样的欺世之言触目皆是。由此及彼,流沙河甚至说一个不爱中国汉字的人,奢谈爱国,真是别有他图。流沙河由对故乡的深爱,进而对四川文化的熟稔,终而到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这样由小及大的方式,充分表明了他脚踏实地、不玄虚高蹈、诚实不欺的为人及治学风格。中年诗作《故园六咏》对故乡固有深挚的爱,晚岁的《芙蓉秋梦》,更是就记忆所及,将听闻和身历的成都,娓娓叙来,细大不捐,深婉不迫。但我想说的远不止此,我要说他对四川文化的研究及热爱,依旧寻着“对知识的纯然热爱”的路子在延续。姑举几例,以存其实。
流沙河读古书时常能与现实中的某些物事结合起来,这样的比附当然不是搞影射史学,大多只及古今语言之间的关系,尤其以关涉四川方言及文化为多。今天四川话中的不少俗语,其源甚为古雅。譬如我们常说一个人散淡闲逸、无所约束为“散眼子”,其实是从庄子的“散焉者”而来。形容一个人没有考虑、没有计划的“弗虑弗图”,是从《诗经》而来。比喻一个人处于昏昏噩噩的、混乱状态的“恍兮忽兮”,是从《老子》而来。川人常食“羹浇饭”却误作“盖浇饭”,流沙河考其出自梁代顾野王的《玉篇》:“饡,羹浇饭也”,乐山话“羹”读若羔(今乐山话与川内其它地方语音不同,正因杨展抗张献忠屠蜀有功,得以保存乐山一部分四川土著之故),由此转为“盖”。
流沙河有个发现,凡是方言中不易写的字,可能就是古字。比如四川人比较喜欢形容宽敞的词是宽绰(读若巢,巢与绰可以音转)。这是盐道街的一位语文老师告知他的,其父是流沙河的朋友,并称他为叔叔。但流沙河说在这字上,他就是我老师。陈麻婆豆腐大家都知道,但酌(读若读)豆腐之酌(读),一般人都写不来。流沙河后来读李劼人的《死水微澜》中有酌豆腐的写法并有注释,才恍然大悟。在一些好言大事者看来,这些当然是不足挂齿的餖飣琐屑之事,岂足道哉!然读书及搞学问还是如此做来比较踏实。那些喜欢大踏步前进的人,就让他们赶快前去,站领所谓的制高点好了。
最后用我的一次亲身经历,来印证流沙河《飞蛾儿是绋维》一文所言不虚。四川人拉架子车(架架车),超重时,必有人从旁协助,俗称拉飞蛾儿。车辐老就曾协助流沙河拉过飞蛾儿。但飞蛾儿不易解,流沙河读《礼记.檀弓》里的一段话:“吊于葬者必执引,若从柩及圹皆执绋”,却豁然开朗。他解释说:“柩车前头拉索曰引。棺柩左右系曰绋。绋是挽棺绳,缒棺下葬用。”我无数次看死者下葬,但真正执绋抬棺却只有一次。
那是大二暑假回乡,碰着一位年岁较大的堂嫂去世。她为人谦和,对我小时候关照有加,故我亲自抬棺,以表不忘曾经照拂之情。抬棺的人都是本村的青壮劳力,他们都嘲笑我,说我手无缚鸡之力,来混着玩。我便执一绋,绋都是很结实的棕绳,抬到几里地外的场窝砣安葬。抬棺,“引”固然是重头,然每一绋(棺木两边,大约每边五绋)所分担的重量亦不轻,因为抬棺者不能完全依着平日里走的路行进。按我们那里的习俗,抬棺(我们那里叫抬丧)一般只能走直路,绕得太多,死者的灵魂便不能到达那里(相反为死者拿火的至亲则要绕来绕去的走,免得死者的灵魂跟着他回来)。不能走平坦的路,逢高坎则直登而上,遇河则直接趟水而过,执绋者必须用力拉紧,与前后抬主杆者配合,合力跃进。故绋不只是“缒棺下葬用”,而是抬棺必不可少的牵引力量。正如拉超重架架车一样,须从旁协助,才能成事。可见拉架架车的“拉飞蛾儿”,与抬棺执绋的道理完全相同。
流沙河(1931-) 原名余勋坦,当代著名诗人、学者,四川金堂人,四川大学肄业。建国后,任川西《农民报》副刊编辑。1957年1月,与白航、石天河、白峡等在成都创办《星星》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借物咏志的散文诗《草木篇》,“反右”运动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其成为“大右派”。1978年平反后到金堂县文化馆工作,后来回到《星星》诗刊做编辑。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诗集、诗论、随笔、小说集等30余部,其作品获过全国优秀新诗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