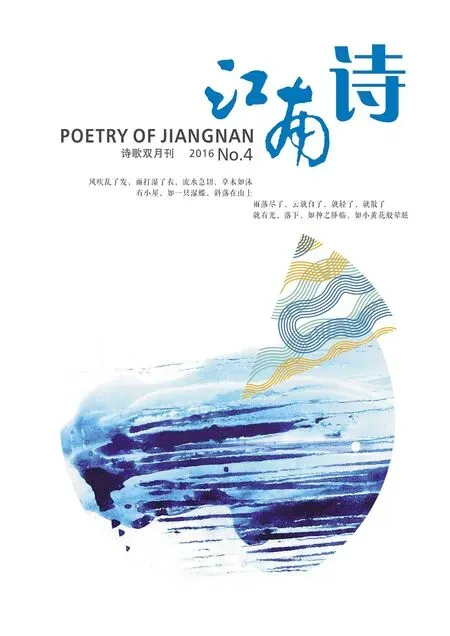抖落积雪和灰尘的寂寂冷杉
2012-04-29霍俊明
霍俊明
在北京夏天的一次诗歌会议上,我和马永波在嘈杂的鼓楼大街上和后海边谈到了远人和远人的诗歌。确实多年以来,作为同时代人我一直在观察和关注着远在湖南的还未曾谋面的诗人。我承认,远人安静的独具魅力的诗歌还没有被同时代的诗人同行们所真正理解。当在接连几个夜晚读完远人的诗歌时我首先想到的却是一个冬末春初的奇异场景,而在我看来这个场景更像是包括远人在内的“70后”一代人生存境遇和诗歌写作情境的对应性象征。
2010年3月14中午,鼓楼西大街62号。此时应该算是春天,但北京此刻却在漫天大雪中。我从家里徒步冒雪前往一次诗人聚会,那种清凛、激动的感觉好久都没有了!巨大的雪花飘落在泥泞轰响的北京街头!看到雪中立交桥下的冰面,鼓楼、德胜门高顶上的白雪,还有像我一样黑色莫名的人群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感觉!因为来得稍微早一些,我又顺着鸦儿胡同到了后海边。因天气稍微转暖的原因,水面上已经没有冰了,只看到茫茫的雪落在渺渺的寂静沉沉的黑暗水面上。这多像我们的生命状态,多像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如今博客和网络时代如此巨大的诗歌写作更多的是无声和迅速地消解在时代的水面之上,而哪片诗歌的雪花能够在如此情势之下获得长久?这就是诗人和诗歌的宿命。我把岸边栏杆上的积雪攥紧投进水面,看它们漂浮、溶化、消失。从后海回来时再一次经过小巷深处的广化寺。我已经是很多次与它谋面,但它对于我来说仍然是陌生的。我在纷纷的大雪中第一次注目寺庙门口的楹联:“烟波淡荡摇空碧,楼阁参差倚斜阳”。我们一次次从喧嚣的闹市街头走过,我们却同样一次次与真正的诗歌擦肩而过。
一
远人应该算是“70后”诗人中“出道”较早的一位,多年来他在文学尤其是诗歌的道路上仍然默默举着内心的火把,不断耐心地去擦拭飘落的满眼生活的灰尘,不断抖落凛冽的白雪和寒霜。尽管远人近年来也将视野投注到小说和影视等创作上,但是他留给我的仍然是一个诗人的形象。一定程度上远人仍是一位“聚光灯”之外的诗人,换言之他自足、内潜、沉静、不事张扬的诗歌写作个性使其时时处于夜晚一样的黑暗的包围之中,“仿佛有很多很多年 / 我独自在黑暗里听着那些上涨的声音”(《等车》),“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储存起 / 在黑暗里诞生的语言?你以什么样的步履 / 完成一首越冬的歌”(《岁末:十四首十四行》)。而我在这个时代看到了那么多不纯粹的诗歌写作者,看到了那么多心事重重、心怀鬼胎的诗人,看到了那么多的诗人在用非诗歌的东西招摇撞骗,看到了那么多被诗歌选本、诗歌奖项、诗歌活动和诗歌批评“宠坏”的时代献媚者和个人趣味的极端主义者。像远人这样的在“黑暗”和“自省”中仍然在默默低吟和歌唱的诗人反倒会在更持久、更有力、更自觉的向度上赋予其诗歌成色的独特和饱满,诗歌在内心和时代所发出的回声会更具膂力。安静代表了更为持久和顽健的精神力量,读远人的诗,我不断获得的是安静和感怀,一定程度上安静成了诗人的“获救之舌”。远人的诗歌方式更像是相当耐心和细心的抽丝剥茧的过程,不毛糙,不矫饰。平静、开阔、自然的叙说中诗人不断显现出灰色背景下的波澜,不断擦拭被灰尘蒙垢的生存纹理和已经被惯性和经验磨损的生动细节,“你通过灰尘,要辨别这个 / 世界的影子,它总是在灰尘里 / 动荡。你伸出的手要抓住它 / 可它总是滑开,像一条泥鳅 / 它摆动的尾巴充满着黏性”(《灰尘在这里落下》)。而到了远人这样的不尴不尬的年龄和身体感知的愈益洞悉,诗歌不能不被愈来愈突出的精神问题和感知方式所牵引,“捶打”、“追问”、“命运”就成了难以回避的关键词。诗歌打开的是一条条通向幽暗的时光深处和内心空间的小径,“你可以通过它 / 潜入我结痂的伤口;你可以在空荡荡的 / 林子里,触到我旅程里疲惫的足迹”(《岁末:十四首十四行》)。远人无论是在具体的生存场景中还是在怀想式的空间里都不能不面对时间和内心的双重考验与捶打,记忆是残梦一样的无助,而面对现实和个人历史的记忆更是艰难的。在迅疾转换的时代背景中包括远人在内的这些从年龄上绝不年轻但也不算衰老的“70后”一代已经显现出少有的沧桑与尴尬,现实与理想、诗歌与存在、真实与虚无的矛盾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贴近略显世故而又追寻纯洁的一代人发着低烧的额头。远人近期的诗歌在葆有了一以贯之的对生存现场深入探问态度的同时也频频出现了返观与回顾的姿态,这也不无印证了布罗茨基那句准确的话——诗歌是对记忆的表达。诗人开始在现实与想象的时间河流中对个体的真切命运和实实在在的生存空间浩叹或失声。远人诗歌中的回溯和记忆的姿态恰恰是以尖厉的生存现场和个人化的发现为前提的,这些返观陆离光线中记忆斑点和个体不断被置换、掏空和挤压的诗行是以空前强烈的悖论性的反讽为叙写特征的,“我感到一切都在继续,一度挽留过我的秋天 / 也在风中驱赶我,像驱赶一棵连根拔起的树”(《岁末:十四首十四行》),“只有这块在城市的街道、街道的草坪里 / 躺着的石头有点不一样。它大概是想 / 尝试另外一种命运,但从来就没有另外一种 / 命运,另外的只有消失、吞没,以及遗忘”(《这块石头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在远人的一些诗歌中,我领受了无处不在的“日常”的力量以及“日常”背后巨大的“黑暗”,我也最终看到了一代人的生存就像是黑夜深处中的一场暗火。是诗歌在维持着内心的尊严和发现的快乐以及失落的忧伤与无助,是诗歌驱赶着世俗和时光隧道深处的黑暗却也同时布满了一道道茫然的阵痛伤口和无以言说的苍凛与自嘲。远人的诗歌尤其是近期的诗作大抵保持了一种平静的不事声张的描述和发现性的话语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远人诗歌的视点,他不断在屋子里、办公室、窗前、阳台、室外、站台、车内、树下、街角、闹市和广场上,不断在午后或夜晚降临的空间里充当了一个细心而敏锐的观察者、发现者、叩问者和描述者、介入者以及自我盘诘者的角色,“我一直在观察这个世界—— / 我爱过它,现在已不那么爱它 / 我也恨过,但现在一点也想不到去恨// 我一直观察这个世界,一直观察我自己/ 现在我不再观察自己,我忽然愿意 / 只观察这个世界,即使它现在 // 只是一小块天空,它在不停地破碎 / 我忽然感到一种相信,它的破碎 / 在告诉我宁静,就铺在了这个时刻”(《下午的雪》)。我想这种“日常化”和个人的视点呈现的是远人大多的时候处于在场的“远望者”的姿态,无论是观察、回想、描述和冥思都在扇形中得以展开和拓殖。但是诗人的这种眺望、抬升和诗歌中的“远方”却一次次被墙壁、玻璃和建筑、树冠以及更为巨大的内化的装置和障碍所割断和阻拦,远望成了无望,“远方”成了黑暗中的虚无,“我在屋子里看着外面 / 玻璃把我和这个城市隔开 / 夜里有点冷了,有几颗星星 / 在很高的地方燃烧……我还是在这个角落 / 它封闭、单调,像一个简单的抽屉 / 我的影子在墙上移动 / 像树林,把自己设法种到远处 // 窗子在打开,现在远处是一片黑暗”(《远方是不能治愈的疾病》)。“远方”同时也成了爱情和生命中相遇过后茫茫无期的隔绝与无望,“我皮肤里长出一丛丛灌木,它低矮,但足以把我覆盖,我的灌木里只有一条蛇在游动……你离开了我,我现在多么想把头埋进你玫瑰的腹部!埋进我曾经流在那里的泪水——我多么想把你的腹部,再一次变成蓝色的、喘息的海洋”(《今夜,我在远方看你》)。这种张望与阻绝、提升和压抑的张力关系体现在远人大量的诗歌写作践行当中,这甚至构成了诗歌的底色和基调。当诗人在日常生活的间歇打开窗口试图拨开远方迷雾之下的真相和清晰图景时,似乎无处不在的“树冠”一样的遮挡却成了最为显豁的事实,而这个高大的意象同时又承担了难以企及和参透的神秘和奥义,“树冠的完成有赖于它上升的力度。我发现它总是挡开任何目光深入的企图。其全貌的不可把握形成它赋予出的暗影与玄奥。而在我们对它不断地仰望里,树冠却把我们在无边的地下抛得更远。于是,在我和树冠之间,我感到那不可到达的距离近乎某种神性。——树冠仿佛是进入时光的一节锐利之物。在它的内敛里,令人感到自身的限度突不破胆大妄为的梦想。它高踞其上的位置,令人类的命运也难以染指。围绕着它,是一种魔幻和梦想者的沉溺。当我在仰望时看见一枚飘下的落叶,我确认那不过是一只树冠暂且君临大地的化身”(《笔记:20页单词》)。在漫无边际的时间风雪、生存迷瘴和时代风暴中,诗人正如那棵高耸的但是已经“日渐衰老的植物”,用思想的头颅、用诗歌的身躯完成人生和生命的诗行,那枝头震落的白雪是诗人内心面对自我、时代的灵魂颤悸。在诗集《树下》中,我发现远人的诗歌意象谱系非常耐人寻味,几乎很多诗歌中都出现了树(树叶、树干、树影、树枝、树冠、树林、灌木、橡树以及比喻化和想像情境下的“树”的意象)、石头和水的核心意象。这三者的同时或交替出现使得远人的诗带有“传统”和现代的双重意味。在这些高大、坚硬(水则同时兼具了柔软和坚硬的质地)的场景和客观对应物前诗人个体的脆弱、不安、平静、冥想都获得了真切而聚焦式的呈现,这也同时呈现了想像的真实和重构的可能。然而更深层的含义还在于其中的一部分诗充当的只是暖煨内心的想象方式,比如组诗《山居或想象的情诗》,诗人营设的场景更多来自于一种想象和渴念,“这时候我就什么也不想,这时候我就只是 / 长时间看着窗外,几只吹口哨的红雀从远处飞来 / 它们落在我们屋前——那堆劈好的木材上面 / 那些木材,堆在那里后,就一直散发睡眠的香味”(《山居或想象的情诗》)。这也正如诗人所引用的阿摩司·奥兹的诗句——“这种生活你从未了解过,这种生活你曾由衷地渴望接触”,二者之间形成了深含意味的互文和相互打开。时间是如此莫名的强大!值得注意的是尤其是近些年远人的诗歌大多是以秋天为背景和抒写的场域,当然这种秋天既是装置性的,又是隐喻和氛围调性上的。而这些带有过渡、分界性质的“中年”心态和记忆势能的写作带有明显的“秋天”般的质地。秋天的背景明亮而暗淡,冷寂而喧响,平静而紧张,“我已无法做到,在身边干净的石椅上 / 安详地落座。我一个秋天的经历 / 便是掩埋在果园的尽处,仰着脸 / 等候向晚的潮润,凉凉地浸入我的呼吸”(《岁末:十四首十四行》),“现在轮到我了,一个没有人的 / 草地,草叶已经枯黄,尽管 / 秋天还在远处,一条细细的水 / 已开始携带满身都是皱纹的落叶”(《在深草里坐着》)。在远人“秋天”般的诗歌话语谱系中整个生存场域在时光的强大斑点中被无处不在的宁静而忧伤的词语所隐喻和牵引,“无人看见我被时光碾碎的一生”(《在车厢》)。时间的巨大钟表和秋日下的河流所呈现的好像都是一个卑微的被囚禁的“秋虫”,它们已经错过了青草和露水,只有被迎面而来的庞大的季节风暴所带走。远人近期的这些返观陆离光线中记忆斑点和反观内心景观的诗行是以空前强烈的悖论性的反讽为叙写特征的,“时间的本身在写作里只是一个虚设的座位,我在那里落座,只意味着给自己增添一个旁观的幻影。”基于此,处境的尴尬、生存的悖论、记忆的两难都在这些带有忆述性质的诗歌文本中不断得以夹杂着质疑与肯定的印证与呈现,这在组诗《保存的记忆》中有鲜明的印证。时间幽暗的深井旁,仍然有人在试图打捞往事,察看记忆的成分和颜色。诗人似乎仍然在等待,即使时间和场景总会倏忽而逝,但是愈是如此,那一切曾经的、拥有的、真实的往昔才会一次又一次在时间的暴风雨中被诗人并不强大的内心所接纳和细细的抚摸。当现实的列车、生存的列车甚至是时间的列车带给诗人一个个起点和一个个没有归宿的终点的时候,诗歌则成了作为生存个体的诗人反复寻找、反复确认自我的一种方式,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生存的一个个白日梦想,这些永远都难以实现的梦想在一个个记忆的影像中得以接续和完成,尽管这种接续和完成可能不是完美的,甚至更多的时候是悲剧性的。越是到了“中年”,诗人对世事和自我的洞透越是深彻,而这种洞透的结果是让一代又一代人自认为最熟悉的现实带有了不可确证的虚拟性和寓言性。而这就是诗歌和诗人带给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他在不断一意孤行的向我们自以为深知的生命和现实甚至历史深处掘进,他最先领受了挖掘过程中的寒冷、黑暗,也最终发现了现实表层之下的粗砺与真相。
远人无疑对“身边之物”投注了尽量宽广的考察视阈,他在审视和叩问的过程中并没有呈现出简单而廉价的二元对立的冲动与伦理机制的狂想,而正是这种融合的姿态反而使得以上的二元对立项之间出现了张力、弥散和某种难以消弭的复杂和“暧昧”。诗歌写作的平静、深沉的姿态使得远人既不是一个旧式乡土的守旧者,也不是一个故作先锋的批判者,但是他却同时在诗歌写作中呈现了一个复杂的观察者和介入者尴尬的面影,而这使得他的诗歌具有了繁复的空间和可能。而远人的诗歌显然并非扮演了个人和日常叙事中小感受、小反思者的角色,而是有意识在文本的尽可能拓展的巷道上延展自己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展现个人的命运轨迹和更为深切的时代寓言。
1999年之后尤其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人们谈论最多的恰恰是时代和文学的娱乐精神,而忽视了一个即使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时代其写作的难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是同样困难重重的事实。而远人却清醒地认识到更多的诗人和评论者沉溺于个人甚至荒诞的后社会主义时代主流美学伦理温柔的天鹅绒般的牢笼之中,而他则继续在和“帕斯捷尔纳克”们交流,而呈现的场景则更为繁复。简单的肯定和否定都只是少年和青春期写作的表征,而中年式的在肯定、犹疑、前进、折回之间展开的辩驳和诘问方式在远人这样的兼具“青年”和“中年”特征诗人这里不能不日益显豁的呈现出来。在远人为我们打开的生存暗箱面前,我最终看到了一代人的生存就像是黑夜中的一场暗火。他在维持着内心的尊严和发现的快乐,他驱赶着世俗的黑暗却也同时布满了一道道并不醒目但却难以愈合的伤口和无言的苍凉与自嘲。那些诗作洞穿了生命的困厄,却打开了梦想的小径上一个又一个荒草丛生的恐怖的深渊与陷阱。诗歌写作作为一个人的内心“宗教”和乌托邦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清洁”和对社会进行矫正的功能,但是我们看到的仍旧是无边无际的龌龊、喧嚣、混乱和荒诞。在理想主义的乡村愿景的丧失和不断欲望勃起而精神萎顿的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夹缝之中,在精神的自我挖掘、奔突和深度沉潜中,远人用诗歌发现了时代的疾病,同时也目睹了人性的痼疾。远人的诗歌始终坚持在看似日常化的真实生存场景和地理学场域中设置大量的既日常化又不乏戏剧性、想象性的同时寓含强大暗示能量和寓言化的场景。在这些苍茫的黑色场景中纷纷登场的人、物和事都承载了巨大的心理能量,更为有力地揭示了最为尴尬、疼痛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时代的华美衣服的肮脏、褶皱的真实内里。我想远人所持有的更像是“聚光灯”之外黑暗中的诗学,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重复光明、天空和玫瑰,作为创造者和发现者代名词的诗人有必要有责任对大地之下的黑暗之物予以语言和想象的照亮与发掘。基于此黑暗的地下洞穴中细碎的牙齿所磨砺出的“田鼠”般的歌唱正契合了最应该被我们所熟悉然而却一直被我们所漠视的歌唱。好的诗人都是时代的兢兢业业的守夜者,这个守夜者看到了夜晚如何把中国的乡村变成了一口深井,看到了一个推土机和搅拌机如何建造起一个个虚无的钢铁城市。在生存的夹缝中唤醒故乡的记忆肯定是尴尬的。这种无处不在的孤独甚至些许的恐惧感却成了现代人的梦魇。飞速旋转的车轮使乡村城市都患上了时代病。
远人是一个如此耐心的解说家和细心的勘探者,在一些被我们熟知又被一次次忽略的事物身上,诗人用身体和灵魂以及个人化的想象力重新发现和命名了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在一次次的悖论性修辞中打开了一个个既真实又荒诞的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隐秘的入口,“在旷野,火车暂时停了下来 / 车窗外面,有两条废弃的铁轨 / 灰色的枕木托着它,纸屑落在其间 / 又随风飞起,石缝间有枯草生长 / 一切如此自然,这两条没有用的铁轨 / 仍是伸向远方,拐着它自己的弯 / 我不知道它究竟要到哪里,当它 / 在旷野没入,我感到一切是如此孤单”(《两条废弃的铁轨》)。诗人一遍遍擦去世俗的尘垢,从而使的那一个个时光车轮碾压下的物事重新焕发出历久弥新的光泽和裂痕。正是这种安静、精细、幽微而深入的话语方式使得远人更像是在落木萧萧的季节不断抖落浑身白雪的冷杉。它坚硬的针刺、挺拔而布满了岁月刀痕的身躯都呈现出了冷硬背后的并不轻松的时日和成长膂力,当然它也发现了常人难以目视的一面,“它是不是发现了更高的地方?只给我们 / 留下树叶和带缺口的山巅。当它真的消失 / 我们就看着天空——这块天堂的地板 / 在松针的戳刺之下,漏下来很多的星光”(《山居或想象的情诗》)。
二
当1970年代人出生的时候,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此后在1980年代末期开始的翻天覆地的颠覆性转折和“轰响”声中新的社会时代的开始,注定了这一代人不能不生活在这样的尴尬境地——政治的、商业的、城市的广场。而连接杂乱的广场和遥远的异乡的正是黑沉沉的铁轨和寂寞的乡村小站,在第六代导演贾樟柯的《小武》、《站台》、《逍遥游》甚至《三峡好人》电影叙事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70后”一代人在80年代以来的成长故事和生存寓言,“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出生,一直长大十八岁的地方就是城乡结合部,就是能辐射中国广大农村的一个生存空间。我的初中同学、我的亲戚都是这样生活在社会底层,我的感情更认同这样的层面”。
“70后”一代诗人有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特殊的“广场”,而且他们从出生之日起就曾一度生活在政治的集体性的广场上合唱的尾声之中,而如今商业的广场、城市的广场、现代性的广场遍布了中国的各个城市和乡镇。虽然这种宏大的政治的广场在“70后”一代人的现实生活中并没能维持多久,但是这短暂的政治和革命理想主义的晚照却已永远地留存在了这代人身上。而当1990年代的商业和都市的广场取代了政治广场,一块块五彩斑斓的工业瓷砖代替和铺满了曾经的墓地、纪念碑和英雄的血滴,麦当劳和肯德基的快餐方式取代十字架和鲜血成为这个时代新一轮的广场象征,“70后”一代人所面对的却上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的“饥饿”,广场投下的阴影将他们并不高大的身躯深深覆盖。尽管北岛和欧阳江河等人的广场书写与“70后”诗人的广场相同之处在于都具有深刻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对历史、社会乃至个体命运的重新省思,但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到,北岛和欧阳江河他们更多的是强调了内心对时代、宏大的政治历史场景的重新清洗和质问,不约而同是在陈述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历史的强行结束和一个灰蒙蒙的暧昧时代的强行开始。而关于广场的宏大叙事的全面结束还是从远人等“70后”诗人这里开始的。“70后”一代诗人在“广场”上更为关注的是后工业和城市语境下一代人的尴尬宿命和生存的沉重与艰辛。但“不幸”的是北岛、欧阳江河等人的“广场”意识甚至情结并未荡然无存,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继承的背景它仍然在“70后”一代的现实生活、文学阅读和写作以及集体潜意识中存在。在无限膨胀、无限加速度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新的后工业时代的广场正在建成。在这个市场天气的城市广场上,迷蒙的光线照耀的不再是挥舞的铁拳、昂扬的歌声和摇动的红旗,而是迟疑的、沉重的来自某个角落的的青年。当空旷的广场、黄昏、象征时间的割草机和褪色的生活一起呈现的时候,广场更多是沾染上一种空前寂寞的霉味,而这种霉味则是实实在在的个体生活略显冰冷的体味。而广场在他们看来无疑是一个反讽的角色。在雕像与废墟、高大与碎片、重压与尊严、城市与外乡、阳光与阴影的张力冲突中,诗的雕刻刀雕凿的是沉重个体的生存状态。特殊的成长背景和生存环境使得“70后”诗人无形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广场的荣光、血腥、伟大尽管仍在这些怀有理想主义的一代人的身上有着碎片般的闪光,但是更为强大的城市生存的压力和商业、工业的巨大阴影则成为他们首先要面对的难题,所以对于“70后”一代而言广场是直接和生存(城市和乡村经验)联系在一起的,而非像以前的诗人是和革命、战争和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远人在长诗《失眠的笔记·广场》(同时参见《笔记:20页单词》)中对广场的描述和界定基本可以看作这代人具有代表性的整体认识:
它的建立使城市与乡村得以严格的区分。一个广场的位置,与它同义的往往是物质的中心和建构在乌托邦性质上的高点。尽管它提供的不过是十字路口中央的一处花坛、一个喷泉,或者一尊塑像,——就仿佛是城市在它结构里努力生出的幻境,朝着某个梦想的、同时又是垄断的方向延伸。
非常容易看出,在广场上茫然回头的人不会来自城市。广场的巨大平面似乎始终都在拒斥一种另外的命运。可以说,它通过象征所维持的,是不带激情与妄想的世界,这正如随同它的复制而被删除掉的诗篇,在形成之前,就已达到了妥协和某种不明确的授意。因而在我每每穿过这城市的广场之时,我感到的晕眩不是来自日光的照耀,而是在我和城市贫血的关系中,广场所赋予的那种强烈、巨大、以及无言的压迫。
政治年代的最后残存的火焰仍然燎烤着这些19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然而当工业和商业的现代列车在无限制的加速度中到来的时候,理想情怀和生存的挣扎所构成的巨大峡谷呈现了空前的沉寂、尴尬、分裂和焦灼。广场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70后”一代人在由残存的理想主义的尾声向商业时代过渡的重要象征,从集体转向个人的开始。巨大的广场上他们显得如此虚弱,人流攒动的广场上他们却形单影只,公共生活的场域里对于这一代人而言却成了个体、生存、孤独、茫然的代名词和衍生地,“傍晚的广场上你不认识一个人 / 但这恰恰是你想要的效果 / 你的脚步和这里每个人重叠 / 有几个瞬间你觉得你不是你自己 // 如果你真的不是你自己,那你 / 又会是谁呢?你的姓名和经历 / 都在一些阴影里蠕动,没有人能打开 / 你的阴影,你也不可能清楚别人…… / 它们为数不多,也无人注意,实际上这里 / 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区别,在上涨的黑暗里 / 你听到的哭声至今也只有你一个人听到 / 你完全可以说,此刻只有你一个人走过了广场”(《傍晚的广场》)。灯塔倒下后是大片的废墟,前行的路上充满了阗寂无声的压抑。
在远人的诗歌中我看到了幽暗的树林上空不断推远和拉近的时光的景象,看到了树叶响亮的歌唱背后无尽的落寞和孤单,看到了冷杉树上积压的厚雪和负累。而更多的时候,我看见了那从根部直升上来的力量在不断抖落风雪和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