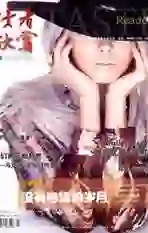做作
2012-04-29方希
讨厌的人虽然各有各的讨厌之处,但是最普遍的一点往往就是做作。做作意味着努力让人相信自己是想象中的那个人,虽然他还不是。儒勒·德·戈吉耶发明了“包法利主义”一词:人所具有的把自己想象成另一种样子的能力。包法利主义听起来很深很学术,其实也无非是做作的另一种说法。
上中学时班上的一位女同学比较倒霉,她倾慕娇弱的女性,罔顾自己身高体壮、虎背熊腰的事实,走路轻摇慢晃,说话声细如喃,动不动还趴在桌上低声啜泣……可惜她的这些努力并未获得任何一方观众的掌声。有一天,她被堵在学校门口,一个隔壁班的黑脸小个儿做出一副流氓的样子,大声宣布女生的罪状:“听说你冒充校花!”挥拳打了过去。这一场景实在是荒诞得有趣,一个在扮演娇羞无邪,一个在演绎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初级黑社会,双方连动手的理由都如此牵强,对自己臆想中的角色的渴慕实在是忠实到家。可惜这个未经排练的对打让彼此都现出了真面目:女同学在吃了两拳之后把娇弱抛置脑后,发起疯狂的反攻,瘦小的男生被打翻在地,在女同学的重拳之下只能苦苦求饶。
做作的男人和女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渴望生活变得更好的人,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时候,便只能改变自己,假装一切已经开始往理想的方面有所进展。深究起来,一个做作的人,本质上是一个有追求的人。
男人讨厌女人的做作,最大的一个原因便是做作增加了交际成本。面对做作的人,你无非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顺应她的角色提示,把自己当成一个称手的道具,一个听话的演员;一种是不理会对方的提示,揭穿她做作的事实。这两种应对之策无疑都比普通交往更费劲。女人讨厌男人做作,比较明显的一个原因便是男人的虚张声势往往透露了他的心虚,而与心虚的男人交往无疑是浪费时间。做作的另一个坏处还在于,做作的人似乎看轻了观众的智力,让人感觉到被当成了傻子。
做作的人也是一些心急的人,他们急于跨越时间、沉淀,希望能走捷径,迅速跳到社会声望更高的阶层。刘易斯·拉普曼写过一本名为《上流社会》的书,嘲讽上流社会的行事风范,不意成为中产阶级意欲进入上流社会的指南。如果说装模作样有手把手的培训手册的话,这本书无疑是操作性最强的一种。比如,在上流社会中,如果要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一定要记住所使用的语言“应该带有略显米色的苍白”;如果一定要批评点什么,要把怪罪的对象说得相当抽象,比如,协议离婚主要是后现代主义生活态度普及造成的恶果;电视不仅毒害了公众的良知,还使文明的举止失去了光芒。一个人表现出有好奇心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所以多好奇也需要表现出司空见惯的样子,否则你有可能被误以为是个侍者。即使你即将破产,也要表现出漠然,向你的同僚要求一千万而不是一百万的赞助,并想象成你是在和你的裁缝讲话……
成功的做作往往很难,即使是“职业演员”。更多情况下,做作的人就像个蹩脚的魔术师,明明台下早已看出穿帮,还要一本正经地在台上演下去。不过有位古人倒是指出了一条出路:“作之不变,习于体成,则自然也。”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坚持做作,做作到习惯和本性打成一片,我们也只能承认,他已经不是个做作的人,他确实上了层次。
方希,20世纪70年代生人,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硕士,专业出版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