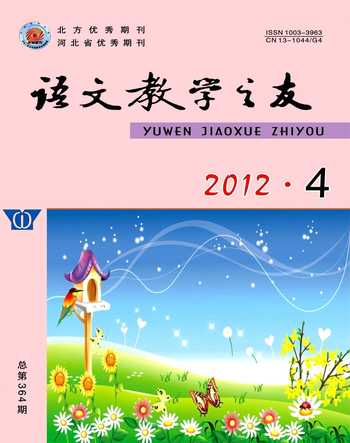探微苏轼心中的孤寂与解脱
2012-04-29石明于淑杰
石明 于淑杰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诗词文俱佳,在古典艺术长廊中闪耀着不朽的光芒。“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他的豪放,“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是他的旷达。米芾借作画对苏轼评价说“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可见,在苏轼的豪放旷达背后,隐藏着情感的孤寂。这种孤寂,是屈原放逐的江畔行吟,是李白游歷天下的决不妥协,是杜甫浪迹天涯的踽踽独行。这种复杂的情感,在他的诗词文中屡有出现,现撷取一二,以见微知著。
一、哀叹人生苦短,忧惧生命无常
苏轼在经历“乌台诗案”后,思想情感上受到很大的挫折,由原来的想要“致君尧舜”以安邦,“西北望,射天狼”以定国,沦为“是处青山可藏骨”的阶下囚,其情感落差可见一斑。元丰三年,在与子由互为唱和的《西江月》中,他感慨“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心凉,”感叹人生的虚幻短促。元丰五年七月,他和同乡道士杨世昌(客)在游览赤壁时,借客人之口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感怀生命的渺小短暂。在同年十月重游赤壁时,又发出了“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的感叹。即景抒情,明言景色变化之快,暗蕴人生在世之短。苏轼在被贬黄州的几年里,诗文中多次有这样的抒怀,为什么产生这样厚重的人生忧患呢?这和苏轼的人生经历有关。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在狱中诟辱备至,命如悬丝,幸得多方营救,才得贬出。传苏轼入狱后,和儿子苏迈秘密约定:若情况凶险性命堪忧,送饭时就送条鱼;若案情平常,就送他一般饭菜。苏迈如约送饭菜至牢内,都无异样。一天饭菜按时送来,苏轼打开一看,竟是一份鲈鱼!万念俱灰之下,遂挥笔写就两首绝命诗,托付看守转交苏辙。谁知提心吊胆之下,又送来了日常菜蔬。苏轼暗中探问,才知儿子因故外出而把饭菜之事托付他人,却未事先告知约定,因而让苏轼虚惊一场。从这一段典故中可以看出,苏轼当年狱中之凶险,环境之恶劣。后贬居黄州,生活拮据,前途黯淡,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是,从天而降的巨大灾难,使他认识到人生之无常,生命之卑微。由此可见,诗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并非偶然,实为情感发展之必然。
二、感慨仕途坎坷,忧叹民生疾苦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受到朝廷排斥打击,被贬黄州,人生一片茫然。元丰五年十月,他与客再游赤壁,那时“时夜将半”,眼前所见巉岩如“虎豹”、“虬龙”、“危巢”、“幽宫”……令人望而生畏,心旌震荡,客遂“不能从”,自己亦“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乃至于 “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在这里,苏轼运用了象征手法,以“虎豹”、“虬龙”、“幽宫”等象征了人生之坎坷,仕途之艰难;心中的压抑无处发泄,则用“长啸”缓解;山川的变化,亦可见草木为之含悲,山河为之色变。作者虚言景物,实写心中冤屈。他恐惧于仕途险恶,也只能顺其风雨飘摇,“听其所止而休焉”。传统知识分子都把入仕实现政治抱负作为最高理想,但人生险恶,宦海沉浮,不免志向难酬,积郁难伸。无独有偶,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借梦境写出了自己仕途的坎坷,他用“熊咆”、“龙吟”、“列缺”、“霹雳”……隐喻仕途的凶险;用“栗深林”、“惊层巅”、“丘峦崩摧”这些景物变化,寄寓人生的震荡;又以“魂悸魄动,惊起长嗟”,写出了内心的怖惧。两位文豪有很多相同之处:同样的才华横溢,同样受到朝中小人的构陷,同样仕途之路坎坷不平。遂使二人以相同笔法,抒发心中愤懑不平之气。就此点来说,两文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苏轼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心中涌动的依然是报效朝廷、建功立业的激切热望。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眼前如画的江山美景,让他追慕周瑜“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不世业绩;在苏州的田产被风潮荡平,他却不以为意,说“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他仿佛看到黄州雪后明年的“麦千车”,而“人饱”将使我“愁无”,这不禁让人想起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高尚情怀,虽说苏轼自己境遇坎坷,心中惦记的却是国计民生,这是何等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苏轼虽遭贬谪,但“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仍表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高尚节操,这不能不说是士人的楷模,后世之垂范了。
三、寂寞犹如孤鸿,悠闲宛若桃源
苏轼政治上的坎坷不平,宦海中的升降沉浮,影响到了他的生活态度。他初到黄州,在家则杜门面壁,消除“妄心”;出门则“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以求解脱。这一段人生经历,在他心中留下的是深深的孤寂与忧郁。
一次酒醉后他回到居所,几次敲门,家僮都“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他手拄拐杖立于江边,面对滔滔江声,反思官场往事,他要“忘却营营”,他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是他对人生的反省,也是对以后人生道路的规划。当然,他并不是要归隐,而是要在黄州开始他新的人生。
但他的人生依然孤独,越是夜深人静,越显出孤独。在诗文中,他形容自己“飘渺孤鸿影”, 那孤鸿“共为竹林会”,那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他以“孤鸿”自况,虽孤独,但绝不随俗浮沉。他“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他“起舞徘徊风露下”, 他与月共舞,与影同行,与酒共醉,唱着一曲凄美的挽歌。这是一种对人生的宣泄,也是一种对逆境的抗争,更是一种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他没有沉沦,面对坎坷境遇,他随遇而安,以田园生活为乐。闲暇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以种田帮补生计。他喜欢这里的景色,“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他赞美百姓的劳动生活,“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他喜欢这里的田园生活,“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田园劳作,让他忘忧;欣赏美景,让他展颜;农后余闲,让他怡然自乐。
苏轼是个旷达乐观之人。他安守住心灵的家园,虽然孤独寂寞,但却宠辱偕忘、超然物外。他用这种方式守住了心中的那份宁静与平和。
四、纵情山水之乐,显卓拔之不群
苏轼感叹生命之卑微,仕途之险恶。但他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坚持着自己对国家和民生的关切,他的人格魅力不仅于此。苏轼思想比较复杂,儒、释、道兼而有之,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让他顺其自然而不悔其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让他刚韧坚强而积极用世。道家和佛家的影响让他超然物外而与世无争。他既有儒家的坚毅执着,也有佛家的超脱虚无,更有道家的率真自然,形成一种全新融通的哲学思想和行为模式。
在《黄州寒食》其二中,苏轼对他的生活状况有这样的描写“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据其中描写,屋如渔舟,缺衣少食,可谓欲哭无泪,欲诉无声,人如槁木,心如死灰了。但坚强的苏轼,凭着他融通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突围了。
靠饮酒、赏景、吟诗诵赋以解脱
在苏轼的诗歌中,饮酒作诗章句比比皆是。“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而让他“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面对孤独,则听“耳得之而为声”的“江上之清风”,赏“目遇之而成色”的“山间之明月”,可谓纵情山水,吟诗诵赋,饮酒为乐以度余闲。这是传统文人墨客遭到不幸,试图解脱自己的常用途径。李白的“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杜甫的“千金买一醉,取乐不余求”;陆游更是用“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给自己饮酒找到了依据。我们看到苏轼很多诗歌都是在酒后创作,大概找的就是“惟酒可忘忧”的境界吧。
靠哲理感悟而解脱
哲理诗词,是我国古代诗词园地中的亮丽奇葩。一枝独秀而异彩纷呈,是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充满着知识性、趣味性和启迪性,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雄辩的说服力。
苏轼在《慈湖峡阻风》中说:“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且并水乡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诗人说人生道路充满了“巉岩”,即使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也充满着复杂的矛盾,它唤醒诗人:只有认识“巉岩”,找到对付困难的方法,才能游刃有余,攻坚克难。在《前赤壁赋》中,他借客人之口感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但笔锋一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道出了万物皆永恒这一命题,使客人“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
靠豁达的胸怀而解脱
苏轼的包容,是一种坦然。他在《定风波》中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不仅是对大自然的态度,更是对人生坎坷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平和恬淡。苏轼的包容,是一种旷达。他从黄州谪所被召回,便前往金陵同王安石相会。这时的王安石正赋闲在家,门庭冷落。听说苏轼造访极为感动。他亲往迎接,“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二人同游蒋山,诗酒唱和,相处甚欢。后王安石赠诗,苏轼酬和说“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惟有这种旷达胸襟,才会有苏轼和王安石的握手言和,才能成就两位文坛大家的一段佳话,为后人传颂。
苏轼贬谪黄州后,历练成性格中的顺其自然和豁达乐观,成就了他顺逆安处的淡定与平和;心中块垒的消弭,则成就了他破茧化蝶后的豪迈、自由与奔放,由此开创了他文学创作的新境界。“乌台诗案”之对于苏轼,无异于他生命的涅槃。这种涅槃重生,点燃了他生命中美的绽放,洞启了他人生中的漫漫求索路,这让我们看到一个尘封年代的剪影,洗却铅华,如流星般,点亮了那个久远年代的诗画情怀。
参考文献:
①王蔚编选《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清)上疆村民2006年版。
②游国恩王起 主编《中国文学史》 1963年版。
③《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选编1989年版。
④胡云翼选注《唐宋词一百首》 1978年版。
(作者单位:延庆县第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