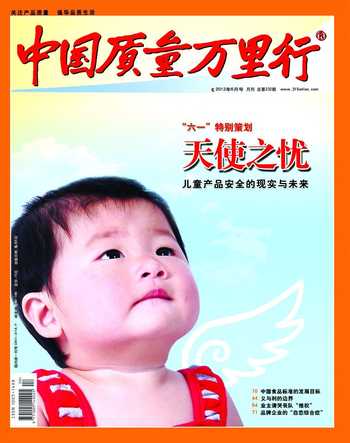义与利的边界
2012-04-29李迎丰
李迎丰
我们讲“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一边是“依法维权”,另一边是“似乎不合道德”,孰轻孰重?本不难判断。
“恶创造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这里说的恶是指“私利”。我们没理由要求作为“经济人”王海的动机“只讲义不讲利”,只要他合法,重利无可非议。
前不久,中国质量报及深圳各媒体都登载了一条消息并引发热炒:深圳市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职业打假人”的举报,并将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重罚深圳乐购超市,此举赢得市民喝彩。
是“依法维权”还是“不合乎道德”
据悉,深圳市监管部门已依法处罚了该超市,似乎此事已告一段落。但该超市对王高彬等职业举报人的身份提出质疑所引发的争论仍是媒体特别是网民的热议话题,这本身就令人深思:乐购超市不反省自己的过错,一味强调这种“知假买假”的职业打假行为是为了牟取私利,有悖中国的传统,属于不道德行为,动机严重不纯,不算真正的消费者,社会不应鼓励和纵容这种行为。如果他们不要钱,只是单纯地进行举报和对超市进行监督,就应该表扬和鼓励。
这种说法——这类企业惯有的说法——似曾相识。这使我想起前几年在某些地方出现的法院以购物的数量太多、动机不纯、不合乎道德为由“不承认购假索赔者为消费者”的判例。可以看出一些人甚至司法人员以道德观来判断、评价消费者作为“理性经济人”正常的、合法的维权获利行为,更多地仅凭个人的“经验法则”,以根本不能作为判断依据的“动机”和“购物多少”来判断是否真正的消费者,来曲解法律的客观适用性,而无视这些消费者依法维权的正当合法防卫性及对侵权者的震慑作用。
我们讲“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一边是“依法维权”,另一边是“似乎不合道德”,孰轻孰重?本不难判断。这其实是以“实质性正义”否定“程序性正义”的畸形做法,而且其所谓的“实质性正义”的本身和前提往往都是虚无的,不符合我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这无疑助长了制售假冒伪劣、诚信缺失厂商的不法行为——比如深圳这家乐购超市的“振振有词”,不利于建立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机制及公平和谐的经济竞争和消费氛围。
重复博弈方能治理诚信缺失
按照博弈论的观点,在只进行一次或有限几次的博弈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标准的纳什均衡——即非合作的博弈均衡——是卖给对方低质量的产品,即出现“坏车挤垮好车”、“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而无限次重复的博弈是治理诚信缺失行为的最好办法,是建立信用的关键。
消费者依法维权就是人为地增加博弈的次数,使那些有欺诈失信行为的经营者有所顾忌,有所收敛。而如果消费者不主动依法维权,那么高兴的只是那些有欺诈失信行为的经营者,他们永远乐于玩这种一次性博弈游戏,因为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就是这种一次性买卖的主体。
因此,要强化全民维权意识,鼓励、引导消费者——包括“职业打假人”——主动依法维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运用。消费纠纷大都属于民法调解范围,而民法中有一特点:民不告,法不究。因此,要用便捷的渠道,适当的利益补偿和低成本的实现手段来鼓励消费者依法维权。
我希望被侵权者勿以“利”小而不为,而要懂得为的是权益和尊严;希望其他同是消费者的“旁观者”不要成为像鲁迅先生所深恶痛绝的“无聊的看客”;更希望那些手中有裁量权的法官不要以居高临下的“道德贵族”来强调和谴责所谓的“动机”。
美国波士顿有一座犹太人遭屠杀纪念碑,上面铭刻着一位名叫马丁·尼莫拉的德国新教牧师在二战后留下的带有深深忏悔之意的短诗:“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鲁迅先生和马丁·尼莫拉牧师的感受给我们的启示是:在那些诚信严重缺失的丑恶面前,在那些侵害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权利行为面前,哪怕这些事情看似离我们很远,或自己不是直接受害者,每个人都要以我们的良知和正义“站出来”说“不”!只有消费者都联合起来,那些制售假冒伪劣的侵权者才会真正成为过街老鼠。这里有一个“搭便车”的问题:众多消费者被侵权,少数维权者却要自己承担代价成本。所以作为“守夜人”的政府就应有一定的利益激励手段来引导大家主动维权。
当然,经济秩序的规范,最需要的是制度、法律体系,管理市场秩序主要靠国家行政部门。但是,也同样需要广大公民在法律的框架下共同作为,并且是与立法目的一致的积极、主动的作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双倍赔偿”,就是想以经济利益调动受欺诈的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积极性,就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和正常的交易秩序,是法律赋予消费者在索赔时的一种权利。法律就是通过这种价值衡量和利益机制,让社会力量发生作用,让政府与消费者结合起来,共同规范经营者的行为,营造良好的消费氛围。
“职业打假人”是正义的反击
“职业打假人”的义利观、道德观是媒体上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我认为,“职业打假人”(王海为代表)的行为是在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那些充满竞争意识、权益意识的消费者对制售假冒伪劣者、诚信缺失者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的反击,是中国消费者在走向成熟过程中自觉运用法律武器向“违法者”讨要说法的针锋相对的较量,属于特殊意义的“以身试法”。这也向我国的司法界提出了是依法办事还是依传统的道德办事的问题。
有不少人——包括厂商、法官、政府官员和不少同是消费者的人——对王海、王高彬等嗤之以鼻,认为其动机不纯,视其为“刁民”、“假冒消费者”。前几年在一些地方都有法院判这种“知假购假”再依法索赔的“王海”败诉(也有很多地方判胜诉),是因为他们买的东西数量太多,超出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范围,不是真正消费者。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消费者?买多少又是消费者与非消费者的界限?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与美国的《布莱克法律词典》对此有几乎完全相同的解释,而这种定义被绝大多数国家认同:“所谓消费者,是指购买、使用、保存和处理商品或服务的个人或最终产品使用者。”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消费能力、消费欲望以及与一件物品使用频率有关的消耗速度因人而异,千差万别。其实这些判例的背后,这些法官心中深层的因素是他们认为“王海”的动机不纯,不合道德。如果他义务打假,则值得推崇。其实这是传统的重义轻利道德观念的极端表现,这是一种不切合这个时代大多数人实际思想水准的道德观。
“恶创造历史”
——合法的重利无可非议
大家知道: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的主要配置方式是受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调剂来完成的。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道:“一般说来,单个的个人实际上既没有增进公共利益的打算,也不知道他的行为增进了多少公共利益。都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最终增进了社会的利益,通过追逐自身的利益,他对社会利益的不断的促进作用甚至比他想要这么做时更为有效。”亚当·斯密认为在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协调的秩序,能把个人天然的、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追逐私利的欲望转化为社会的利益。
恩格斯也说过“人们通过每一个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嘲笑费尔巴哈:当他说“善创造历史”时,他以为自己说出了多么高明的论断,殊不知,老黑格尔早就说出了比他高明得多的论断,这就是“恶创造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这里说的恶是指“私利”。我们没理由要求作为“经济人”王海的动机“只讲义不讲利”,只要他合法,重利无可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