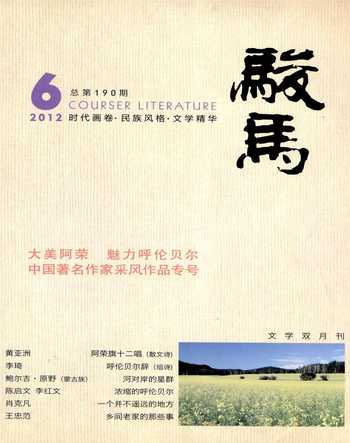浓缩的呼伦贝尔
2012-04-29陈启文李红文
陈启文 李红文
当你走进这样一片大地,只有一种感觉,一种永无止境的感觉。
此时,像大地一样辽阔的夜幕正在降临,我感觉漫长的旅程真正开始了,而那个预定的方向,依然处于一种未知的神秘状态。当阿伦河的流逝声从呼伦贝尔澄明的夜色中清澈地传来,我涣散的神思已经下意识地集中在一个意念上,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了一条河流,一条正在时间和空间中流淌的河流,这个世界充满了流动的呼吸。
抵达阿荣已是夜深了,即便在这深沉的夜晚,也能感觉这一方水土的干净。每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都要下意识地仰望天空,没有意料之外的事物出现,这苍穹之上是永远映照着人间的月亮、星星,还有透着月光和星光的云絮,干净得像羊毛一样。尽管我一直带着平静的表情,却压抑不住内心的震惊,震惊的是那一种超尘出世的渺远和清晰,清晰得仿佛可以看清整个宇宙。
这一夜我失眠了,但似乎又与窗帘上那过于明亮的月光无关,让我失眠的还是河流,她在我似睡非睡的恍惚中从深夜一直流到了天亮,我的焦虑不安又或许与潜伏在这河流四周的许多未知事物有关。事实上,这一方水土在天亮之前对于我还是一个神秘的未知区域,有太多的事物在恍惚的状态不断地发生和纠缠。感谢呼伦贝尔的太阳,它几乎在凌晨三四点钟就亮了,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就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清晰,清晰地呈现出了这个世界。
穿过满街比我起得更早的忙碌人群,我心无旁骛,几乎是直奔我憧憬已久的那条河。
当我第一眼看见她,我的心莫名地颤了一下。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一条单纯如水的河流了。或许是期待得太久,或许是她那过于柔弱的清流更能牵扯人的神经。接下来,一路上,我一直默不作声地跟着她,看着她,一条纯美而清新的河流,斜斜地穿过那吉镇,仿佛正从无尽的岁月中缓缓流来,面对喧嚣的尘世,她始终保持着一种优雅、从容而舒缓的自然节奏与旋律。不能说这是一条大河,最宽的河面也不过三四十米,也不能说是长河,她再长也只有三百多公里。但这样一条河,却养育了汉、蒙、回、满、朝鲜、达斡尔、俄罗斯、鄂温克、鄂伦春等二三十个民族,全中国又有多少这样的河流呢?我的脑子里涌现出一个个词语,如水乳交融,如血脉相连,然而这些词语在一条河流面前显得是多么的苍白和矫情,还有什么比一条河流更能形象地诠释这一切?
那吉镇也是这条河安排的一种命运。这里是阿荣旗旗人民政府驻地,在内地就该叫县城了。这座小城快活地拥挤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很热闹也很漂亮,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异域的气息,很多牧民的腰上、屁股上还挂着铮亮、锋利的刀子。而他們黝黑的面孔,被毡帽的阴影遮挡着,让人感觉到一种来自大草原的神秘。但这里还不是草原,这里只是草原、森林和河流之间的一座城池。有河流的地方必有丛林,换句话说,有丛林的地方必有河流。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自然法则。这簇拥着一条河流的树林,从阿伦河谷蓬勃地蔓延到王杰广场、抗联英雄园、丁香园、滨河公园,这不是一座城市营造的风景园林,这是一座森林里的城市。很多树已老态龙钟,长出了几百年才能长出的皱纹。它们躬身站在一条河边,就像一个守望儿孙的老人。清凉的晨风一阵阵地掠过耳边,掠过耳边的还有绿色的树枝,这让我有些忘形,忘形中又难免产生错觉,感觉我已提前走进了大兴安岭森林。
又该说说这个地名的意思了,这在别的地方根本用不着,然而到了这里,你却不得不一次次地诠释,否则你就读不懂这里的一切。那吉,这也是一个因水而生的名字,鄂温克语——鱼非常多的地方。用我家乡的话说,这里就是一个“鱼窝子”。听河边的一位蒙古族老人说,以前这河岸还是一片沙滩,开春后,很多乌龟王八便会爬到沙滩上,在被太阳晒得很温暖的细沙上扒个坑,把蛋下在坑里,一个沙窝子有时候会下四五十个蛋呢。下完了,又用沙子把蛋埋上。你看不见那些蛋了,但过一段时间,你就会看见成群结队的乌龟王八崽子们在沙滩上爬呀,爬呀,有的连眼睛还没有打开,但它们绝对不会爬到另一个地方,它们闭着眼睛也知道一条河在哪里。在这沙滩上下蛋的还有蛇。蛇有时候会吃掉乌龟蛋,但也守着这些乌龟蛋,很多人就是因为怕蛇,才不敢去碰那些乌龟蛋,一不小心就碰到蛇了。那时候这河里的鱼也多,太多了,每到鱼汛期,也就是鱼的交配繁殖季节,那些鱼在河里你追我赶,一河的水泼剌泼剌响,鱼多了,打鱼人也多,一网撒下去,可打上来一百多斤。甚至根本不用撒网,可以拿葫芦瓢舀鱼,这里的老百姓流传下来一句俗话:“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那时候啊,呼伦贝尔和大兴安岭就有这么多的狍子、野鸡,就有这么多鱼,也没说不准打,一年一年地打,但阿伦河里的鱼怎么也打不尽……
一个蒙古族老人的讲述,不像是讲述一段历史,而是在讲述一段童话。那时的他也就是一个孩童,而那时这里的一切也仿佛停留在童话时代。但此时,两个天命之年的男人,只能直面眼前的现实。眼下,这河岸边早已没有什么沙滩了,从河道到河岸都被整治得牢固而又笔直,我们徜徉在河岸上,这河岸是一条用钢筋混凝土筑起来的城市景观大道,这所有的树木和花草,也是经过人类反复修整过的。但这就是现代化的进程之一,你若问在这河畔溜达的人,没有谁会在那深一脚浅一脚、还有野草疯长的河滩上溜达。幸运的是,河水依然清澈透明,河床上还铺满了漂亮的鹅卵石,这河里的鱼还不少,但一看就不是野生的,而是人养的。它们好像很喜欢拥挤在一起,很多的鱼,闹成一团数都数不清了,还有鱼一个劲地往里边钻。一眨眼,这宁静的河流就变得纷乱起来,波浪翻涌,水花四溅,有的鱼还在互相追杀,我眼睁睁地看见一条大鱼把一条小鱼一口吞进了大嘴里。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大鱼吃小鱼,而且不吐骨头。这让很多鱼都惊慌地蹿出了水面,然而这也是非常危险的,我看见一只鱼鹰蹲在一块石头上,它浑身的颜色和这块石头一模一样。这鱼鹰的速度超过了我的想象,连眨一下眼也来不及,一条蹿起来的鱼就被它又尖又长的嘴巴叼住了,旋即又拍着翅膀飞走了。
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一直隐忍不言,也一直带着平静的表情,很可能,我已经成了一个灾难的同谋。那些无辜的鱼类永远不会懂得人类此时的心理,我正在心中窃喜,有强者对弱者的猎杀,才有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的丛林法则,这条河至少还保留了部分野生的自然状态,一条生物链还没有完全断裂。然而,当人类沦为大自然的弱者,我又将情何以堪?
如果不是这蒙古族老人告诉我,我是不可能把眼前这条阿伦河和灾难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条缓慢起伏的河流竟然也会兴风作浪,以泛滥的方式给阿荣人带来了一次次洪灾。有些事,你觉得简直不可能发生的事,只要猛地一想,立刻就恍然大悟了。阿伦河是一条中小河流,但又绝不是一条孤独的河,当你把阿伦河和嫩江、松花江等大江大河联系在一起,对她制造的灾难你就一点也不会感到吃惊了。阿伦河是嫩江的支流,嫩江又是松花江的支流,這所有的水系是联系在一起的,否则就是一条死河了。1998年在长江流域暴发特大洪水时,松花江上游和嫩江流域先后发生了三次大洪水,嫩江支流诺敏河、阿伦河、雅鲁河、绰尔河、洮儿河在一夜之间仿佛都从柔情似水的母亲变成了张牙舞爪的魔鬼——洪魔。这也是二十世纪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的最大的一次洪水,阿伦河的水位、流量都超过了历史最高值,也远远超过了按十年一遇设计的防洪能力。十多年过去了,那惊天动地的巨浪还一次又一次地在阿荣人的记忆里猛扑,洪水扑向堤坝,撕开了一道道裂口,那浑浊的浪头仿佛是一群放出来的猛兽,凶狠地扑向农田、村庄、道路、桥梁,还有草原上的蒙古包和牛栏、羊圈,天苍苍,野茫茫,但不见草原,只有泛滥的洪水在四面八方汹涌,几乎淹没了整个世界。
许多阿荣人目睹了这一切,又不敢相信这一切,哪怕在回忆中,他们也不敢相信这个让他们无比惊愕的事实,老天啊,一条阿伦河,怎么突然就会有这么多水呢?仿佛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啊。这也的确是一个值得人类反复追问的灾难性事实。在经历了一场大洪灾之后,阿伦河也因此成了众多水利专家反复研究和剖析的一个标本。这不止是为了治理一条阿伦河的洪水,而是为了探索一系列中小河流防洪的对策。——这其实也是我对这条阿伦河特别关注的原因。
我来这里时,阿伦河河道整治工程已经开始实施了,这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工程,就是阿荣旗河西新区防洪大堤工程。如今的水利建设,已经不是狭义的水利了,现代人的视野越来越开阔,每干一个工程都会考虑到它举一反三的综合效益,也就是所谓乘法效应。譬如说阿荣旗河西新区防洪大堤,防洪只是目的之一,这是一个集防洪、交通、生态景观和城市新区开发为一体的综合工程,总投资四个多亿。这对一个旗已经是大手笔了。现在工程还在加紧施工,但一幅如同实景的蓝图已经在工程指挥部竖立起来了。指挥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就对着这幅蓝图,给我们讲解:这一堤防工程级别为Ⅱ级,设计防洪标准要超过五十年一遇,堤防与水域之间预留180米跨度,形成亲水平台,并将被打造成市民的一个休闲区域。而这道大堤既是一条拥有双向八车道的城市大道,也是防洪抢险的应急通道,还是一条滨河景观大道。沿着这条景观大道流淌的阿伦河,也将被打造成一条景观河。有了这道大堤的守护,防洪堤西移后形成的六平方公里土地便不再受洪水威胁,这对于阿荣旗是一块宝贵的开发用地,相当于现在的半个那吉镇,如果开发出来,可新增十万城市人口,这也为阿荣旗退牧还草、退耕还林提供了人口转移的巨大空间。阿荣旗现有人口三十多万,如果能从草原牧区和大兴安岭林区再逐渐转移出十万人口,来发展阿荣旗的第三产业,无论是从城市综合功能、宜居水平和经济发展,都会把阿荣旗推向新一轮的黄金发展期。而更重要的还是随着人类的主动退出,那些草原和森林将会成为真正的大草原和原始森林。
听了这样一番介绍,让我打心眼里佩服这些阿荣人,他们很牛,不但要把一个水利工程打造成为东北地区的一大亮点,一个不但景色美,还要发挥出综合效益的精品工程,从水利的意义上看,这一水利工程,又何尝不是当代水利事业的一种华丽转身。这话似乎有点滥了,但事实上这也正是现代水利转型的真谛。而更重要的还是,一场灾难已经让人类的大脑更有了一种理智上的清醒,应该给大自然留下更大的空间,只有当人类和大自然成为同谋,大自然才不会和灾难成为同谋。否则,人类永远都是灾难的主角,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
我也该转身了。接下来的一段路,不是顺着阿伦河的流向,而是逆水而行。沿着一条阿伦河,从那吉镇上溯不远,就是新发朝鲜民族乡。内蒙古自治区的每一个乡几乎都是民族乡,但新发乡却是唯一的,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的朝鲜民族乡。朝鲜族是勤劳的农耕民族,在辽阔的呼伦贝尔大地上,这里也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农耕区,而且是稻作区。阿伦河两岸都是黑油油的泥土,连一条土路也是松软黝黑的,土壤里掺杂着大量的腐殖质,脚踩下去软绵绵的,一种触不到底部的感觉,不知这大地有多么深厚。一个地方拥有这样肥沃的黑土地,真是什么都肯长,大豆、玉米、马铃薯、葵花、水稻,还有各种小杂粮。阿荣旗是全国著名的产粮大县,也是全国优质商品粮基地县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五个大豆主产区之一,素称“粮豆之乡”,粮食生产能力高达三十亿斤。此时正是端午节前后,也是一年中万物生长最旺盛的季节,这让人更感觉到这一片乡土的灿烂,阳光普照,黄金遍地。
走进新发朝鲜民族乡,在众多的农作物中,长势最喜人的还是水稻。这一方水土,不愁没有水,地上、地下都是水,挖一条渠道,就能从阿伦河里把水引到水田了。若还嫌麻烦,在地上随便开个口子,也有泉水从地底下咕嘟咕嘟地冒出来。这真是一片奢华的乡土,这里的朝鲜族老乡喝的不是河水,而是更加甘甜清纯的山涧泉水,他们甚至用山涧泉水来种水稻,想一想,也知道这里的大米饭有多香啊。这里人种稻子的历史也很长了,在东北还很少有人种稻子时,这些在战乱中从朝鲜、韩国逃离而来的朝鲜人就开始在这里种稻子了。“阿伦新米”,是这里打造的一个著名绿色品牌,远销海拉尔、北京、俄罗斯。名不虚传,在这里,我吃到了有生以来最好吃的大米饭,米粒圆润碧透,煮出来的米饭油亮,醇香,实话实说,这比我在玉田皋吃到的大米饭更香、更可口,这里的水质也比那儿好得多。
我是跟着一条阿伦河走向大兴安岭的。
河流离大山越近,越是清冽,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净洁得近于虚无。只有当你看到了翻起的浪花,听见河水在尖叫,你才会发现那是一条河呢。这样的发现,一定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果然,等到走近了,就看见了河床上横亘着一块块大石头。这石头是从山上滚下来的,滚下来的不但只有石头,还有被连根拔起的大树,看着这样一棵全须全尾的大树,不知在山上长了多少年头了,好端端的,是谁又有这么大的力气把它们连根拔起了呢?不用说,只有山洪和泥石流才会有这样大的力量。我站在通往库伦沟的山道上,朝大兴安岭深处看,这一带山岭证实了我的猜测,很多的倾斜的山坡都被山洪和泥石流冲出了一道道沟壑,有的地方甚至被掏空了,变成了危险的悬崖,那些树也只能以悬空的方式长着,它们的生命力又是如此顽强,整个树蔸都暴露在外面,悬在空中,却依然向着天空不屈地生长。看了这危险的生命,我心里十分清楚,它们的命运已不是什么悬念,只要一场不大的山洪,它们就会随着一块块山石冲下来,顺势翻滚到河谷里,让河水发出更大的沸腾和尖叫。
大兴安岭太大了,但我知道,只要跟着一条阿伦河,就不会走失。
大兴安岭脚下,就是无边无际的草原牧场,这里的草原虽然没有呼伦贝尔大草原辽阔,但牧草更加茂盛、鲜美,那些在草原深处游动的牛羊和马群,都长得毛光发亮。如果不是它们给草原带来了一些动感,你会觉得这里一切都是时空之外的静物。草原上,还有一些被岁月抛弃的旧什物,一辆蒙古牧民的高轮车,不知经历了多少风吹雨打,看上去已是一副骨骼,但依然坚固无比。但对于一个不熟悉草原的人,这里布满了危险的陷阱,譬如说那些草长得最深最茂密的地方,那其实不是草原而是巨大的沼泽湿地,最危险的不是那长得淹过了肩膀的草丛,而是那些随时可能会让你陷入没顶之灾的“大烟泡”。何谓“大烟泡”?大烟泡就是最危险的沼泽。人过沼泽,你看不见哪里是沼泽,但沼泽却知道你,哪怕稍微有点响动,立刻就会腾起一股沼气,恰似大烟泡。而等你看见大烟泡时,你想抽身而退就已经来不及了。这也是大自然为人类设置的禁区之一。哪怕你看见有人陷入了沼泽,看见那从烂泥中伸出来的手臂,但你却不能去拽他,你一拽,连自己也陷进去了。但这样的沼泽,野兽们都可以经过,连牛马这种高大的动物也能轻松涉过,沼泽上也有路,它们都知道,但人类不知道。
汽车一直在大兴安岭脚下疾奔,沿途几乎看不见村庄,也很少看见车辆和行人。但偶尔会惊见在树丛和荒草中一蹿一蹿的身影,那是一种毛茸茸的棕黄色野兽。这对我们这些孤独的旅人是最惊喜的发现,有人大叫起来,鹿,野鹿!但一个与我们同行的蒙古族兄弟立马就纠正了这一错误的认识,不是鹿,是狍子!其实,一只狍子的出现并不稀奇,但那是以前,现在别说狍子,连一只小兔子的出现也令人感到惊奇了。狍子也是一种鹿科动物,而且是傻得出了名的,在查巴奇鄂温克族乡,我听一个鄂温克族老猎人说过,别的野兽一听见枪响就会逃得无影无踪,只有这个傻狍子还睁大了眼睛对着枪口张望,它到底想要看清什么呢?但这个世界不会给它第二次逃命的机会,第二颗子弹准确地击中了它,当猎人走到它身边,它依然圆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很多人都以为让这傻狍子丢掉性命的就是它们天生的好奇心,但这位蒙古族兄弟又一次纠正了这个严重的错误,这个季节正是狍子的哺乳期,它一旦发现了危险就会一蹿一蹿地猛跑,这是为了把危险的敌人从它们的幼崽那里引开,而它之所以不躲避猎人的枪口,也是害怕你把枪口转向它的幼崽。
当他把一种生灵的命运讲到这里,一车人都寂静了,每个人的神情都近于悲戚,如同默默地凭吊着什么。
长途汽车颠簸了漫长的一天,我们才在夜晚十点多钟抵达库伦沟原始森林。
这个地方不能不来,南有九寨沟,北有库伦沟。
在这个异常炎热的夏天,我在库伦沟经历了寒冷的一夜。大兴安岭的“兴安”也是满语,意为最寒冷的地方——极寒处。但天一亮,气温又像大兴安岭的太阳一样眼看着就升上来了,然后就感觉太阳一直在直射。阳光如此强烈,或许与这里的天空非常洁净有关,这里的天空干净得不见一丝云翳,阳光几乎是无遮无拦地照射下来的。这也让整个库伦沟层次分明,骄阳之下,层林尽染。
最早知道大兴安岭,是在中学的地理教科书上: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茂密,是我国重要的林业基地之一,主要树木有兴安落叶松、樟子松、红皮云杉、白桦、蒙古栎、山杨等。但事实上,这应该是二十世纪前的大兴安岭。从二十世纪初开始,随着第一条横贯大兴安岭山区的铁路——从齐齐哈尔到满洲里的中东铁路修通,人类就开始大量采伐这里的木材,尤其是在日本侵占东北后,又从中东铁路的南北各段修建多条铁路进入大兴安岭,他们的目的之一,就是大肆砍伐这里的树木。而这样的砍伐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但没有停歇,由于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木材,砍伐也变成了更大规模的砍伐。到了1987年5月6日,一场灾难性大火席卷了大兴安岭,摧毁了一百万公顷林木,这场灾难也被称为“五六大火”,又因黑龙江流过林区,又称“黑龙大火”。如今,在大兴安岭已经很难看到真正的原始森林了,这里大多数都是过伐林,也就是近几十年来营造的原始次森林。
走进一片阔大的白桦林,这么大一片白桦林还真是很少看见,感到很震撼。但令人震撼的是这片树林之大,而不是树之大。这里的白桦树一看就没有太深的岁月。而那些参天古树,也只有通过这里老人们的回忆才能想象,譬如说那些樟子松,不知长了多少年头了,都成了神树了,几十个人围成一圈,手牵着手才能合抱。这样的古树据说在库伦沟还有,但我们这些外人是走不进去的。我在呼伦贝尔看到的最大的一棵古树,就是查巴奇鄂温克族乡的那棵神树,一棵长了四五百年的榆树,这也是鄂温克人的敖包神树,鄂温克人说这里是山神歇脚的地方,他们在树下设下了图腾崇拜的祭坛。
而在这里,库伦沟,我只能像我的蒙古族兄弟图特戈一样诚实地说,我没有看到真正的原始森林,那么,从库伦沟上到大兴安岭峰顶,又能否看到原始森林呢?大兴安岭的最高峰海拔两千多米,而我们要登的大兴安岭的南高峰——图博勒峰,也是阿荣旗境内的最高峰,这对我们是一次极大的挑战。
说是一座高峰,又几乎看不见山峰。事实上也是这样,或许是一座大山太伟大了,反而无法让峰峦凸显出来吧。大兴安岭南起于热河高地——承德平原,北至黑龙江畔,南至西拉木伦河上游谷地,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是内蒙古和东北最大的山系,也是内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的分水岭,为重要的气候分带。夏季海洋季风受阻于山地东坡,大兴安岭东麓雨水充沛,呼伦贝尔和阿荣旗正好处在东麓,而西坡则比较干旱,这干旱的地方又正好是辽河流域了。
我们在茂密的森林里缓慢地爬山,绝对没有攀登险峰的感觉,山坡很平缓,但爬起来特别累。随着山势的缓慢递升,树木也在变化,从蒙古栎、落叶松到樟子松,不同的高度生长着不同的森林。当云杉出现时,我们已经爬不动了。但没有人问还有多高呢?只是问,还有多远呢?我们难以逾越的仿佛不是一个高度,而是这缓慢而漫长的坡度。给我们带路的人一直在说,快了,不远了。但眼前,依然只有苍莽山野无穷无尽地延伸。大兴安岭太大了,大得足以令人绝望了。眼看着我们已经爬不动了,一辆火红色的森林防火运兵车开来了。事实上,我们就是坐着这火焰般的运兵车爬上山顶的。但爬上了山顶,登上了一座比图博勒峰更高的防火瞭望塔,从这里一眼能望出几十公里远,即便在这样的高度,我也没有置身于山顶的感觉。山顶浑圆,地形平滑。我四下张望了许久,最终也没看清大兴安岭的样子。
一个著名诗人说,大兴安岭是平的。
但我却压根就没有看清楚大兴安岭的模样,大兴安岭是看不见的。
还想再看看,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有一种东西一直嗡嗡嗡地追赶着我们又叮又咬,看上去像是牛虻,这里人叫瞎蠓,黑压压的,成群地飞舞着,哪里有人类,就会被它们包围。这嗜血的小动物,一旦嗅到了血的味道就会发起凶狠的攻击,连牛仔裤也能被它们叮透。只要被牛虻叮上了一口,就会迅速地红肿起来,又痒又疼。我们几乎是从山上逃下来的,几乎每个人都伤痕累累,或许那里原本就是它们的领地,我们只是一群贸然闯入的入侵者。
有人说,应该在这山上多洒一点杀虫药,就没有这么多瞎蠓了。
这时候,我们的蒙古族兄弟却慢声慢气地说了一句,如果人类把蚊子都治没了,大自然就彻底消失了。
有一种声音,是下山时听见的。是水声,四面八方都是水声,在这起伏的森林里哗哗流淌,仿佛有千万条河流在这大森林里奔涌。但我没有看见河流在哪里,只看见了那被嫩江和松花江的许多支流深深切割的沟壑。虽说没有看到河流,但我早已知道,每一条河流的源头都是山。一条绵延千里的山脉,其实也是水脉,它是黑龙江、松花江、嫩江水系和辽河水系的分水嶺。大兴安岭是东北最伟大的山,也是东北诸河之父,嫩江、松花江和黑龙江等众多河流的源流以及支流,几乎都源出于此。这世界上除了看得见的河流和看不见的河流——隐秘的地下河,至少还有两种水源:一种是雪山冰川,那是天然的固体水库;一种是森林,这是天然的绿色水库。看不见的大兴安岭,却是一座谁都看得见的巨大的绿色水库。这漫山的森林正在激起了水的喧哗,没有下雨,太阳一直直射着,但我已经浑身湿透了。
有人把阿荣旗喻为浓缩的呼伦贝尔,这里也的确浓缩了呼伦贝尔所有的风景。走遍天下江湖,难得这里还保留了一片真正的净土,一片几乎没有经过人工雕琢的原生态净地。仰望大兴安岭的天空,不是干净,而是圣洁,这样的蓝天和白云,我只在青藏高原上看见过。从蓝天、白云到清新的空气,从河流、湖泊、湿地、山林到这里恒久而深厚的大地,可以说,这里的一切像她的名字一样干净、清洁。早就听说阿荣有多美,当我走在这辽阔的大地上,才真正懂得了庄子的那句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无言的阿荣,以无言的方式完成了一种从天空到大地的演绎,大美的演绎。
(责任编辑 高颖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