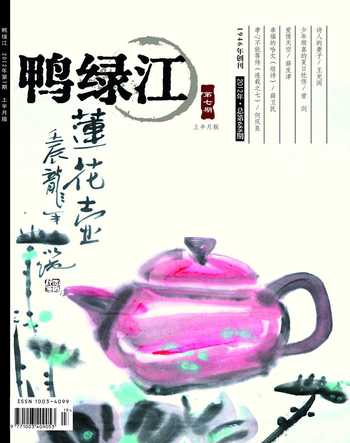诗人的妻子
2012-04-29王充闾
王充闾,国家一级作家。辽宁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兼任南开大学、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散文集《清风白水》《沧桑无语》《何处是归程》《历史上的三种人》《龙墩上的悖论》《张学良人格图谱》等三十余种。散文集《北方乡梦》译成英文、阿拉伯文。《春宽梦窄》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鲁迅文学奖”。
一
在妇女地位低下、“妻以夫贵”的旧时代,凭借着丈夫的权势与财富,作威作福,颐指气使,飞黄腾达的女子,数不在少。皇帝之妻、宰相之妻、状元之妻,自不必说,即使是六品黄堂、七品知县的妻子,也统统被称为命妇。唐代的命妇,一品之妻为国夫人,三品以上的为郡夫人,四品的为郡君,五品的为县君。清制,命妇中,一品二品称夫人,三品称淑人,四品称恭人,五品称宜人,六品称安人,七品以下称孺人。反正都是有封号、有待遇的。
但是,诗人的妻子不在其内,除非丈夫做了大官,否则,不但享受不到那些优渥的礼遇,生活上还会跟着困穷窘迫。这就引出了幸与不幸的话题。套用过去那句“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老话,也可以说,一为诗人之妻,便只有挨累受苦的份儿了。这是不幸。但是,如果嫁给一个真情灼灼、爱意缠绵的诗人,生前诗酒唱和、温文尔雅自不必说;死后,他还会留下许多感人至深、千古传颂的悼亡诗词——这也是不幸中之大幸吧。
此刻,我首先想到了苏东坡的三位妻子。她们都姓王,死得都比较早,一个跟随着一个,相继抛开这位名闻四海的大胡子——苏长公。
先说苏公的第一任妻子王弗。虽然岁数很小,却知书达理,聪慧异常,对丈夫百般体贴,成为丈夫仕途上的得力助手。曾有“幕后听言”的故事流传于世。苏东坡这个人,旷达不羁,待人接物宽厚、疏忽,用俗话说:有些大大咧咧。由于他与人为善,往往把每个人都当成好人;而王弗则胸有城府,心性细腻,看人往往明察无误。这样,她就常常把自己对一些人的看法告诉丈夫。出于真正的关心,每当丈夫与客人交谈的时候,她总要躲在屏风后面,屏息静听。一次,客人走出门外,她问丈夫:“你花费那么多工夫跟他说话,实在没有必要。他所留心的只是你的态度、你的意向,为了迎合你、巴结你,以后好顺着你的意思去说话。”她提醒丈夫凡事要多加提防,不要过于直率、过于轻信;观察人,既要看到他的长处,也要看到他的短处。苏东坡接受了妻子的忠告,避免了许多麻烦。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年轻貌美、精明贤惠的妻子,年方二十七岁,便撒手人寰,弃他而去了。
东坡居士原乃深于情者,遭逢这样的打击,情怀抑郁,久久不能自释,十年后还曾填词,痛赋悼亡。这样,由于嫁给了一位大文豪,王弗便“人以诗传”,千载而下,只要人们吟咏一番《江城子》,便立刻想起她来——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上阕抒写生死离别之情,面对知己,也透露了自己的因失意而抑郁的情怀,“凄凉”二字,传递了个中消息;下阕记梦,以家常语描绘了久别重逢的情景,以及对妻子的深情忆念,
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她小苏长公十多岁。自幼,她就倾心佩服姐夫的文采风流,姐姐故去,锐身自任,相夫教子,承担起全部家务。她默默地支持苏轼度过了一生中崎岖坎坷、流离颠沛的二十多年。其间,东坡遭遇了平生最惨烈的诗祸:“乌台诗案”——以“谤讪新政”的罪名,被抓进乌台,关押达四个月之久。这是北宋时期一场典型的文字狱。
熟读过《后赤壁赋》的当会记得其中这样一段:“客曰:‘今者薄暮,举纲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不时之需。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那位说“我有斗酒”的妇人就是王闰之。由于被大文豪的丈夫写进了名篇,因而亦传之不朽。
王闰之死时,东坡居士已经五十八岁。他忍不住涕泪纵横,哭得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当即写下了这样一篇深情灼灼的祭文:
呜呼!昔通义君,没不待年,嗣为兄弟,莫如君贤。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
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顷,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
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尚飨!
全文分三部分,开始说闰之是贤惠的妻子、仁德的母亲,视前妻之子,一如已出;接上说,丈夫屡遭险衅,仕途蹉跌,她能安时处顺,毫无怨言;最后作出承诺:生则同衾,死则同穴。
“通义君”指王弗,这是王弗殁后朝廷对她的追号。“没不待年”,是说王弗去世不到一年,他与闰之的婚事便定了下来,因为王弗留下的幼儿急待人来抚育。“三子”,一是王弗留下的,加上闰之自己生育的两个。
苏东坡被贬黄州,闰之“从我南行”,生活十分拮据,困难时吃豆子、喝白水,妻子也欣然以对;待到丈夫接受两郡封邑,收取许多赋税(意为富裕),她也并没有怎么欢喜。即古人所说的“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孰馈我田”,有学者研究,元丰二年七月发生乌台诗案,苏东坡下狱,闰之为了营救丈夫,不得不向父亲求救,父亲拿出很多财产让她去京城打点。
妻子死后百日,苏东坡请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和尚为王闰之诵经超度时,将此十张画像献给了妻子亡魂。待到东坡去世后,弟弟苏辙按照兄长的意愿,将他与闰之合葬在一起,兑现了当初的承诺。
苏东坡的第三任妻子,也姓王,名朝云,字子霞,年龄小于东坡近三十岁。她从十一岁即来到王弗身边,后来被东坡纳为小妾;流放到岭南惠州时,只有她一人随行,两人辛苦备尝,相濡以沫。在她三十四岁这年,东坡曾写诗《王氏生日致语口号》,中有句云:“天容水色聊同夜,发泽肤光自鉴人。万户春风为子寿,坐看沧海起扬尘。”可是不久,惠州瘴疫流行,朝云即染疾身亡。东坡悲痛异常,觉得失去一个知音。
明人曹臣所编《舌华录》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苏轼一日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一婢女应声道:“都是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苏轼也未首肯。爱妾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认为“实获我心”。
朝云死后,苏东坡将她葬在惠州西湖孤山南麓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筑亭纪念,因朝云生前学佛,诵《金刚经》偈词“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而逝,故亭名“六如”。楹联为:
从南海来时,经卷药炉,百尺江楼飞柳絮;
自东坡去后,夜灯仙塔,一亭湖月冷梅花。
还有一副楹联: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妙在以东坡口吻,状景描情,极饶韵致。
说到死后有丈夫赋诗悼亡,人们会自然地想到唐代元稹的妻子韦丛。她死了以后,有人统计,元稹至少为她写了十六首诗,就中以写于妻子殁后两年的《遣悲怀》三首,为感人至深,影响最大: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诗从生活细事入手,句句都是写实。“最小偏怜”云云,说的是韦丛是太子太保韦夏卿之幼女,从小锦衣玉食,生长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中。二十岁时嫁过来,那时,元稹还是一个穷书生,家境十分贫寒:“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正是当时境况的写照,于今已成辛酸的记忆。婚后第七年,韦丛便因病离开人世。这七年,正是元稹勉力上进、奔走仕途之时,处境既不稳定,生计又很艰难,他们一直过着“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苦日子。后来,元稹才开始发迹,可是,夫欲照拂而妻不稍待,说来悔恨无及。所以说,这是令人倍感惆怅的诗。陈寅恪先生说:《三遣悲怀》“所以特为佳作者,直以韦氏之不好虚荣,微之之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因能措意遣词,悉为真实之故。夫惟真实,遂造诣独绝欤”!
三首诗层次分明,开始叙写旧日生活苦况,追忆妻子生前的夫妻情爱,并抒写自己的抱憾之情;接着写妻子去世后诗人的悲思,写了在日常生活中引起哀思的几件事。为了避免睹物思人,将妻子穿过的衣裳施舍出去,将妻子做过的针线活原封不动地保存起来,不忍打开;最后,写由妻子之早逝得到的人生感悟,想到世事无常,人寿有限。从悲君中引出自悲,从绝望中转出希望,期望来生再作夫妻。但很快就悟解到,这不过是一种虚空的幻想。那么,究竟怎么办呢?最后落到“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上,仍然是无可奈何。
元稹还写过《离思五首》七绝。之四是: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宣示了与韦丛的爱情的唯一性,读来同样予人以特别的震撼。
二
“三王一韦”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个幸运的卢女,她是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的妻子。卢氏的父亲卢兴祖是两广总督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母亲也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而她更是生得清丽妩媚,宛如出水芙蓉,不仅娇好美艳,体性温柔,而且高才夙慧,解语知心;配上俊逸潇洒、玉树临风般的纳兰公子,二人真是天生一对。婚后,两人相濡以沫,整天陶醉得像是淹渍在甘甜的蜜罐里。随着相知日深,爱恋得也就越发炽烈。小小的爱巢为纳兰提供了摆脱人生泥淖、战胜孤寂情怀的凭借与依托。任凭外间世界风狂雨骤,朝廷里浊浪翻腾,于今总算有了一处避风的港湾,尽可以从容啸傲,脱屣世情,享受到平生少有的宁贴。
婚后,二人在绮罗香泽的温柔乡里,尽享鱼水之欢。这有纳兰的诗词为证:
水榭同携唤莫愁,一天凉雨晚来秋。
戏将莲■抛池里,种出花枝是并头。
十八年来坠世间,吹花嚼蕊弄冰弦,多情情寄阿谁边。
紫玉钗斜灯影背,红绵粉冷枕函偏,相看好处却无言。
——调寄《浣溪沙》
在任何情况下,意中人乐此不疲的相互欣赏,相互感知,都是一种美的享受。朝朝暮暮,痴怜痛爱着的一双可人,总是渴望日夜厮守,即便是暂别轻离,也定然是依依相恋,难舍难分。有爱便有牵挂,这种深深的依恋,最后必然化作温柔的呵护与怜惜,产生无止无休的惦念。
纳兰这样摹写将别的前夜:
画屏无睡,雨点惊风碎。贪话零星兰焰坠,闲了半床红被。
生来柳絮飘零,便教咒也无灵。待问归期还未,已看双睫盈盈。
夫妻双双不寐,絮语绵绵,空使灯花坠落,锦被闲置。他们也知道,这种离别皆因王事当头,身不由已,祷告无灵,赌咒也不行,生来就是柳絮般飘泊的命了。既然分别已无可改变,那就只好预问归期了,可是,她还没等开口,早已秋波盈盈,清泪欲滴了。一副小儿女婉媚娇痴之态,跃然纸上。
暂别尚且如此,那么,终古长别呢?简直无法想像。
不可想象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三年时间不到,刚刚二十一岁的卢氏就香消玉殒了。时在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这晴天霹雳,震处纳兰公子蒙头转向,好长一阵子,他失去了反应,不会吃,不会喝,不会哭,不会说,白昼昏昏,夜不成寐,这冷酷的现实,无论如何,他也不能接受。
灵柩在入葬纳兰氏祖茔皂荚村之前,临时停放在京西阜成门外的一座禅院里,位置相当于今日的紫竹院公园。这里原是明代一个大太监的坟茔地,万历初年在上面建起了一座双林禅院。这个期间,痴情的公子多次夜宿禅林,陪伴着夜台长眠的薄命佳人,度过那孤寂凄清的岁月。
忆生来,小胆怯空房。到而今,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
他知道爱妻生性胆小怯弱,连一个人独自在空房里都感到害怕,可如今却孤零零地躺在冰冷、幽暗的灵柩里,独伴着梨花清影,受尽了暗夜凄凉。
夜深了,淡月西斜,帘栊黝暗,窗外淅沥潇飒地乱飘着落叶,满耳尽是秋声。公子枯坐在禅房里,一幕幕地重温着当日伉俪情深、满怀爱意的场景,眼前闪现出妻子的轻颦浅笑,星眼檀痕。他眼里噙着泪花,胸中鼓荡着锥心刺骨的惨痛,就着孤檠残焰,书写下一阕阕情真意挚、凄怆恨婉的哀词,寄托其绵绵无尽的刻骨相思。
心灰尽,有发未全僧。风雨消磨生死别,似曾相识只孤檠。情在不能醒。
生死长别,幽冥异路,思恋之情虽然饱经风雨消磨,却一时一刻也不能去怀。他已经完全陷入无边的痛苦之中而不能自拔,迷离惝恍,万念俱灰。除了头上还留有千茎万茎的烦恼丝,已经同斩断世上万种情缘的僧侣们没有什么两样了。
一阕《浪淘沙》更是走不出感情的缠绕:
闷自剔银灯,夜雨空庭。潇潇已是不堪听。那更西风不解意,又做秋声。城柝已三更,冷湿银屏。柔情深后不能醒。若是情多醒不得,索性多情!
情多、多情,醒不得、不能醒……回旋宛转,悱恻缠绵。沉酣痴迷,已经到了无以自解的程度。深悲剧痛中,一颗破碎的心在流血,在发酵,在煎熬。
在旧时代,即使是所谓的“康熙盛世”,青年男女也没有恋爱自由,只能像玩偶似的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随意摆布;至于皇亲贵胄的联姻,往往还要掺杂上政治因素,情况就更为复杂了。身处这样的苦境,纳兰公子居然能够获得一位如意佳人,实现美满的婚姻,不能不说是一桩幸事。不过,“造化欺人”,到头来他还是被命运老人捉弄了——称心如意的偏叫你胜景不长,彩云易散。一对倾心相与的爱侣,不到三年时光,就生生地长别了,这对纳兰公子无疑是一场致命的打击。
脉脉情浓,心心相印,已经使他沉醉在半是现实半是幻境的浪漫主义爱河之中,想望的是百年好合,白头偕老。而今,一朝魂断,永世缘绝——这个无情的现实,作为未亡人,他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因而,不时地产生幻觉,似乎爱妻并没有长眠泉下,只是暂时分手,远滞他乡,“影弱难持,缘深暂隔,只当离愁滞海涯”;他想像着会有那么一天:“归来也,趁星前月底,魂在梨花。”当这一饱含着苦涩味的空想成为泡幻之后,他又从现实的想望转入梦境的期待,像从前的唐明皇那样,渴望着能够和意中人梦里重逢。虽然还不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但却总嫌梦境过于短暂,惊鸿一瞥,瞬息即逝,终不惬意。
一次,他梦见妻子淡装素服,与他执手哽咽,临行时吟出两句诗:“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醒转来,他悲痛不已,题写了一首《沁园春》词: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阑曲处,同倚斜阳。梦好难留,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遗容在,只灵飙一转,未许端详。重寻碧落茫茫。料短发、朝来定有霜。便人间天上,尘缘未断;春花秋叶,触绪还伤。欲结绸缪,翻惊摇落,两处鸳鸯各自凉。真无奈,把声声檐雨,谱出回肠。
这样一来,反倒平添了更深的怅惋。有时想念得实在难熬,他便找出妻子的画像,翻来覆去地凝神细看,看着看着,还拿出笔来在上面描画一番,结果是带来更多的失望:
凭仗丹青重省识,盈盈,一片伤心画不成。
他几乎无时无日不在悲悼之中,特别是会逢良辰美景,更是触景神伤,凄苦难耐。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同夕)如环,昔昔都成■。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面对银盘似的月轮,他凄然遐想:这月亮也够可怜的,辛辛苦苦地等待着,盼望着,可是,刚刚团圆一个晚上,而后便夜夜都像半环的玉■那样亏缺下去。哎,圆也好,缺也好,只要你——独处天庭的爱妻,能像皎洁的月亮那样,天天都在头上照临,那我便不管月殿琼霄如何冰清雪冷,都要为你送去爱心,送去温暖。
目注中天皎皎的冰轮,他还陡发奇想:妻子既然“衔恨愿为天上月”,那么,我若也能腾身于碧落九天之上,不就可以重逢了吗?可是,稍一定神,这种不现实的想望便悄然消解了——这岂是今生可得的?
海天谁放冰轮满?惆怅离情。莫说离情,但值凉宵总泪零。只应碧落重相见,那(哪)是今生!可奈今生,刚作愁时又忆卿。
人处在幸福的时光,一般是不去幻想的,只有愿望未能达成,才会把心中的期待化为想像。纳兰公子正是这样。当他看到春日梨花开了又谢的情景,便立刻从零落的花魂想到冥冥之中“犹有未招魂”,想到爱侣,期待着能够像古代传说中的“真真”那样,昼夜不停地连续呼唤她一百天,最后便能活转过来,梦想成真。于是,他也就:
为伊判作梦中人,长向画图清夜唤真真。
妻子的忌日到了,他设想,如果黄泉之下也有阳世间那样的传邮就好了,那就可以互通音讯,传寄信息,得知她在那里生活得怎么样,与谁相依相伴,有几多欢乐、几多愁苦:
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
情到深处,词人竟完全忽略了死生疆界,迷失了现实中的自我。意乱情迷,令人唏嘘感叹。一当他清醒过来,晓得这一切都是徒劳,便悲从中来,辗转反侧,彻夜不能成眠。但无论如何,他也死不了这条心,便又痴情想望:今生是相聚无缘了,那就寄希望于下一辈子,“待结个他生知已”;可是,“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像今生那样,岂不照例是命薄缘浅,生离死别!
他就是这样,知其不可而为之,非要从死神手中夺回苦命的妻子不可。期望——失望——再期望——再失望,一番番的虔诚渴想,痛苦挣扎,全都归于破灭,统统成了梦幻。最后,他只能像一只遍体鳞伤的困兽,卧在林荫深处,不停地舐咂着灼痛的伤口,反复咀嚼那枚酸涩的人生苦果。
他正是通过这种层层递进的痴情泛溢,这种超越时空的内心独白,这种了无遮拦的生命渲泄,把一副哀痛追怀、永难平复的破碎的情肠,将一颗永远失落的无法安顿的灵魂,一股脑地、活泼泼地摊开在纸上。真是刻骨镂心,血泪交迸,令人不忍卒读。
三
不堪设想,对于皈依人间至纯至美的真情的诗人——元稹、苏轼、纳兰来说,失去了爱的滋润,他们还怎能存活下去?爱,毕竟是他们情感的支柱,或者说,他们的一生就是情感的化身。他们都是为情所累,情多而不能自胜的人。他们把整个自我沉浸在情感的海洋里,呼吸着,咀嚼着这里的一切,酿造出自己的心性、情怀、品格和那些醇醪甘露般的千古绝唱。他为情而劳生,为情而赴死,为了这份珍贵的情感,几乎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与泪水,直到最后不堪情感的重负,在里面埋葬了自己。
这种专一持久、生死不渝、无可代偿的深爱,超越了两性间的欲海翻澜,超越了色授魂与,颠倒衣裳,超越了任何世俗的功利需求。这是一种精神契合的欢愉,永生难忘的动人回忆、美好体验和热情期待,一朝失去了则是刻骨铭心的伤恸。
情为根性,无论是鹣鲽相亲的满足,还是追寻于天地间而不得的失落,反正诗人们哭在、痛在、醉在他们的爱情里,这是他们心灵的起点也是终点,在这里,他们自足地品味着人生的千般滋味。
生而为人,总都拥有各自的活动天地,隐藏着种种心灵的秘密,存在着种种焦虑、困惑与需求,有着心灵沟通的强烈渴望。可是,实际上,世间又有几人能够真正走入自己的梦怀?能够和自己声应气求,同鸣共震?哪里会有“两个躯体孕育着一个灵魂”?“万两黄金容易得,知音一个也难求!”即使有幸偶然邂逅,欣欣然欲以知已相许,却又往往因为横着诸多障壁,而交臂失之。
当然,最理想的莫过于异性知己结为眷属,相知相悦,相亲相爱,相依相傍。但幸福如纳兰,如苏轼,如元稹,不也仅仅是一个短暂而苍凉的“手势”吗?
当然,也多亏是这样,才促成这三位诗人以其绝高的天分、超常的悟性,把那宗教式的深爱带向诗性的天国;用凄怆动人的丽句倾诉这份旷世痴情。有人说,一个情痴一台戏。作为情痴的极致,诗人们在其有限生涯中,演足了这出戏,也写透了这份情。“情在不能醒”,多少为情所困的痴男怨女,千百年来,沉酣迷醉在他的诗句之中。
艺术原本是苦闷的象征。《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有言:
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
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那么,元稹、苏轼、纳兰呢?自然是寄哭泣于他们的诗词了。
作为出色的诗人,他们都怀有一颗易感的心灵,反应敏锐,感受力极强,因而他们所遭遇与承受的苦闷,便绝非常人所可比拟。为了给填胸塞臆的生命苦闷找出一条倾泄、补偿的情感通道,他们选定了诗词的形式,像“神瑛侍者”那样,誓以泪的灵汁浇灌诗性的仙草。
在经历过深重难熬的精神痛苦之后,诗人们不是忘却,也没有逃避,而是自觉强化内心的折磨,悟出人生永恒的悖论,获取了精神救赎的生命存在方式。在这里,他们把爱的升华同艺术创造的冲动完美地结合起来,以诗意般的情感化身展现出生命的审美境界,把个体的生命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结晶出一部以生命书写的悲剧形态的心灵史,它真纯、自然、深婉、凄美,突破了时空限制,具有永恒的价值。
诗人都是“性情中人”,有一颗赤子之心。他们听命于自己内心的召唤,时刻坦露着真实的自我,在污浊不堪的“人间何世”中,展现出一种新的人格风范。他们以落拓不羁的鲜明的个性之美和超尘脱俗的人格魅力,以其至真至纯的清淳内质,感染着、倾倒着后世的人们。尤其像纳兰这样的短命诗人,他像夜空中一颗倏然划过的流星,昙花一现,但他的夺目光华却使无数人为之心灵震撼。他那中天皓月般的皎皎清辉,荡涤着、净化着也牵累着、萦系着一代代痴情儿女的心魂,人们为他而歌,为他而泣,为他的存在而感到骄傲。
在今天,元稹也好,苏轼也好,纳兰也好,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解读诗性人生的一种文化符号,有谁不为这种原始般的生命虔诚而永远、永远地记怀着他们。
那天,应邀在市图书馆举行《纳兰性德及其饮水词》讲座,我刚刚走下讲台,就见听众席上走出一个女孩子,递过来一摺纸页。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首即兴诗:
从他身上 / 看到自身存在的根源 / 据说 / 他 / 就在我的前边 /距离不近 / 可也不能算远 / 往事虽在时间之外 / 空间代价却是时间/只要一朝 / 获得超光的时速 / 那就坐上飞船 / 追寻历史/ 赶上三百年前 / 参加过渌水亭诗会 / 再在太空站上 / 共进晚餐——我和纳兰
清代学人陈其泰评论《红楼梦》时说过:“宝玉温存旖旎,直能使天下有情人皆为之心死。”那他比起纳兰公子,又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