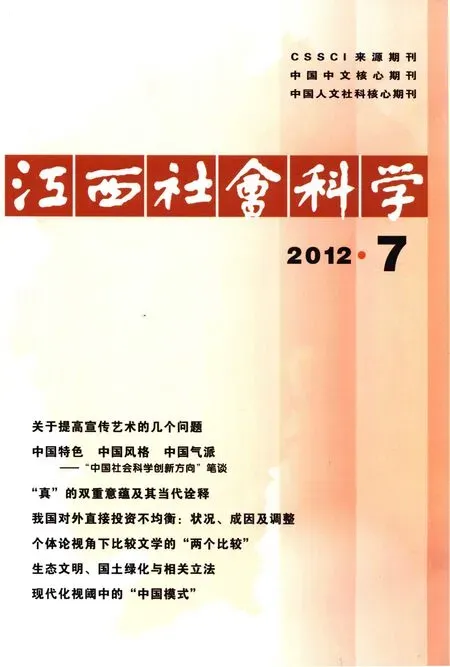启蒙现代性叙事与黑格尔的承认哲学
2012-04-18陈良斌
■陈良斌
启蒙现代性叙事与黑格尔的承认哲学
■陈良斌
承认哲学;主体间性;启蒙现代性;解放政治
20世纪中后叶,西方学者对黑格尔承认哲学的重新发现和全新诠释,不仅颠覆了黑格尔作为主体性哲学集大成者的传统形象,而且通过发掘承认命题与20世纪主体间哲学的理论勾连,使黑格尔自身显现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激进色彩。一般来说,黑格尔承认哲学的提出主要缘于对启蒙所倡导的主体性立场的反思,黑格尔主张从个体的“我”走向交互承认的“我们”,这是他对启蒙现代性规划开出的一剂“主体间性”药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对黑格尔在启蒙现代性进程中的复杂性地位进行重新审视,进而廓清这样的理论问题:黑格尔究竟是一位保守主义的代言者,还是一个激进的现代性异端?
一、启蒙现代性与承认的提出
启蒙至今,解放政治的历史叙事对于现代性的成长影响至深,以至于吉登斯指出,从近代到现代,无论是激进主义、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共同受解放政治的支配”[1](P247)。因为解放政治体现了一种普遍的人类历史观念,即所有人类历史都趋向一个作为终极目的的自由王国。所以,在启蒙规划的召唤下,林林总总的现代性理论其实都只是“解放政治”母题的一种具体叙事。[2]但各种纷繁的解放叙事显然都忽略了实现解放的历史路径。启蒙之后,上帝死了,解放政治的实现就再也没有神的羁绊,因此解放政治首当其冲要解决的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主客对立的结果是人不断地尝试主宰自然,但却无时无刻不受到自然的制约。随着近代生产力革命的爆发,物质基础逐渐达到极大丰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完成现代化,开始率先进入现代化的高级阶段——大众消费社会。在这里,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标志着物质的束缚已经达到极大缓解,主体与客体的矛盾终于得到了真正的和解,如果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语境来说,那么物质文明已经非常强大,所以在主客体的矛盾得到缓解或解决的背景下,解放政治剩下的最后一个制约就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矛盾。
如何摆脱他者的束缚成为现代性进程中挥之不去的一个主题。在黑格尔看来,主体之间的冲突就是承认哲学所要克服的核心问题。黑格尔的解决之道就是扬弃主体间的矛盾冲突,以交互承认的方式实现主体间的和解,这就是承认哲学的解放逻辑。具体来说,主体只有在他者承认的中介下才能回到自身,才能获得真正具体的自由,反过来,他者亦然。同时,交互承认本身所蕴含的前提就是将他者视为与主体自身均等的人,否则双方只会导致虚假的不平等承认的出现,而不会实现真正的承认。在黑格尔看来,承认哲学构成了实现解放政治的一种可行的历史叙事,同时承认哲学也构成了对启蒙现代性规划的一种反思的视角。在此基础上,黑格尔逐步丰富并完善了他的承认哲学,使之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承认哲学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学界对于黑格尔承认体系的建构过程始终众说纷纭①,笔者主张将黑格尔的承认哲学作为一个成长的连续体系,承认的脉络贯彻黑格尔思想发展的各个时期。因此,按照时间的顺序,承认体系的发展可以大致划分为耶拿早期和成熟期这两个阶段,成熟期阶段并不存在对于早期学说的抛弃。耶拿早期以《耶拿手稿》系列为代表,而成熟期以《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为代表。在《耶拿手稿》中,承认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爱与冲突。爱将交往双方统一起来。自我通过他者获得自身的实存。因而将自我与自身的内在关系经由他者的中介达成一种同一。因此,每个人都是通过他者和在他者之中成为自为存在。但是这时的黑格尔认为真正的承认只能通过生死斗争才能获得,所以个体之间靠爱的情感来维系的联系只能是有瑕疵的。这就必须过渡到另一类型——冲突。这种承认类型直接反映了市民社会的形成及其法律规范的产生,它们都是以成员间的相互承认为前设的。在这里,为承认而斗争可以被理解成个体为反抗侵犯(犯罪)或法律而发起的斗争。黑格尔规定了他者对所有物的侵占或否定构成了达成相互承认的必要前设,承认斗争正是由侵犯而产生的。被侵犯的这个客体与占有它的自我意识或自为存在的个体紧密相连,正是在客体中,个体找到了自身。事实上,所有物的侵犯影响着主体在自觉的个性中最深层的私人结构。随着侵犯的开始,个体为了获得承认,一场生死之争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3](P125-127)黑格尔特别强调了承认斗争和死亡是实现纯粹自我意识或精神的必要阶段。在这里,黑格尔选择将承认的欲望激进化至“斗争到死”的地步。“承认的原则不是自我限制,而是对他者的否定,它的实施没有任何限制。”[4](P144)可以看出,黑格尔的思想已开始发生一种转变,他在试图克服自由主义立场的缺陷,但这种克服不是通过约束它的基本前设,而是激进地将个人自由推进到极端或“否定性”,根据他的解释,这种否定性凸显了个人的主体性自由,进而构成了现代自然法的基石。
可以肯定的是黑格尔的观点在耶拿时期发生了相当的改变。尤其是他的实践哲学从绝对伦理性的概念逐渐发展成国家理论,这是对自由原则内在批判的结果,同时国家理论因而也为个人自由给予了更多的空间。这可能是对黑格尔对于政治古典主义概念的态度转变的最好的证明。”[4](P149-150)因此,承认哲学对于黑格尔而言,其实可以被看做为一种克服国家与个人之间对立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法国大革命其实并没有成功。因此,进入成熟期之后,黑格尔进一步站在承认的立场上将这种对于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关注深化下去,而在耶拿早期,黑格尔所构筑的国家概念则始终是高悬于个人和权利领域之上,他甚至十分赞同马基雅维利关于政治的观点,强调城邦中市民“顺从”的重要性,因此,正是承认哲学给黑格尔带来了这种巨大的转变。在成熟期中,最初的一个标志就是主奴之间“承认辩证法”的提出,黑格尔在这里提出了奴隶的解放是经由劳动的陶冶而实现的,因而提出了一条承认的替代路径,也就是劳动。通过主奴之间的冲突,黑格尔把为承认而斗争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他也发现了冲突模式的局限性,因此,黑格尔希望能找到一条克服的途径,最终他回到耶拿早期关于爱的模式,希望以爱来溶解交往的双方,并将爱视为相互承认的理想模式。这种理想模式虽然能够理想地克服冲突,但它并没有穷尽伦理的形式与内涵,按照黑格尔的设想,国家才是相互承认的最高阶段和实体性自由的实现,但是黑格尔对于国家相对应的承认形式并没有详加论证,因此,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按照这种设想提出了团结的模式[5](P127-134),作为国家层面相对应的承认类型而与前面的家庭、市民社会的承认类型相对应。
二、承认方案与主体性的诊断
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是独立自主的“大写”的人,因此,“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6](P1)。当人们在“二战”后陷入启蒙价值的迷思之后,就会越发理解黑格尔的深刻。黑格尔对于启蒙现代性的主体性立场始终保持一种明确的批判态度,但他并不简单地就认为主体性是错误的、需要抛弃的,而是给出了黑格尔式的辩证式诊断。他认为,启蒙现代性的主体性立场来源于笛卡尔-康德式的主体性理解,现代性倾向于将这种唯名论的主体性原则理解为一种抽象的个人主义,主张个体的主观自由,在黑格尔看来,这仅仅是主体性真理的一部分,因而是片面的。而在国家的起源上,以卢梭为代表的个人主义主张将国家的概念建立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黑格尔对此更是持否定的立场:“他(卢梭——笔者注)所理解的意志,仅仅是特定形式的单个人意志,他所理解的普遍意志也不是意志中绝对合乎理性的东西,而只是共同的东西,即从作为自觉意志的这种单个人意志中产生出来的。……为了反对单个人意志的原则,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基本概念,即客观意志是在它概念中的自在的理性东西,不论它是否被单个人所承认或为其偏好所希求。”[7](P255)(译文有改动)据此,黑格尔认为社会契约论是把伦理国家与市民社会误解和混淆了。为了克服启蒙现代性的个人主义倾向,同时为了能达到作为伦理共同体的国家理论,黑格尔主张恢复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共同体的传统来超越现代性的原子论,也就是提倡整体大于并优先于部分,个体应当在国家中获得真正的自由。但黑格尔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对现代性的诊断显然不是简单地回到古典国家,而是采取扬弃的方式以辩证的态度对古典国家观同样进行了批判。黑格尔相信,现代性中也必然要求交互承认,同时也必然包含着主观自由。这意味着黑格尔的观点与柏拉图的立场相反,也就是认为善是良善意志,同时正是因此,善没有现实地脱离主观自由的行为,“其结果,普遍物既不能没有特殊利益、知识和意志而发生效力并底于完成”[7](P260)。离开了自由,善将始终是抽象的[8](P116)。
由此看来,黑格尔虽然对于现代性所标榜的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提出了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所构想的国家共同体是以牺牲个体为代价的,同样,黑格尔虽然主张恢复古典传统,却并不是回到淹没个体的古典国家中去。黑格尔的高明之处就是既看到了两者都具有合理之处,同时也抓住了两者的片面之处,因此他将两者分别比作抽象的集体主义和抽象的个人主义,而他的任务就是在克服抽象个人主义和抽象集体主义的缺陷之后去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在此基础上,黑格尔的现代性诊断就是对古典的集体主义与现代的个人主义进行扬弃的同时,提出了第三种选择。在这个选择中,交互承认成为黑格尔所倚重的一个重要的批判维度。黑格尔首先从自为的存在出发,提出作为主体间性的“我们”。自为的存在在黑格尔那里具有两重截然不同的含义:一种是直接或抽象的含义,也就是第一人——“我”;另外一种是中介的和更为具体的含义,也就是第一人的复数形式——“我们”。黑格尔认为,直接的自为存在是抽象的、正式的和空无的,因此实践地表达在行为中就是任性(Eigensinn)或自我主义。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直接的自为存在仅仅是承认的出发点,而不是其基础。所以交互承认的过程是从简单的、直接的自为存在发展到中介的、有限制的主体间性的自为存在,也就是从“我”到“我们”。[9](P152)于是,“我们”是个体的联合,扬弃并扩大了他们的自我同一,同时要求和依赖于对他们个体自由的保护。这是对原初自为存在的一种交互式的丰富和扩充。同时,相互承认并不是在我和你之间简单地保持一种主体间的对话,它呈现为一种有机统一的形态,即意味着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之间的辩证的统一。个人从而在“我们”之中作为整体获得更大的同一性。因此,黑格尔是以“我们”的交互承认替代了费希特和谢林的“我就是我”的观念论范式。
在这里,交互承认将主体性转化为主体间性,而这与古典思想中整体大于并优先于部分的观点是一致的,同时个体也将充分的交互承认作为发展主观自由的目标,并在普遍性的社会意识中达到顶点。所以,交互承认是国家的一种理想统一体,是对黑格尔国家理念的现实诠释。承认将黑格尔的实体性自由与主观自由相统一。一方面,当现代性倾向于把主观自由进行原子化解释时,黑格尔就通过他者将主体性去中心化;另一方面,在他者中将主观性改造为伦理的主体间性。扩展了和去中心化的主体性不仅向伦理实体或实体性自由开放,而且在这些实体中发现自身,也就是在更大的整体中承认自身。因此,实体性自由不是他律的,而是包含着将自由现实化的必要条件[8](P266)。于是,只有在交互承认中自由和主观性才能得到充分发展,进而产生了客观精神。黑格尔相信承认的最终结果就是精神,而我就是我们。在这里,“精神就是规定的客观社会世界,一种客观理性的结构,或伦理实体”[8](P118)。
在此基础上,黑格尔回到对古典思想和现代性规划的诊断和改造上,认为两者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但是他们都是以片面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所以黑格尔的选择就是由交互承认构成的自由和公正的共同体来克服双方的片面性。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共同体并不是给定的或是一种自然共同体,而是一种已实现的精神的共同体,它是通过自由来实现的。现代性与它的主观自由以及古典城邦与它的社会结构概念都表达了自由共同体的基本维度和内涵。但是,它们自身对于共同体的阐述显然都是不完善的。在黑格尔看来,启蒙现代性的主体性思维对于基于规范文化的探讨是不充分的,因为这样的主体性会造成差异的绝对化。而古典思想的集体主义虽然为其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结构和内容,但是最终会导致权威极权主义而无法容纳主观自由。由此看来,双方的缺陷其实都能被另一方所弥补:现代主观性如果能满足特定文化结构上的条件,也就是整体优先于部分,就能克服自身的局限。相反,古典的整体机构只有通过主观自由的扩张同时经由交互承认进入主体间性作为条件,才能达到批判的实现[8](P118)。所以,黑格尔的做法其实是通过承认作为中介,使古代和现代和解,也就是“在伦理实体提供主观自由的内容与目标的同时,主观自由是一种为伦理实体的实现和现实化的工具”[8](P268)。只有完成了这种和解的国家观,也就是结合伦理实体和现代主观自由,才能最终实现实体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对此,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明确地指出:“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但具体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的领域中那样),而且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通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7](P260)
三、抽象的“我们”与黑格尔的困境
黑格尔站在交互承认的立场上完成了对现代性的诊断和批判,以主体间性的“我们”来替代主体性的“我”成为他的解决方案,但是黑格尔专注于构建一种抽象精神的思辨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我们看不到有血有肉的历史性主体,虽然主体处在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想的承认状态,拥有具体的自由,但是具体的自由依然是一种抽象的权利。显然,黑格尔推崇的是在思想深处爆发革命,而不是在现实中体会真切的主体间性,这也是他与马克思的最大区别。马克思主张哲学应当改造世界,而黑格尔的哲学只是解释世界。因此,密纳发的猫头鹰永远只是在黄昏才能起飞,哲学的解释永远落后于历史的车轮。由此看来,黑格尔的承认方案抑或现代性的诊断无论持何种激进的语调,他的立足点始终决定了其本质上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在黑格尔的承认体系中,比较明确地确立了承认的两种模式,即冲突与爱。冲突的模式换句话说就是为承认而斗争。在主奴关系中,两个主体为了获得承认而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而发生冲突,虽然由于一方的畏惧而出现了主人和奴隶的结局,但是这种关系却是不稳定的,奴隶在黑格尔看来才是真正推进历史的动力,奴隶通过劳动的陶冶,扬弃了自身的欲望,从而超越了主人,但是这种超越只是在奴隶的意识之中,在奴隶那里,真正的超越显然必须通过现实中新一轮的冲突并且战胜主人才能获得。于是,奴隶成了主人,但是这样的颠覆只会造成恶的循环。在这里,主奴的关系无法调和,在根本上其实是如何处理个人主义与集体/共同体价值的矛盾,因此,黑格尔虽然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为我们指明了一条主体间的发展方向,但是他的保守性却注定了他无法在现实中真正地解决矛盾所在。
由于前路无果,黑格尔最后倾向于回到耶拿早期所提出的爱的模式来获得对冲突模式的化解之道,但是,显而易见,现实的冲突不可能依靠爱情来解决。虽然主体们在爱之中抛弃了自身对他者的排斥,并在爱之中相互融合,但是,黑格尔却忘记了处于爱情之中的主体对于其他主体仍然具有排斥性,而成为亲情的爱则局限于血缘的纽带,对血缘之外的他者亦具有排斥性。所以,爱注定了它只能存在于婚姻和家庭的范围内,一旦扩大至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范围,就无法利用爱来消解主体间的承认冲突,因此爱的模式只能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无法现实地改造冲突模式下的恶之循环。因此,黑格尔的方案只会变成一种空中楼阁。按照黑格尔后期的思路,在伦理国家的层面应该还要建立一种更为高级的承认模式,但他在这里却戛然而止。霍耐特正是受此启发,根据这条思路发展出了第三阶段的承认模式,即团结的模式,但是,团结的承认模式并非霍耐特所说的那么完美,这种模式似乎更适用于市民社会,而非国家的层面。因此,迄今对于国家层面运作过程中的主体间承认形态,仍然缺乏确切的规定。那么回到原点,主体间的承认抑或和解究竟该如何来达成呢?马克思对此曾经提出了一种替代性方案,那就是根据历史的条件来选择具体的道路,换言之,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用冲突的手段来完成的就用冲突去实现历史,能够实现承认的条件下就使用承认来进行主体间的和解。
除了爱与冲突的承认模式,黑格尔其实还潜在地提出了另一种劳动模式,只是他对于劳动与承认的关系没有继续探讨下去。劳动模式在耶拿早期首先是作为个体占有物品的手段,实现了主体自身的对象化,并物化为排斥所有他者的符号,从而开启了所有权概念的肇端,为主体实现与他者之间的交互承认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劳动是作为实现了满足他者需求的工具手段,是主体体验承认的媒介,也是对交互承认的补充,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做是交互承认的一种构成元素。此外,黑格尔还在劳动的异化和工具/机器的异化的探讨中,将异化劳动看做是对人的否定,同时也是对交互承认的一种否定而对待。而在奴隶的解放中,黑格尔则强调劳动在奴隶颠覆主奴之间不平等承认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劳动的陶冶下,奴隶意识由为他的存在成功地转向了自为的存在[10](P247-248)。因此,这时的劳动显然是被视为对承认模式的一种替代,这种替代模式的潜在价值却在爱以及国家对承认辩证法的超越之后被搁置了。黑格尔的保守性决定了他对劳动模式的放弃,但是劳动的模式在日后却激发了马克思的灵感,劳动范畴最终成为马克思承认构架的一块基石。
综上可知,黑格尔试图从“我”到“我们”的主体间性来调和个人与集体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但是,“我们”终究是抽象的“我们”,同样,黑格尔那里也有世界历史,但我们看到的只是抽象的历史。对此,杜威则十分恰切地抓住了黑格尔的症结所在,他认为黑格尔的调和似乎“能应付对于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社会主义的一切异议,免除柏拉图和边沁两人的错误”,但是,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以一般的观念概括特殊的情境”,他抽象的伦理国家的设想“把附属于普通观念的意义和价值放在特殊的具体情境上面,遮盖了它的缺陷,隐蔽了迫切改革的需要”。所以,它“纵然不是有意的,却抵抗着法国革命所掀起的激进思想的潮流,而筑起了用以支持当时的政治局势的一个堡垒”[11](P114-115)。
注释:
①迄今为止,国际学界对于《耶拿手稿》中的思想是否与此后黑格尔成熟时期的哲学体系一脉相承,也即承认主题是否贯穿黑格尔整个思想体系始终存有较大的分歧,而这也成为当前黑格尔承认学说的研究热点之一。一方认为耶拿时期的理论体系是黑格尔早期不完善的思想,并为其自身所抛弃,因此承认理论只存在于早期,这方以霍耐特和哈贝马斯为代表;另一方则以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特瑞·平卡德(Terry Pinkard)、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耶拿时期所建构的思想体系为黑格尔成熟时期的宏大哲学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石,而承认学说则是黑格尔思想体系中一直被遮蔽的一条重要的理论线索,它贯穿于其思想的始终。
[1](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2]姚大志.朝向二十一世纪的西方哲学[J].浙江学刊,2002,(1).
[3]G.W.F.Hegel.Hegel and the Human nature:A translation of the Jena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Spirit(1805 - 1806)with commentary.Ed.& trans.Leo Rauch.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3.
[4]Vladimir Milisavljevi,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Hegel’s Jena Writings, Belgrade Law Review(Annals of the Faculty of Law in Belgrade), International Edition,2007.
[5](德)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6](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8]Robert R.Williams.Hegel’s Ethics of Recognition.Berkeley &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9]Robert R.Williams.Recognition:Fichte and Hegel on the Other.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10]G.W.F.Hegel.System of Ethical Life(1802/3)and First Philosophy of Spirit(Part of the system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1803/4).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79.
[11](美)杜威.哲学的改造[M].许崇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20世纪中后叶,西方学者对黑格尔承认哲学的重新发现和全新诠释,不仅颠覆了黑格尔作为主体性哲学集大成者的传统形象,而且发掘出黑格尔内蕴的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激进色彩。一般来说,黑格尔承认哲学的提出主要缘于对启蒙所倡导的主体性立场的反思,黑格尔主张从个体的“我”走向交互承认的“我们”,这是他对启蒙现代性规划开出的一剂“主体间性”药方。黑格尔推崇在思想深处爆发革命,而不是引向现实的实践,因而无论语调如何激进,他的理论基点就决定了其承认哲学本质上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B516.35
]A
]1004-518X(2012)07-0039-05
陈良斌 (1981—),男,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江苏南京 211189)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2YJC720004)、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11MLC008)、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项目编号:2011SJD710001)、东南大学人文社科重大引导项目(项目编号:SKYY2011001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龚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