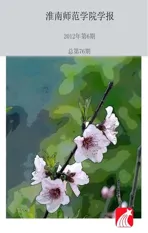唐宋词的研究现状
2012-04-13叶帮义
叶帮义
(1.复旦大学 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433;2.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芜湖 241000)
词学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显学,而唐宋词的研究,更属于词学研究的重阵。大致说来,现代意义上的词学研究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领域:文献学研究、本体学研究、文化学研究、词史研究,以及由新观念、新方法催生出来的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就从这几个方面介绍唐宋词研究的现状,并就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浅见。
唐宋词的文献学研究是词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采用校勘、笺注、编年、辑佚、辨伪等方法,对不同形式的词籍(包括词集、词论)进行整理,涉及考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诸多领域。现代词学的文献学奠基人是唐圭璋先生。早在解放前,他就以个人之力完成了《全宋词》的编撰,获得学界的好评。解放后,他一方面完成了《全金元词》的编撰,还委托王仲闻对《全宋词》加以修订,使这部宋词研究的基础性文献的质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上世纪80年代,孔凡礼的《全宋词补辑》(中华书局1981年),对《全宋词》作了不少增订,有关宋词的一代总集逐步趋于完善。《全唐五代词》的编撰也在20世纪不断地推陈出新,30年代出版了林大椿 《唐五代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0年代又有张璋、黄畲合编的 《全唐五代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90年代出版了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著的《全唐五代词》(中华书局1999年),后出转精,为学界研究唐五代词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文本。
与总集编撰工作一道进行的是词的别集、选集的整理。目前,比较重要的、存词较多的唐宋词人的别集,基本上得到了较好的整理,其中詹安泰编注的《李璟李煜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夏承焘的《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中华书局1958年)、王仲闻的 《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姜书阁的《陈亮龙川词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徐培均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钟振振校注的《东山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增订本)等,堪称典范之作。有的别集还出现了不同的整理本,如苏轼的词集,20世纪初就有朱祖谋的编年本《东坡乐府》,后来龙榆生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东坡乐府笺》。80年代以后,又相继出现了石声淮、唐玲玲的《东坡乐府编年笺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薛瑞生的《东坡词编年笺证》(三秦出版社1998年),邹同庆、王宗堂的《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等整理本,各有胜义。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著名词人的词集也有多种整理本。选集的整理亦颇受词学界的重视,如《花间集》的整理,1949年以前就有华连圃的《花间集注》(商务印书馆1935年)、李冰若的《花间集评注》(开明书店1935年),50年代又有李一氓的 《花间集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80年代以后,李谊、房开江、于翠玲、周奇文、王新霞、高锋、朱恒夫、沈祥源与傅生文等学者也对其做了不同形式的整理,为学界阅读和利用这部唐五代词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唐宋人选唐宋词》,将包括《花间集》 在内的现存几部由唐宋时人完成的唐宋词选本,经过一番整理,加以汇编,不仅有利于词集的校勘和考辨,也有利于对唐宋时期的词学思想进行专题研究。
词论资料(包括词话、序跋等)的整理也是词学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其成果早期主要见于唐圭璋的《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再版),该书收集了部分宋人词论资料(如王灼的《碧鸡漫志》、张炎的《词源》、沈义父的《乐府指迷》等)。80年代以来,学界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出版了不少词论资料汇编,如施蛰存主编的《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张璋编纂的《历代词话》及其续编(大象出版社2002年、2005年),钟振振主编的《历代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1995年,其中《两宋词纪事会评》未出版),龚兆吉编的《历代词论新编》(北京师大出版社1984年),吴相洲、王志远编的 《历代词人品鉴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朱崇才编纂的《词话丛编续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均不乏唐宋词的评论资料。还有不少专门收集唐宋词评论资料的著作,如唐圭璋编的《宋词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金启华主编的 《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张惠民编的《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孙克强编的《唐宋人词话》(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施蛰存、陈如江辑录的《宋元词话》(上海书店1999年),吴熊和、王兆鹏等主编的《唐宋词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邓子勉《宋金元词话全编》(凤凰出版社2008年)。这些著作从各种笔记、野史、诗话、文集中勾勒出丰富的论词资料,取材广泛,可补《词话丛编》之不足。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不少专门的作家资料汇编,如苏词汇评、李清照资料汇编、张孝祥资料汇编、辛弃疾资料汇编、吴文英资料汇编等。这些著作将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论词资料汇编在一起,极大地方便了学者的检索,省却了不少翻检之劳。
此外,饶宗颐的《词集考》(中华书局1992年修订版)、王兆鹏的 《词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4年)、蒋哲伦与杨万里合著的《唐宋词书录》(岳麓书社2007年)、邓子勉《宋金元词籍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对包括唐宋词在内的现存各种词籍作了叙录、考辨,为学界整理各种词籍提供线索,指示门径,颇有贡献。
随着现代科学手段的普遍运用,学界推出了不少关于唐宋词的电子文献。与纸质文献相比,这类文献不仅便于携带和保存,更因其有诸多检索功能而为学界青睐。但此类文献良莠不齐,必须与传统的纸质文献配合方可放心使用。
唐宋词的本体学研究主要考察词体,着力从音乐和文学的角度来揭示词体的特色,涉及词调、词谱、词律、词韵、词的宫调、词的鉴赏、词的美学研究等。其中,词调、词谱、词韵、词律、词的宫调等是词学研究的特色所在,但也是词学研究的难点所在。这是因为,词谱、词韵、词的宫调等的考察,大多离不开对词与音乐的关系的考察,而流传下来的关于词与音乐的史料很少,解读起来也非常困难,如果不是对音乐研究本身有一定素养的学者,几乎很难从事这类研究。解放前这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燕乐、张炎《词源》、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之旁谱研究等方面。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著作并不多见,仅见洛地《词乐曲唱》(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和《词体构成》(中华书局2009年),刘崇德《唐宋词古乐谱百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燕乐新说》(黄山书社2003年)、《姜夔与宋代词乐》(与龙建国合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年)等。总的来说,当代学界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很难超越前人,因而更多是从艺术的角度来揭示词独特的美学特色与艺术魅力,此即词的文艺学研究。
词的文艺学研究,即通过鉴赏、美学研究等方法对词体进行艺术研究。与其他文体相比,词的音乐属性比较突出,因而从音乐的角度对词的本体进行研究,自是必然。但词本身有其文学属性,特别是词在发展过程中,音乐性渐渐减弱,而文学性逐步增强,因而对词进行文艺学的探讨,亦属题中应有之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颇为重视词不同于诗的艺术个性,指出:“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缪钺在《诗词散论·论词》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比兴,诗尚能敷畅而词尤贵蕴藉。”作者还将词体的文学特性概括为四端(文小、质轻、径狭、境隐),认为这是词体之所以能“离诗独立”的主要原因。王、缪二人关于词体的分析,颇为后学称引,并一直启发学界对词体的艺术特性加以细致的分析,叶嘉莹、万云骏、钱鸿瑛等人堪称继武。万云骏《诗词曲欣赏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叶嘉莹与缪钺合著的《灵溪词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钱鸿瑛的《词的艺术世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在揭示词的文学特征方面都有精到的见解。刘永济的遗著《词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在融会古人论词精义的同时,对词的艺术性的阐释亦颇有新见。施议对在其师吴世昌有关词学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词体结构论,主张从结构入手探讨词体的本质,并已通过对屯田家法、易安体、稼轩体的解读作了较为成功的尝试(参施著《宋词正体》)。
80年代中期以后,学界从美学的角度研究唐宋词,以期揭示出唐宋词独特的美学面貌。杨海明《唐宋词风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从风格的角度探讨唐宋词的美学风貌及其流变,是较早从事这一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其后,邓乔彬的《唐宋词美学》(齐鲁书社1993年)、杨海明的《唐宋词美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孙立的《词的审美特性》(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张惠民的《宋代词学审美理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杨柏岭的《唐宋词审美文化阐释》(黄山书社2007年),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唐宋词的美学研究。与此同时,有些学者则从主题、意象等角度专题探讨唐宋词的艺术特色,细化了词的本体研究,如张仲谋《论唐宋词的“闲愁”主题》(《文学遗产》1996.6)、刘尊明《论唐宋词中的“闲情”》(《文学评论》2007.4)、赵梅《重帘复幕下的唐宋词:唐宋词中的“帘”意象及其道具功能》(《文学遗产》1997.4)等。
对词的艺术研究,往往离不开对词作本身的细读,亦即词的鉴赏。夏承焘的《唐宋词欣赏》(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沈祖棻的《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是较早从鉴赏的角度研究唐宋词的两部著作,对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古代文学鉴赏热的形成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叶嘉莹的《唐宋词十七讲》(岳麓书社1989年)以其细腻的文本分析和深入浅出的理论阐释,进一步扩大了唐宋词的当代影响。这些著作连同上海辞书出版社等机构出版的各种唐宋词鉴赏辞典,吸引了一批青年学子从事词学研究,对词学研究的学术建设和队伍建设均有贡献。
唐宋词的文化学研究主要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词的创作和词史演进中出现的某些现象进行文化学的阐释。如果说词的本体学研究主要是从内部入手研究词的本色,那么词的文化学研究主要是从外部入手,努力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阐释词体形成与演进的各种原因,以期解决单纯的艺术研究无法解释的词学问题。这一方法的提出,得益于80年代古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方法热”。早在1989年第2 版的《唐宋词通论》重印后记中,吴熊和就指出词是在综合各种复杂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我们应该开拓视野,加速这方面的研究”。80年代以来,唐宋词的文化学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一是从音乐文化角度研究唐宋词,如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王昆吾《唐代酒令艺术》(知识出版社1995年),对词与音乐的关系加以考辨,有一定的创获。任半塘的《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与杨晓霭的《宋代声诗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从音乐文艺的角度,对唐宋声诗加以细致的考辨,这对我们理解声诗与词的关系不无帮助;二是研究词与歌妓制度的关系,不仅有大量的单篇论文,而且出版了不少专著,如李剑亮的《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沈松勤的《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对此也有专门的研究;三是研究词与商业文化、城市生活的关系,如王晓骊的《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杨万里的《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四是研究词与民俗等社会文化的关系,如黄杰的《宋词与民俗》(商务印书馆2005年);五是研究词与儒释道文化的关系,史双元的《宋词与佛道思想》(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刘尊明的《唐五代词的文化观照》(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对此均有论述,崔海正的《宋词与宋代理学》(《文学遗产》1994.3)、张春义的《宋词与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则对宋词与宋代理学(新儒学)思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六是研究唐宋词与当时的士风、世风之间的关系,如韩经太的《宋词与宋世风流》(《中国社会科学》1994.6)、王晓骊的 《“逐弦管之音,为侧艳之词”:试论冶游之风对晚唐五代北宋词的影响》(《文学遗产》1997.3);七是研究唐宋词与地域文化(尤其是南方文化)的关系,如杨海明的《试论宋词所带有的“南方文学”特色》(《学术月刊》1984.1)、《试论唐宋词所浸染的 “南国情味”》(《文学遗产》1987.1),以及崔海正的《宋代齐鲁词人概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汤涒的《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八是研究宋词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品格,如沈家庄的《宋词文体特征的文化阐释》(《文学评论》1998.4)、孙维城的《“晋宋人物”与姜夔其人其词:兼论封建后期士大夫的文化人格》(《文学遗产》1999.2);九是以当代意识观照唐宋词,分析其所蕴涵的人生内涵,代表性著作是邓乔彬的《宋词与人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杨海明的《唐宋词与人生》(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此外还有将唐宋词与当代的流行歌曲加以比较研究的著作。
唐宋词史的研究。唐宋词史一向是词史研究的重点。不少学者综合运用考证、鉴赏、文化学等方法,进行唐宋词史的研究,包括词人的个案研究、流派(或群体)研究、时段研究、专题史等诸多领域。其中,词人的个案研究是词史研究的基础,涉及作品的编年、词人生平事迹的考证、年谱和传记的编写、词史地位的评价。王国维的《清真先生遗事》开启了现代词学编撰词人年谱的先河,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 堪称现代词学中这一领域的典范性作品。夏著之后,相继出现了邓广铭的《辛稼轩年谱》(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王兆鹏的《张元幹年谱》(南京出版社1989年)、韩酉山的《张孝祥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程章灿的《刘克庄年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严杰的《欧阳修年谱》(南京出版社1997年)、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新编》(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孔凡礼的《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徐培均的《秦少游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2年)、方星移《宋四家词人年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著作①类似的著作还有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王兆鹏、王可喜、方星移合著的《两宋词人丛考》(凤凰出版社2007年),方星移的《宋四家词人年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此外,郑骞的《宋人生卒考示例》(台北:华世出版社1977年)、邓子勉的《宋人行第考录》(中华书局2001年)、李裕民的《宋人生卒行年考》(中华书局2010年)也涉及到宋代部分词人生平的考证。。宛敏灏的《二晏及其词》(商务印书馆1935年)对二晏的生平与创作加以全面的考察,堪称现代词学中个案研究的代表性著作。80年代以后词学界也涌现了一批个案研究的力作,如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齐鲁书社1989年)、叶嘉莹的《论咏物词之发展及王沂孙之咏物词》(《四川大学学报》1986.4)、施议对的《论稼轩体》(《中国社会科学》1987.5)、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齐鲁书社1990年)和《周邦彦传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邓乔彬的《论姜夔词的清空》(《文学遗产》1982.1)和《论姜夔词的骚雅》(《文学评论丛刊》第22 辑)、王筱芸的《碧山词研究》(南京出版社1991年)、金启华和萧鹏合著的《周密及其词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钟振振的《北宋词人贺铸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钱鸿瑛的 《梦窗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为80年代以来唐宋词史的编撰和唐宋词的综合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已有的作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温庭筠、李煜、柳永、苏轼、秦观、李清照、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等名家(特别是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三家),不仅有大量的单篇论文,还出版了各种研究专著、论文集②如苏轼词的研究,90年代以来就出版了不少专著,包括崔海正 《东坡词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刘石《苏轼词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唐玲玲《东坡乐府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陶文鹏《苏东坡诗词艺术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蒲基维《东坡词章法风格析论》(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保苅佳昭《新兴与传统:苏轼词论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饶晓明《东坡词研究新思维》(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郑园《东坡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这些著作都很好地推动了苏词的研究。。
流派(或群体)研究或时段研究也是词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即有专章论述唐宋词的流派,开启了80年代以来词派研究的先声。刘扬忠的《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初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再版)堪称唐宋词流派研究的集大成著作。该书不仅翔实地考察了唐宋词流派演变的“过程”,还着力揭示出唐宋词流派形成与变化的历史动因。余传棚《唐宋词流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着重考察了唐宋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花间词派、婉约派、颓放派、豪放派、雅正派。除了这些通论式的著作外,学界也不乏对具体词派所作的专题研究。王兆鹏的 《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和肖鹏的《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是大陆词学界较早进行唐宋词群体(流派)和时段研究的两部专著。新世纪以来,学界又相继推出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如高锋的《花间词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诸葛忆兵的《徽宗词坛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彭国忠的《元祐词坛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年)、牛海蓉的《元初宋金遗民词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郭锋的《南宋江湖词派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单芳的《南宋辛派词人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丁楹的《南宋遗民词人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金国正的《南宋孝宗词坛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流派(或群体)研究或时段研究,不仅促进了词的分期和流派研究,也深化了词史的研究,使词史演进中某些群体或时段的面貌更为清晰地展示出来。
词人的个案研究与群体研究直接推动了唐宋词史的编撰工作。词史的编撰包括通史与断代史两种。早期的词学通史有刘毓盘的《词史》(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1年)、吴梅的《词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2年)、王易的《词曲史》(神州国光社1932年)、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大陆书局1933年),但体例比较单调,论述亦较单薄。80年代以后相继出版了许宗元的《中国词史》(黄山书社1990年)、金启华的《中国词史论纲》(南京出版社1992年)、艾治平的 《婉约词派的流变》(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黄拔荆的《中国词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这些通史式的著作虽然格局稍大,但因其并非建立在对个案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对词史的把握比较简单,其成就远远不及唐宋词的断代史研究。唐宋词史的编撰在解放前就有胡云翼的《宋词研究》(中华书局1927年)、薛砺若的《宋词通论》(开明书店1937年)。80年代以来,随着个案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唐宋词史的整体把握不断加强,学界推出了不少有影响的唐宋词断代史著作,如杨海明的《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融历史分析与美学评价为一体的唐宋词断代史著作,对唐宋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文学现象和创作实践,都做了深刻而精辟的论述。此后,谢桃坊的《宋词概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陶尔夫、诸葛忆兵合著的《北宋词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以及陶尔夫、刘敬圻合著的《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1992年),木斋(王洪)的《唐宋词流变》(京华出版社1997年)与《宋词体演变史》(中华书局2008年),刘尊明的《唐五代词史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邓乔彬的《唐宋词艺术发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著作,也对宋词的发展情况作了细致的描述。其中,邓著《唐宋词艺术发展史》特色尤其鲜明,堪与杨海明的《唐宋词史》、刘扬忠的《唐宋词流派史》并称为新时期以来三部标志性的唐宋词史。90年代以来,不少博士和硕士论文从事专题史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细化了唐宋词史的研究,如邓红梅的《女性词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对唐宋女词人的研究,路成文的《宋代咏物词史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对两宋咏物词史的探讨,以及徐安琪的《唐五代北宋词学思想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对唐宋词学思想史的考察。
新方法、新观念与新的唐宋词研究领域。随着新方法和新观念的介入,特别是传播学与接受美学理论被引入词学研究领域,唐宋词的传播史与接受史研究颇受学界关注,这不仅直接推动了90年代以来学界对词史中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经典化历程的研究,也大大加强了以往文学史研究中比较单薄的影响史研究。有的学者还将这种研究与统计学的方法结合起来,使文学分析与数据统计相互印证,既有实证依据,又有理论支撑,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研究过于依赖印象式批评的方法,使以往某些模糊的认识得以清晰,如刘尊明与张春媚合写的《传播与温庭筠的词史地位》(《文学评论》2002.6)、刘尊明和田智会合写的《试论周邦彦词的传播及其词史地位》(《文学遗产》2003.3)、刘尊明和王兆鹏合写的《从传播看李清照的词史地位:词学研究定量分析之一》(《文献》1997.3)、刘尊明和王兆鹏合写的《本世纪东坡词研究的定量分析——词学研究定量分析之一》(《文学遗产》1999.6)、王兆鹏《宋词名篇的定量考察》(《文学评论》2008.2)、龙建国《唐宋词与传播》(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杨雨《传播学视野下的宋词生态》(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朱丽霞 《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李冬红 《〈花间集〉 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张璟 《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钱锡生 《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陈水云《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谭新红《宋词传播方式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一个学科的建立,往往伴随着对自身研究过程的不断反思。这样,关于本学科学术史的研究就应运而生了。现代词学也是如此。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后期,伴随着整个学术界撰写学术史的热潮,词学界也推出了一批词学史著作,如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巴蜀书社1993年)、方智范等《中国词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邱世友的《词论史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朱崇才《词话史》(中华书局2006年)。只是这些著作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古代词学研究的梳理方面,对20世纪的词学研究关注不多。曹辛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曾大兴的《词学的星空:20世纪词学名家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则弥补了这一缺陷。鉴于现代词学中与唐宋词的研究最为充分,有些学者专门总结历代学者对唐宋词的研究成果。刘扬忠的《宋词研究之路》(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崔海正的《宋词研究述略》(台北:洪叶文化事业公司1999年)就属于这类著作。张幼良的《当代视野下的唐宋词研究论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则着重考察了80年代以来的唐宋词研究现状。高峰的《唐五代词研究史稿》(齐鲁书社2006年),刘靖渊、崔海正的《北宋词研究史稿》(齐鲁书社2006年),邓红梅、侯方元的《南宋词研究史稿》(齐鲁书社2006年)等著作,则全面总结了唐五代词、北宋词、南宋词,从产生到21世纪初的研究成果(包括海外的研究成果)。这些学术史著作,在回顾学界已有的学术成果,总结各种学术观念、学术方法的同时,也不乏对今后词学研究的种种展望和设想,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选题。
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思路:就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唐宋词研究在文献整理和作家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文献整理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工作,它的充分与否直接影响到作家研究。唐宋词的研究之所以长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显学,与文献整理的充分密切相关。今后在这方面要想取得大的突破,比较困难,除了需要进一步拓展整理范围之外,还应该对已经整理出来的文献进行加工、提高(如《词话丛编》的补辑、笺注;利用今人编撰的的《全宋文》、《全宋诗》,全面整理宋代的词学资料)。就作家研究而言,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过于集中在少数名家身上。这既容易出现大量的重复,也使得其他词人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因此,今后的作家研究,既需要将名家研究推陈出新,也应继往开来扩大研究范围,不能把研究视野局限在为数不多的名家身上。不过,作家研究与文献整理均属于传统的研究方法,短时间内是很难取得突破的。这既是目前的唐宋词研究给人推进不大的原因所在,也是目前学界愿意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新方法的运用的心理动机。总的来说,新方法的引入对唐宋词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尤以词的文化学研究最为引人注目。词的文化学研究及其与当代意识的结合,打破了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味以政治标准来评价文学的做法,将词的外部联系拓展到其与文化各个层面之间的关联,不仅开阔了视野,而且增强了词学研究的当代性,开拓了词学研究的新领域。不过,有的研究演变成了纯粹的文化学研究,这就失去了文学研究的本来意义。因此,词的文化学的研究要坚持文学的本位,尤其是要注意词的本色,不能简单地将词作为文化研究的材料。就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有些方面的研究比较充分(如唐宋词与歌妓制度的研究),但也还存在一些薄弱的领域,如宋词与党争的关系就较少深入研究;宋词与理学虽有少量论著,但论述仍不够充分;至于由部分论著引出的宋词与宋型文化之间的关系,更是一个引而未发的课题;唐宋词与当代文化之间的联系也有许多可供挖掘的地方,如唐宋词与新诗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目前看来,最为薄弱的是词的本体学研究。从音乐的角度来审视词体,不仅存在文献资料有限的制约,也存在着研究者专业素质欠缺的因素,因此学界从这个角度审视词的本体的人并不多,成果也有限;已有的本体研究,主要属于词的文艺学研究,而这种文艺学的研究,又主要是通过词与诗的对照来揭示的,思路仍然是传统的,也是比较单调、狭窄的。其实,词体特色是相对于其他文体(尤其是诗歌)而言的,要揭示词体特色,自然要与其他文体加以比较。但诗词的对照仅仅是词体比较研究的一个方面。词在形成自身特色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其他文体的影响(如诗、赋、文),还会以各种方式影响到其他文体。这种文体之间的交融与互渗,虽然不乏零星的论文加以探究,但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如何从文体学的角度来揭示词体特色,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