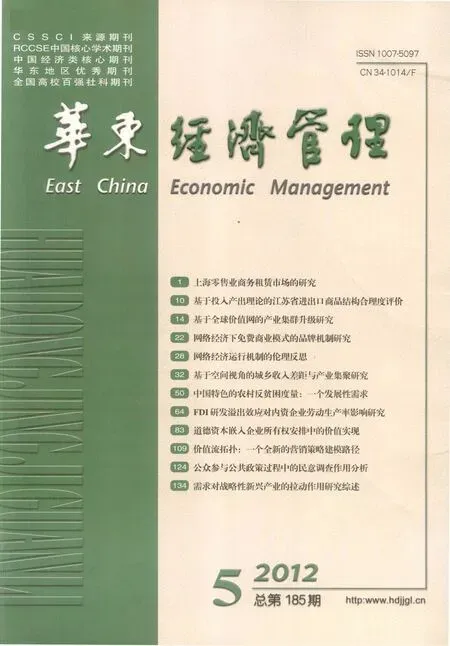网络经济运行机制的伦理反思
2012-04-12何华征
何华征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9)
据2011年12月We are social发布的报告称,中国有4.85亿网民,互联网普及率36%,每月新增用户约1000万,网购用户1.73亿,网购用户平均每人每年网购支出600美元,淘宝网每分钟卖出4.8万件商品,2011年11月11日当天,淘宝网交易额达到8.17亿美元,平均每秒9456美元。然而有消息称,中国电子商务已经“入冬”,形势并不乐观,据21世纪经济报报道,“凡客”CEO陈年为“凡客”2011年制定了100亿元的销售目标,然而,逼近年终,“凡客”高层称,“凡客”2011年最终的营业收入约为35亿元。这一数据与他们100亿元目标相去甚远。然而,我们仍然毫无足够的证据和理由认为网络经济就进入了冬天。为了网络经济的良性发展,我们除了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权衡、猜度、预设、重构、解读外,事实上,它还需要我们更多地对其予以伦理的关照和审查。
一、伦理视域的新经济运行机制
(一)正反馈与垄断
在网络经济中,正反馈强烈地渗透、奔涌在产品与服务之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形成了新的垄断者。他们看上去颇像一个时代潮流的领袖,实则只能充当大众偶像明星的角色。网络经济的弄潮儿就像明星选秀活动一样流行于人们的习惯与心理预期之中,它使真正领袖的、英雄的人物不再具有神秘的力量。没有人可以为着一个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而振臂高呼,也没有一个人的振臂高呼能够引起人们的内心共鸣,引起人们的崇高感。明星经济学家们和偶像企业家们围绕着眼球经济的注意力搔首弄姿,卖弄风骚。此种意义上,网络经济学是一个英雄没落的经济形态。在这个时代,一切媚俗的东西被抬到如此的高度,以至于任何内敛的修养都被视为学究的无聊而加以嘲笑。人们不断地复制着自己的情绪和某些隐私,在公众的网络世界中请求被确认为一种普遍的情怀。网络经济的赢家,一定是能够侦探到这种气氛的他(企业或个人)。
网络经济中抢先进入市场的企业,通过以低成本获得达到临界点的客户而坐拥丰厚的利润源泉。因为转移成本的缘故,后来者纵便持有更为先进的技术也不一定能够吸引到足够的客户。技术的风险如何成为道德的风险?在康德的道德律令之外,道德本身正在经验着一场风险考验。
效率的衡量要与人的生活本身挂钩,否则容易导致把手段当做目的,从而使道德的审视失去了裁判官的效力。以人类福祉增进的程度衡量技术进步与市场上胜者为王的流行准则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遵从道德性的各种技术努力不一定能得到事实上的认肯,这就给道德带来了履约的风险。践行道德所付出的成本与其收益将不成任何比例,甚至出现负向的比例关系。那么机会主义的盛行则势必不可阻挡。这样,正反馈将导致一场灾难:漠视一切尊严和崇高,追求暴利。
(二)反垄断的双重遭遇
瓦里安认为,一个垄断者的关键特征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市场力。他能够出售的产量,作为其索要价格的函数而持续响应。他与竞争厂商不同的是:他是市场价格的制定者而不是接受者[1]。平狄克与鲁宾费尔德也认为,作为产品的唯一生产者,一个垄断者处于一个特别的位置。它对市场上的产量有完全的垄断权。当然,垄断者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无法在价格上随心所欲。对于完全竞争厂商,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而对有垄断势力的厂商,价格大于边际成本[2]。网络经济中,虚拟信息相关产品生产的边际成本与价格之间已经不能说明和解决问题,因为几乎所有的网络产品都是边际成本递减。因此,衡量网络经济中垄断的标杆应该是市场占有率和垄断行为(对行业门槛的把守和禁闭)。
网络经济为经济垄断提供了沃土。除了垄断本身的界定之外,对垄断的态度亦出现了相悖的两种观点,它们来自两个方向:网络经济的经营者呼吁反垄断,而消费者对此不以为然。“提出反垄断要求的不是广大消费者,而是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竞争对手。”[3]淘宝围攻案中,部分中小商户因准入门槛的问题而集体围攻淘宝商城,很多就是打着反垄断的旗帜。当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把注意力放在是否存在垄断行为上的时候,其实顾客对此漠不关心。垄断遇到了甚至完全相反的市场遭遇:中小商户极力反对大型网络经营者垄断市场,而消费者则倾向于对大型网络经营企业给予信赖。理智的消费者都不愿意为在中小商户那里购买商品和服务而承担风险。这样一来,无论中小商户反垄断的呼声再高,其经营的前景也得不到任何保障。网络营销必然带来垄断,而这种垄断只要建立在“非完全独占”的基础上,它对市场的良性发育并无先天的损害。在这里祈求伦理的关照而过于限制垄断企业的发育,其实并不是一种道德的行为;相反,是对广大消费者安全感的伤害。网络经济中的自由竞争,只是迈向垄断竞争的一个阶段而已。而不完全的垄断,将会给消费者带来信任感。这样,垄断和正义的秩序并不矛盾。
(三)成本虚构与人的贬值
在网络经济条件下,一般认为,交易成本要比在传统经济中低得多。网上交易的成本很低,同时它还突破了传统经济的时空限制。网络经济条件下信息技术的发展,必然导致人们搜集、甄辨、整理信息所耗费的成本降低。然而,这种理论上的推论能否得到事实的经验证明,则是另外一回事。相反的情况会这样出现:
一是尽管事前交易成本降低(假如信息对称可以得到保证的话),然而交易中的成本和事后成本则会升高,如果网络经济局限在实体商品和服务交易的范围内。网络经营企业控制某些行业的话语权,会比实体连锁经营所耗费的统治成本更为低廉,而结果更为可怕。实体连锁经营所需要的垄断成本远远高于网络垄断的成本。看似无孔不入的实体连锁店无论怎样发展,总会为中小商业资本的运营留有生存余地。在互联网上,中小商业资本的命运很难取得一种乐观的确定性。然而,事后交易成本的高昂以及为了凸显市场优势而不得不奉行的低价策略,使得企业不得不寻求一种新的成本代偿机构。这种成本代偿机构——在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之后——很自然的是各种制造业组织。显然,网络交易成本的所谓“降低”,只是一种转嫁罢了。在特定情况下,当实际的“就在你家隔壁的”各种商店通通关门之后(假如可能的话),消费者必须做好为网络垄断经营企业迅速膨胀的交易成本和贪欲买单的心理准备。由此可见,“显然”的交易成本的减低,是伴随着两个可能的结果出现的:其一,垄断导致的地方经济的萎缩,实体市场繁荣景象的消失,中小商业资本成为网络经营大佬的网中之鱼;其二,制造业以及消费者需要为高昂的事后交易成本买单,网络经营者横行于市场。
二是过度信息带来交易成本的升高。信息的透明度很难彰显信息的对称性。(作为假设)网络经济通行天下之时,假如知识的普及已经不再是令人担忧的事情,那么信息本身的审核制度则不能不说将成为新的难题。这一难题得不到解决的话,言谈信息对称性为时尚早。虚拟世界不能仅仅凭借我们“实在”的情怀改善其德性。法律作为最低的道德准则,怎样制定可操作的信息审核制度?面对琳琅满目的信息,人们如何识别真伪,如何甄别优劣?这种信息过剩必然带来交易成本的升高。而各种基于用户评价的引导信息并不能排解人们做出购买行为时的犹豫与困惑,至少与人们面对真实商品和服务相比是这样的。网络经济学所谓的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优化资源配置需要加上一连串的前提条件。作为企业,面向消费者的信息对称会带来许多风险,增加巨额成本。而对消费者来说,有效信息通过合理途径进行反馈,意味着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被无偿征缴。信息对称性的增强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两者同时成为可能,这只是一个比较浪漫的假设。这一假设的前提是把人的生命(时间)的价值约定为零。从伦理上讲,这种对人本身价值的贬损是不能被谅解的。以上两个方面,从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贬值的立场,对网络经济学关于成本普遍降低的独断论预设提出了质疑。
(四)定价策略
在网络经济中,通常采用两种价格歧视:个性化定价和群体定价[3]。个性化定价建立在对消费者主观评价和偏好的准确估算之上,对消费者心理的侵略成为获取利益最大化的有效手段。因此,在个性化定价中,100美元、10美元、1美元将可能成为相等的物值,也就是说,可以交换相同的使用价值。亦即:若某商品(服务)一人愿意以100美元购买,一人愿意以10美元购买,一人愿意以1美元购买,则最大的收益是111美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厂商就必须使同质产品和服务自我分化,扮演不同的角色,给予不同的“标签”(身份的符号化)。消费者在被揣测和被设计中完全变成了资本奴役的对象。越是在利润最大化的冷冰冰的思考中取得科学理论地位的价格策略,越是对传统美德(童叟无欺)的反动。而此种反动,于个体消费者是一种不公平,于竞争对手进入市场亦构成了严重的障碍。群体定价把消费者按口袋的殷实程度和消费习惯划分成不同群类,其实质并没有离开个性化定价的框架,只是一种被抽象的形式而已。
在网络服务定价中,基于使用情况的定价法较少被采用,而平坦式服务定价法广泛流行,用户对服务质量的要求被置之不理。对所有用户采取统一价格,使形式上的平等取代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消费者对网络服务的享受时间长短不一、品质要求不同、占领的信息量和信息质的差异统统不被考虑,在公平的名义下,消费者不得不为完全闲置的网络付费,为拥塞不堪的信息流分担时间成本。尽管这种定价的变更很容易在技术上被突破,但经营者对此往往不屑一顾。比如在我国,每天使用1小时或20小时,网络的基本费用支出是大体一致的,服务提供商仅仅提供按年度或半年计费的方式。
(五)合作竞争的可能与困境
“网络经济下的垄断不同于传统垄断,它是竞争性与垄断性并存,具有可垄断性和可竞争性的双重特性。”“在网络经济中,正反馈机制、高固定成本与低边际成本的特性、产品技术的不相容性、网络外部性和消费所产生的锁定效应等,决定了垄断产生的必然性。同时,由于产品具有高技术含量和短生命周期等特点,网络经济中的垄断是不稳定的。一项创新或一个新产品,有可能一举彻底打败原有的垄断厂商。”[3]垄断者凭借核心技术获得的垄断地位稍纵即逝。这就是说,在信息技术时代,垄断已不可能完全排斥竞争。它对创新的压制还没有达到令人担忧的境地。
垄断作为竞争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非结盟和非密谋的寡头垄断和竞争性垄断事实上是可以被接受的,而且是必需的。竞争性垄断市场结构保持了高度的竞争,并且由于垄断企业提供强大的人力和财力支持,而有利于在沉没成本巨大的情况下进行技术创新。在网络经济条件下,信息和知识作为基本资源所固有的扩散性和共享性,使得任何一个企业,包括垄断者都无法独占这些资源,基于资源独占的垄断不复存在。这种“临时垄断”的身份迫使垄断企业保持很强的技术创新的内驱力。低效率和保守在网络经济的垄断状态中显然是一种不当的描述。首先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反垄断问题需要审慎考虑。因为其与传统经济中垄断对创新的阻碍以及对消费者的危害有所不同的是,网络经济中,适当的垄断有可能促进创新,提高效率,并增进消费者的利益。其次是价格“合理化”的标准难以鉴定,在维护公平正义的作为中,政府和行业协会将面临更大的智慧考验。
二、电商伦理失控的可能性及危害
(1)主体模糊化。经济违约与违法的道德处罚目标模糊化,虚拟空间使得受罚的主体有了“隐身”的可能,道德制约机制的有效性也许会减低。
(2)差距扩大化。自由竞争普遍要求利益均沾,而强势媒介的渗入势不可挡地造成了注意力垄断。这种垄断造成大规模的实体店经营困难,大量员工的失业,财富的集中加剧。与此同时,由于现代物流的相对滞后和集中,农村电子商务的开拓与发展依然处于低级阶段,城乡差距拉大。
(3)困难隐性化。网络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经济的地域限制,但电子商务只要与实体经济挂钩,就不可能完全摆脱这种限制。网络汽车、电脑等大型商品的销售,一方面消除了距离的障碍、信息(商品符号和概念)代替商品本身,计算机通信线路代替店铺。另一方面,销售的便捷化设想并不符合消费者的体验意向。消费者如何体验后才购买商品,以及购买商品后的售后服务跟踪的担保机制很难建立。这样反复的交涉,其交易成本不是降低而是增多。
(4)代价多重化。售货员变成送货员,网络经济情何以堪?消费者的便捷是建立在大量送货员的繁琐辛劳之上的。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网络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三重牺牲:消费者获得便捷而牺牲了生活的情调;服务员为了获得收入而不得不牺牲更多的体力,然而不一定获得更高的报酬;经营者节约了场地、仓储等成本而不得不支付更高的流通费用。
(5)地位躯体化。社会名望与社会地位的“被躯体化”[4]成为当代伦理学不得不考虑的一个新元素。网络经济下社会重新分层,并且将会使其在符号社会中的“标志”更加鲜明。这与人类的全面进步是否相容?与人们的平等要求是否相容?养尊处优的精英阶层更加便捷地支配着众多的社会底层劳动者。同时他所支配的实际费用大大低于表现为明显奴役的等级社会的上层统治者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恰恰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的精英人士(看上去有点矛盾的词语)的享受并不因为支付的成本低廉而减少商品或服务的效用。躯体行为被当做社会地位与名望的符号或表征。“随着个体‘躯体化’,随着身体成为名望和救赎的物品,成为基础价值”,“(主体)在目前属于他的社会超特权中安顿下来。”[4]
(6)信用资本化。“相互信任是合作成功和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信任能降低双方的交易成本,为双方创造额外价值,并提高生产、交换的效率。”“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3]搜索引擎的竞价排名,为各网络企业(产品)提供了基于资本实力的先后次序,它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对消费者的误导,信息显著度模糊了信息本身的品质,消费者的偏好被搜索引擎的提供者役使,自由的选择变成了一种被预设的选择,网络信息的可靠性进一步降低。二是对网上创业和创造活动的一种不良导向,存在为劣币驱逐良币煽风点火的隐性危险,使得初创期经营者或低利润经营者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流失。特别是对于公益性较强的产品和服务具有较大的屏蔽性破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海量信息的湮没。信用被当做资本来利用的结果是对信用本身的改装和虚拟化——以信息显著度来确立信用等级,作为牟利的工具。那么信用与德性的关系逐渐淡化,甚至成为其反面。
三、哀叹还是憧憬:网络经济的伦理建构
网络经济和网络经济学的内涵是如此丰富,因此,道德批判不能仅停留在先验预设的伦理框架中罗列其种种弊病与优点。在网络经济中,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是需要引起思考的重大话题,也是贯通整个基于公平正义的伦理立场的批判语境。科技力的发展使得网络经济以崭新的面孔迅速在全球铺开。网络经济被网络经济学家们吹嘘成科学发展的可靠路径。一般认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就是证明:财富、收入或者说商品的增加通常是获得更多福利和幸福的前提。”[5]然而现实的危机已经初露端倪,网络经济学必然需要面临伦理视角的重新审视。
(一)被强化了的斯密悖论
造成新经济忧思的缘由,理当追溯到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所困惑的斯密悖论。其实斯密不存在悖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宣扬和标榜的人的那种基本德性,在之后的《国富论》中只是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人性自私作为经济理性的假设前提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种经济学惯用的模型(没有这种假设,经济学的合法地位就难以得到保证)。而这种假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则正是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开头所说的,“人,不管被认为多么自私,在他人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理,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使他人的幸福成为他幸福的必要条件……即使最残忍的恶棍,最麻木不仁的匪徒,也不至于完全没有这种感觉。”[6]如果说《国富论》探讨的是如何敛财和增加国民财富的形而下的层面,那么《道德情操论》则是形而上的出发点和背景。它是这样一个圆圈:最自私的人也有基本的善;为了国民财富的最大化,自私(在遵从基本善的基础上)是应当被允许的;追求国民财富的目的应使人们更加幸福,回到人的善性上来。网络经济学同样给自身制造了一个悖论:信用作为道德律令是无条件的,然而被作为资本加以利用。这样做的结果是:信用不再成为一个道德专门词;另一方面却由于诚信危机而导致经济上付出巨大代价。目的被当做手段来使用,结果人们只能收获彼此的不信和猜疑。斯密没有悖论,如果有,也只是一种有着极大的故意嫌疑的误读。这种悖论被强化的结果是,人性自私的理性被无限膨胀和夸大,使得经济处于不可遏制的无序状态,经济学家和道德家们不得不“一声长叹”:网路经济环境下人性的改造终究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二)把被颠倒的东西颠倒过来
在网络经济中,知识取代劳动、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地位,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同时,全球化使得劳动、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大为降低。在知识这个生产要素中,知识内容相对而言并不重要,知识能力才是关键性的;知识内容并不稀缺,知识能力才是稀缺的[3]。诚如知识能力是一种稀缺资源,道德感受能力和道德创造能力同样是网络经济良性发展不可多得的稀缺资源。劳动的异质性使得劳动的价值通约必须通过产品的市场交换来确定。知识价值论以一种理性暴力式的权威行使独裁统治,社会被智力资本重新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公平正义的前提被不断修改,禀赋差异造成的利益分配悬殊成为一种客观现实。不平等成为公平的“时代特征”,平等是对人们创造积极性的否定,因此,潜能的蕴藏量正在为社会划分出新的等级,而贡献率正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把效率作为目的,而把公正当做手段,这是经济不道德的根源。可以预见,如果不把这种被颠倒的关系颠倒过来,公平正义作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的话,效率作为目的是不可靠的。换句话说,随着传统经济逐渐向新经济的变迁,道德的规范作用对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持续、稳步增长会产生无可替代的作用。正如厉以宁先生所说,“道德力量调节是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以外的第三种调节。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道德力量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也是法律所替代不了的。”“我们可以说,道德力量是超越市场,超越政府的。”[7]把道德当做对经济学的一种不屑的纠缠的看法,正是企图在目的与手段之间制造一种无法沟通的障碍。而此种态度的重新端正,则有可能意味着新经济春天的到来。
[1]哈尔·瓦里安.微观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248.
[2]罗伯特·S·平狄克,丹尼尔·L·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258-269.
[3]盛晓白,韩耀,徐迪,等.网络经济学[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102-311.
[4]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32-133.
[5]布鲁尼,波尔塔.经济学与幸福[M].傅红春,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
[6]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谢宗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2.
[7]厉以宁.道德力量调节的重要和独特作用[N].北京日报,2011-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