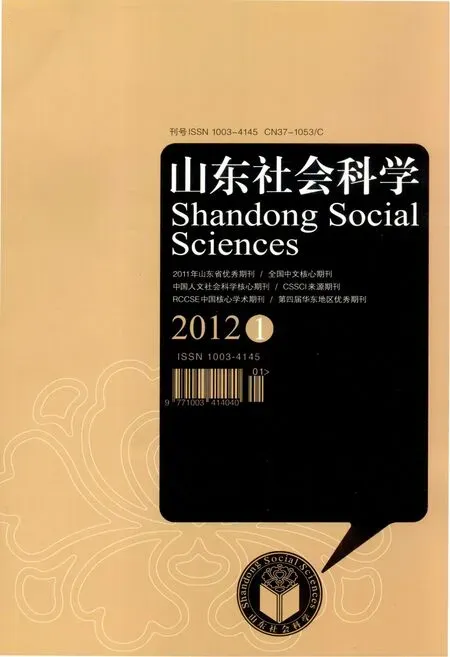“猫”在诗中的媒介作用
——林健文和艾略特诗学比较研究
2012-04-12江玉娇朱超超
江玉娇 朱超超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猫”在诗中的媒介作用
——林健文和艾略特诗学比较研究
江玉娇 朱超超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马来西亚籍中国诗人林健文(1981-)和英籍美国诗人T.S.艾略特(1888-1965)生活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环境里,却因身世相似,对诗歌创作有着类似的审美情趣和相同的社会理想。他们俩都借用“猫”作为媒介或隐喻,以其行为特征、生活习惯、“恋家”天性、“地盘观”理念等,传达了三个信息:首先,形象地再现了现代人的困惑、无奈、消极的人生——存在主义的自由意识;其次,深刻地表达了作者身处一地、心系两地的情怀——返乡之忧的家园意识;其三,详细地提供了在后现代文化语境解构“逻各斯”、“中心”之后的重建秩序的范式——后现代主义秩序意识。两位诗人的不同思想表现在:前者的秩序范式建立在佛教思想之上,后者的秩序范式建立在基督教思想之上。
猫;自由意识;家园意识;秩序意识;林健文;艾略特
林健文是马来西亚获过多项创作奖的最年轻的华人作家之一,出生于1981年,16岁开始发表诗歌,至今,发表诗歌100余首,出版诗集一部:《猫住在一座热带原始森林》。T.S.艾略特于1888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艾略特6岁开始写诗,共发表诗歌200余首和一部诗集:《老负鼠的务实猫》。《老负鼠的务实猫》共有15首诗歌,1939年出版,80年代改编成音乐剧“猫”,在全世界各地演出。此外,艾略特的三首长诗:《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7)、《荒原》(1922)、《四个四重奏》(1943),这三首长诗尽管没有对猫的直接描述,但猫的意象随处可以捕捉到。这三首诗的影响使艾略特于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尽管林健文和艾略特生活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环境里,却因身世相似,对诗歌创作有着类似的审美情趣和相同的社会理想。他们俩都借用“猫”作为媒介或隐喻,以其行为特征、生活习惯、“恋家”天性、“地盘观”理念等,传达了三个信息:首先,形象地再现了现代人的困惑、无奈、消极的人生——存在主义的自由意识;其次,深刻地表达了作者身处一地、心系两地的情怀——返乡之忧的家园意识;其三,详细地提供了在后现代文化语境解构“逻各斯”、“中心”之后的重建秩序的范式——后现代主义秩序意识。两位诗人的不同思想表现在:林健文的秩序范式建立在佛教思想之上,艾略特的秩序范式建立在基督教思想之上。
一、自由意识
猫是动物中最懒的动物之一,通常一天能睡18个小时,沙发、窗户、角落是它们睡觉和活动的场所,因此猫有“懒猫”的绰号(杜玛);猫有“健忘动物”的称号,因为它们不会刻意记住对它们无利可图的事情;猫有“夜间聚会”的习惯,因此,俗有“夜猫子”的外号;猫有“自由者”称誉,享受绝对的自由,因为猫是独居生活者,也不打扰他人的生活(加藤由子)。林健文和艾略特均借用猫的懒散、贪睡的性格、安于现状的生活态度、迟疑不决的癖性、自由行事的生活方式等作为媒介,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视角,深刻地描写了现代人困惑、犹疑、失望的人生观。如:“偶尔如猫,懒散躺在沙发等待每个黄昏降临”;“三言两语,打发时间最残酷的方法/竟然是忘记/地下铁的冷酷;猫的懒散;随手丢弃的花瓶/永远是对的,错觉”(林健文)。“那黄雾的背脊摩擦着窗玻璃,/那黄雾的口鼻摩擦着窗玻璃,/它用舌尖舐黄昏的各个角落,/在排水沟的潭潭上徘徊不去/让烟囱里掉下的煤灰落在它背脊上/偷偷溜过阳台,突然纵身一跃,/又注意到了这是个柔和的十月夜晚,/在房子附近蜷起身子睡着了”(《情歌》,艾略特)。在这些诗行里,叙述者描写没有规律生活的现代人,就像“夜猫”一样:夜晚是自由的,想睡觉就躺下来,肚子饿了就出去猎食(杜玛)。“偶尔在后巷发现你曾说过的猫/猫在觎觎我摆卖的/爱情”;“你躲在我眼角左倾45度处/没有灯光的角落”;“猫,一直藏匿在我们中央”;“一直发生在周围的现象都可以被伪造”;“畏缩成你每夜能看见的包矮星/和历史一起徘徊时间的边缘/自由荡游天庭地府”;“你的命,已注定在书写笔记的纸上/没野心干涉政治/实验的宇宙在梦里变成/过境的游客”(林健文)。猫的爱情观的特征是: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猫的生活:孤单、寂寞,它们不是过群居生活的动物,而是单独生活者;猫是安于现状的动物,因此没有冒险的勇气;猫是行动自由的动物,也不介入他人的生活(加藤由子)。叙述者在以上的诗行里恰恰借用猫这些习性,阐释了现代人极其消极的人生观:对爱情犹豫迟疑,对政事漠不关心,对他者猜疑不信,对自己固守寂寞、放荡自由。这些借用猫的媒介和透过叙述者的视角观察到的困惑、犹疑、病态正是20世纪初存在主义哲学书写的特征:存在是偶然的、荒诞的;人生是虚无的、无意义的。因此,“人的自由是绝对的,因为人生活在一个孤立无援的世界上,人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上帝、科学、理性、道德等对人都不相干,也就是说,它们都不能告诉我们生活的真理、生活的方式,同时,它们就对人也没有任何的控制和约束的作用”(萨特 )。正因为如此,人有绝对的自由意识,同时也遵守着存在自觉的规则。
二、家园意识
俗话说:“狗恋人,猫恋家”。对猫来说,熟悉、习惯了的家的周围是自己的狩猎场,如果主人搬到其他地方,无论路途有多远,它们肯定会回到能够确保自己的猎物、过去属于自己地盘的狩猎场,因为在“家乡”,他们有稳定感和安全感,猫是具有“家园意识”最强烈的动物种类之一(加藤由子)。那么,怎么理解“家园意识”呢?
1943年,海德格尔在《返乡——致亲人》的演讲稿中,阐释了“家园意识”的审美情趣和美学内涵。他说:“在这里,‘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源要素中存在。这一空间乃由完好无损的大地所赠予。大地为民众设置了他们的历史空间。大地朗照着‘家园’。如此这般朗照着的大地,乃是第一个家园‘天使’”(《荷尔德林诗的阐释》,海德格尔)。艾略特的《老负鼠的务实猫》的第一首诗叫“给猫取名”,每只猫有三个不同的隐喻名字,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名字,“第一个名字是家人使用”(《老负鼠的务实猫》,Eliot),因此,每个猫都有“在家感”,都是“家园天使”,“存在的明朗者”。家里的“成员”论资排辈,领袖猫最大,各守其职,各具风采,性格各异。年长的领袖猫要在众多猫中选择其中一只,将其作为天使送往天堂,获得重生。这又恰巧体现了海德格尔的“家园意识”存在论所具有本源性的哲学与美学关系:“大地与光明,也即‘家园天使’与‘年岁天使’,这两者都被称为‘守护神’,因为它们作为问候者使明朗者闪耀,而万物和人类的‘本性’就完好地保存在明朗者之明澈中了”(《荷尔德林诗的阐释》,海德格尔)。这里的“大地”、“家园天使”即为“世界”与“天”之家,而“光明”与“年岁天使”则为“人”与“此在”之意,共在这“此在与世界”、“天与人”的因缘与守护之中,作为“存在的明朗者”得以闪耀和明澈。然而,林健文诗中的“猫”与人群直接成为家庭成员,享受“在家感”,成为彼此间的“存在的明朗者”,“猫爬到琴键上/我继续每夜作与现实不符称的梦”(林健文)。海德格尔在其演讲中进一步说:“诗人的天职是返乡,……这乃是返乡的忧心”(《荷尔德林诗的阐释》,海德格尔)。这段话语告诉人们诗人追求的审美目标就是“返乡”,“返乡”体现的是一种更深层的“家园意识”。这种切近本源的“返乡”之路就是作为“存在”的“神秘”的展开之路,通过守护与展开的历程实现由神秘到绽出、由遮蔽到澄明,最后才能“诗意地栖居着”,因为,这同时是审美的“家园意识”得以呈现之途。这便是“家园意识”的双重涵义:“返乡之忧心”、“守护之使命”。在这一点上,身世相似的林健文和艾略特均借用猫“恋家”的天性作为隐喻深刻地表达了他们的“返乡之忧心”。对“家园意识”的双重涵义,海德格尔在1927年的《存在与时间》详细地说明了“此在与世界”的在世关系,这种关系包含着“人在家中”的“家园意识”和“茫然视其所在的不在家的畏惧感”。林健文和艾略特的诗歌都表达了作为诗人在“茫然视其所在”的畏惧下,寻找“家园意识”本源的艰难经历。“你将会记得,必需抛弃旧版的地图/而你习惯性的安排让我忘记前世记忆的结局/不是我愿意的”;“当大禹,回到神话不曾面对的城邦/多灾难的人民/依然逼切等待/治水的英雄”(林健文)。艾略特的“家园意识”比林健文的“家园意识”更宏大、更深远。艾略特视地球为一家园。《老负鼠的务实猫》中的猫各有三个不同的名字,代表着全世界不同的种类,集聚在一个家庭里,象征着各州的大统一。此外,继《老负鼠的务实猫》之后的《四个四重奏》,虽没有对“猫”的直接描写,但里面却充满了“猫”“返乡”的意象。艾略特的“返乡”不仅仅是返回英国或美国,而是回归“伊甸园”:“脚步声在记忆中回响/沿着我们没有走过的那条走廊/朝着我们从未打开过的那扇门/进入玫瑰园……/进入我们的最初世界”(《四个四重奏》,艾略特)。
三、秩序意识
虽说猫恋家,但如果主人把家搬到很远的地方,那猫就不得不寻找新的地盘,建立新的家园。猫是将地盘看得很重的动物,所谓地盘就是能够确保其安全与粮食的空间,其地盘观的理念是:以安全第一为理念,缩小地盘范围,通常在两个屋区之间,地盘里没有始终和上下之分,没有边缘和边界之别。在里面,自己自主又自由(加藤由子)。《猫住在一座热带原始森林》的开篇之作就借用了“猫恋家以及猫的地盘观”,以物理的、现实的、文化背景的空间为描写对象,把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地的距离压缩为一体,使两国构成一个时空秩序:“我在一座光线穿越不过的原始森林……在两个屋区来回奔走”;“在留下异国边界轨迹的网路上徘徊/在和我相约的梦境重逢”;“二十世纪不再存在任何国界/鱼族画上界限的海岸线,消失”(林健文)。此处,猫的“足迹”暗示了叙述者建立新家的艰辛以及渴望构建现实和梦幻之间的秩序的愿望。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标题是:“燃毁的诺顿”、“干赛尔维其斯”、“东库克”、“小吉丁”。“燃毁的诺顿”、“东库克”分别指他祖先曾经在英国居住过的一座乡间住宅玫瑰园遗址和村庄;“小吉丁”是他祖先曾经在英国居住过社区的小教堂;“干赛尔维其斯”是他曾祖父来到美国后第一个生活区的一个景点——马萨诸塞州海边的一处礁石。艾略特借用他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四个地点作为《四个四重奏》的标题,同样以物理的、现实的、文化背景的空间为描述对象把过去和现在的欧洲和美洲建构在同一个时空中:“现在的时间与过去的时间/两者也许存在于未来之中,/而未来的时间却包含在过去里”;“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四个四重奏》,艾略特)。
此外,两位诗人以猫的家族观作为建立和谐社会秩序和精神家园的范式:“木马旋转时以圆的边缘急速/转动世界的主轴/开动命运的齿轮”;“我想起神,曾教导世人/和平共处……/在一个没有神的国土/人民快乐生活”(林健文)。艾略特的《老负鼠的务实猫》诗集以猫为媒介,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借用猫的习性、癖性描写人与人之间、家族与家族之家的关系,其最终宗旨体现在第二首诗中:“家有序,快乐多”(《老负鼠的务实猫》,Eliot)。“在这里,如果一切顺当,事事如愿,/我们便会死于那绝对的父爱之中,/父爱不会离开我们,而是处处保护我们”(《四个四重奏》,艾略特)。此处的“父爱”暗指猫的“爱无止境”的思想。林健文有相似的描述:“和我藏身多年的赤道一样/在零距离的空间和时间里/相遇,或重逢。/尽管曾经远离地球表面/爱,只是快乐的回转游戏/永远没有边缘/也没有终点”(林健文)。以上诗行体现了猫的“家族观”。猫是没有血缘或家族概念的动物。不管是谁的孩子,只要像亲子一样生活过,就是亲子;只要像兄弟姐妹一样生活过,就是兄弟姐妹,母猫都会照顾需要照顾的小猫,即便那小猫不是亲子(加藤由子)。以上的诗行也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两位诗人建立秩序的不同根基:林健文的诗歌体现的是佛教轮回思想,其时间是循环的,以生死轮回为主要表现,其秩序是在生与死之间不断地更新,因此“没有边缘,没有终点”。这是猫的“家族观”范式体现:四海皆兄弟,天下一家人,爱无止境(杜玛)。而艾略特的秩序观所表现的是基督教父爱至上信仰,其时间是线性的:上帝创世——末日审判——毁灭——救赎:“我的开始之日便是我的结束之时”,“我的结束之时便是我的开始之日”(《四个四重奏》,艾略特),其秩序是在毁灭与拯救中不断地重建。这是猫的“地盘观”范式体现:搬离老家后,不得不在新家附近建立自己的地盘,不断地搬家,就有不断地重建(加藤由子)。
总之,两位诗人借用猫作为媒介或隐喻,以相似的审美情趣对现实人生的困惑、迷茫进行了种种哲理性思辨,同时又借用猫的天性和行为习性为困惑中的人们寻找建立“爱无止境”的社会范式和时空秩序的链接点,这种借用动物作为诗学媒介的引人深思的思考,足以为后现代主义的“破碎”、“分裂”、“无中心”、“漂泊无定”、“无意义”的否定态度提供一个隐形的对比和可以遵循的显性参照,为后现代主义“世界是荒谬无序,存在是不可认知的”的否定价值观找到了一个重新思考人生、道德、传统、历史等问题的肯定出发点,让艺术家再一次承担起崇高神圣的社会职责:维护社会秩序,建构审美秩序,同时也为后现代主义“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解构“逻各斯”的哲学和诗学思潮提供一个反思:在尊重差异、对立、多元的前提下回归本体,重建逻各斯和信仰。
[1]Eliot,T.S.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 of T.S.Eliot 1901 -1962.London:Faber& Faber,1969
[2]让-保罗·萨特[法]:《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3]艾略特[英国]:《艾略特诗选》,赵萝蕤、张子清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加藤由子[日]:《爱猫,就该懂猫》,周晓晗译,武汉出版社2009年版。
[5]马丁·海德格尔[德]:《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6]马丁·海德格尔[德]:《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7]马修·杜玛[加拿大]:《猫英语》,千太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8]林健文[马来西亚]:《猫住在一座热带原始森林》,有人出版社2009年版。
I106.2
A
1003-4145[2012]专辑-0023-03
2012-05-18
江玉娇(1964—),女,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人文学院比较文学方向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比较诗学。朱超超(1987—),女,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规划课题“中西诗学中‘共象’与‘异象’研究——透过T.S.艾略特诗学思想”(课题编号:09YJAZH09)的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宋绪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