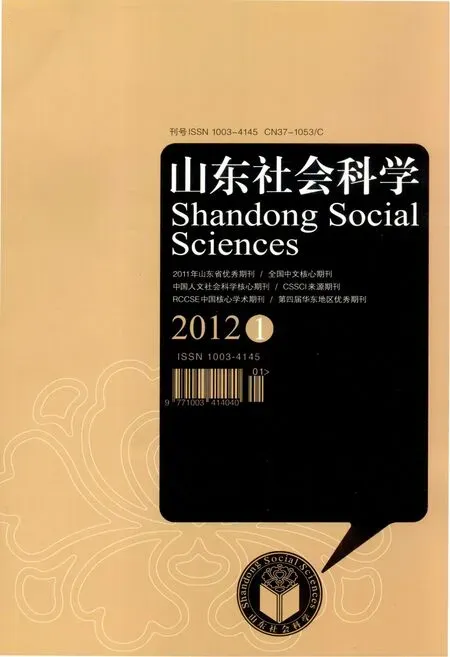试析小说《时震》中的艺术特色
2012-04-12刘海霞
刘海霞
(哈尔滨师范大学公共英语部,黑龙江哈尔滨 150025)
试析小说《时震》中的艺术特色
刘海霞
(哈尔滨师范大学公共英语部,黑龙江哈尔滨 150025)
库尔特·冯尼格的小说《时震》是一部典型的黑色幽默小说,小说延续以往小说的黑色幽默风格,但将关注的焦点移至文化方面。本文主要分析了小说《时震》中的艺术特色,包括滑稽模仿、互文性特征、拼贴、后现代的叙事法等。
滑稽模仿;互文性;拼贴;后现代的叙事法
《时震》是库尔特·冯尼格的最后一部小说,在《时震》中,作者仍然是通过他所擅长的科幻模式,以黑色幽默的笔触,反映了“挣扎于困境之中的文化人和艺术家”所处的困境。黑色幽默小说旨在表现“黑色”与“幽默”的双重效果,传达深邃而复杂的生存体验。在《时震》中,为了突出小说荒诞和超脱的内涵,小说采取了种种艺术特色,如滑稽模仿、互文性特征、拼贴、后现代的叙事法等。
一、滑稽模仿
滑稽模仿(parody),也被称为戏仿、拙劣模仿、讽刺诗文等。这种模仿以现有作品的情节或特色为模仿对象,目的是为了达到滑稽可笑的艺术效果。它是一种调侃,一种游戏,由此可见作者的玩世不恭。滑稽模仿在《时震》中主要有三种形式:借用、颠覆和对文学形式的模仿。
(一)借用,即“将某一历史人物或某一历史时间或其他文本的内容或其他语境中的人物、事物直接搬到现有文本中。”借用历史进行滑稽模仿使曾经被颂扬过、评判过的历史在黑色幽默小说里失去其原来崇高面目。这种荒诞不羁传达的是一种滑稽的宣泄,犹如历史面前无可奈何的小丑。这种借用制造了鲜明对比,读者更能意识到现代生活的悲剧性和面对如此悲剧只能发出的无可奈何的笑声。虽然借用历史或其他作品中的事件或人物,但黑色幽默小说对这种借用是经过艺术处理的,要么极端变形,要么夸张塑造,因而小说更能揭示现实社会的荒诞与凶险,更表现了人在如此凶险的社会前的悲观与绝望。当冯尼格在《时震》中把英国传奇亚瑟王的的圆桌骑士们用枪武装起来时,这种滑稽让人为之一笑,可仔细体会,这种模仿背后的悲哀却也是无奈的,被现代武器武装起来的圆桌骑士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还会做出千古流传的英雄行为吗?高科技武器给人类所带来的灾难恐怕很难让人想到武装起来的圆桌骑士将会有什么英雄行为,现代社会的暴力和凶险一览无余。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和美国内战也被冯尼格借用了一回。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却使印第安人口从两千多万锐减到二十万左右,这就是为了文明所要付出的代价吗?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意义顷刻间让人产生怀疑,正如冯尼格所质疑的,人类对诸如另一个半球的存在、核能利用这类伟大的发现,是否真使得人的生活变得比以前更加美好?美国内战被作者戏称为“臭名昭著的不文明的国内战争”,因为美国内战英语是Civil War,而civil一词既有“国内的”又有“文明的”意思。通过这些借用,人类所谓的文明受到读者的质疑,滑稽一笑之后有了深度的思考。
(二)颠覆,“这是在借用的基础上突出表现的滑稽模仿的一大特征,即表面上模仿文本的内容,借用文本的人物,主旨却在于颠覆其中的意义和传统,产生‘反英雄’的艺术形象。”颠覆是一种对已熟知历史或文本的大逆转,因而效果要比单纯借用更加强烈,给人以超强震撼力。西方人对《圣经》是非常虔诚的,创世纪里记载了上帝如何创造万事万物和人,上帝被描绘成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撒旦被描绘成上帝的反面,他狡猾、卑鄙、邪恶。《时震》中冯尼格颠覆了《圣经》中对上帝和撒旦的叙述权威。他肆意篡改“创世纪”,撒旦被描述成一个善良女人,上帝则高傲而愚蠢。“当上帝说‘让天上出现光’而光出现时,撒旦开始对上帝心存忧虑。她开始疑心重重,‘他到底想干什么?他还要走多远?他是不是想让我帮他收拾这一副烂摊子?’”当上帝完成了他的创造,冯尼格写到,撒旦无法取消上帝已经完成的事。但她至少可以让上帝创造的小玩具少一点痛苦。她发觉了上帝未曾察觉的东西:活着意味着要么乏味得要命,要么害怕得要死。于是她在一个苹果里装入各种想法,至少可以用来解脱烦闷。这里撒旦做的事情并不是基督教所谓的“罪恶”,她只是想帮忙,正如冯尼格在文中所叙述的,“撒旦用来医治社会病疾的秘方,偶尔会有严重的副作用。但她努力推广的成绩,并不比现今声誉最好的药房来得逊色。”作者对“创世纪”的另类阐释,颠覆了传统价值观念中善与恶的界限,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人类,但他对自己的创造物却及其冷漠,毫不关心,关怀着我们的是善良的撒旦,只是她关心的方法有点副作用。这样的颠覆和嘲弄不但使读者感到震惊,更能激发读者深入思考,重新思考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积累起来传统的价值观。
(三)对文学形式的模仿,“即黑色幽默小说在滑稽模仿人物和事件的同时往往采取了对某一种小说形式的模仿。”冯尼格的《时震》延续了作者以前作品的形式,即对科幻小说的模仿,只是《时震》中假设的是时间倒退十年的情况。2001年2月13日下午2点27分,宇宙经历了一次自信危机,暂时厌倦了无穷无尽的扩展,决定寻乐子调剂以下,于是时空统一体出现故障,宇宙一下子缩回到十年前的1999年2月17日。就在时间再次向2001年运行过程中,所有的人或物,都得将十年的经历重新经历一遍。生活困境在小说中进行着一成不变的重复,而“时震”结束时,世界上又出现了一片不堪收拾的混乱。虽然小说披着科幻的外衣,但描述的是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状况的现实。借助科幻模式,作者得以将人类生存困境夸张表现,更能够使人类意识到人类生存环境的糟糕透顶和文化的一文不值。
总之,滑稽模仿是《时震》中呈现黑色幽默的的最重要的艺术手法,突破了传统小说的思维模式,在真实的本质里添加了引人发笑又发人深省的结构和内容,使得《时震》在滑稽的形式下埋藏了深刻的内涵,以荒诞的内容一举击中社会生活脆弱的神经和命脉。
二、拼贴
拼贴一词来源于法语“collage”,原来指粘贴的绘画技巧,文学中的拼贴指“作品中时常被加入各种内容上不甚相关的片断,或者各种具有拼贴效果的内容,如图片、外语、典故、菜单、广告等,使作品呈现出复杂的内涵和独特的艺术效果”。拼贴在《时震》中的使用使小说的内容扩大到文化的范畴,因而作品呈现出的内涵更加丰满,作品更具有张力。《时震》由六十三章外加一个序言和后记构成,然而各个章节之间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段落之间似乎也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人物和事件的发生发展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整部小说就是一幅由碎片拼贴而成的拼贴画。冯尼格把这种碎片理解为现实的本质:“我们周围的世界没有秩序……相反,我们必须就范于混乱的要求。”
除了上述的拼贴类型外,《时震》中还有一些小幅的拼贴画、一些外语如德语、拉丁语、法语以及歌词、诗歌、笑话等镶嵌在文本中。在拼合成《时震》的各个片段中,有不少关于作家、艺术家的故事,有真实的,也有虚构的。不管是历史话语,还是小说话语,都在指涉现代社会的无序和人类生存的困境,由此可见文化危机带来的灾难感。
小说中最引人注意和深思的拼贴恐怕是作者所讲的五个故事:
故事之一:巨蟹星座布布星上有三姐妹,大姐是画家,二姐是作家,都受人尊重,三妹则受人冷落。为了报复,她同隔壁疯人院的疯子一起发明了电视机,节目很吸引人,看节目也不需要动脑。从此两个姐姐不再受人崇拜,三妹成了英雄。“年轻的布布人没有必要继续培养想像力,因为他们只要按一下开关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热闹放纵的破烂货”。世界颠倒了,原来崇高的事物,被随着科技发展而来的“破烂货”所取代,文化受到科学技术的冲击。作家想说的是:科技时代可能导致“文化瘫痪”,导致文明的崩垮。故事在结束时说:“布布人成了当地星系中最冷酷无情的生物”。
故事之二:作曲家索尔顿·佩帕隔壁一个五音不全的男孩,借助电脑软件,谱写了一部模仿贝多芬但质量尚可的弦乐四重奏。作曲家遭到彻底羞辱,被弄得“哭笑无常”,艺术家被先进科技逼入绝境。音乐创作成了机器生产,生活体验和激情都没有意义。“五音不全”但懂电脑的孩子也可以占领音乐圣殿。作者似乎在质问:这是文明的进步,还是文明的倒退?
故事之三:一个智商不高的高中女生,借助专门电脑软件,设计出可供施工的娱乐中心图纸。建筑设计师弗兰克不信,到电脑商店试验,结果电脑按照他的所有要求,很快设计出一座双层停车库。弗兰克回到家里,当着妻子和孩子的面,举枪自杀。人不再有用,创造性的劳动已没有意义,艺术家成了多余的人。
故事之四:作者的哥哥伯尼·冯尼格是实验科学家,从来对艺术嗤之以鼻。他以两片瓷砖挤压各色颜料团然后展开的方式,创作了现代绘画,并举办个人艺术展。他的举动不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而是一个实验科学家向艺术界提出的挑战。“很显然他希望看到那些盛气凌人的艺术评论家在面对他幼稚但又狡猾的问题‘这是不是艺术’时,额头冒汗,一脸傻相。”[9]艺术家被科学家玩弄,什么是艺术?评价艺术的标准早已使得艺术评论家们“额头冒汗”,难以一说,艺术的地位岌岌可危。
故事之五:刺杀林肯的凶手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有一个私生子。此人的第四代孙子弗兰克·史密斯是个演员,身高不足五尺,长着上方削尖的耳朵——这是传说中魔鬼的形象。他在《林肯在伊利诺斯州》一剧中主演林肯,大获成功。刺客的后代扮演着英雄,魔鬼的脑后出现光环。戏剧艺术的存在,结果只是对现实生活的刻薄挖苦。
这些故事把文学、音乐、建筑设计、绘画、舞台表演这五大艺术门类拼贴在一起,并进行了间接的“评说”。虽然大多故事异想天开,但作者的意图准确无误:艺术与现今世界已难相容。冯尼格在《时震》中甚至故意不用“绘画”、“音乐”、“小说”等现成词汇,因为它们已经名不正、言不顺了。他不怕繁琐,把绘画称作“涂着颜料的平面”,把音乐称作“不同高低长短的声音组合”,把小说称作“26个发音符号、10个数字和8个左右标点符号的特殊横向排列”。这正是极其科学的定义,但却难掩滑稽之感,艺术的精神内涵被掏空了,披着科技外衣的艺术只剩下没有灵魂的躯壳。冯尼格对拼贴的使用使读者陷入深深的思考:艺术是什么?失去灵魂的艺术是荒诞的,失去艺术的社会更无法摆脱荒诞。
三、互文性特征
著名的叙事学家杰拉尔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在他的《叙事学词典》中是如此定义互文性的:互文性指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简单的理解,互文性就是一种话语或文本与其他话语或文本的关系。根据程锡麟的介绍,互文性在文学作品中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引用语、典故和原型、拼贴、滑稽模仿以及“无法追溯来源的代码”。小说《时震》之所以给人带来“黑色”和“幽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小说中所引用的其它文本的理解,小说中对其他文本的引用扩大了小说本身的内涵,这种明显的对话关系使作家能够完成与阅读者之间的沟通和对话。
冯尼格在《时震》的开篇就提到了海明威和他的作品《老人与海》,他重述了故事梗概并在小说发表时问一个渔民对此有何感想。这个渔民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个白痴,“他应该把鱼身上的好肉割下来,放在舱底,余下的留给鲨鱼”。冯尼格很快纠正了那个渔民对小说所作的字面上的理解,“出现在海明威脑子里的鲨鱼很可能是那些批评家”。我们无法证实海明威是否真有这样的想法,哪怕只是在潜意识中,但是把《老人与海》放到冯尼格设定的框架中进行解读,是非常贴切的,而且也使人耳目一新。“老人”显然是作家,在满是“鲨鱼”的逆境中徒然抗挣。他的劳动所获,那条象征艺术成果的马林鱼,被穷凶极恶的“鲨鱼”撕咬得仅存骨头。当时海明威已很长时间没有出版像样的作品,引来人们对他的非议和攻击。于是他努力推出这样一部具有广阔想象空间和阐释余地的小说,在其中进行了充分的自我表述,小说也为海明威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冯尼格在他小说前言中坦言:“我那条臭不可闻的大鱼名叫《时震》”。其实,在“臭不可闻”这一修饰中,当然是调侃多于自谦。联系海明威与冯尼格的处境,冯尼格以《老人与海》开篇就不难理解了。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其作者所处的困境可见一斑。
四、后现代的叙事方法
黑色幽默小说家的叙事风格呈现出典型的后现代特色,“作家往往用破碎、片断的语言追求叙述的松散型,用淡薄、反讽的语气达到‘黑色幽默’的效果,以多维的视角反映现实的荒诞和虚无,体现出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小说《时震》中,典型的后现代叙事特色就是它松散的叙事结构。小说《时震》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情节,也不具备传统小说紧凑的结构特点。传统的时间顺序,以及前因后果的逻辑思路在《时震》中找不到一点影子,相反,小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片断和琐碎的堆积,内容上毫无逻辑,意义不确定,没有一个传统小说所谓的中心。当然并非小说没有意义,只是小说的意义要靠读者从琐碎的片断中去推敲研读。正如冯尼格对这个世界的评论“我们周围的世界没有秩序……相反,我们必须就范于混乱的要求。”因此,作者松散的叙事风格成为这种绝望无序最好的表达方式。
《时震》中后现代的叙事方法还体现在叙述者与作者的概念上。在这部小说中,叙述者和作者的概念非常模糊。叙述中,我们常常发现作家本人跳入作品中,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评论,甚至对小说以及对作家本人的自我评判。作家并未将叙述权威交给叙述者,不但如此,作家的经常出现还消解了叙述者的叙述权威,使读者更加意识到小说的虚构性,社会现实的虚构性。在《时震》中,虽然没有作家以往作品中的那种时间旅行、星际旅行等方式,但小说叙事中对时间的处理是非常特别的:宇宙经历了一次自信危机,暂时厌倦了无穷无尽的扩展,决定寻乐子调剂一下,于是时空统一体出现了故障,宇宙一下子缩回到十年前。这种独特时空处理方式使得小说真实与虚构重叠,确切说,读者很难分辨出虚构与真实的界限,正是在这种虚实相间的意境中,小说的意义得以充分阐述:人类所追求的自由意志用处何在?十年重播中自由意志不起任何作用,而当重播结束后,已戒除了自由意志的面对自由意志束手无策,结果导致一片混乱;当美国文学艺术院终于被派上用场,成为陈尸所时,艺术所处的尴尬境地让人只剩下无可奈何的苦笑。
反讽语气也是《时震》中典型的后现代叙事特征的体现之一,当然也是小说成为黑色幽默小说的原因之一。美国文学艺术院成为陈尸所,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废墟,基尔基·特劳特一句没有意义的话“你们得了病,现已康复,赶快行动起来”却成为良方,所有这些悖论无不透着作者的反讽。
综上所述,小说《时震》的艺术特色是很丰富的,典型的黑色幽默的艺术特色突出了作者对社会对人类的关注。科技带给人类的不是文明,更多的是混乱和难以避免的灾难。冯尼格的小说引起了现代人对人类命运和前途的思考。
I106.4
A
1003-4145[2012]专辑-0005-03
2012-05-11
刘海霞(1977—),就职于哈尔滨师范大学公共英语部讲师,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责任编辑:宋绪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