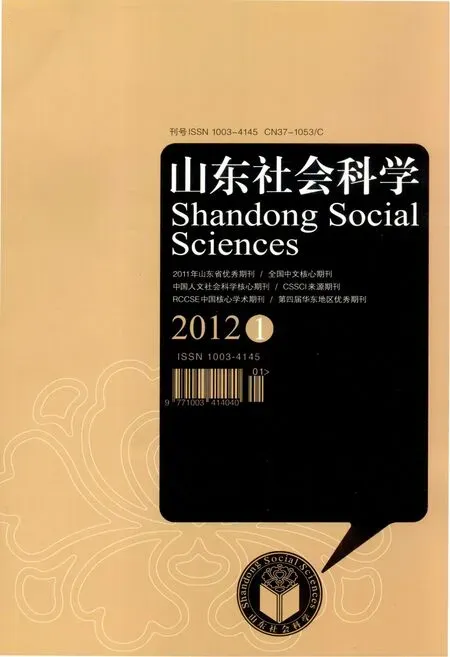春节“回家”传统的现代困境及对策分析①
2012-04-12王学文
王学文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北京 100009)
春节“回家”传统的现代困境及对策分析①
王学文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北京 100009)
面对“如何过好春节”这一问题,我们难以给出放之四海皆准的答案,而通过分析春节的历史和现实,可以将春节的核心主题归结为“回家”,从而将问题聚焦于“让每个人春节都能回家”。解决好春节“回家”传统的现代困境,让每个人有“家”可归、有“家”能归、有“家”愿归,就成为当下学术研究、政策制定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指向。
春节;回家;传统;现代困境
春节之于中国人的意义已经不需要再多着笔墨。从古至今,从上至下,从老到幼,从男到女,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人们都在一直感受着、寻求着、实践着“过好春节”的主题。春节在国民的生活体系、情感天地、精神世界和民族国家的构建中一直担当着重要角色。然而,目前的现实是,每临春节就会出现种种话题,广泛涉及国家的假日体系、交通安保、旅行度假、劳动保障、文化传承保护、社会心理等各个层面。于是,“如何过好春节”,在今日业已成为不仅仅关乎个体、家庭和社区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众说纷纭的问题,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解读视角,将各种认识、方法加以整合,以便厘清我们的理念、方向和策略。
众所周知,春节是我国分布最广泛、涉及人口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传统节日。尽管如此,我们仍基本可以将春节中纷繁多样的内容概括为辞旧迎新、祭神敬祖、亲朋联谊、游艺娱乐等几个有限的主题。当然,这些相对稳定的主题因地域差异、城乡之别、阶层之别、民族不同等因素的影响,其表现会有所不同,各地区、族群对于“如何过好春节”的理解和需求也自会出现差异。同时,从社会发展、时代变迁角度来看,春节的内容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这种动态变化应该是一种文化事象在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存在、传承、发展的常态,但为什么人们总发出年味变淡的慨叹,甚至于提出“保卫春节”的宣言,总有一种关于“春节如何过”的忧虑在政府、学界和各阶层民众中蔓延呢?究其原因除了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考虑外,还在于当下春节的状态和变迁情况与各阶层民众对于春节的心理期许和接受程度之间的不相适应。通过分析种种不适应的社会现象及文化心态,我们会发现,很多在春节期间发生的纠结都可以归结到“回家”这一主题上。
一、“回家”:春节的核心
根据节日文化的指向或倾向,我们可以大致把节日划分为内向型为主的节日、外向型为主的节日和双向型节日。②“内向型为主的节日”是指节日内容主要在家庭、家族和社区展开,以促进群体凝聚、社会团结为主。如有的节日是为某一血缘群体所独有,例如苗族鼓藏节,其缘起与苗族一个支系有关,过此节的为同属于一个“鼓社”(以血统宗族形成的地域组织)的村落。“外向型为主节日”是指节日的内容侧重婚姻、交友等社会关系的拓展,如苗族姊妹节、水族卯节等。“双向型节日”则是指内外兼顾,既有对内凝聚,也有对外拓展巩固的节日内容。笔者的这种分类并不准确,因为节日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事项,通常有复合性的内容和功能。这里作此区分,仅为提供一种认识的视角。春节,就其总体而言属于以内向型为主的节日,是一个与“熟人社会”③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密切相关的节日,它是在一个特殊时段让人回归家庭、家族和社区的节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回家”这一传统一直深入人心,根深蒂固,而且不分阶层、民族、性别和年龄每个人,每到春节时段都会从情感到行为倾向于对这一传统的遵从。
一方面,传统春节的大部分活动是在家庭、家族、社区中展开的,而且尤以家庭为重。民国时期,流行于北京的一首民谣将北京春节的流程表达得特别生动细致:“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写对子;二十五,扫尘土;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首;三十晚上坐一宿;大年初一挨家走。”显然,老北京忙年的全部节俗活动都围绕着家庭而展开。而在春节期间的祭灶、接全神、拜四方、祭祖等信仰活动,一方面多以全家为单位而进行,另一方面多以保佑全家幸福安康为仪式指向。虽然在正月期间,还有赶厂甸庙会、去东岳庙烧香,到白云观祭星和会神仙等在家庭空间之外的民俗活动,但也多是亲属同去,且不会离家太远,就近就便。
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春节期间士农工商各行各业都有一定的假期安排。这既有来自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规定,也有各行各业自发形成的习惯。《燕京岁时记》载有“封印”一俗,“每至十二月,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四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①[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封印”后公事停止,但大事仍可照办,这种安排与现在每年一度由国务院发布的年度放假安排相似。春节期间商户也要关门,如民国时老北京的商铺多半在正月初六才正式开张。这一全民普适的、一律遵从的假期安排,除却让全体国民在辛苦一年普遍得到放松休息之外,也试图从法规和民俗的角度为人们能够在春节时都能回到家庭、家族和社区与亲朋一起团聚的权利提供保障。民国时期有一篇论文写道:
尤其是远居在外职业的家主,或游学的子弟,到了这时,也得回家同享天伦之乐。若家中有年老双亲,到年节,更得回家拜年省亲,以尽子女之道,所以腊八以后,我们常常在道路上,看见一个个担囊负物的归客,以及那三五成群放了年假归家的学生,假如事情羁身,赶不及祭灶,至迟也必须于除夕之日,不顾一切的跑回家来,大家欢聚,来共同过这一年一度的佳节。②权国英:《北平年节风俗》,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社会学学士论文,1940年,第96页。
除了上述在外工作、求学之人回家,我们还注意到传统上嫁出去的姑娘在春节期间也有回家的习俗安排,老北京俗话所说的“正月十六接姑奶奶”即此。
通过相关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民国时期或更早些时候的春节节俗,但我们无从获知当时是否也有“年味变淡”之类的焦虑。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当前过春节的形式和内容都已经发生、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回家”这一信条式的节日核心并未有太大变化。春节“回家”这一命题,从过去到现在,从情感上到行为上,都不曾改变。正因为这一核心没变,才有“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执著和当下涉及上亿人流动的春运,以及我们每到春节来临前的期盼、节日中的迷茫,和过节后的隐隐失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春节是中国人的时间元点和空间元点,“在新的时间元点来临之际回归空间元点,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本能渴望。而春节正是中华民族的时间元点,因此,当期盼归家这种强烈的情感需要汇成巨流,又经过年复一年的反复强化,就积淀成了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③陈建宪:《春节:中华民族的时间元点与空间元点》,《民俗研究》2010年第2期。
至此,“如何过好春节”的问题,可以进一步聚焦到“如何让每个人在春节时都能回家”的问题上。这个问题的解答并不简单,因为现代生活节律已经将我们的生活空间予以极大拓展,我们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已经大大降低,我们与家族、家庭的距离正在日益拉大,我们的生活方式更加多元,所回之“家”也更加多义。一言以蔽之,春节“回家”的传统遭遇到现代困境。家在哪里,能不能回家,怎样回家……这在当代社会中已经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
二、我们的“家”
“家”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意义:一是空间意义上的家,即一个可供生活居住的空间、一座建筑;二是血缘意义上的家,即由夫妻和孩子构成的核心家庭,由祖父母、父母和未婚子女构成的主干家庭和以血统关系为基础的家族;三是精神意义上的家,即我们所追求的某种生活方式或情感所系的精神家园。
在传统农耕社会里,与“家”有关的上述三层意义基本是统一的。春节所回之“家”,既是呱呱坠地之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地,是远行者日夜牵挂、魂牵梦萦之地,也是其最终叶落归根之地;这里既有父母孩子,也有亲戚朋友。那时候,大部分人不曾离家,春节回家的问题并不突出。而一旦进入现代社会,“家”本身也变得难以把握,上述三个层面的意义日益呈现出分离的趋势,人们对“家”的理解和需求更加多元。
首先,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转型的时期,原来的农业社会体系与发展中的工业社会体系、信息化社会体系交叉并置,适应这种状态的社会秩序、规则和核心价值还不完善,人们的精神、情感、需求和行为由此处于种种纠结之中。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和快节奏生活的挤压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开始有意识地去寻找和体验传统民俗的文化和情感,也就是人们通过求学、经商、工作等各种方式所远离的、努力去改变的传统意义上的“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管当下处于怎样的情境,心底里都珍藏有关于“家”的一份记忆,那里是充满亲情的、温暖的、放松的、恬静的情感港湾。春节期间,这种记忆被释放出来,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情绪和行为。即使是时下流行的春节外出旅游现象,表面看来是离家,其实也是对于“精神家园”的刻意寻找。
其次,在当今社会,“家”变得很不确定。一是举家搬迁现象越来越多。家与土地的联结趋于松驰,因职业、家境等原因,从农村搬到乡镇、从乡镇搬到县城、从县城往更大城市搬迁的情形越来越常见。二是“父母在哪,哪里是家”这句俗话所代表的传统观念已经名不副实。目前的状况是,由于子女外出打工或在外定居,为了照顾孙子或在外子女为了照顾父母的方便,父母随在外子女同住的情况正越来越多。三是在多地置业设家,根据需要有选择地居住,家处于变动的状态之中。四是春节期间年轻夫妻“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的现象开始出现。在传统的婚姻观念里,女方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猴子满山走”,在某种意义上是脱离娘家到夫家,春节时虽然有回娘家的习俗规定,但其“家”的意识更多的指向夫家。然而在现代的婚姻观念里,夫家、娘家趋于平等,都是家。于是,每到春节就会为了回哪个家或者先回哪个家而开始纠结,也就有了今年春节回娘家、明年春节回夫家的现象,甚至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显然,在现代社会里,核心家庭逐渐成为主流,而主干家庭和家族逐渐趋弱。因为距离或时间等因素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之间在日常生活和节日中的互动已经大受影响。
三、春节“回家”传统的现代困境
基于以上对“家”的阐释,我们可以进一步梳理春节“回家”传统在现代社会中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可将之归结为三种情况,即无“家”可归、有“家”不能归和有“家”不想归。
无“家”可归,在这里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无家栖居。在这里,“家”更多的是指称精神意义上的家园。当工业文明强势主导着我们的生活,城市化进程迅速地吞噬着传统的农村,建基于农耕社会的“家”的体系、“家”的文化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与此同时,城市社区和文化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人们对于“家”的全部期许。于是,每临春节人们想要回家时,才发现他所期望的“家”只存在于记忆之中,于是有了“过年越来越没意思”的慨叹。
有“家”不能归,是指有些人不是春节不想归家,而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归家。为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一部分人注定在春节期间不能回家,如士兵、驻外人员、值班人员、交通安保人员等。还有一部分人为保证城市人的需求而不能回家,如宾馆餐厅、家政保姆等服务业人员。此外,还有因为买不到票而无法回家的人,和因为经济原因而不能回家的人。实际上,这里指涉了春节期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如春节加班人员的权益保障问题、农民工问题、交通运输问题等。
有“家”不想归的情况,并不关注某些个体的具体因素,而是指一类人的选择问题。有“家”不想归者,包括一些不适应原来“家”的生活方式的人员,和难以承受春节回家所发生的经济支出、人情往来等人员。有“家”不想归的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春节归家传统势微的一种征兆,其根本原因是“家”的吸引力在降低,是传统的家园情感和在此基础上的习俗约束力出现弱化的结果。
四、对策分析:让每个人都能“回家”
“如何过好春节”,由此成为一个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大问题,牵涉到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中传统与现代、城市与农村、国际与国内等各种需要把握和处理的关系。因此,春节研究也就有众多的视角。一些学者采取文化的视角,比较关注春节的历史、变迁和春节文化的保护;有一些学者采取社会的视角,比较关注当下春节期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春运、农民工讨薪、春节用工荒等;还有一些学者采取经济的视角,比较关注假日经济、拉动内需等问题。本文所提出的“回家”这一春节的核心主题,在过往的春节研究中尚未见专题论述。从春节“回家”这一核心主题切入,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春节内涵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抓住当前有关春节种种问题的共同点,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首先,要注重社区文化,加强家园建设。在以往推动春节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我们较多关注节日气氛和节日活动,而忽略了与春节紧密联系的作为“家”和社区的价值。居住家园、亲缘家园和精神家园,关于“家”的这三层意义的实现最终都离不开社区。抓住了社区,也就抓住了春节文化保护、传承的载体。家园感,其实是一种认同感、归属感。我们通过加强社区文化建设,目的就是要培养、维护、强化这种家园感,使人们心中有“家”,春节时有“家”可归、有“家”愿归。
其次,要强化“还节与民”的思维。这一提法虽然还需要进一步商榷,但这样提法本身是希望引起各界对当前传统节日文化保护过程中的造节、办节等现象的关注。节日,是民众的节日,但在当前的很多节日活动中,民众处于失语、失位的状态,成为节日的边缘人和节日仪式的点缀者、表演者。“还节与民”,就是让节日回归到民众生活之中,自己的节日自己过,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民众自主操作和参与。具体到春节,这是一个以千家万户之“家”为核心的节日,如果我们抛离开这一核心去推动春节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其最终的结果必然会与我们的初衷相背。
再次,要强调春节文化,淡化春节经济。发展节假日经济有其合理性,但我们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过年,而是因为要过好年而发展经济,绝不能本末倒置。在极端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了回家的传统,没有了春节文化,春节经济是无从谈起的。而只要让每个人都能回家过年、过好年,春节经济自然就会实现。
最后,要用制度来保障春节期间每个人的“回家”权益。在传统社会,春节期间整个社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停摆状态,但现代民族国家的运转不允许出现这种停摆,这就导致了一部分人注定春节无法“回家”。在我们的相关政策制度中,要充分考虑这部分人,特别是农民工群体、服务业群体的“回家”权益。
毫无疑问,居住意义上的、血缘意义上的和精神意义上的“家”,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不可或缺。解决好春节“回家”在现代社会里的种种困境,也就为“过好春节”提供了基本的保证。就此而言,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体都应该基于如下共识并有所作为:保护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春节文化,重视对这一“精神家园”的保护和传承,让所有人在春节期间有“家”可归;用政策、制度保证公平、正义,保障每个人春节“回家”的权利,让所有人有“家”能归;用科学发展的眼光和增进全体国民幸福指数的理念,让所有人有“家”愿归。
C912.4
A
1003-4145[2012]01-0098-04
2011-12-09
王学文(1979—),男,内蒙古赤峰人,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陆晓芳sdluxiaofang@163.com)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李松主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的讲话、文章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启示,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