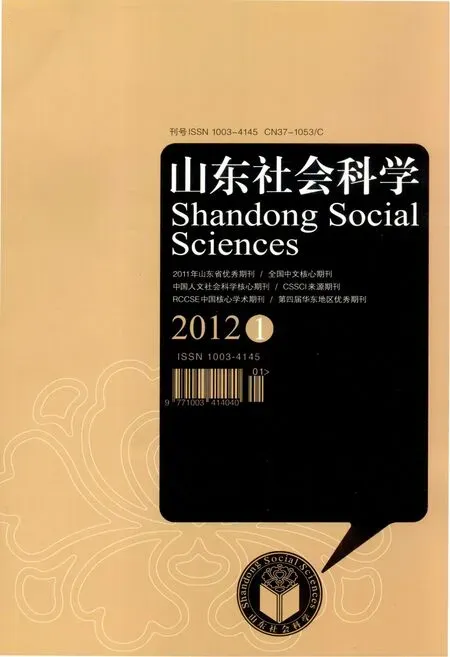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变及其对当代思潮的影响
2012-04-12金瑶梅
金瑶梅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变及其对当代思潮的影响
金瑶梅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有着独特的地位。它在演变过程中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分别对以哈贝马斯、普兰查斯、拉克劳与莫菲等人为代表的当代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的思想是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回响。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演变;当代思潮
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一块“热土”。自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开创了一条既不同于第二国际也不同于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径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从不缺乏对“意识形态”这一问题的研究,从早期的代表人物葛兰西到最新的“后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拉克劳和莫菲,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层出不穷。其中,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可谓独树一帜,对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另辟蹊径的重要作用。在阿尔都塞的视阈中,“哲学”与“政治”这两个术语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他试图通过“哲学基本上是政治的”这一命题来实现两者的紧密结合。纵观阿尔都塞的一生,他的学术生涯处处映射出政治生活的缩影,而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又不断凸显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哲学才思。正是出于对政治时局的密切关注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度思考,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探究始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敏锐性,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其学术思想中最富有独特性和创造性的意识形态理论。对此,J·拉雷在1983年出版的《一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字典》一书中评价道:“在最近的20年里,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作了最有影响力的探讨。”①T.Bottomore edited: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33.
一
哲学家的一生往往伴随着持续不断的思考,有些哲学家穷其一生的才智在同一个观点上不断纵向推进并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一个精深的理论体系,而另一些哲学家则会在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阿尔都塞显然是属于后一种类型的,在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演变过程中存在着前后分期的现象。伊格尔顿曾经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过这样的概括:“他所做的是从拉康式的精神分析与葛兰西著作中不十分明显的历史主义特征的结合中,获得一种意识形态的、非常有力的和独创性的理论;在他著名的文章《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及专著《保卫马克思》的片断中可以找到的正是这种理论。”②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200页。这里提到的一篇文章和一本著作分别代表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指他在发表于1965年的代表作《保卫马克思》中的相关论述;后期主要指他在写于法国“五月风暴”之后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的相关论述。这两个时期之间围绕着意识形态问题存在着一个从认识论角度向社会学角度转变的过程,也存在着一种对意识形态的性质与功能等认识上的巨大差别。
首先来看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阿尔都塞从认识论角度重点论述了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对“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①Louis Althusser,For Marx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London:NLB,1977,p.231.他还提出意识形态具有必要性、强大性、强制性、想象性、能动性以及实践功能等多种特征,而科学则具有反幻想性、反意识形态、反经验主义等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将意识形态与科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意识形态”是个负面的概念,是由社会的统治阶级所营造出来的对未来的虚假追求,而“科学”则是个正面的概念,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探索性追求,虽然两者都属于不同于“生产实践”与“政治实践”的一种新的实践方式——“理论实践”的范围,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属于两种不同的理论生产方式,从而相互对立,没有连续性。继而他又将这一结论运用到针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1845年之前马克思的思想是弘扬人道主义的,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1845年之后马克思的思想则是反人道主义的,属于科学的范畴。马克思从青年时期到成年时期,由于创立了新的历史科学而导致了自身理论深层结构的裂变,这一裂变既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断裂,又是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历史性断裂。不难看出,阿尔都塞这一时期认为意识形态虽然在社会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但它主要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是非永恒的、在特定社会中出现的历史性的存在物,一切属于科学范畴的先进理论都应当与其史前时期的意识形态性质彻底决裂,也就是说,意识形态要想转变为科学必须经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质的飞跃,这就是“认识论的断裂”。这一时期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最终指向是为了反对人道主义与主体的经验认识论。如果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进程来看,阿尔都塞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以葛兰西为代表的正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路径,因为葛兰西更多地是将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同时也没有廓清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的对立界限。
第二个时期虽然与第一个时期间隔不是很久,但是由于经历了法国“五月风暴”的洗礼,阿尔都塞开始从社会学角度来反思意识形态与当代社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他以探究“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是如何得到保证的?”这一问题为契机,引出了对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两大功能的探究:一是意识形态作为个人和其真实存在之间想象性关系的再现;二是意识形态将个人构建为主体的功能。他还区分了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不同以及两者起作用的不同途径。为了进一步论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性质,他又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意识形态没有历史。”②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阿尔都塞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不再将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历史性的存在物,而是作为永恒的、物质性的存在物;不再是为了反对人道主义与主体的经验认识论来进行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而是为了研究意识形态、尤其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当今社会中的功能以及在将“个人”传唤为主体过程中的作用;不再纠缠于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的强烈对抗性,而试图通过思考重点的转移来实现对这一问题的遮蔽。正如詹姆逊撰文指出的那样,当阿尔都塞在后来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提出“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意识形态将永远存在”之时,“这就意味着阿尔都塞已经抛弃了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传统形式”。③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页、第239页。阿尔都塞本人也在写于1970年的《自我批评材料》中对自己前期提出的“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这一观点进行了反思:“我没有公开地用真理和谬误相对立的‘传统’提法……也没有用认识和无知相对立的提法……而是用了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提法。我敢说,这最后的提法比前面两种更糟。”④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30页。后期阿尔都塞主要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核心概念完成了向以葛兰西为代表的正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众所周知,文化霸权是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亮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观点的提出显然受到了葛兰西这一思想的影响。阿尔都塞自己坦言:“这就是我——追随葛兰西——称之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制度的东西,它指的是一整套意识形态的、宗教的、道德的、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审美的以及诸如此类的机构……”。⑤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前后演变使其呈现出某种体系内部的复杂性,这一复杂性又通过围绕着它所进行的各种声音的激烈争论而逐步转变为体系外部的复杂性,从而蕴含了生发出其后各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可能性,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阿尔都塞学派”的普兰查斯及“后马克思主义”的拉克劳与莫菲等人都受到了阿尔都塞的理论辐射,他们的思想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深远影响及其在当代的回响。
二
以探究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为重点的前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的进一步崛起,它旨在与一切人本主义的学说形成理论对峙。阿尔都塞这一时期的理论引发了人们对“科学与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关系?”、“科学是不是意识形态?”及“科学与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分别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的追问。在这方面,沿着阿尔都塞所开辟的道路进行积极探索的当属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他对前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所作的继承与开拓最为典型。
被誉为“当代黑格尔”的哈贝马斯以其关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理论著称。这一理论受到了两条意识形态解释路线的影响,其中一条是哈贝马斯的前辈、同属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另一条则是阿尔都塞前期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学术掌门人,霍克海默并没有像很多思想家所做的那样仅仅为科学给现代社会带来的繁荣景象额手称庆,而是很早就开始讨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并清醒地界定了科学的社会功能:它和一切形而上学一样都带有意识形态的成分。马尔库塞则在《单向度的人》这一代表作中充分论证了科学技术具有浓厚的政治性和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他们的这一批判风格为哈贝马斯所继承。与此同时,哈贝马斯也吸收采纳了前期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有关思路,在此意义上,他可谓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完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他对前期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继续将“科学”与“意识形态”这对范畴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在哈贝马斯1968年为纪念马尔库塞70周年诞辰而写的论文《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在提出“科学技术是当今社会中的第一生产力”的前提下,与阿尔都塞一样,重点阐述了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
第二,继续将意识形态视为一个否定性的、产生消极作用的概念。前期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作为科学的对立面、一个否定性的概念来进行批判,哈贝马斯也采取了同样的理论立场。他指出:“当今那种占统治地位的、相当呆滞的、在幕后起作用的、把科学变成偶像的意识形态,较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不可抗拒和无孔不入,因为随着对实际问题的掩盖,它不仅仅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特殊的阶级利益作辩护和压抑另一个阶级的局部的解放需求,而且又侵袭了人类的要求解放的旨趣本身。”①② ③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选自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6页、第425页、第438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对意识形态,尤其是当今社会中以科学技术为主导形式的意识形态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它阻碍了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甚至阻碍了整个人类的自我解放进程。
第三,继续将意识形态视为一个历史性的存在物。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扮演意识形态的职能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必须要对其进行批判和超越,对“科学技术”这一意识形态应当如此,对于整个意识形态也应当如此。他特别指出:“意识形态同意识形态批判是同步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在资产阶级出现以前是不会有‘意识形态’的。”②②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选自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6页、第425页、第438页。这充分说明:具有否定和消极性质的“意识形态”在哈贝马斯那里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物。此外,他还在承认“意识形态和阶级理论概念的运用范围证明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③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选自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6页、第425页、第438页。这一前提下,试图重建马克思借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设想的范畴框架。
尽管哈贝马斯在以上三个方面继承了前期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观点,但是他们的理论存在一个本质性的区别:阿尔都塞认为科学和意识形态是截然对立的,而哈贝马斯则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具体而言,从阿尔都塞的视角来看,意识形态的强大虚幻性或者说欺骗性在于它已经不是意识的一种形式了,而化身为人类世界的一个客体,甚至是人类世界本身,它被无条件地强加于人们,人们则丧失了选择与拒绝的权力,所以,作为真理性认识的科学必须不断地与意识形态作斗争,从而抛弃意识形态的问题框架。阿尔都塞这样说道:“科学只是在不断摆脱那些窥伺、袭击和缠绕它的意识形态的条件下,才能成为在历史的必然中的自由科学。”④Louis Althusser,For Marx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London:NLB,1977,p.170.换言之,不断地与意识形态作斗争,是科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条件。从哈贝马斯的视角来看,随着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迅猛发展,它逐步转变为第一生产力,并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面貌取代了原先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主导意识形态——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这一趋势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得以日益凸显出来,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科学技术造成了人的工具行为的不断“合理化”,又通过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归因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使人们丧失了对国家政治事务的兴趣,这样一来就导致了整个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化”。哈贝马斯这样说道:“解决技术性问题决不依赖于公众的讨论。公众的讨论反倒会动摇政府活动的任务基于表现为技术性任务的结构。所以,国家干预主义这种新型的政治,要求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非政治化。由于排斥了实际问题,所以公共领域失去了其政治功能。”①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选自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第431页。他又对“科学技术统治论”进行了评价:“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渗透入非政治化的人民大众的意识之中的隐蔽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天地里,它担负起了能促使合法化的力量源泉。这种意识形态的非凡成就是:它使社会的自我理解脱离交往活动的参照系,脱离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而用一种科学的模式取而代之。”②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选自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第431页。
从上述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如何界定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关系上,哈贝马斯与前期阿尔都塞有着全然不同的立场。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当成科学的对立物,其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他关于“科学与意识形态相断裂”的学说显示了其对历史发展非连续性的关注及对传统线性渐进科学观的否定。在分析一种理论的发展时,阿尔都塞似乎更侧重于“停顿”。而不是“连续”。但是,理论在真空意义上的全然“断裂”是站不住脚的,新思想总是诞生在旧理论的胎胞之中,阿尔都塞式的“断裂”难免有武断臆想的成分,其对“科学”与“意识形态”的严格划分,从某种程度上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而哈贝马斯的观点恰恰试图克服阿尔都塞这一理论的弱点,他通过将科学技术确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意识形态,打破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二者之间的壁垒,又通过对这一特殊意识形态的本质及特征的深刻揭示,最终实现了对整个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贝马斯以“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命题实现了对早期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超越。阿尔都塞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来说明他的科学主义,而哈贝马斯则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一致来论证他的反科学主义。尽管意识形态在他们眼中都是一种消极、负面的东西,但由于对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不同阐述,他们对科学的性质的认定就大相径庭了。
三
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创新概念为特征的后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反响。詹姆逊指出:“当有人把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公式跟社会再生产的难题结合起来,一切就都改观了。前者随之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运动,同时我们还需要对社会世俗权力作出全新的说明,而这正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阿尔都塞学派具有影响力的观念在功能上所提供的。”③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4页。作为阿尔都塞的亲密学生和学术同路人,普兰查斯首当其冲受到了这一理论的影响并由此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形成了自己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独到见解。具体而言,一方面,他在国家与阶级理论的大框架下阐明了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必要性、在社会结构分布中的主导性以及与生俱来的幻想性,并试图通过这些观点回应阿尔都塞前期的相关论点;另一方面,他主要针对后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批判,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认为阿尔都塞没有把“国家机器”和“经济机器”区分开来,从而削弱了经济机器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提出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再生产:一是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这种形式的再生产需要特别研究《资本论》第二、第三卷中所讨论的关于资本在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的流通关系及剩余价值的实现;二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这种形式的再生产基本上是在企业的外面进行的,它是通过付给劳动力用于自身再生产的物质资料——工资来得到保障的;三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是国家机器进行干预的唯一领域。他这样解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就绝大部分而言,它是通过国家权力在国家机器中,即一方面在(镇压性)国家机器中,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的行使而获得保证的。”④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68页。而在普兰查斯看来,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论逻辑,必然会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国家只有一个镇压作用和一个意识形态作用。“用这种‘国家=意识形态+镇压’的概念是永远也不能理解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分析的。”⑤Nicos Poulantzas,Fascism and Dictatorship,London:NLB,1974,p.303.他一方面同意阿尔都塞的看法,即把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分为军队、法庭、监狱、警察法院系统及内务部等,把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分为教育机器、宗教机器、文化机器、信息机器、阶级合作的工会机器等,另一方面他又不同意阿尔都塞对经济机器的存在及其作用的漠视。他认为要在“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前面加上定语“严格意义上的”这几个字,又提出:“正如存在着国家机器一样,就下面这一术语的最严格意义而言,也存在着经济机器,‘商业’或‘工厂’作为人们占有自然的一种中心的事业,物质化和具体化了它们在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关系相结合中的经济关系。”①Nicos Poulantzas,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London:NLB,1975,p.25.普兰查斯“经济机器”概念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阿尔都塞关于国家机器的理论。
第二,认为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解释是不妥当的。虽然阿尔都塞提到了意识形态的相对自主性,但他是以一种描述性方式提到的。在另一方面,阿尔都塞又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是由于进行统治的意识形态,而进行统治的意识形态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就只通过“意识形态”而被抽象地归结为国家政权的统一。依普兰查斯所见,阿尔都塞的这种解释是牵强的。因为它忽略了阶级斗争的因素,忽略了不同阶级之间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忽略了国家政权的位置错乱。最后,普兰查斯得出结论:“我觉得必须强调说,要是不把这些观点弄得十分清楚,我们就有落入到被现代改良主义所宠爱的对葛兰西的‘官方’解释中去的危险。”②Nicos Poulantzas,Fascism and Dictatorship,London:NLB,1974,pp.306 -307.
除了普兰查斯,后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还对以拉克劳和莫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影响。“后马克思主义”是当前西方学术界在解读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一股最新思潮。近年来,随着一批相关论著的传入,已经在我国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它的思想渊源来看,阿尔都塞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曾经对它起到过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正如英国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斯图亚特·西姆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演变历程》中指出的那样: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起了很大的激发作用。③参见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拉克劳和莫菲在20世纪60年代都是阿尔都塞的信徒,他们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尤其是其后期理论中得到了启发,到了70年代的中后期,他们开始对阿尔都塞的相关理论进行批判。
拉克劳和莫菲对后期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主要表现在:对后期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阐明的“意识形态将个人召唤为主体”这一思想表示肯定并进行了拓展。拉克劳在1977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这样说道:“大众—民主的质询不仅没有准确的阶级内容,而且是绝妙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领地。每一个阶级同时作为阶级和人民在意识形态层面进行斗争,或者相反,通过将其阶级目标描述为共同目标的终结,力图把一致性给予其意识形态的话语。”④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London:NLB,1977,pp.108 -109.在这段话中,拉克劳将阿尔都塞所阐释的关于个体通过被“召唤”或者说“质询”为主体的理论加以扩大化,提出了意识形态将人民群众“召唤”或“质询”为丧失阶级特性的主体这一观点。在拉克劳看来,既然是意识形态把个体“召唤”或者说“质询”为主体的,那么这就说明政治主体并不是由什么必然性逻辑所决定的,而完全取决于偶然性的意识形态的霸权。拉克劳把阿尔都塞所提出的“意识形态将个人召唤为主体”的过程解释成是一些“中立”的意识形态要素在“接合”中将“身份”甚至“阶级属性”赋予个体的过程。
当然,作为以“批判和解构”为一贯风格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克劳和莫菲对后期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批判。他们关注的焦点是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所隐含的“阶级还原论”。阿尔都塞在此文中指出了将富有多样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统一起来的是一个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他还阐明了统治阶级维护自己地位的方法:“任何阶级都不能长期地掌握国家权力,而不同时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机器或在其中施行霸权。”⑤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第121页。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最终依赖于社会形态的历史,因此也依赖于结合进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的历史,以及在其中发展的阶级斗争的历史。”⑥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第121页。对于阿尔都塞这种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做法,拉克劳和莫菲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坚持在否定“阶级还原论”的前提下讨论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问题。按照他们的理解,存在着中立的意识形态要素,对于意识形态“阶级归属”的问题应该予以拒绝,这是因为在一种瞬息万变、崇尚多元价值观、主体角色多样化的后现代状况中,“坚持本来就成问题的阶级斗争观念已经毫无意义”。⑦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59.拉克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一书中,一方面批判了后期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的“阶级还原论”,另一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接合”的观点:意识形态由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元素构成,每一种意识形态元素并不是非要从阶级属性的角度对其加以判定,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取决于不同意识形态元素之间的连结方式。拉克劳、莫菲所说的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实质上就是指消解在意识形态上的“阶级还原论”,确认存在着非阶级意识形态要素。显然,这一观点扩大了意识形态结构的相对自主性,这是对后期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修正和超越。
纵观当今世界,在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影响下,意识形态问题又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探究意识形态问题的社会思潮。而一旦我们深入考察这些社会思潮就不难发现,它们与阿尔都塞、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若要真正地把握和认识这些社会思潮,就必须探讨它们是怎样从阿尔都塞、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出发并对之进行修正和改造的。
B089.1
A
1003-4145[2012]01-0019-05
2011-10-12
金瑶梅(1975—),女,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责任编辑:周文升wszhou6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