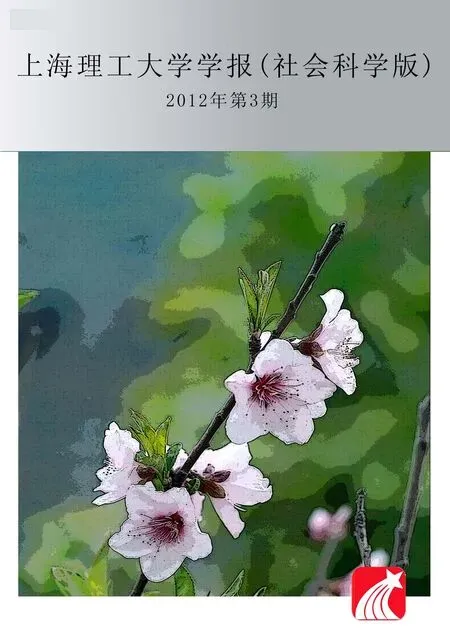没有宗教的宗教——论詹姆斯·鲍德温对宗教的解构与回归
2012-04-12宓芬芳1谭惠娟2
宓芬芳1,谭惠娟2
没有宗教的宗教——论詹姆斯·鲍德温对宗教的解构与回归
宓芬芳,谭惠娟
(1. 浙江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杭州310053;2.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杭州310058)
美国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的宗教情感经历了从信仰到背叛再到回归的过程,其宗教观与德里达“没有宗教的宗教”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解构主义角度出发,分析鲍德温以《向苍天呼吁》和《阿门角》为代表的宗教主题作品对上帝中心主义的消解,解读其没有宗教的宗教观。鲍德温在解构和批判伪善、狭隘的现实上帝的同时,极力塑造公正、博爱的民间上帝,从而实现对宗教的回归。他对上帝爱恨交加的矛盾情感,是由其社会历史背景、个人心理发展,以及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走出自然主义抗议文学窠臼、走向以黑人文化为基础的新型现代黑人文学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
詹姆斯·鲍德温;《向苍天呼吁》;《阿门角》;宗教;解构
美国著名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Arthur Baldwin,1924—1987)14岁成为牧师,17岁称看透上帝的伪善与无能离开教堂,投身写作。三年的布道经历对其生活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鲍德温的文学创作以宗教主题为依托,凭借深刻的宗教象征和燃烧的布道激情脱颖而出。1953年,鲍德温完成并出版第一部宗教素材的长篇小说《向苍天呼吁》(,下文简称《向》)。同主题剧本《阿门角》(,1958,下文简称《阿》)、小说《假如比尔街能说话》(,1974)、《就在我头上》(,1979)相继问世。鲍德温对宗教的情感还体现在他临死前创作但未发表的戏剧《欢迎之桌》()中。“‘欢迎之桌’象征着一张另一个世界的桌子——教堂的祭坛,在这张桌子上,疲惫的旅客将找到他们渴求的‘牛奶和面包’……”这部作品陪伴鲍德温走过生命的最后一刻,最能体现其崇高愿望,即走出教坛,走向世俗,用笔端向世人传播爱的福音,让所有人以平等的身份欢聚一堂。此外,鲍德温的散文《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1961)、《下一次将是烈火》(,1963)等都展现了他福音布道式的雄辩文风。鲍德温究竟是宗教信仰者,还是背叛者,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过于对立,只有完整动态地把握鲍德温以宗教为主题的文学创作,结合其人生经历和个人言论,才能正确认识其宗教观及成因,从而客观评价其为挖掘黑人宗教文化做出的卓越贡献。
对于鲍德温的宗教信仰,评论界普遍称他为上帝的“背叛者”,认为其文学作品渗透着浓厚的反宗教情绪。桑德拉·奥尼尔认为鲍德温对基督教的强烈指责“开启了当代反基督教的闸阀,开创了脱离圣经为写作基础的美国黑人文学”。罗尔夫·伦丁认为鲍德温是个“没有信仰的人”。陈世丹教授认为鲍德温“把宗教表现为资本主义种族社会使黑人甘心被白人奴役并忍受种族迫害的麻醉剂……”,而笔者认为彻底否定鲍德温的宗教信仰是对其人生和文学作品的扭曲。“鲍德温对基督教的抗议是发展于他对基督教禁戒的内在认识和他个人对信仰和上帝追求基础之上的。”他从未放弃对上帝的求索,他曾指出:“教堂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地方,……没有任何音乐敌得过教堂里的音乐,没有任何戏剧比得上教堂里的仪式。……身处正在布道的教堂里,我有时候感到巨大的力量和荣誉,……我们相互分享彼此的痛苦和欢乐。”鲍德温所批评的是制度化、刻板化的基督教教义及基督教无法真正满足宗教所代表的道德信条的问题。本文从解构主义角度出发,通过分析鲍德温以《向》和《阿》为代表的宗教主题作品对上帝中心主义的消解和对民间上帝的重塑,解读鲍德温没有宗教的宗教观及其成因,从而解答这个重要的历史问题:鲍德温是上帝的信仰者,还是背叛者?
一、鲍德温与德里达宗教观的相似性
仔细阅读鲍德温的文学作品,笔者发现其宗教观与雅克·德里达“没有宗教的宗教”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德里达把西方传统的哲学称为“在场的形而上学”,其解构主义理论旨在颠覆“一个中心、一个本原、一种绝对真理”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而全知全能的上帝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产物,上帝高高在上,代表真理与权威,万物是上帝的补充物、对立面和客体,是被支配、被观看、被征服的对象。德里达把解构主义运用到对传统上帝和宗教的解构之上,不断质疑、挑战和解构传统独断的有神论,使宗教从传统有神论的独断论中转化出新意。因此,解构主义视角下宗教思想是“一种非传统宗教独断论的独断……这样的宗教将剔除传统宗教中那些制度化的教条或僵死的独断论,其本质乃是脱离信仰条款的约束……”在1994年“宗教的回归”主题研讨会上,德里达指出“宗教回归必然涉及到宗教的解构……并在解构之中,宗教来创新肯定自身,实现普遍的博爱与和解”。可见,德里达对宗教的“解构”并不是对宗教本身的解构,而是以新的思维重塑崭新的上帝形象,即用道德和公正来定义的“没有宗教的宗教”。
鲍德温逃离教堂投身写作的人生经历及其文学作品对上帝的剖解和阐释,与德里达对宗教的解构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通过分析背叛上帝的圣徒形象来解构和批判教堂里排外、单一的耶稣形象。另一方面,通过探讨圣徒的生活经历和命运结局重构博爱、公正、赐予快乐的民间上帝。鲍德温对上帝的解构和批判不是对上帝本身的解构,而是对制度化的教条或僵死的上帝独断论的批判,从而根据自己的思维方式通过创作来重新定义宗教和上帝。他的宗教情感经历了从信仰到背叛再到回归的过程,他对“宗教的回归”建立在他对宗教本身的理解之上,是对传统宗教的挑战和延拓。德里达的“没有宗教的宗教”并不是“取消主义”,也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多元宗教的价值体现。同样,鲍德温对上帝的解构和批判是探索和重构上帝的前提,体现了鲍德温对多元宗教价值观的思考。
二、对上帝的质疑和批判
小说《向》和剧本《阿》分别塑造了少年和青年时期的鲍德温形象——约翰和戴维。约翰虽然一直徘徊在对上帝的困惑和质疑中,但最终获得拯救;而戴维却放弃教堂钢琴手的职务,与母亲逃离教堂,追求音乐梦想。鲍德温对上帝的解构和批判充分体现在约翰对上帝的质疑、戴维对上帝的背叛以及加布里埃尔和玛格丽特等教徒对上帝旨意的曲解中。
约翰的所见、所闻、所感不仅惟妙惟肖地再现了黑人的宗教生活,而且生动地展现了鲍德温孩提时代的宗教经历。上世纪哈迪·克拉伦斯指出:“鲍德温的第一部小说所描述的宗教文化和70到80年代黑人宗教现状非常相似。”小说通过对约翰在困惑和挣扎中得到救赎、皈依宗教的心理变化的描写及其继父、母亲、姑姑对过去生活的回忆,无情地抨击了黑人宗教的伪善,揭示了鲍德温对当代黑人教堂里上帝的质疑和困惑。
首先,约翰皈依宗教的最初动机是寻求上帝的庇护,逃脱继父的控制。约翰生活在拥有四个孩子的继父家里,难免遭到父亲的唾弃和母亲的冷落。继父不但未遵守承诺,善待约翰,而且还在肉体和精神上凌辱他:“约翰长的是撒旦脸。那上挑的眉毛,那粗硬的头发在眉毛上方形成的V字形……两只大眼睛,宽而低的前额,三角形的鼻子,大嘴巴,下巴颏上有一个隐约可见的裂口……这个裂口是魔鬼的手留下的记号。”他对约翰的形象妖魔化,造成其罪恶感和人格分裂,成为他成长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心理障碍。继父还把亲生儿子的堕落无故归因于约翰,认为约翰剥夺了他们的长子地位。为了战胜继父,约翰别无他法,只能皈依宗教,指望得到上帝的庇护。
黑人惨淡的生活现状使约翰对上帝充满质疑和困惑。白人的奢华生活与黑人的贫苦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百老汇大街上白人无需祈祷,便能身穿绫罗绸缎,手带珠宝玉器,享受人间美味。而不管黑人如何虔诚地祈祷,都得住在拥挤不堪、肮脏丑陋、充满灰尘、汗臭、尿味和家酿酒的哈莱姆贫民窟里。黑白人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现状使约翰纳闷:为什么白人无需祈祷便能过上如此优越的生活,而不管黑人在上帝面前怎样卖力歌唱、哭泣、叫喊,都得活得如此狼狈?
上帝容不得世俗的性爱和跨种族之爱,这不得不使约翰对上帝产生质疑。当天早晨,约翰有了性觉醒,手淫了。从生理学上看,这一现象是正常男性性成熟的表现,但在黑人原教旨主义下成长的约翰却因此背上了沉重的罪恶十字架。年轻牧师伊莱沙和埃拉·梅相互倾慕,因在敬拜上帝时走乱步子而遭严厉训斥,少男少女青涩的情感因此夭折。此外,继父加布里埃尔扭曲上帝博爱的旨意,教育约翰憎恨白人。老师的关怀,校长的肯定,老人的微笑都让约翰质疑继父的上帝所倡导的狭隘的爱。鲍德温在散文《下一次将是烈火中》感叹:“教堂里没有爱。这是一张隐藏着憎恨自我和他人的绝望面具……当我们被告知要爱‘所有人’时,我以为我们该爱每个人。但是,不是。我们只是去爱自己认为该爱的人,并不包括白人。”约翰的质疑揭示了鲍德温对现实上帝的无情批判:基督教教义下的上帝是狭隘、偏激、制度化的专断主义者。
此外,鲍德温通过刻画加布里埃尔虚伪可憎的教徒形象,揭示了扭曲上帝形象的罪魁祸首。加布里埃尔曾是个吃喝嫖赌、打架斗殴、抛妻弃子的浪荡子。在前妻的帮助下,他皈依了宗教,但不过多久,便与名叫埃丝特的女子鬼混。当得知埃丝特怀孕时,他偷了妻子的积蓄强迫埃丝特离开,以此掩盖罪行。他不仅间接害死了埃丝特,而且未能承担照顾私生子的责任。为了维持牧师的地位,他不敢与亲生儿子相认,眼睁睁地看着他横尸街头。可笑的是,他不仅把大儿子的死推卸到情人埃丝特身上,而且还把二儿子的堕落归结到妻子伊莎贝拉和养子约翰身上。通过塑造加布里埃尔这个伪善的牧师形象,鲍德温提出质疑:“上帝为何指派内心如此丑恶的人来充当其神圣的使者?”
剧本《阿》对上帝的解构和批判更进一步。正如小说《向》一样,《阿》被众多评论家片面地定格为反宗教作品。《阿》揭示了“神学的恐怖”,它告诉读者教堂只是黑人短暂的避难所。
通过剖解玛格丽特变化发展的宗教观,鲍德温有力地消解了教堂里制度化的、刻板的上帝形象。玛格丽特是位专横跋扈、自私自利的牧师,她的上帝不仅禁止教徒享受世俗的幸福,还残酷地处罚无辜者。她因饥饿失去胎儿,但是总武断地认为这是上帝对她与丈夫快乐生活的惩罚。“上帝要我离开。我们一直像动物一样,像孩子一样活着,只知道寻欢作乐……我一直在想我们不能这样下去——过去我们太快活了。”当丈夫垂死时,她不顾儿子的恳求,远赴费城做布道。在她眼里,爱情是罪恶的根源,而像莫拉教徒那样的老处女才值得尊敬和骄傲。她教育孩子不看滑稽书,阻止教友开载酒车谋生,禁止戴维欣赏父亲的爵士乐。这些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教堂里却是罪孽。玛格丽特对上帝的诠释无疑是鲍德温批判和控诉上帝的重要手段。
看到儿子出走,丈夫垂死,教徒为教堂开支争吵,玛格丽特对她笃信的上帝逐渐产生怀疑。教友的指责——“……当你不能善待你能亲眼看到的教友时,你怎么可能去爱你看不见的上帝?”——使玛格丽特从对上帝的迷信和曲解中清醒过来。丈夫的爱情使她再次回归到爱情和亲情中,她承认“没有人能像卢克那样让我开心……我心里仍然爱着他”。玛格丽特逃离教堂无法避免,因为她误解了上帝的旨意,没有找到赐予幸福的上帝。
随着剧情的发展,戴维愈加清晰地认识到上帝的无能和虚伪。他否认自己的音乐天分是上帝赐予的;为看父亲的爵士乐表演,他拒绝跟母亲赴费城做布道;当父亲垂死时,他拒绝下跪祷告;当几个音乐爱好者多次来到教堂,他深信是钢琴声而不是教堂的布道吸引了他们。在父亲的鼓励下,戴维选择离开教堂追求音乐梦想。可见,对于上帝的丑恶面目,戴维比约翰看得更清楚,他深信教堂里的上帝无法满足人们对爱和理想的追求。
通过对约翰的质疑、戴维的叛逃和加布里埃尔与玛格丽特可恶行径的抨击,鲍德温彻底解构和批判了传统宗教的独断论,暗示着其信仰的彻底瓦解。但是,解构并不是完全取消其意义,而是给它一个全新的解释。在解构宗教的同时,鲍德温用自己的方式重构上帝形象,并对宗教的意义做出崭新的阐释。
三、对上帝的改造和回归
德里达批判海德格尔的本体论神学,反对宗教的圣化观念以及把形象固定化的认知方式,这是他“没有宗教的宗教”的缘由所在。在“没有宗教的宗教”里,可以找到一个宗教性的决断所具有的全部激情和责任。鲍德温小说《向》和戏剧《阿》中各人物的生活经历和命运结局,就是其充满激情和责任的宗教性决断的具体体现:上帝严惩了罪恶,拯救了善良。
约翰最终得到上帝的拯救,而加布里埃尔却落得妻离子散的下场。约翰得到上帝的拯救是肯定的,精心安排的故事细节有力地证明了这点。约翰的救赎发生在他生日当天,这暗示着他将获得重生。母亲为约翰特意准备的生日礼物是对他最好的鼓励。当天,约翰感到欣喜若狂,心中萌生无限力量,犹 如“引擎”、“巨人”、“暴君”、“征服者”和“救世主”。其次,约翰在与教友伊莱沙的搏斗中第一次获胜,预示着他获得拯救的时机即将到来。再者,文本中频繁出现的宗教象征和布道言辞证明了救赎的真实性。“约翰看见了主……一道他无法忍受的灵光照亮黑暗……他觉得自己逃离了黑暗、烈火、死亡的恐怖,正在上升,与圣徒们相会……他那飘忽不定的灵魂已经坚定地同上帝的爱互相交汇;牢牢地固定在那千古不朽的磐石之上……光明与黑暗已经接吻,永远结合在一起。”
虽然加布里埃尔在上帝的眼皮底下为所欲为,但他的罪孽最终未能逃脱上帝的惩罚。他的私生子横尸街头,二儿子放荡不羁,对他充满仇恨。当他打妻子耳光时,儿子诅咒他说:“不准你打我母亲的耳光,那是我的母亲。你这黑杂种,你要是再打她,我向上帝发誓,我会杀死你。”加布里埃尔的悲惨下场证明鲍德温笔下的上帝是惩恶扬善、公正公平的救世主。
《阿》中,鲍德温某种程度上把上帝批判得体无完肤,以至于多数评论家都指认鲍德温为上帝的背叛者。这种片面的定论源于西方神话盛行的“非对即错”、“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德里达“没有宗教的宗教”对西方神话中的二元对立做出解构,这与鲍德温对宗教的理解不谋而合。虽然鲍德温一开始就意识到“上帝是白人”的历史现实,皈依宗教后又逃离教堂投身写作,但是上帝告诫人类要相互怜悯、仁慈、谦虚、温柔和忍耐的思想在鲍德温内心深处扎根,这是他主张用爱来融合黑白种族的非暴力抗议创作的主要原因。鲍德温对上帝的情感貌似矛盾,实属统一,他努力通过写作塑造博爱的民间上帝。故事结尾异常和谐,当玛格丽特决定离开教堂时,她对教友们说:“热爱上帝要我们去爱他的子民——所有子民,所有人!——跟他们一起分享痛苦与欢乐,从不计较需付出多少代价!”
玛格丽特这段肺腑之言是她一生最震撼的布道,她告诉大家热爱上帝是要去爱所有人。在西方神话中,上帝一直处于“在场”的地位,他是创世者,控制着整个宇宙,而世界上的人们始终处于“缺场”的地位,他们必须以上帝为中心,把自己放在一个卑微的地位。而这段布道与这种神话背道而驰,它把人与人之间的爱提升到对上帝的爱的高度。鲍德温在严厉批判上帝的同时,隐晦地向读者传达了重构上帝形象的可能和期望。上帝不再是“本原”、“中心”和“真理”,而是“道德”、“公正”和“博爱”。鲍德温摆脱传统信仰的束缚,对宗教做出彻底解构,证明上帝的可改造性,从而实现了对宗教的回归。他通过作品呼吁人们为这个伟大的工程奉献力量:“人类能够扩大、改造上帝的本质,这将是每个人创造力的永远体现。”
四、鲍德温宗教观的成因
尽管鲍德温与杜波伊斯(W.E.B. Du Bois,1868—1963)、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1914—1994)都高度肯定黑人宗教在黑人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可他们的宗教观却不尽相同。在杜波伊斯看来,奴隶解放前,上帝是欺骗者,他宣扬的“宗教宿命论深入人心,这在‘汤姆叔叔’这个人物形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婚姻成了闹剧,懒惰是种美德,财富意味着偷窃……在教堂的阴影下,白人和黑人的家园被摧毁,他们开始习惯得过且过,抗争中的希望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愠怒中的绝望。”在解放运动中,上帝是无能者,他不但袖手旁观,而且企图无故邀功。解放后的今天,上帝仍然无视黑人的生活状态,他逃避问题、随波逐流。“如今,教堂已发展成大型的社交和商务机构,为教徒提供信息和娱乐,谨慎地逃避黑人内部或外部不愉快的问题,用语言或行动说教:及时行乐。”杜波伊斯对上帝的批判是自始自终、毫无掩饰的。而埃利森则恰好相反,他对上帝的信仰是肯定的,永恒不变的。这在其小说《六月庆典》中的黑人牧师希克曼身上得到了体现:他希望通过把白人继子桑瑞德培养成牧师来解决黑白种族问题,尽管困难重重,但他从未放弃用宗教福音去感化桑瑞德。埃利森借希克曼之口阐释了他的信仰,“我们要把主的话看作是食品和住所,我们要把主的话看作是建造一个新国家的基石……即将上帝的话转换为一盏明灯,这样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与杜波伊斯不同,鲍德温的不幸童年使他对上帝抱有特殊期待,即得到上帝的庇护,摆脱继父的控制和恶劣的生活现状。然而,鲍德温也不像埃利森那样笃信上帝,当他发现上帝无法帮助自己得到解脱,未能主持公道、传播爱时,他便开始质疑上帝。其次,黑人民族的历史使鲍德温对宗教因爱生恨。从黑人奴役到种族隔离再到种族歧视,鲍德温对不公平的美国社会深恶痛绝。当上帝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和社会现状时,鲍德温开始质疑和憎恨上帝。这就是鲍德温离开教堂投身写作的原因。此外,鲍德温勇于挑战,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性格也使他不盲目轻信上帝。他放弃体面的牧师职业投身写作,通过文学“弑父”反对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1908—1960)的自然主义抗议小说及公开创作同性恋文学等事实,都体现了他不同寻常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对上帝的质疑、批判和改造正是他敢于挑战、赋予创造力的性格所致。
虽然鲍德温的一生都未停止对上帝的解构和批判,但是,他对上帝的爱根深蒂固,贯穿其一生。他曾感叹:“宗教这个问题……真切地困扰着我。”哪怕在他身患食道癌,危在旦夕时,鲍德温还不忘提及宗教。戴维·李明在《鲍德温传记》中指出:他意识到宗教在他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内在词汇”方面。至于更宽泛的问题,他不“相信”上帝,但是,他能感觉到——尤其是在他单独一个人时——“上帝的某些意义。”
鲍德温对上帝的爱无法抗拒,这种爱驱使他不停探索上帝的真谛。一方面,宗教作为美国黑人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在鲍德温的内心深处扎根。宗教不仅使黑人得到了群体的归属感,减轻了他们的孤独与恐惧,而且使他们长期受压抑的情感得以宣泄,由此维持心理健康。作为黑人民族的一员,鲍德温深受宗教影响,他离开教堂并不代表他背叛上帝。另一方面,不幸的孩提时代促成鲍德温急功近利的性格,黑人宗教是其寻求文学创作突破的重要手段。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正经历着走出自然主义抗议文学窠臼,走向以黑人文化为基础的新型现代黑人文学的重要变革,鲍德温顺应时代潮流,极力挖掘黑人宗教文化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鲍德温认为斯陀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l811—1896)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批判了奴隶制,但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赖特的《土生子》则把黑人描写为没有传统、习俗、宗教仪式和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空壳,否定了黑人人性的复杂性,使黑人形象刻板化。为了突破黑人自然主义抗议文学的局限性,鲍德温着眼于挖掘黑人复杂人性和传统文化,旨在建构黑人文化身份,而黑人宗教也便成为其重要内容。
五、结论
不可否认,鲍德温的宗教观和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自相矛盾”的思想观念和创作风格。这也是鲍德温遭受评论界严厉批评,在文学上始终无法超越赖特的重要原因之一。残酷的黑人 历史与现实造就了鲍德温近乎自相矛盾的宗教观和创作思想,而这一定程度上也与他急功近利的性格有关。
导致目前少许企业的抵扣链条断层的缘由主要包括两方面:首先是现行政策不允许抵扣某些支出,或者没有这方面的抵扣政策;其次是实际操作阶段,抵扣有政策,但是又出现不可抗的因素导致不能及时有效地抵扣税额。
然而,尽管鲍德温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存在种种不足,但是,我们无法否认他的宗教观的可贵之处以及他在挖掘黑人宗教文化和探索新型黑人文学创作风格上的先锋作用。鲍德温是上帝的黑皮肤革命家,他对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上帝唯我独尊的权威提出质疑,用“跨种族之爱”颠覆上帝中心主义,消解中心,使处于边缘位置的“世俗之爱”去边缘化,呈现出“世俗之爱”的独特魅力。解构是期待他者的降临,解构是向死而生。鲍德温通过对宗教的解构和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重构了公平和博爱的民间上帝,“他不在黑人教堂里,而在家庭的亲情、情人的爱情、民族的关爱中。”“与斯陀夫人和赖特着眼于描写黑人对外部世界的反应相比,鲍德温已开始注意刻画黑人的内心世界……明显呈现出‘向内转’的趋向。”鲍德温透过表象看到本质,他对宗教的解构和回归,是他挖掘黑人文化真谛,展现黑人人性,定位黑人身份的重要手段,体现了他文化研究思想和叙述手法的独创性和超前性。
[1] Leeming D. James Baldwin: A Biography[M].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94.
[2] O’Neale S. Fathers, gods, and religion: percep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ethic faith in James Baldwin[C]//Fred L. Standley, Nancy V. Bur. Critical Essay on James Baldwin. Boston: G. K. Hall & Co., 1988.
[3] Lunden R. The progress of a pilgrim: James Baldwin’s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J]. Studia Neophilologica, 1981, 53(1): 113-126.
[4] 陈世丹. 《向苍天呼吁》: 走向一种生态社会[J].山东外语教学, 2011(4): 62-68.
[5] Lynch M F. A glimpse of the hidden god: dialectical vision in Baldwin’s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C]//Harris T. New Essays on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31.
[6] Baldwin J. The Fire Next Time[M]. New York: Dial, 1963.
[8] Derrida J. The Gift of Death[M]. Translated by David 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9] 陆扬.德里达、瓦蒂莫和伽达默尔:没有宗教的宗教[J].社会科学, 2006(12): 166-171.
[10] 单纯.论德里达的宗教思想[J].国外社会科学, 2004 (5): 26-33.
[11] Clarence E. Hardy III. James Baldwin’s God: Sex, Hope, and Crisis in Black Holiness Culture[M].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2003.
[12] Baldwin J.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C]//Baldwin J. Early Novels and Stories.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98.
[13] Macebuh S. James Baldwin: A critical Study[M]. New York: Third Press, 1973.
[14] Gounard J F. The Racial Problem in the Works of Richard Wright and James Baldwin[M]. Translated by Rodgers J J. Westport: Greenwood, 1992: 179.
[15] Baldwin J. The Amen Corner[M]. New York: Dial Press, 1968.
[16] Du Bois W.E.B. The Souls of Black Folk[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9: 140-145.
[17] 拉尔夫·埃利森.六月庆典[M].谭惠娟, 余东, 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128-129.
[18] Baldwin J, Mead M. A Rape on Race[M]. New York: Dell, 1971: 83.
[19] 谭惠娟.詹姆斯·鲍德温的文学“弑父”与美国黑人文学的转向[J].外国文学研究, 2006(6): 130-138.
Religion without Religion—A Study of James Baldwin’s Deconstruction of Religion and His Return
Mi Fenfang, Tan Huijuan
(1.,,,;2.,,,)
James Baldwin, a famous African—American writer,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n the view of black religion: from believing in God, to leaving the church, and then returning to write about it. His religious view bears great similarity to Derrida’s “Religion without Religion”. With decon- structionist guid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Baldwin’s d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religion and his view on religion, Religion without Religion, based on an intensive reading of his religious writings represented byand. While deconstructing and criticizing the hypocritical and incompetent God in the fundamental church, Baldwin tries to reconstruct a just and loving secular God, thus to realize his return to religion. His love and hate for God, contradictory but reasonable, is related to his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personal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trend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ture in 20th century from the naturalist protest literature to modern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
I712.44
A
1009-895X(2012)03-0223-06
2012-01-14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资助项目(2009Z218);浙江省外文学会专题研究资助项目(ZWZD2009029)
宓芬芳(1982-),女,讲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E-mail: fenfangmi1982@yahoo.cn
① 笔者译,原文为“There is something in it.”(见文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