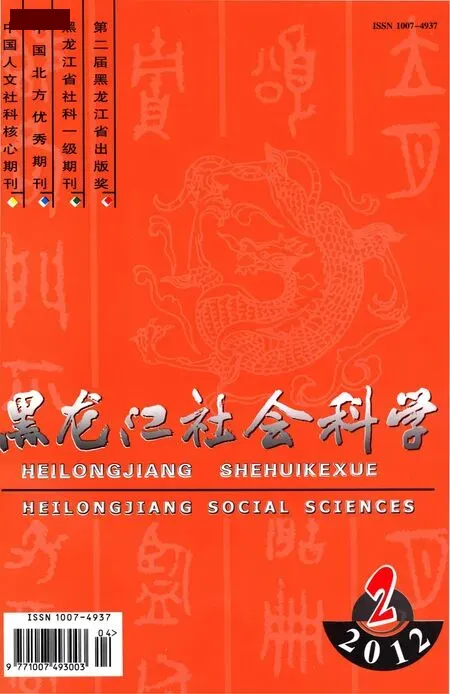变异学视野下的《爱卿传》和《夜归荒宅》的比较研究
2012-04-12易国定
易国定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116080)
变异学视野下的《爱卿传》和《夜归荒宅》的比较研究
易国定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116080)
明清小说东传对日本江户小说的繁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翻案明清小说的基础上,日本出现了大量的读本小说,而通过对《剪灯新话》中的《爱卿传》与《雨月物语》中的《夜归荒宅》两部作品的比较,可以看出其中展现的审美的民族性和创新性。
比较文学变异学;读本小说;明清小说;瞿佑;上田秋成;翻案;改写
关于明清小说对日本江户读本小说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起,学界不断有一些相关专著和论文发表,其中,严绍璗、王晓平、李树果、马兴国等先生的研究成果显著。学者们都对明清小说与日本江户读本小说之间的关系,做了事实上的考证研究,具有朴学的扎实功底。笔者试图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清晰地梳理出二者之间的影响变异关系,由此也证明了学者严绍璗提出的日本文化是“变异复合体”的论断。本文以《爱卿传》和《夜归荒宅》(浅茅宿驿)的比较为个案,以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视角对上田秋成志怪小说的创作进行发生学上的考察,聚焦上田秋成如何将引进的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过程,即去中国化,致力于和风化(他国化)时,所展现的审美的民族性和创新性。
一、上田秋成改作的文化语境和意图
在明代被翻改的小说中,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是最典型的案例,在日本和韩国都有以此为底本翻改的作品。《剪灯新话》的内容多叙写情爱,书中多艳语情词,颇合当时人的爱好,一时仿效者纷起,以至于闹到在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时,有人上书请求禁毁此书,从中可以看出其影响。亦可见明初士人所受到的文化钳制,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剪灯新话》被禁,才促使它向外流传。
《剪灯新话》出现后,很快传入了日本和韩国。据日本禅僧策彦周良的《策彦和尚初度集》记载:是他第一次入明时(天文九年,明嘉靖十九年),在宁波用私费买了《剪灯新话》和《余话》。次年策彦将这两部书带回日本。另外,在禅僧景徐周麟的《翰林葫芦集》第三卷中,有题为“读《鉴湖夜泛记》”的诗一首:“银河刺上鉴湖舟,月落天孙窃夜游。又恐虚名满人口,牛郎今有辟阳侯。”根据这首诗所注的年代推断,是日本文明十四年(1482)秋之作。由此可以表明《剪灯新话》最晚在15世纪已传入日本。据说最早翻译介绍《剪灯新话》的是儒臣林罗山,在他自编的《怪谈》中,摘译介绍了《剪灯新话》卷一中的“金凤钗记”。另一部成于天文年间(1532—1554)的书《奇异杂谈集》又翻译了《剪灯新话》中的《金凤钗记》、《牡丹灯记》、《申阳洞记》三篇小说。
《剪灯新话》传入日本的时代,正是日本新兴的市民阶层——町人阶层壮大的时代,由于德川家康在1603年基本上统一了历经百年战乱的日本,国内局势稳定,工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江户、京都、大阪三个经济文化发达的都市,围绕着三都出现了大量的城市市民和商人,构成了由商人组成的町人阶层。町人阶层不仅是文化艺术的生产主体,也是文化艺术的消费主体。从而逐渐形成了属于市民阶层的町人文化。日本文化由贵族文化品味开始转向拥有启蒙教育和文化娱乐功能的大众文学趣味。而《剪灯新话》以其新奇怪异的内容和艳丽流畅的形式,尤其是小说中“有文、有诗、有歌、有词、有可喜、有可悲、有可骇、有可嗤”(《剪灯新话》序四)的各类人和事,颇受日本广大町人的喜爱。为了对抗儒学和新国学的复古主义思潮,处在市民阶层的小说家们,比如浮世草子作家井原西鹤开始写一些“好色物”和“町人物”,这类小说表现了处在“四民制”(士、农、工、商)中的最底层的町人享受生命的本能欲望,和游戏人生的思想,一时间游戏文学兴盛,而更多的草子作家为了满足市民寻求刺激的心理,寻找一些神仙鬼怪、荒诞不经的故事来敷衍。他们开始借鉴中国古代传奇、志怪小说的题材和笔法,试图在创作中开创新的领域,这样就促成了读本小说的产生。由都贺庭钟的《英草纸》开端,为“读本之祖”,继后其弟子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将前期读本小说的创作推向一个高峰。
二、上田秋成改作的方法及意义
上田秋成的《今古怪谈雨月物语》(简称《雨月物语》)对《剪灯新话》的接受与模仿,从小说的名字的由来就可见一斑,它是参照《剪灯新话》中的“牡丹灯记”,把鬼魂出没的时间描写成“天阴雨湿之夜,月落参横之辰”。小说的题目,取其中的雨和月命名,用以代表鬼怪之意[1]。
《雨月物语》一书共五卷九个短篇小说,其中引用了许多中国古典文学和典故。笔者将《雨月物语》和《剪灯新话》等中国文学的关系梳理如下:《雨月物语》中的《白峰》、《夜归荒宅》、《佛法僧》、《吉备津之釜》、《青头巾》、《贫富论》多是受了《剪灯新话》中的《龙堂灵会录》、《爱卿传》、《天台访隠录》、《牡丹灯记》、《天台访隠录》启发,而另外三篇《菊花约》、《梦幻鲤鱼》、《蛇性淫》则分别翻改《喻世明言·范巨卿鸡黍死生交》、《古今説海·鱼服记》、《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雨月物语》至少有六篇很明显是改作《剪灯新话》的作品,而其他三篇则是改作了“三言”、《五杂俎》等中国古典小说。我们来探讨上田秋成改作《剪灯新话》为《雨月物语》时,是如何致力于本土化,去中国化的,也就是中国的原典如何被他国化的。上田秋成大致是围绕小说的要素:背景、人物、情节、结构、主题入手的,下面以《剪灯新话》中的《爱卿传》和《雨月物语》中的《夜归荒宅》作比对,考察上田秋成改作中国小说时采用的主要方法及由此而发生的变异现象。
1.时代背景的变异
上田秋成在以中国古典小说为底本改作时,不是简单的原样照搬,而是转换故事发生的时代、场景,以符合日本社会的风貌,使之本土化,让日本读者在接受作品时有一种亲切感。背景的变异是日本作家改作中国小说最易做到的,《雨月物语》的《夜归荒宅》将故事发生的背景设定为亨德四年(1455),此时的日本正处在战乱频仍的镰仓时期,这样男女主人公生离死别的悲剧命运,就有了日本社会历史的背景因素,而没有采用架空历史的做法。所以说上田秋成的志怪小说是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来表现现实。在谴责战乱带给人民深重的灾难这一主题上,《雨月物语》的《夜归荒宅》与《剪灯新话》的《爱卿传》是十分一致的。但在对人物和情节的处理中,二者表现出十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
2.人物的姓名、身份及关系的变异
中国人的姓氏制度和日本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更换姓名,改变人物的身份是本土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爱卿传》中的男女主人公是富家子赵子和嘉兴名妓罗爱爱,而之相对的《夜归荒宅》中的男女主人公分别改为商人胜四郎和妻子宫木,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除了贵族一般的民众是没有姓氏的。所以男女主人公是只有名字的。小说不仅更换了当事人的姓名,而且也改变了当事人的身份,以符合日本社会商人开始活跃的时代特征。此外,作者还根据表达主题的需要,替换人物的设置,改变出场人物之间的关系。比如在《爱卿传》中为表现罗爱爱的孝顺和坚贞,宣扬儒家一女不事二夫的封建伦理道德,在小说中特设了婆婆和恶霸刘万才的形象,用一定的笔墨描写了罗爱爱与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而在《夜归荒宅》中上田秋成对这种中国儒家的道德诉求,并不感兴趣,为了表现日本武士和市民都十分崇尚的“信义”思想,而设置了漆间老翁这个人物,他因为感念宫木的纯情和贞信,安葬宫木。由此看出,《爱卿传》体现了瞿佑士人的儒教价值观,而《夜归荒宅》则体现的是日本町人的价值观。
3.情节的变异
小说的情节结构是小说最主要的构成因素,“情节的翻案是翻案文学的核心,情节的翻案造成了翻案文学其他因素的类似性。背景与人物的置换多是表面的现象,具体描写与原作相当类似,这是情节的翻案造成的……翻案作品在保持原作基本情节的前提下,多大程度上变异,没有明确的规约,完全是作家的自由”[2]。正是这种自由,才给作家在翻改他人作品时,以显示其自身创作个性、才情的空间和可能性。而作家通常会通过扩写、缩写或删改等手段,对情节进行变异,而这种变异既是本土化的过程,又显示了作家在接受他国文化原典时的模仿和改造的能力。而情节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作者要表达的主题思想的变化。从上面的《爱卿传》和《夜归荒宅》情节对照,来看作者是如何将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加以变异,以符合日本的社会现实和日本人的审美取向的。
首先,两部小说所写的男主人公离家的原因和其妻子对丈夫离家的态度迥异。《爱卿传》中的富家子弟赵子是为了求取功名而离开江南老家进京的,其名妓出身的妻子罗爱爱十分支持丈夫,爱卿对丈夫说:“妾闻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丈夫壮而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岂可以恩情之笃,而误功名之期乎?君母在堂,温凊之奉,甘旨之供,妾任其责有余矣。”[3]俨然一个中国古代妇德的楷模。而《夜归荒宅》中的胜四郎则是因为家道中落,为求取钱财,不顾妻子的感受而离家的。宫木对丈夫的离家,颇不情愿,以一个女人的柔情和缠绵试图挽留住丈夫。然而丈夫任性,于是只好约定丈夫秋天返家。上田之所以这样处理这个情节,完全是出于对日本独特的文化特点的考虑,因为日本江户时代没有科举制度,而广大的市民阶层也不可能走入仕途,于是经商成了他们的谋生之路。而上田秋成对女性也无儒家的道德要求,宫木身上丝毫没有中国传统女性为成就丈夫的事业而忍辱负重的品德,她只是一水的柔弱,只是任情地表达自己对丈夫的依赖和信靠,小说表现了日本女性的柔弱品性,和日本文学的阴柔之美。
其次,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在丈夫走后的遭际和死因不同。罗爱爱在丈夫离家后,侍奉患病的婆婆,并为婆婆下葬。表现了中国传统美德的“孝”道。罗爱爱先是替夫尽孝,后又为夫守节,为保贞洁终自缢身亡。在罗爱爱这个从良的女子身上,瞿佑寄托了浓重的封建道德理想,于是罗爱爱成了“忠孝”、“贤淑”、“贞洁”的化身。而宫木的感情似乎来得更单纯些,只因为与丈夫有个秋日相见的约定,她不肯在战乱时逃离家乡,为避恶人的骚扰整日闭门不出。终至死在荒宅中。在宫木身上体现了江户时期市民阶层的“情义”和“信义”观念。
最后,两部小说的结尾处理可以说是大异其趣。《爱卿传》的结尾是一个劝善彰德,生死轮回的果报故事,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对一个像罗爱爱这样如此淑德的女性的安抚,就是让她下辈子投胎做男子。由此看来瞿佑的《爱卿传》的主旨在弘扬儒家的人伦思想和佛教的业报观念。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在中国的文学中没有真正的悲剧,只有悲喜剧。《爱卿传》把原本一个生离死别的大悲剧,硬是用佛教果报的思想扭转为一个生命轮回的喜剧,小说原本的悲剧色彩被消解了,所以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乐感文化。而上田秋成在《夜归荒宅》的结尾部分,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创作的自由,利用日本关于亡灵可以往来于幽明两界的传说,虚构了一个穿越生死的怪异情节,而在讲述这个怪异故事时,作者采用了胜四郎的叙事视角,让故事的真相在胜四郎知道后,作为读者的我们才随后知晓。小说写七年之后,胜四郎回到家中,家还是老样子,妻子宫木依然活着,只是人憔悴了许多,见到归来的丈夫,宫木感到所有的委屈都得到了补偿,是夜夫妻二人团圆。读到这里大家都会以为这是个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局,如果这样故事岂不平淡。不曾想,上田笔锋陡转,居然告诉我们其实宫木早已为鬼,家园荒芜成为墓地。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尾,其实是宫木“痴情”性格的极端表现。小说最后用漆间翁的一首哀悼儿女的和歌收束。上田秋成着重表现的是至真至纯的性情,对信义的执著,同时又有着一种日本式的哀切的感情。这与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的物哀精神是相通的。上田秋成将怪异提升为美,具有浓郁的幻想和浪漫的色彩,同时又有着浓厚的人情味和人间性。可以说,上田成功地去中国化,恰切地表达了日本情趣和日本人的审美取向。
从上述对《剪灯新话》中的《爱卿传》与《雨月物语》中的《夜归荒宅》两部作品的比较,可以看出两部作品之间的关联,二者在情节上有很大的相似性,这是因为翻改的缘故,但上田秋成并非对中国小说作翻译式的改编,而是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对中国原典作“和风化”的变异处理,以符合日本传统的审美情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采用的模式:从模仿到变异。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很好地融合和汉文化,有模仿更有超越,由此将日本江户读本小说推向成熟。
[1]李树果.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8.
[2]张哲俊.东亚比较文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72.
[3]上田秋成.雨月物语[M].阎小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33-34.
J4
A
1007-4937(2012)02-0133-03
2011-12-28
易国定(1965-),女,湖南宁乡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日本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