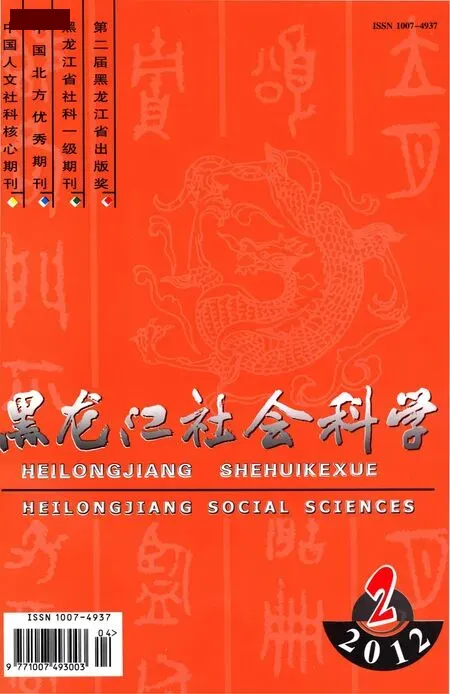施特劳斯的文明理想:美国式自由民主抑或古典精英主义
2012-04-12王升平
王升平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学报编辑部,广州510053)
施特劳斯的文明理想:美国式自由民主抑或古典精英主义
王升平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学报编辑部,广州510053)
在施特劳斯的视阈中,古典政治哲学也是一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古典政治哲学由于认识到了自然正当的界限而避免了虚无主义的可能,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则因对主体性和个体权利的过度强调而可能导向虚无主义。施特劳斯的文明理想是一种“普世皆贵族”式的、以对自然正当的遵循和敬畏为基础的文明理想。对于这种理想图景的实现,施特劳斯寄希望于“自由教育”,但实际上,“自由教育”能否有助于其理想图景的实现,还要取决于哲学的可教性等诸多因素的限制。
列奥·施特劳斯;自由民主;自由教育;古典政治哲学
关于列奥·施特劳斯的文明理想问题,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这一方面是由于施特劳斯“对自然正确和建立在城邦之上的共同体”[1]5的关注,以及对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批判,使得主流的自由主义者们认为,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是对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尤其是美国体制的威胁;另一方面是在自由主义者们激烈地批判施特劳斯思想的同时,施特劳斯学派的部分学者们又强调,施特劳斯并非自由民主的敌人,而是自由民主的朋友,例如布鲁姆就认为,施特劳斯“对美国的制度有着深深的感情”,施特劳斯不仅不认为自由民主制是可怕的、反而认为它是美国“人民最可靠的朋友”[1]6。那么,在施特劳斯眼中,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究竟是不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状态?如果不是,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政治状态是一种符合自然正当的理想状态?本文试图从施特劳斯的相关文本出发,在考察古典自然正当论与现代自由民主的价值紧张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
一、自由主义的古今之辨: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代自由主义
对于施特劳斯的政治理想图景,首先关涉的是施特劳斯与现代西方自由民主的关系问题。而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之前,我们必须追问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我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受现代政治哲学的影响,我们在论及自由主义时,往往理所当然地把自由主义理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那种以强调个体性、强调个体权利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忽略了自由主义在古代所可能具有的不同含义。因此,在考察施特劳斯的文明理想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对自由主义的含义进行探讨,以揭示出自由主义及其所主张的自由民主是否与古典意义上的自然正当存在着某种契合的可能。
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一般是指一种区别于社群主义的、以强调人的个体性为基础、强调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学界一般将其根源追溯至洛克(洛克较早明确提出了政府的根本任务在于保护私有财产,最佳的政府形式是“民选的议会掌握最高权力的政府”[2]的主张,这种主张从理论上奠定了现代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的基础)。如果从上述意义上理解自由主义,其仅仅是现代性的产物,它伴随着现代个体观念的发现而产生,是现代权利意识崛起的产物。而在前现代时期,个体首先被理解为社会和城邦中的个体,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被当成人的首要特性。
但是就自由本身的含义而言,并不是说只有个体观念和权利优先意识得以确立,才可能存在自由。当我们把个体观念和权利意识当成自由的根本时,实际上是把现代性兴起以来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前提,以至于忽略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式的古希腊政治哲学思想中实际上也包含着自由主义的内容。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的基本指向之一,就在于重新发现了古典意义上的自由和古典思想中的自由主义。施特劳斯认为,古典时代也存在着自由主义,他所主张的复归古典政治理性主义,实际上就是要复归一种古典式的自由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保守主义者的施特劳斯,实际上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在施特劳斯的观念中,“今天的保守主义恰恰是最初的自由主义”[3]3。但是,我们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古典的自由主义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为是自由主义的?它与现代的自由主义有何不同?
在《自由教育与责任》一文中,施特劳斯专门就古典自由主义对自由之内涵的理解进行了阐释。在施特劳斯看来,自由的“原始的政治含义几乎与其现在的政治含义截然相反”,因为,最初意义上的自由人,“就是区别于奴隶、行动自由的人”[3]10。在施特劳斯看来,古典自由主义所理解的自由,就是一种可以自由支配自身的状态。奴隶之所以不自由,是因为他们受制于主人,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而主人的自由,正是源于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行动,做自己兴趣之内的事。根据施特劳斯的逻辑,真正拥有自己时间的自由人,主要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拥有一定财富的绅士,但获取和管理财富不会占有他们太多时间”[3]10,由于能够不费太多时间而获取较多财富,能够不费较多时间而管理好自己的财富的人必定只是少数,因此,“绅士生活只是为少数富人保留的”[3]11。绅士因为拥有谋生的足够财富,同时也具备足够的闲暇,因而他们是能够潜心于研习政治和哲学的人。另一类可能是,一个人具有哲学家的气质,他虽然生活清贫,但他并不为生计而奔波,而是将获取真理作为他最大的满足。因此,哲学家之区别于绅士之处在于,“绅士必须要富有才能做好他分内之事,而哲人守于清贫”[3]13。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最为直观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自由的主体的转变:古典意义上的自由是一种为少数人所享有的自由(无论是绅士,还是哲学家,在社会中都是少数),而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则是一种普遍化的自由、是一种人皆享有的抽象之物。现代政治哲学对自由的这种普遍化和抽象化,使得权利战胜义务成为政治社会中的至上的方面,大众在这个过程中似乎成为自身命运的决定者。但是,在施特劳斯看来,这种胜利的实质是以流俗取代了自然正当,一旦流俗与自然正当在某个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中不是同一的,那么,这个政治共同体中的正义也就无法得到保证。
根据施特劳斯的看法,将流俗置于自然正当之上并使其成为社会运转的基础,其结果必然是导致西方自由民主的虚弱。从价值论的视角来看,西方自由民主的虚弱,主要表现在自由主义对宽容的强调与对“区分敌我”的忽视上。现代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宽容,体现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宽容主要表现为国家对社会自由的无止境的承认、表现为国家对于社会意见的绝对中立和不干涉。然而,正如施米特所言,这种带有绝对性的中立和不干涉对于政治生活本身而言是致命的。因为,“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4]138,或者说,政治的根本就在于政治主体要在相互对立和冲突的意见中表明自己的立场。因此,依据施米特的看法,试图要取消政治的对立性,实际上是要为“普遍均质国家”的出现铺平道路,它指向的是一个无政府的、无政治的世界,这只能是一种空想。“政治乃是一种命运,因此人们无法逃避政治”[5]2。施特劳斯对于施米特认为政治的根本在于区分敌我的观点基本上是认同的,因为,施特劳斯之所以批判现代虚无主义、之所以强调必须回归自然正当,正是要重新肯定决断的重要性——人们必须在善恶好坏之间做出决断,这是政治的本性之所在、也是人们寻求美好政治生活的必然要求。因此,政治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有关政治的决断也是人类无法避免的命运。换言之,由于社会中的意见的对立和冲突的存在,使得政治层面的决断显得极为重要,无论站在哪个角度,政治主体首先都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而不能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方式来处理社会以及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的争端。然而,西方自由民主所强调的宽容原则和价值中立原则则正是要放弃这种决断。西方自由民主的这种宽容和中立表明,它实际上所持有的是一种无原则的政治哲学,一种什么都可以的政治哲学,它的结果是导致人们“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6]86、导致西方社会“对于它的目标不再确定”[7]3。
根据施特劳斯的逻辑,要克服西方自由民主的这种软弱性,关键在于将那种以同意为核心的政治原则转变成古典式的那种以智慧为核心的政治原则。以智慧为核心的政治强调的根本点在于对自然正当的服从,由于对自然正当的服从首先要求人们明白什么是自然正当,这就使得以寻求自然正当为要务的哲学精英显得尤其重要。现代西方自由民主所立基的同意原则,使得大众以数量上的优势控制着数量上占少数的绅士和哲学家,从而使得社会成为一个随大众文化而逐流的社会,社会被流俗所统治,而专家也成为流俗的注解人,不是专家引导流俗,而是流俗引导专家。然而,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现代西方自由民主中的流俗引导专家实际上也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它或许是大众统治,但又并非如此,因为事实上大众无法进行统治而只能受精英统治,即那些不论何种缘由而得以位居高层,或很有可能进入高层的团体”[3]3。换言之,大众统治很可能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统治,由于大众反思能力的欠缺,往往无法区分什么是符合自然正当的、什么是不符合自然正当的,由此也就决定了他们存在着被某些怀抱不良目的的精英的意见所引导的可能。如果是这样,西方自由民主就很可能成为某些掌握较强的信息传播能力的精英实现其目的的工具,由于这些掌握较强的信息传播能力的精英并不必然是品德高尚的人,因而,以大众同意为核心的政治,实际上也存在着使社会失范的巨大风险。
总之,施特劳斯所主张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能够凸显智慧、凸显知识精英的主导地位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以对公共义务的强调为核心的自由、是一种以社会总体利益为中心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施特劳斯对于现代自由民主政制显然不会持一种简单接受的态度。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施特劳斯对现代自由民主政制的批判并不能说明施特劳斯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敌人。因为,根据对古典政治理性主义传统的理解,理想城邦与现实城邦并不一定是统一的:理想城邦是哲人根据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自然正当而构想出来的,它具有强烈的理想性,这种理想要转化为现实,有赖于现实的“机运”[6]89等各方面的因素,也就是说,它的实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换言之,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中的理想城邦首先是一种言辞中的城邦,它可以成为现实城邦的指引,但由于外在条件的限制,理想城邦并不一定会转化为现实中的城邦。在现实条件和偶然性因素的限制下,哲人们往往退而求其次,淡化“自然权利或自然法”的观念、将“智慧与同意相调和”[8]155,承认一个低于理想城邦、但是现实可行的最佳城邦——这样的城邦虽然不是理想状态中的最佳城邦,却是现实状态中可行的最好城邦。因此,尽管在施特劳斯的思想中,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并不一定是那种符合自然正当的理想政治形态,但是它在施特劳斯看来,至少是现实可行的政治形态中的相对较好的政制形式。或者说,尽管现代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有着无法避免的虚无主义这一致命缺陷,但在施特劳斯的观念中,它并不是不可补救的,通过一定的哲学教育,可能使这种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
二、施特劳斯政治理想图景的具体形态
既然美国式的现代自由民主不同于言辞中的理想政治制度,那么,施特劳斯的所谓言辞中的理想制度又是怎样的?这种理想制度与现实的自由民主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差异?根据施特劳斯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将施特劳斯所构设的理想政治制度的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理想城邦中的主导者,一定是通晓自然正当的、接受过哲学教育的人,或者说,他们必须是懂哲学的人。施特劳斯认为,懂哲学的人有两种可能:一是接受过哲学教育的绅士,一是哲学家本身。受过哲学教育的绅士是以哲学家为师的人,他们“愿意接受哲学,也就是说,愿听从哲学家”[7]37,但在生活方式上,他们却是以政治活动等为业的人;哲学家则是真正的智慧者,他探求自然正当、探求理想的政治状态,“他被宣称拥有人类智力所能及的所有和最高层次的卓越品质”[3]5,但是,他并不愿直接统治。这是因为,由哲学的求真特性所决定,哲学家对于政治实践本身并不感兴趣,对政治实践的参与,必然会消耗哲学家进行哲学思考的时间,这是哲学家所不愿意的;如果纯粹以哲学家的理想状态来规范现实社会,将导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冲突,它不仅可能给现实的政治社会带来伤害,而且也可能伤害到哲学家自身,无论是哪种情况,哲学家都不愿意看到。所以,哲学家对于政治的引导,是通过对有哲学志趣的精英和绅士的引导来实现的,绅士参与政治,但只是部分地接受哲学教育和进行哲学思考,他的主要任务是将那些具有可行性的哲学思想转化为政治现实,使政治现实不偏离自然正当的标准、使政治现实无止境地接近于理想的政治状态。在这里,政治家对哲学家的观点存在一个过滤作用,它过滤了那些可能引起哲学家与大众意见冲突的观点、从而确保了哲学家与大众之间的和谐、也确保了政治社会的稳定。
其次,哲人是自然正当的发现者,而自然正当则是进行社会立法、安排社会分工的依据。循着柏拉图的思路,施特劳斯认为理想的政治状态是有着良好的社会分工、人们各司其职的状态。但是,大众对究竟什么是适合自身的却并不一定明晰,因为,“并非每个人都知道在一般意义上什么对人而言是善的,并且,在特殊意义上,并非每个人都知道对每个个体而言什么是善的”[9]147。施特劳斯认为,理想的政治状态要得以维持,就不应将这种社会分工的选择权完全交由社会个体自我决断,而应交由有智之人来加以引导,这样才能使个体的职位选择符合自然正当的标准,从而推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
再次,理想的民主状态是一种全民皆贵族的状态。在施特劳斯那里,民主本身可以是构成理想政治状态的一种形式,但前提是,民主并不是简单地让数量上的优势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真正的民主应当体现智慧、体现自然正当。现代自由民主所强调的那种民主制要想符合自然正当,或者说,现代自由民主制要想实现哲学家与大众之间的和解,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民主国家中所有或大多数成人都是有德之人”[3]3。也就是说,真正的民主制,应当是一种凡成人都接受过哲学教育、由全部理性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只有在人人都接受哲学教育的前提下,大众才不至于被意见所左右、也才能更好地接受哲学思想,从而缓和意见与哲学之间的冲突。
三、自由教育与精英塑造:施特劳斯的政治理想图景是否可能
由上述分析可见,从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施特劳斯对哲学精英在社会中的功能进行了特别的强调:哲学精英既是自然正当的发现者,也是那种古典式的普遍贵族意义上的民主制得以可能的前提。但是这样一来,根据施特劳斯的逻辑,一种政治理想图景要转化成为现实,必然要涉及一个哲学教育的问题,即如何培育起能够有效承担发现自然、正当、重任的哲学家的问题。另外,哲学精英是可以养成的吗?这一问题又牵涉了两个具体层面的问题:一是哲学精英的形成究竟是取决于先天因素还是后天养成;二是自由教育是否可以使哲学教育常识化,从而使大众普遍接受哲学继而使原初意义上的民主成为可能?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施特劳斯有关政治理想图景的思想,主要来自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根据柏拉图的看法,精英虽然与后天的养成密不可分,但他却也与人的先天气质密不可分。在柏拉图看来,人具有三种可能的天性气质,即理性、意志和情欲,这三种气质在每个人身体上的分布不一,也就使得具有不同气质的人分别适合于不同的岗位。柏拉图根据人的气质具体进行了三种分类:“相应于理性的是国家的统治阶级,其天赋职能是以才智管理国家;相应于意志的是武士阶级,其天赋职能是勇敢、善战、保卫国家;相应于情欲的是劳动阶级,其天赋职能是安分守己的为自己为国家进行生产劳动”[10]32-45。如果根据柏拉图的上述逻辑,人适合于做什么首先取决于人的先天气质而非后天教育,后天教育如果说有必要的话,不在于它能否改变人的气质,而在于它能够对人的先天气质进行因势利导,使这种气质特点得以发挥出来。换言之,在柏拉图那里,试图把情欲占主导的人培养成统治者或者试图使意志占主导的人成为生产劳动者,都是违背人的天性的、是不合理的。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同样构想过一种由人的先天性情所决定的等级制,他将人区分为主人和奴隶,并认为主人和奴隶的气质差异的形成主要关涉的不是后天的教育和培养,而是人天生的性情。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人役使奴隶之所以具有正义性,是因为城邦中存在着天然的奴隶,这种天然的奴隶由于“太愚蠢而不能引导他们自己,或是只能做一些比力畜所能做的事情稍微好一点的工作”[7]23。根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可见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做哲学家,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要培养真正的哲学家,首先必须采取的步骤是要对潜在的哲学家进行甄选,以遴选出那些理性在其性情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具有成为哲学家的天生气质的人。
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传统一样,施特劳斯也强调了大众化的甄选对于发现潜在的哲学家的重要性。施特劳斯认为,对潜在的哲学家的甄选,是通过自由教育来实现的。所谓自由教育,在施特劳斯看来就是一种通过对历史上出现过的最伟大的思想家的作品的阅读和理解,来“塑造完美品格,实现人类卓越”、“唤醒每一个人自身卓越的伟大的气质”的教育。自由教育是一种“大众文化的解毒剂”,它所要对抗的是“大众文化的腐朽”,要纠正大众文化“固有的只生产‘没有灵魂和洞察力的专家及没心没肺的酒色之徒’的倾向”[3]4。换言之,自由教育是针对大众而展开的一种古典传统教育,而之所以需要这样一种古典教育、之所以要诉诸历史上的“伟大心灵”,在施特劳斯看来,是因为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有原来意义上的那种伟大的哲人,他们不再倾心于完备的知识、不再“追求智慧,追求有关最重要、最高层次和最广泛的事物的知识”[3]6,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教育要么是顺应流俗的、前反思性的,要么是倾向于培养专业化和技能型人才的,这样的教育方式压制了“伟大心灵”的出现,从而使西方现代性问题的解决缺乏真正具有哲学见识的引领者、开拓者。施特劳斯认为,由于自由教育着眼于培养“伟大心灵”,因而它是为现代性问题的化解储备人才的一种必经途径。而对于自由教育的政治功能,施特劳斯认为其最根本的就在于它是使现代民主走向那种原始意义上“普世皆贵族”的民主的一种可能途径,“自由教育是我们从大众民主向原始意义的民主攀登的梯子”[3]4,它不仅提升大众,也通过发现潜在的哲学家和伟大心灵来为现代自由民主中的虚无主义困境的化解提供一种可能性。从施特劳斯对自由教育的强调中我们不难看出,就哲学精英是否可以养成这一问题而言,施特劳斯持有较为乐观的态度,根据施特劳斯的逻辑,自由教育正是发现精英、培养精英的一种可行之途。
其次,让我们转向有关哲学精英是否可养成这一问题的第二层面,即自由教育能否使哲学教育常识化的问题,或者说,自由教育能否使社会总体的认知水平得到整体化的提升问题。不难发现,根据施特劳斯的看法,如果要回到原始意义上的民主,即那种“普世皆贵族”意义上的、每个人都具有代表自身的良好能力、每个人都具有理性反思的良好能力的民主,首要的前提是社会中的所有人、或至少是大多数人都能通过自由教育而成为理性之人、成为具有哲学思考能力的“贵族”。尽管施特劳斯认为自由教育是针对大众的,但他并不认为自由教育具有使大众普遍“贵族化”的功能,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述,在施特劳斯那里,自由教育是一种通过大众化的、普遍化的古典教育、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挖掘潜在的哲学精英的一种途径;也就是说,自由教育实际上是一种精英教育,施特劳斯通过自由教育所试图达至的,也并非使全社会的哲学素养普遍提升,而是将那些具有成为哲学家潜质的人召入研究哲学的队伍。这就意味着,在施特劳斯的视阈中,原始意义上的“普世皆贵族”的民主,终究只可能是言辞意义上的,而不可能是现实意义上的,至少这种意义上的民主不可能通过自由教育这一途径达至。事实上,在施特劳斯看来,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冲突是永恒存在的,政治意见永远不能通过一定的教育而完全转变成为一个符合哲人理想的世界,从而使政治的意见世界与哲学的真理世界之间达成统一。这表明,施特劳斯通过自由教育所试图要达到的只是对现代西方自由民主政制的一种改良,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改进的思路,而根本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有更进一步的探讨和思考,而这种探讨和思考,也正是政治哲学之所以必须存在的原因。
[1]布鲁姆.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M].张亲樟,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2]吴恩裕.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
[3]列奥·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M].马志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4]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列奥·施特劳斯.施米特与政治法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6]贺照田.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7]Leo Strauss.The City And Man[M].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
[8]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9]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M].Chicago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10]王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比较研究[J].政治学研究,2001,(4).
D091
A
1007-4937(2012)02-0034-05
2011-12-07
王升平(1982-),男,湖南新化人,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