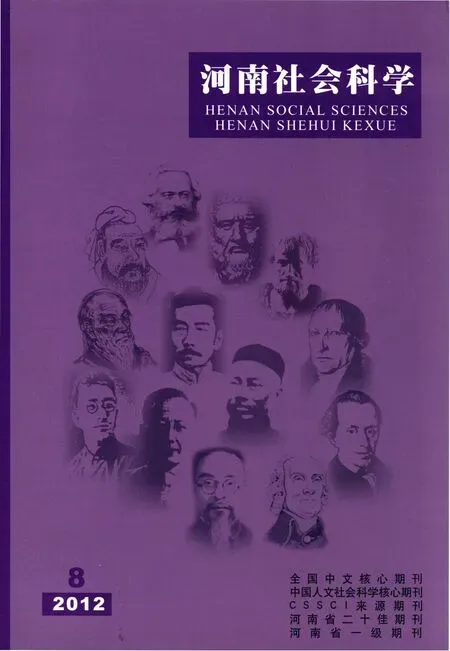新诗诗体学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兼论新诗诗体学的构建策略
2012-04-12王珂
王 珂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新诗诗体学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兼论新诗诗体学的构建策略
王 珂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一、新诗诗体学建设的历史回顾
在新诗史上,诗人的秩序与自由及文体自觉与文体创造、诗体的破坏与建设及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等矛盾尖锐,一直存在新诗是否需要诗体,特别是定型诗体的“诗体之争”,即自由诗派与格律诗派之争。“中国新诗将近80年的艺术运动,自由与格律的交替变奏已成规律之一。乱中之齐、同中之异、律中之变,既是创造者的美感要求,又是鉴赏者的习惯心理”[1]。在新诗史上,每当有人推崇“文体自由”甚至“诗体大解放”时,就有人出来反对,最有代表性的是朱经农“对抗”胡适,宗白华“修正”郭沫若。1918年6月5日朱经农于美国给胡适写信说:“……‘白话诗’应该立几条规则。……要想‘白话诗’发达,规律是不可不有的。此不特汉文为然,西文何尝不是一样?如果诗无规律,不如把诗废了,专做‘白话文’的为是。”[2]胡适毫不客气地回击他:“我们做白话诗的大宗旨,在于提倡‘诗体的解放’。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推翻;这便是‘诗体的解放’。因为如此,故我们极不赞成诗的规则。”[2]1920年2月,宗白华尖锐地指出:“沫若君说真诗好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这话自然不错。……我们对于诗,要使他的‘形’能得有图画底形式的美,使诗的‘质’(情绪思想)能成音乐式的情调。”[3]宗白华甚至在致郭沫若的信中直言:“沫若兄:……你《天狗》一首是从真感觉中发出来的,总有存在的价值,不过我觉得你的诗,意境都无可议,就是形式方面还要注意。”[4]
如果按照胡适的观点,新诗是“诗体大解放”的产物,打破了“无韵则非诗”的做诗“信条”,诗体在新诗中都不存在,研究新诗诗体的新诗诗体学也就没有了研究对象,当然没有学术价值。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诗体一直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胡适的白话诗“尝试”并非无源之水般的“弑父”式写作。他创作白话诗前,非常重视中外诗歌的诗体经验。他不仅采用外国的自由诗诗体,如英语意象派诗人的自由体诗体写作,还采用过外国的定型诗体,用英语写过十四行诗。他在1924年为侄儿胡思永的遗诗作序说:“他的诗,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之的嫡派。”[5]“有组织,有格式”正是对“诗体”的重视。胡适倡导“诗体大解放”,并没有完全摒除诗体。“用韵,他说有三种自由:(一)用现代的韵,(二)平仄互押,(三)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方法,他说需要用具体的做法”[6]。胡适的“用现代的韵”和“有韵固然好”,说明他并不极端地反对诗的韵律。
新诗革命没有真正实现“诗体大解放”,更没有革掉“诗体”的命。这一时期的“口号”与“创作”有巨大脱节。在创作界,确实出现过短暂的“诗体大解放”,如散文诗被当成了新诗的发展方向。徐志摩、穆木天等人都是通过写散文诗走上诗坛的。徐志摩早期也推崇自由诗。“他对诗歌特征的理解是‘分行的抒写’,是散文的分行抒写”[7]。因为过分强调“作诗如作文”,导致了“文”与“诗”两种文体的混乱,一些散文也被标明是“散文诗”。如俞平伯的《〈忆〉序》,刊于1923年5月15日中国新诗社编的《诗》第二卷第二号时,标明是“散文诗”。一些标明是“诗”的作品甚至与散文没有什么区别。如胡适的《一念》,发表于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全诗如下:“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儿,总不会永远团圆;/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我笑你一秒钟走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我这心头一念:/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忽在赫贞江上,忽到凯约湖边;/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遍地球三千万转!”[8]朱自清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把它作为开篇之作。当时为了强调白话诗是打破了“无韵则非诗”这一中外诗歌通行原则的“新诗”,除出现了“散文诗”的称谓外,还出现了“无韵诗”的称谓。这类形态的诗歌被称得最多的是“白话诗”,如《新青年》最早发表胡适的这类诗的是《白话诗八首》(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译介外国诗歌通常采用的是“无韵诗”或“散文诗”。如《新青年》发表泰戈尔的译诗时用的是“无韵诗”。很多刊物发表屠格涅夫、波德莱尔的译作时多标明是“散文诗”。
小诗体的流行说明当时新诗渴望建立新诗体,甚至饥不择食,一种连诗人都不承认的“诗”居然成了新诗的经典诗体,也说明新诗应该有诗体才能正常“运转”。1932年清明节,冰心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副》登出的时候,是在‘新文艺’栏内。登出的前一夜,伏园从电话内问我,‘这是什么?’我很不好意思的,说:‘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9]“我终觉得诗的形式,无论如何自由,而音韵在可能的范围内,总是应该有的。”[9]她1959年还说:“现在,我觉得,当时我之所以不肯称《繁星》、《春水》为诗的原故,因为我心里实在是有诗的标准的,我认为诗是应该有格律的——不管它是新是旧——音乐性是应该比较强的。”[10]
20世纪20年代中期出现了诗体建设的第一个高潮,1926年堪称“新诗诗体建设年”,诗体受到高度重视。朱自清1934年8月31日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写《导言》时总结了这段诗体建设历史:“闻一多氏的理论最为详明,他主张‘节的匀称’,‘句的均齐’,主张‘音尺’,重音,韵脚。他说诗该具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音乐的美指音节,绘画的美指词藻,建筑的美指章句。他们真研究,真试验;每周有诗会,或讨论,或诵读。……新诗形式运动的观念,刘半农氏早就有。他那时主张(一)‘破坏旧韵,重造新韵’,(二)‘增多诗体’。……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想创新格律的,是陆志韦氏。他的《渡河》问世在十二年七月。他相信长短句是最能表情的做诗的利器;他主张舍平仄而采抑扬,主张‘有节奏的自由诗’和‘无韵体’。……闻氏作情诗,态度也相同;他们都深受英国影响,不但在试验英国诗体,艺术上也大半模仿近代英国诗。梁实秋氏说他们要试验的是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装进外国式的诗意。这也许不是他们的本心,他们要创造中国的新诗,但不知不觉写成西洋诗了。这种情形直到现在,似乎还免不了。”[6]正是因为有很多诗人致力于诗体建设并取得了较大成绩,朱自清在总结1917—1927年新诗诗体格局时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若要强立名目,这十年来的诗坛就不妨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6]即是说在新诗草创期,就出现了自由诗派与格律诗派的对立与共存。
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现代格律诗的第二个高潮,何其芳成为领袖。1954年4月11日,何其芳认为:“我们说的现代格律诗在格律上就只有这样一点要求:按照现代的口语写得每行的顿数有规律,每顿所占时间大致相等,而且有规律地押韵。”[11]现代格律诗在当代受到了很多诗人的拥护,出现了“老去渐于诗律细”现象。1985年,邹绛结论说:“现代格律诗虽然讲究有规律的节奏,有规律的押韵……但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东西,写现代格律诗要比写旧体诗词容易得多了。有些写惯了自由体的诗人不是在有意无意间也写出了符合或基本符合现代格律诗要求的作品么?”[12]艾青主张“散文美”,是自由诗派的领军人物,在中晚年也不极端反对诗的格律。这种现象不但说明新诗诗人和古诗诗人一样,具有自觉的诗体意识,也说明新诗不是与诗体无关的抒情文体。
不可否认,自由诗在新诗史上占有主导地位,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极端的自由诗观,不但有胡适的“作诗如作文”和郭沫若的“诗是写出来的”等极端诗观,还有很多诗人提出相同观点。俞平伯在1920年12月14日说:“我对于作诗第一个信念,是‘自由’。……我最讨厌的是形式。”[13]废名于1943年在《文学集刊》第1集上发表了《新诗应该是自由诗》:“我们的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只要有诗的内容然后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不怕旁人说我们不是诗了。”[14]2009年8月,吴思敬高度肯定了废名的自由诗体观:“‘自由’二字可说是对新诗品质的最准确的概括。……而对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理解,恐怕也不宜把‘自由诗’狭隘地理解为一个专用名词,而是看成新诗应该是‘自由的诗’为妥。废名说:‘我的本意,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只要有诗的内容然后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不怕旁人说我们不是诗了。’这里所谈的与其说是一种诗体,不如说是在张扬新诗的自由的精神。”[15]
回顾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初新诗草创期历史,不难发现新诗诗体学与新诗同时诞生。尽管还没有形成系统学说,但是“诗体”、“格律”、“音乐美”、“建筑美”、“诗行”、“诗节”、“音步”等今日新诗诗体学的基本术语,已经成为人们谈论新诗的关键词,还出现了多次新诗是否需要诗体和如何建设诗体的诗体之争。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新诗史就是诗体之争的历史,也是新诗诗体的建设史,更是新诗诗体学的成长史。
二、新诗诗体学建设的现实透视
尽管闻一多、林庚、废名、何其芳、朱光潜、朱自清、艾青等人都论及诗体,特别是闻一多和何其芳堪称“新诗诗体学家”,但是他们没有出版系统的诗体学著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新诗诗体学才迎来第一个春天。当时新诗的流行带来了新诗理论的繁荣,出现了吕进的《新诗的创作与鉴赏》(1982年)、吴思敬的《诗歌基本原理》(1987年)等十余部新诗理论著作。当时自由诗流行诗坛,这些诗歌著作尽管没有提出“诗体学”概念,但是已经涉及诗体学的重要内容“诗歌类型学”,特别是吕进的《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不但对自由诗、新格律诗等多种诗体作了明确的界定,还高度肯定了诗的“音乐美”和“建筑美”,堪称新诗史上第一部未冠名的“诗体学”著作。在此基础上吕进在90年代推出了《新诗文体学》等越来越纯粹的新诗诗体学著作。
世纪之交,新诗诗体学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出版了十多部相关著作。如吕进的《中国现代诗体论》、骆寒超的《论新诗的本体规范与秩序建设》、骆寒超和陈玉兰合著的《中国诗学——第一部形式论》、许霆的《旋转飞升的陀螺——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史论》和《趋向现代的步履——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综论》、许霆与鲁德俊合著的《新格律诗研究》和《十四行体在中国》、笔者的《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造》、《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新诗诗体生成史论》和《诗体学散论——中外诗体生成流变研究》……一些新诗史和新诗论著也无法绕开“诗体”,如周晓风的《新诗的历程1919—1949》、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唐的《一叶谈诗》、蓝棣之的《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吴开晋的《新诗的裂变与聚变》、公木的《公木诗学经典》……
吕进、骆寒超等人甚至提出了“诗体重建”。1997年骆寒超在武夷山“现代汉诗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新诗诗体应该走格律化道路:“新诗体式的现代化问题也必须考虑……我们认为新诗不管怎么说总是要走律化之路的,但外在的声韵必须和内在的情韵作适度的应和,不能搞模式。具体点说,应把律化之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上:在约束中显自由,在自由中显约束。只有做这样的双向交流,才能使运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新诗求得形式的规范化定型。”[16]2009年,他与陈玉兰倡导“格律体新诗”:“在不违反已定形式规范原则的前提下,今后新诗坛要鼓励大家既采用回环节奏型形式写格律体新诗,也采用推进节奏型形式写自由体新诗。而尤其要提倡写这两大形式体系综合而成的兼容体新诗。”[17]2012年吕进还强调说:“重破轻立一直是新诗的痼疾。当下的新诗面临三个‘立’的使命:在正确处理新诗的个人性和公共性的关系上的诗歌精神重建;在规范和增多诗体上的诗体重建;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推进三大重建,新诗才能摆脱危机,重新成为中国文学的王冠。”[18]
近年越来越多的新诗理论家主张新诗应该有文体及诗体规则。谢冕2012年4月20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很多诗歌没有章法,其实诗歌是最讲规则的文体。”[19]也有人反对,叶橹甚至认为“诗体建设”是“伪话题”:“有关‘诗体建设’、‘诗体重构’的议论依然时起时伏。这些理论的提倡者虽然都是学养有素的学者,但是我却觉得他们是不是把精力浪费在一个‘伪话题’的理论上了。”[20]
从新诗史上不同时期的“诗体之争”不难看出新诗诗体建设的艰巨性。“诗体之争”不但说明诗体是新诗无法回避的话题,也说明新诗诗体具有特殊性。这些“诗体之争”消解了诗体建设的力量,也让人们意识到诗体研究在新诗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中的重要性,还意识到建立新诗诗体学的必要性。新诗史上最重要的三次“诗体之争”分别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50年代和21世纪初。第三次“诗体之争”学术性最强,参加的新诗学者最多,为新诗诗体学的全面建设打下了基础。2009年8月16日到8月19日,在武夷山召开了“21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五届研讨会暨‘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张炯在开幕词中说:“这次会议来了很多名家:既有主张格律诗的代表,也有提倡自由体的代表。……我相信,通过不同主张和观点的交锋与互补,一定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推进我们对于现代汉诗的表现技法的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也会促进我们对于发展现代汉诗的大方向的把握。”[15]会议确实取得了这样的效果。
正是诗体的多元格局和新诗理论界的学术民主带来了近年新诗诗体学研究的繁荣。这种学术民主是前所未有的。笔者是吕进的硕士和吴思敬的博士后,但是并没有因为师生关系及学派关系影响自己的诗体观。吴思敬主张自由诗,吕进主张格律诗,笔者主张建设准定型诗体,适当偏向格律诗,但是与吕进又有差异;吕进认为新诗诗体建设重点在音乐形式建设,王珂更强调视觉形式,即“诗形”建设。近年在格律诗派和自由诗派各自的内部也形成了多种派别。万龙生、王端诚、晓曲等与黄淮、周仲器、思宇等都倡导格律诗,但在这种诗的称谓、分类及写作方法上都有差异,万龙生等称为“格律体新诗”,黄淮等称为“新格律诗”、“现代格律诗”或“现代汉语格律诗”,周仲器坚持用“新格律诗”。周仲器、黄淮等主张建设相对宽松的新格律诗体,万龙生、王端诚等人主张建设严谨的格律体新诗。
近年诗体学研究尽管进展较快,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研究难度较大,需要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将诗体理论与创作实验结合,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要求较高,导致研究人员数量偏少,特别是中青年新诗学者很少有人愿意投入此项研究。研究方法单一,研究对象陈旧,多数学者受到闻一多、何其芳的格律诗理论束缚,无视新诗的书写方式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现状,导致研究出来的诗体理论无法推广应用。
近年诗体研究的最大问题是一些基本概念混乱,如最基本的概念“诗体”就有多种定义,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诗体是诗的音与形的排列组合,是诗的听觉之美和视觉之美的排列组合。诗歌文体学就是研究这个排列组合的形式规律的科学。从诗体特征讲,音乐性是诗与散文的主要分界。从诗歌发生学看,诗与音乐从来就有血缘关系”[21]。“所谓诗体,是具有稳定构造、标志诗的类别形式的特殊的符号系统。诗体的基本特征就是公用性,集中反映了诗体自身所具有的形式方面的特征”[22]。“所谓诗体,指的是诗歌的具体存在方式……这种诗体既可以说是诗歌作品的言语结构模式,但又不仅仅是所谓的‘形式’,而是还具有某种本体的意义”[23]。这些诗体定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新诗的本体,即确定了新诗诗体学基本的研究内容,但是仍然缺乏系统性、公共性和稳定性,严重影响了研究的全面深入。
近年的新诗诗体研究普遍缺乏外国和中国古代文体及诗体理论的有力支持,也缺乏从纵向上对新诗史,特别是百年诗体建设历史的全面深入考察,更缺乏从横向上对同一时段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新诗的比较研究,如两岸四地(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与海外[东南亚(以老移民为主)、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新移民为主)]的现代汉语诗歌的文体特征及诗体方式颇有差异。
三、新诗诗体学建设的未来展望
新诗诗体学必须借鉴已有的文体学及诗体学的研究成果。新诗诗体学要借鉴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文学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文化文体学、话语文体学、批评文体学和计算文体学,建设以包括新诗文类学、新诗语言学、新诗意象学、新诗生态学、新诗功能学、新诗文化学、新诗政治学、新诗传播学、新诗诗美学等为主要内容的新诗诗体学。
中外文学研究中的文体学和诗体学既古老又年轻。诗体学是文体学的组成部分,通常把研究诗歌文体的文体学称为诗体学。两者又有差异,传统意义上的文体学偏向艺术风格学,诗体学偏向艺术类型学。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类型学也包括文学分类学和文学风格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类型学偏向文学体裁学和文学形态学。现代文体学主要研究某种文体的文体特征和文体价值,特别重视文体的生存状态和外部环境,重视文本的体裁特征、本质及其规律研究,是语言学、文艺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文学类型学(文学功能学)、文学修辞学(文学技巧学)和文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是研究的重点,强调在特定语境中研究语言体式的特色。由于新文体的产生周期由过去的每50年减为每10年,文体学在当代受到高度重视。现代文体学源于19世纪俄国形式主义及布拉格学派。巴利、索绪尔、雅各布森、哈利德、苏珊·郎格、波斯彼洛夫、卡冈、巴赫金、卡勒都为文体学的发展作了贡献。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涌现出了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文学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等众多学派。80年代受巴赫金对话理论影响的话语文体学被高度重视。90年代受福柯话语理论影响,出现历史/文化文体学,认为文体学的任务是揭示和批判语言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中国很早就有文体研究,如刘勰的《文心雕龙》、许学夷的《诗源辨体》。中国当代文体学研究最早在外文系,如1978年王佐良在《英语文体学研究及其他》一文中主张文体学将语言学和文学融合。20世纪90年代文体学才受到中文系学者,特别是文学理论界的重视,北师大出版了“文体学研究丛书”,童庆炳的《文体与文体的创造》把文体分为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三个层面:体裁——语体——风格,认为文体与作家个性、时代精神、历史文化相关。2003年中山大学成立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褚斌杰、杨仲义、吴承学等学者的古代汉诗文体学成果颇丰。
传统意义上的“诗体”指诗的“体裁”、“体式”,有时也指“风格”。西方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黑格尔的《美学》,到卡冈的《艺术形态学》、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中国从《尚书》、《毛诗序》,到刘勰的《文心雕龙》、许学夷的《诗源辩体》……都有关于诗体的论述。西方诗体学偏重诗歌语言的听觉形式和视觉形式研究,如诗节、诗行、音步、抑扬格或扬抑格等,语体是诗体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诗论的诗体兼顾体裁和风格。近年,随着文体学、艺术类型学、艺术形态学等的繁荣,国外诗体研究受到重视。如英语诗歌在诗的形体和诗的音乐与具体的诗体类型,如十四行诗、具象诗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中国古诗诗体研究也较繁荣,出版了杨仲义的《汉语诗体学》等专著。新诗诗体学需要将古代汉诗与现代汉诗、外语现代诗与汉语现代诗分别视为不同语言体系和不同思维方式产生的抒情文体,意识到新诗诗体学不但必须有别于外语诗体学,也有别于古代汉诗诗体学。但是仍然需要借鉴古代汉诗诗体学和外语现代诗诗体学的研究方法,提出构建策略。
建立全面科学又富有特色的新诗诗体学,是新诗理论界的当务之急。如在讨论新诗本体时,既要重视本质主义视阈中的本体,重视这些约定俗成的诗歌观念:诗是最高的语言艺术,诗是人类语言智能的典型范例,诗通常是韵文,新诗是现代汉语诗歌,新诗是具有现代精神特别是自由精神的诗歌,新诗是打破“无韵则非诗”做诗信条的自由诗……更要重视关系主义视阈中的本体,尤其要重视新诗的形式本体——多种诗体、混合本体——多种文体、表现本体——多种技法。新诗诗体学必须研究以下基本问题:“何为新诗?”(新诗的文体特征)“何为诗体?”(一般的诗体概念、范畴及中外诗体理论的历史和评价)“何为新诗诗体?”(特殊的诗体概念、构建)“新诗如何生成?”(新诗文体生成的文学本体研究和社会文化研究)“新诗为何要以及如何建立常规诗体?”“新诗诗体为何定型难?”……
目前诗体研究存在研究方法落后、理论缺乏操作性等问题,导致诗体构建策略偏颇,如极端强调诗体的格律化或自由化,新诗诗体的理论体系更没有建立。虽然已经有了多部优秀的新诗史(论),如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等,却没有完整的新诗诗体的生成演变史(论),更没有纯粹的新诗诗体理论专著。但是涉及诗体的新诗文体的某些局部研究较有成就,如吕进的新诗文体学研究、骆寒超的古代诗体与新诗诗体建设研究、姜耕玉的新诗的语言形式研究、许霆的十四行诗和新诗诗体流变研究、台湾丁旭辉的诗的图式研究和林于弘的诗的“固定行数”研究、荷兰柯雷的新诗的音乐性研究、美国杜国清的网络诗学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已经构成了新诗诗体学的重要内容,呈现出诗体研究的光明前景。如果继续寻找新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视角,如在对已有的文体理论及诗体理论的全面梳理研究、诗体理论的基本构成研究、诗体的流变特点研究、外国现代诗歌的文体诗体特点考察、新诗诗体的全面重点研究基础上,构建当代新诗诗体理论,提出21世纪现代汉语诗歌的诗体重建策略,完全可以完成新诗诗体学的全面构建。
纵观中外诗史,特别是诗体流变史,不难发现诗体具有艺术价值和政治价值,既有艺术规范及艺术革命的潜能,也有政治律令及政治革命的潜能,是诗的文体功能及文体价值和诗人的存在意义及生存方式的显性表现。诗体研究实质上是诗的本体研究。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形式本体”、“混合本体”和“表现本体”,新诗诗体三者兼具,特别是当代及未来的新诗,是由多种诗体(定型诗体、准定型诗体和不定型诗体)共存、多种文体(散文、戏剧、小说、新闻)共建和多种技法(抒情、叙述、议论、戏剧化)共生的文体。诗体在当代社会更具有特殊价值,不仅是诗的语言体式,而且是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因此新诗诗体学不仅具有诗学的意义,还具有政治学和伦理学的价值。只有坚持新诗是现代汉语诗歌和现代意识诗歌,重视理论的前瞻性和操作性,坚持生态决定功能、功能决定诗体、诗体决定价值的方针,将诗体的基础理论研究、已有诗体的生成流变研究和优秀诗体的应用推广研究有机结合,真正实现跨学科研究,新诗诗体学才能获得更大的学术空间,成为新诗理论研究中的“显学”。
[1]杨匡汉.说诗调——诗学札记之一[A].吕进,毛翰.中国诗歌年鉴·1996年卷[C].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76.(原载《诗神》1996年9月号)
[2]耿云志.胡适论争集(上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1—34.
[3]宗白华.新诗略谈[J].少年中国,1920,1(8):61—61.
[4]宗白华,郭沫若,田汉.三叶集[A].林同华.宗白华全集(第1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227.
[5]胡明.胡适诗存[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420.
[6]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A].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影印本)[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2—8.
[7]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31.
[8]胡适.一念[J].新青年,1918,4(1):43.
[9]冰心.我的文学生活[A].卓如.冰心全集(第3卷)[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9—11.
[10]冰心.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A].卓如.冰心全集(第5卷)[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127—128.
[11]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A].何其芳.何其芳选集(第2卷)[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153.
[12]邹绛.中国现代格律诗选1919—1984[C].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29—30.
[13]俞平伯.诗底自由和普遍[J].新潮,3(1):75—79.
[14]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A].废名.论新诗及其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3.
[15]王珂,陈卫.51位理论家论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11—12.
[16]骆寒超.新诗的规范与我们的探求[A].现代汉诗百年演变课题组.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C].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259—260.
[17]骆寒超,陈玉兰.中国诗学第一部形式论[A].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730.
[18]吕进.新诗诗体的双极发展[J].西南大学学报,2012,(1):69—70.
[19]王庆环.请维护诗歌的尊严[N].文摘报,2012-05-01(6).
[20]叶橹.形式与意味[A].王珂,陈卫.51位理论家论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86—87.
[21]吕进.诗歌的外形式与诗体[A].吕进.中国现代诗体论[C].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9.
[22]吴思敬.新诗:呼唤自由的精神——对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几点思考[A].文艺研究,2011,(3).35—42.
[23]周晓风.新诗的历程——现代新诗文体流变(1919—1949)[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5—7.
2012-05-10
林于弘(1966— ),男,台湾台北人,文学博士,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现代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