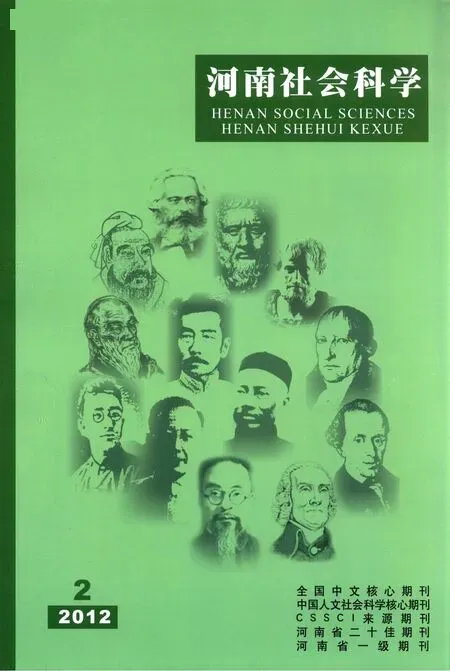祛魅时代的超越之维
——论西美尔生命哲学宗教观及其当代启示
2012-04-12王学锋
王学锋,谢 芳
(1.湖南师范大学 伦理学所,湖南 长沙 410081;2.衡阳师范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系,湖南 衡阳 421008)
祛魅时代的超越之维
——论西美尔生命哲学宗教观及其当代启示
王学锋1,谢 芳2
(1.湖南师范大学 伦理学所,湖南 长沙 410081;2.衡阳师范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系,湖南 衡阳 421008)
西美尔立足于生命哲学的视镜,对祛魅时代现代人的宗教性(超验性)生活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审视,对如何重建现代人的精神信仰世界提出了深刻的洞见。这些洞见对我国当今社会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路径的选择——从外在超验性对象的追崇到内在生命品性诉求的转向,以实现个体自由与社会共契的合致,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西美尔;生命哲学;宗教性;内在形式
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德国著名的社会文化大理论家。西美尔的社会文化理论思想博大精深,与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的思想一起构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理论的“三足鼎立”之势。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指出,整部世界近现代史实际上是一部精神上的祛魅史,而宗教就是这部祛魅史上不断被祛除着的首当其冲的“魔魅”。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降,近代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一步步地驱逐、剿杀着精神世界的“魔魅”。然而,宗教是不是真的退出了世界和个人的精神生活的舞台?西美尔立足于生命哲学的视镜,对其所处时代人的宗教生活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审视,对如何重建人的精神信仰世界提出了深刻的洞见。这些洞见对当前我国社会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实现从外在超验性对象的追崇到内在生命品性诉求的转向,以实现个体自由与社会共契的合致,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一、祛魅:宗教的现代性困境
西美尔首先从生命哲学的视角,对近代以来文化的冲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西美尔认为,文化是生命用以表现自己和认识自己的形式,如艺术、宗教、技术作品、法律作品,这些形式蕴涵生命之流并供给它以内容和形式、自由和秩序,这些形式是富有创造力的生命的框架。但由于它们的独特关系,它们并不具有生命的永不停歇的节奏,框架一旦获得自己固定的同一性、逻辑性和合法性,就不可避免地同产生自己的生命产生一定的距离。“每一种形式一经出现,就立即要求有一种超越历史阶段和摆脱生命律动的效力”①。因而每一种文化形式一经创造出来,便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成为生命力量的磨难。“生命同形式总是处于一种潜在的对抗之中”①。生命永远在同自己的形式做不懈的斗争,所以社会的文化历史过程实际就是永不停歇的生命动力不断挣脱旧形式、建立新形式的过程。西美尔把社会的发展过程视为生命形式的不断更替过程,这一思想相当深刻。
西美尔所处的现代社会的文化正在历经着一个新的斗争阶段,即现代的文化运动不是以充满生命的当代形式反对毫无生命旧形式的斗争,而是生命反对本身形式或形式原则的斗争。也就是说,现代生命正试图摆脱任何固有形式的约束,而向往着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这是一场撼天动地的形上变革,也是人性的自然倾向。当时的社会文化背后蕴藏着一股否定的力量,这股否定的力量正在积极消解各种文化形式。“文化向着生命及其表现的运动几乎蔑视一切形式的东西”②,当时的时代不承认任何传统的东西,承认任何客观的形式被认为会排除人的个性,形式会冲淡一个人的活力,将它凝固,成为僵死的模子。现在一切形式都“消融在生命之流中”,并“日益屈服于生命之流”,生命的最纯粹表现便成了形而上学价值本身,西美尔说“当生命的最纯粹的表现被认为是形而上学这一基本事实,以及被认为是全部存在的本质时,这种表现也就成了核心的观念了。这就远离了知识问题的转化:现在每一个目标都成了绝对生命的一次冲击、一种展示方式或一个发展阶段”③。针对当时社会的这种变化,西美尔敏锐地洞察到生命的意义在追寻着个体化。
与这种大的文化环境相适应,宗教作为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在经历着同样的现代性危机,宗教生命同样不需要固定地表达自己的形式,倾向于把宗教信仰的形式融入宗教生命。尽管他们的宗教冲动仍然存在,但这种原始的宗教冲动再也不能够通过信仰的主体和被信仰的客体来表现自己了,宗教将作为生命的直接表现手段而发挥作用。也就是说,现代人面临着既失去对自身理性的信仰,又失去对伟大历史人物信仰的危险,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身上还有一点真实可靠的就是对宗教的需要。但现代人越来越排斥建制性和教义的宗教,不再将注意力专注于超验的实体,而是回归于灵魂自身的内在体验。为此,西美尔揭示了现代人的困境,他们坚信经验世界和我们的皮肤一样伸手可摸,并使我们得以安身立命,对于多数人来说宗教信仰的超自然目的已根本去除了,而宗教信仰的超验性不容置疑,信仰内容又必须实实在在,甚至比经验世界还要实在。但现代人的迷蒙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知性又无法断定这些信仰内容的存在,所以他们既不会忠心耿耿地信奉某种现成的宗教,也不会声称宗教只是人类的黄粱美梦,这正是现代人的宗教困境,或者说是宗教的现代困境,传统宗教的神秘魔力在现代人这里已经荡然无存。
二、超越之维:从宗教到宗教性的转向
西美尔把生命与形式之间的冲突称为文化危机。西美尔认为在宗教与宗教性之间也存在这种危机,它实际上是文化危机在宗教上的体现。而这种危机进入现代社会,就发展为宗教的现代性危机。针对宗教的这种现代困境,西美尔却于黑暗处察觉了曙光。他认为这不是宗教魔力的消失,而是宗教合乎时宜的转向,并认为我们的责任是应该抓住契机,及时重建现代人的精神信仰世界。西美尔把此种转向称为从宗教向宗教性的转向。西美尔认为宗教的特点在于其超越之维,而不在于其外在的形式。为走出宗教的现代性困境,西美尔从生命哲学的立场出发,坚持了宗教性的取向,宗教性是西美尔生命哲学宗教观的核心。按照西美尔的观点,传统的“宗教”概念主要指宗教的客观建制与独立的教义旨趣,是一种文化形式,一套外在的表现形式,或者是死气沉沉的宗教机构,这种意义上的宗教是同个体的生命过程分开的。而西美尔强调的宗教观念主要是指宗教性,宗教性是一种永不停歇的宗教生命,一种生存品质和感情所向,一种灵魂所固有的形而上学价值所在。宗教性才是宗教的根本,宗教只是宗教性的外在表现形态,如果宗教支配了宗教性,活生生的宗教生命就会枯萎。“宗教存在乃是整个生机勃勃的生命本身的一种形式,是生命磅礴的一种形式,是生命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命运得济的一种形式”④。
基于这种认识,西美尔认为,尽管现代宗教作为生命的异化形式已经日趋弱化,遭到了生命本身的冲击,但是内在于个体生命本身的那种超越的形而上的需求却仍然是生命持续的支撑力量,或者说超越性的宗教仍存在,只是改变其存在的形式,而进入到情感领域,成为一股持久的生命之流,“作为灵魂的现实性,宗教不是已经完成的东西,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过程;——宗教的活力和核心就在于,现有宗教不断进入感情之流,情感活动又必须不停地重新塑造现有宗教”⑤。宗教越来越呈现出个性化。传统的建制宗教向个体灵魂宗教的转向,恰恰是宗教由外在形式向内在本质的回归,这一点被西美尔大加肯定。西美尔认为一旦宗教具有一种独立于思辨之外的明确意义,那么它就是我们“灵魂中的一种存在或事件,是我们天赋的一部分”,“宗教天性最初也是一种天生的规定性”⑥。而由于人是一种具有需求功能的生物,因而人内在的宗教需求总是要寻求一种对象性的满足。而对人之外的某种超验之物、神圣之物的现实性存在已经遭到了现代科学的质疑,看似信仰所追求的形而上的对象性存在已经被消解。然而西美尔认为,现代科学消解了超验之物、神圣之物的形而上存在,并不等于就消解了形而上学的存在(在这一点上,西美尔继承了康德对于人性的分析),“因为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即信仰作为灵魂中现存的事实,本身或许就是某种形而上学!”⑦信仰中洋溢着并表达着宗教存在,其意义与信仰所获得或创造的内容毫不相关。西美尔的这一发现十分重要,这对于现代人重新拯救浮躁的灵魂、挽回人的最后尊严意义重大。事实上是因为有了超验的宗教天性冲动才会有超验的信仰对象,因而人们在信仰某种形而上学的超验之在时,同时也就在实现着生命自身的形而上学之在。在人的宗教性存在之内就蕴涵着形而上学意义。在西美尔看来,灵魂和上帝是同在的,如果我们说在灵魂与超验者之间果真存在着某种宗教关系的话,那么,这种宗教的发生无论如何都发生在灵魂一边,因为“灵魂的现实性”正是这种“宗教性需求”的产生和满足。
而宗教处境的巨大困惑及其未来取决于,“普遍类型的宗教虔诚能否实现由天国实体和超验事实向生命的宗教结构和内在现实性——即个体实存的形而上学的自我意识——的转向。而且,随着这种转向,一切超验的追求和奉献、幸福和失落、正义与仁慈,不再雄踞于生命之上,而是退居生命范围之中”⑧。也就是说,宗教的最大困境并不是宗教信仰的丧失,而在于如何把对外在超验世界的信仰转化为个体生命本身的形上价值。这就意味着宗教作为灵魂存在的现实性本身就具有形而上学价值,因而要把宗教从对外在超验内容的依附中解脱出来,生命不是由宗教来完成的,而生命的完成才是宗教的实现,生命的内在品性即宗教性或超越性。这样,在西美尔这里,宗教就在生命天性中找到了根基,它在现代生存中的地位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换言之,要使信仰内容经受得住存在或不存在的猛烈追问,大概只有精神途径。因此,在西美尔看来,宗教的命运必须进行彻底的转向,只有转向才能赋予自发地进行创造并活跃在那些形态中间的灵魂的宗教存在以形而上学价值。在超验的形而上学的宗教理想遭到瓦解的背景下,现代宗教的重构需要回到个体生命的根基上,以“宗教性”为轴心,把灵魂的宗教存在作为形而上学价值,以此超越内在主体需要和外在客体对象、彼岸神圣秩序和此岸世俗秩序的二元分裂⑨。
三、复魅及其启示:从外在超验性对象向内在生命品性的转向
世界的祛魅如同韦伯所说的禁欲主义那样是那种“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祛魅总的来看是一个进步性的历史事件和发展过程,它不仅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发展起了实用理性和科学技术,使人们处于不断发展和创新不已的无限之中,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观念。但是,世界的祛魅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和危机,世界的祛魅导致信仰体系的解体,人生成为无意义的存在。价值理性日趋式微,工具理性片面发展并走向极致,人们沦为工具性的存在物(王泽应,2009)。
西美尔指出,现代宗教要再一次实现新的转型,方能重构新的宗教价值形式,以满足现代人的灵魂需要,挽救人的尊严,重建现代人的精神信仰世界。尽管现代人对各种外在的宗教极尽排斥之能事,但其灵魂深处又蕴藏着原始的宗教需求与宗教冲动。神秘主义的宗教冲动“将宗教信仰的形式融入宗教生命的模式”,在追求“宗教完美”当中,不再需要规定一个“确定形式的目标”,完全醉心和投身在直面神圣的灵魂敞开的状态。这说明,宗教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活在个体心性里,即使客观的建制性的宗教形态在现代社会消亡了,个体内在的宗教性也不会消亡,“宗教价值”也依然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在灵魂中”。宗教的重新复魅,不在于重新建制宗教体系,而在于如何真正实现由“天国实体和超验事实”向“生命的宗教结构和内在现实性”的转向,或由传统的对外在超验对象的追崇到对内在生命品性的追求的转向,使灵魂的宗教性本身成为一种形而上的价值目的,因为“宗教不是从其所指对象身上吸取其形而上学意义,它的此在本身就蕴含着形而上学意义”。唤醒对于形而上学宗教性的自觉意识和内在信仰,便是现代宗教重建的核心,在世俗性社会里,宗教生活应是一种源自生命天性的灵魂生活。
西美尔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为现代社会普遍的价值失落、人类灵魂的安顿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拯救方案,也给我国当前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提供极大启迪。人们特别是当今社会的青年人既不再崇拜任何过去被崇拜的理想之物,又苦于社会没有对社会独特价值、品性与个性的合理定位,所以各种以表现生命原始冲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现象开始在社会上泛滥,而目前越演越烈的是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社会共同价值信仰缺失。当今社会,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张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采取措施对个体的自由与社会共契的整合已经到了非做不可的地步。如何整合,以拯救个体拯救社会?我想,其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美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即改变对某种超验性对象的追求为注重个体内在品性的培养(这与我国传统儒家的内圣功夫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把个体内在灵魂的超验性需求本身作为一种终极的形而上的价值关怀,体现出一种对生命本身的尊重。我想只有这样,现代的个体灵魂深处的宗教性或者超验性需求方能在生命天性的土壤中找到坚实的根基,飘逸的灵魂才能得到安顿。为此,要改变当今社会物欲横流、社会个体迷茫空虚的现状,首先应该唤醒社会个体对于形而上超验性(宗教性)的自觉意识和内在信仰。从这个角度上说,加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研究与宣传,可能也是现代社会思想道德文化重构之关键所在。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西美尔著,曹卫东等译:《现代人与宗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4、36—37、52、20、48、50、57页。
⑨田薇:《西美尔关于现代宗教形而上学重建的构想》,载《现代哲学》,2011年第3期,第62—66页。
D9
A
1007-905X(2012)02-0048-03
2011-11-10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B18)
1.王学锋(1971— ),男,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学,中外伦理思想史;2.谢芳(1972— ),女,湖南衡阳人,衡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学、伦理学。
责任编辑 姚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