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万丈的日治时期台湾新美术运动
2012-04-09吴垠慧
吴垠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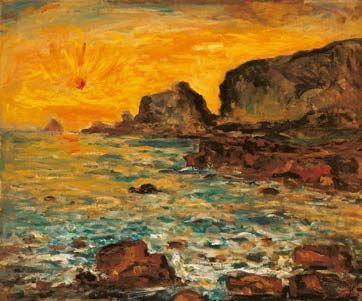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满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最后双方以签署“马关条约”收场,这项条约牵动台湾岛的命运。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和澎湖群岛,台湾自此陷入长达五十九年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也种下台湾社会对于日本、中国之间族群与文化认同的复杂情结:台湾因成为日本殖民属国而加速现代化建设,但却摆脱不了身为殖民地的二等国民身分。
回顾二十世纪台湾美术的发展,我们发现台湾美术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时期是在日治时期奠定的。日本殖民引进先进的教育体制,让台湾人首次接触到油彩、石膏与青铜等西方艺术的素材,并接受西式美术教育训练。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从材料到观念方面完完全全翻天覆地之举,堪称是台湾美术史上的首发革命。本文将以日治时期台湾政经文化背景为经,透过这时期代表性艺术家的生平及其创作为纬,勾勒出日治时期台湾新美术运动的粗浅面貌。
一、明清时期台湾美术的概况
在正式进入日治时期台湾新美术运动的篇章之前,先了解日治时期之前、也就是明清时期台湾美术环境的概况。一六八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郑成功之孙郑克爽在清臣施琅率领大军围攻下投降,台湾进入满清统治范围。明清时期的台湾移民多来自闽粤,因而文化传承也以闽粤母体文化为主要认同对象,以汉人为核心的美术系统可从文人书画、民间工艺和建筑一窥端倪。
这时期台湾的美术承袭“浙派”和“闽习”的绘画风格。风行于明初的“浙派”绘画讲究蕴含生命力劲的速度之美,虽然后来为“吴派”取代,但其风格强烈,影响邻近福建地区画家而形成“闽习”之风,“扬州八怪”的黄慎为其代表。
无论是“浙派”或“闽习”,都是一种展现霸气、不含蓄,浓浊又不清雅的画面气氛,舞墨挥洒之间强调的是个性的表现和意趣的传达,相对于追求淡雅、意境清高的文人书画,经常被批评是“品恶”之作。然而这种夸张且具生命力表现的“狂野”风格,却深受台湾这种开拓性、移民社会的喜爱,代表书画家有林朝英、庄敬夫、林觉和谢彬等人,他们都是台湾土生土长的书画家,也是清代台湾画坛的主干。
此外,大陆来台客寓的文人书画家,如谢管樵、吕世宜等人受到台湾豪门仕绅的礼遇以及社会民众的尊重,在台湾也同样具有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由此可知,截至清末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前,台湾美术展现的样貌,一方面与中国大陆维系着脐带相连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又拥有移民社会特有的区域性审美品味。
二、迈向近代化社会发展的日治初期
日本统治台湾期间为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共计五十年。日本倾全力开发台湾,以科学实用的调查工作为前导,兴建交通、水利、电力、港口等建设,加速都市化的脚步,成功将台湾经济带向资本主义化。另一方面,又从日语教育入手,将台湾带入日本文化圈。一九一〇年代末期,台湾的政经、社会与文化都已进入新的局面。
日治初期,中国水墨书画还受到相当大的尊重和鼓励。治台初始,日人恩威并济,刻意笼络前朝遗老、士大夫,制定“绅章制度”,颁发“绅章”给地方耆老,又举办“扬文会”,汇集前清进士、举人和秀才,征求他们怀抱理想的文章,作为治台资料。在此氛围下,诗文吟诵、书画观摩都受到相当程度的鼓舞。
日治初期台湾著名书画家有吕璧松、潘春源、陈玉峰、李霞等人,尤以吕氏最受尊崇,存世作品颇多,山水、花鸟、人物均有专精。不过,文人书画在一九二七年、第一届“台湾美术展览会”开办后,送展画家的作品在遭受落选命运之后,中国水墨创作者才警觉到情况的严重性。
三、新美术运动萌芽:台北国语学校与石川钦一郎
日治时期台湾美术现代化过程,被称为“台湾新美术运动”,主要透过日籍美术教师的传授和几位日籍艺术家在台落地生根的影响,一面实施西式的美术教育,同时胶彩画(或被称为“东洋画”)与西洋油画的引进,使台湾美术出现了天攘之别的面貌。
提到日人在台推广美术教育,就不能不提“台北国语学校”。该校成立的目的是培育台籍教师,而这也是台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开端。一九一九年改制为“台北师范学校”,一九二七年因学生人数增加,分设台北第一师范与第二师范,前者招收日籍学生,后者全是台籍学生,日籍艺术家石川钦一郎就在第二师范授课。在他指导之下,该校出现许多优秀的台湾艺术家,如第一位水彩画家倪蒋怀、陈澄波、李梅树、廖继春、陈植棋、李泽藩、李石樵等人,都是“北师”毕业,成为名符其实的台湾新美术运动摇篮。
若说推动台湾新美术运动摇篮之手,当属石川钦一郎。石川钦一郎一八七一年生于日本静冈,一八八九年英国水彩画家阿尔富瑞.伊斯特到日本时,石川曾陪伴日本留欧画家川村清雄,担任伊斯特的翻译兼导游,到日本各地写生,种下他日后学习英国水彩的因缘。
一九〇〇年,石川担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翻译官,前往中国天津、辽宁等地,因工作之便到处旅行写生。一九〇七年首度来台,九年之间担任台湾总督府陆军翻译官兼台北国语学校美术教师,与日后投身推动台湾美术运动的倪蒋怀等人有了初步接触。
一九二四年,石川再度来台,直到一九三二年返日的八年期间,他积极推动台湾美术现代化,被封为“台湾新美术运动导师”。石川对待学生有如家人,除了课内指导,一九二四年还组织“学生写生会”、“台湾水彩画会”等,台湾青年在石川带领下,背着画具走向户外,透过“写生”感受自己的乡土。石川本人优雅、和善又专精的形象,不仅成为台湾青年学子的人格典范,也开启青年人对于乡土和艺术的热爱。
石川教授给台湾学生的是带有印象派(外光派)思想的英国水彩技法,水彩是当时台湾社会较能接受的媒材,便于携带又便宜,适合推广。石川本人的画作淡雅又富于诗情,曾在报纸上连载,也受到台湾人喜爱,成为见证当时台湾风情的重要史料,更开启台湾美术史上乡土写实的先锋。
此外,石川和同样在台任教的日籍教师暨油画家盐月桃甫、东洋画家乡原古统与木下静涯等人,一同催生“台湾美术展览会”(简称“台展”)成立,他们向总督府提议成立台湾全岛性美术展览会,提升台湾文化水平,并提供台湾画家更多发表空间,立刻获得总督府的正面响应。
一九二七年十月廿二日第一届“台展”登场,展出一百廿八件作品,东洋画四十件、油画八十八件,是台湾有史以来动员人力最多、规模最大、吸引最多人参与的大型展览。由此可见,石川不仅为台湾美术埋下种子,更协助其發芽成长。
四、风起云涌的台湾新美术运动
日人在台湾实施新式教育的成果,大约在一九二〇年代开始产生作用。出生在一八九五年前后的台湾人,在二十多年后的台湾文化界,展现出不同于旧式文人的样貌,而在美术界,开始有西洋画家和雕塑家出现,且具成就,如获得日本“帝国美术展览会”(简称“帝展”)的第一位台湾雕塑家黄土水、第一位油画家陈澄波,他们的获奖对于台湾美术界来说,都是莫大的鼓舞与标竿。巧的是,这两位艺术家同样生于一八九五年——台湾命运转折的那个关键年;两黄人入选帝展的作品均反映台湾地域性的风土特色,影响当时台湾艺术创作的美学倾向。
1.黄土水:台湾第一位西洋雕塑家
黄土水生于台北艋舺(今“万华”),父亲是木匠,十二岁时父亲过世。一九一一年,黄土水考上台北国语学校。家学加上生长在寺庙多、民间雕刻师多的艋舺、大稻埕周围,耳濡目染之下,黄土水求学期间在图画科、木工科方面的表现相当优异。
经由总督府民政长官等领导高层推荐,黄土水前往日本东京美术学校雕刻科木雕部深造,一九二〇年毕业后直升“实技研究生”。同年,他以台湾原住民孩童吹鼻笛的模样雕刻出《蕃童》一作,入选第二届日本帝展,这是台湾人第一次以文化成就获得日本最高权威机构的肯定,引起台湾社会和媒体极大的关注。
一九二一年,黄土水再以《甘露水》二度入选帝展,这件雕塑被视为台湾新美术运动标竿的经典之作。《甘露水》以西方古典写实主义手法,刻划一位脸庞微微上扬、双腿前后交叉直立,双手向下自然张开的全裸少女,站在贝壳状的半圆弧底座上。从贝壳中生长出来的女子,令人联想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波提伽利的举世名作《维纳斯的诞生》。
目前没有确实数据显示黄土水是否见过这幅名画,不过《甘露水》原本意指台湾信仰中观音大士手持圣水,滋润荒芜大地与人心;黄土水雕刻的女体不若西方人修长的身形,而是东方稍显圆短的身材。虽然采取西方雕塑的原理,但黄土水开拓并掌握了含蓄内敛的东方美感特质。
一九二七年应艋舺龙山寺所托制作《释迦立像》也是融贯东西文化的范例。黄土水取材宋代画家梁楷《释迦出山图》的释迦形象,为了把这位面壁九年仍无法获得真理,决定以出山行动实践而追求真理的道人艰辛形象呈现出来,黄土水放弃石膏翻模,改以质地坚硬的台湾榉木为雕刻素材。
一九二八年,黄土水投入巨型浮雕《水牛群像》创作,长五百五十五公分、宽二百五十公分的巨作,现藏于台北中山堂,刻划五条水牛与三位牧童在芭蕉树园放牧的闲适情景。这件作品是黄土水毕生创作尺幅最大之作,一九三〇年完成,然他也因过度操劳、盲肠炎引发腹膜炎去世,享年卅五。
2.陈澄波:台湾第一位西洋油画家
陈澄波出生嘉义,父亲是前清秀才,幼年即展露对绘画的兴趣,一生最崇拜的艺术家就是梵谷。就读台北国语学校时受到石川钦一郎启蒙,立志成为一名画家,三十岁赴日考取东京美术学校。一九二六年,陈澄波以油画《嘉义街外》入选第七届帝展,是第一位入选的台湾画家,同样引起媒体大篇幅报导。
翌年,陈澄波再以描绘故乡嘉义中央广场的《夏日街头》入选帝展,这件作品他已掌握了南台湾夏日午后明亮、炽热的黄土温度,奠定日后绘画的主要特质。
一九二九年,陈澄波赴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昌明艺术专科学校任教,那年他的画作《清流》代表中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旅沪期间,陈澄波接触中国传统水墨,他将这番体悟融会在油画当中,他的色彩趋向单纯,笔法富于毛笔的柔软趣味,空间处理也呈现水墨高远式构图,他曾表达要从倪云林和八大山人的作品学习线描和擦笔的技法,他说:“我们是东洋人,不要生吞活剥地接受西洋人的画风。”
一九三三年,中日战争如火如荼,台籍的陈澄波因曾留学日本的背景,在抗战期间显得危险,因而返台。一九四五年二战终了,台湾回归“祖国”,能说北京话的陈澄波担任嘉义市第一任参议会议员,从艺术界跨入政界,却在一九四七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中,被国民党军队处决丧命,享年五十二。
陈澄波死后,他的事迹和画作成了禁忌,一九八九年台湾政治解严后才得以平反。二〇〇二年,陈澄波的《嘉义公园》在香港拍卖会上以五百七十九万港元高价成交,创下当时华人前辈艺术家第二高价纪录,仅次于徐悲鸿的《风尘三侠》。二〇〇六年,香港苏富比上拍陈澄波的《淡水》,以三千四百八十四万港元成交,来年《淡水夕照》拍出五千七十二万余港元,再度刷新台湾画家的拍卖纪录,台湾收藏界掀起一股“陈澄波热”。
3.胶彩画取代传统水墨:台展三少年
除了西洋油画、雕塑,充满日本风味的胶彩画也被引入台湾,日治时期称之为“东洋画”。一九二七年第一届台展,“东洋画”一词首度出现,取其和西洋画相对之意,涵盖水墨画、胶彩画等媒材。然而,在乡原古统、木下静涯等日籍艺术家的主导下,胶彩画成了东洋画部的主流。
这两位日籍艺术家因个人品味,形塑了“台展型东洋画”风格,是一种强调观察精确、描绘细腻、笔法繁复、构图严谨,以线描、填彩为主要手法的重彩类型。第一届台展入选的廿五名画家当中,汉人传统书画家几乎全军覆没,年仅十九、二十岁的林玉山、陈进、郭雪湖三人入选,被称为“台展三少年”,这三人日后创作均以胶彩画见长。
林玉山自小接触中国水墨,父亲是民间画师兼裱画师傅,对于传统文人绘画内涵有深层体认。一九二六年受到陈澄波的鼓励,赴日进入东京川端画学校学习西洋画。来年以《大南门》、《水牛》两件写生作品入选台展,声名大噪。林玉山的代表作《莲池》,就是工笔重彩、秾丽缜密的“台展型东洋画”,画面上盛开的荷花和丰满大张的荷叶,泥金淡扫的绢地,在石青、石绿和紫红的花叶对比下,悠闲觅食的白鹭鸶彷如孤高隐士,华丽中不失文雅,单纯中又洋溢着丰美,是台湾胶彩画的经典之作。
幼年也曾追随传统水墨画家习画的郭雪湖,是以水墨画作《松壑飞泉》入选台展,这次台展让他有机会看到日籍评审的东洋画作,那种重写生、讲细节的作风成为他第二届获选特奖的胶彩画《圆山附近》之参考原点。郭雪湖的胶彩可说是自学而成,具有素人倾向,巨细靡遗又讲究细节,画面具有强烈装饰性的特质,一九三〇年他另一代表作《南街殷赈》,描绘台北迪化街热闹景象,参照中国水墨立轴的形式、又敷以日本胶彩,堪称完美的融合。
“三少年”中唯一女性画家陈进,也是日治时期女子学画第一人,被誉为“闺秀画家的代表人物”。陈进出身新竹仕绅世家,在当时能接受高等教育实属不易。一九二五年考入东京女子美术学校,学习胶彩画技艺,毕业后再入美人画大师镝木清方弟子伊东深水及山川秀峰门下,专功风俗美人画。
陈进的胶彩画受到日本风尚影响,当时台湾富贵人家闺阁少女的装扮与生活,如《野分》、《伤春》画的都是身穿和服的女性。一九三二年,二十六岁的陈进首度受邀担任台展评审,为破天荒之举。由于作品不再需要接受他人评审,陈进的创作开始脱离日本美人画的规范,展露出她的母体文化意识,如《芝兰之香》描绘穿着汉人传统结婚礼服的女子,头戴凤冠坐在黑底镶花的中国传统木椅上;《含笑花》则是一位穿着旗袍的妇女带着幼女在花园,这幅画开启陈进一系列以家居妇女小孩生活(多数是以自家姊妹为模特儿)为描绘场景的作品,如《手风琴》、《合奏》、《悠闲》等代表作,笔法细腻、设色雅致,她笔下温柔典雅、诗意幽淡的女性形象深植人心。
五、台展之外:画会带动新美术运动的蓬勃
一九一〇年代晚期,受到近代化教育洗礼的新生代知识分子,带动台湾文化近代化的转型,留学东京的台湾学生扮演重要角色。受到日本“大正民主潮”、中国辛亥革命及朝鲜独立运动的激励,台湾留学生产生自觉,一九二〇年成立民族运动团体“新民会”和“青年会”,鼓吹民族意识。同时,台湾岛内透过日文网络接触国际新思潮,地方仕绅、知识分子在林献堂、蒋渭水的带领下,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含有强烈的抗日政治及社会运动意识。
“台湾文化协会”影响力扩大至各阶层,台湾新美术运动也蔚为成风,画会团体也纷纷成立,一开始发起和主导人都是日籍艺术家与教师,直到一九二〇年代末期才出现台湾艺术家自发组成的团体。
日治期间,台展是提供台湾艺术家“出道”的一条快捷方式,此外就是艺术家个人的展览活动。一九二四年开始,由新一代组成的画会团体,也成为艺术家在大型展览之外,彼此联谊、研习和推动社会教育的重要舞台,也构成台湾新美术运动的重要网络。
明清时期台湾社会便存在文人组成的诗会、吟社,但绘画团体却赴之阙如。日人来台后,基于异乡的孤寂心情以及联系情感,开始在地方组织以书画为研究目的的团体,其中不少是东洋画组织,如“日本画协会”、“黑壶会”等,当时还未有台籍人士、尤其是年轻人参与。
一九二四年,石川钦一郎二度来台,为推动美术教育成立“学生写生会”,成员多半是北师在学生和毕业校友,部分是校外有志之士。为了更有效激发学生研习的风气,在石川主导下,出现台湾新美术运动第一个绘画团体“台湾水彩画会”,有北师校友倪蒋怀、李泽藩、叶火城、李石樵,以及校外的张万传、陈德旺、洪瑞麟、蓝荫鼎等人。
一九二七年,第一个以年轻艺术家为主、在台北自发性组成的“七星画坛”出现,成员有倪蒋怀、陈澄波、陈植棋、陈英声、陈承藩、陈银用、蓝荫鼎等七人,取台北近郊七星山之名,七星又是北斗,位于群星枢纽的地位,成员以此自我期许,每年固定展出,持续三年直到一九二八年结束。
七星画坛成立同一年,陈澄波、颜水龙和廖继春等三位出身台湾中南部的艺术家,也在南部组织“赤阳社”。七星和赤阳两个画会一九二八年在东京合并为“赤岛社”,意指在“阳光照耀下的宝岛”的台湾美术留学生团体。然而,随着一九三一年热衷画会活动的成员陈植棋病逝,赤岛社为之沉寂。一九三四年改组成“台阳美术协会”,发起人有陈澄波、颜水龙、廖继春、杨三郎、陈清汾、李梅树、李石樵和日籍艺术家立石铁臣等八人,目的是在每年秋天台展之外,另在春天举办一场展览,增加画家发表的机会,同时培养新秀,是为“台阳美展”。这是台湾第一个足以和官展媲美的民间策划展,台阳美术协会从当时运作至今已有八十年,是台湾历史最久的画会。
六、回归“祖国”:日治时期的台湾艺术家认同倾向
启蒙于日籍教师,台湾艺术家多数选择去日本修艺深造,除了极少数几位有机会游历巴黎之外,包括陈澄波、郭柏川、王悦之、杨三郎、郭雪湖等人,都曾以“回归祖国”的心情前往中国大陆发展,从事教学、游艺甚至定居。这也反映出日治时期台湾艺术家身处中、台、日之间,彷如夹心饼干的矛盾心情,也产生文化、自我认同上复杂且纠结的情绪。陈澄波之外,王悦之、郭柏川二人是代表人物。
王悦之本名刘锦堂,生于台中,家中经营米店。一九一五年进入东京美术学校习艺,一九二〇年东美还没毕业,首次到中国大陆,先到上海、后到北京,受到国民革命热潮所激动,结识国民党中委王法勤,被收为义子,改名王悦之。一九二一年东美毕业,以侨生身分进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学习,并任职于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教授。
一九二八年王悦之受聘国立西湖艺术院,担任西画系主任,来年回北京,一九三〇年创办私立北平美术学院出任院长,一九三七年过世,享年四十三。王悦之一九二〇年代初的《摇椅》、《镜台》等油画仍保留古典主义手法,同色系中丰富的层次变化予人水墨的联想,二〇年代末期的自画像《芭蕉图》则采水墨画立轴形式,描绘自己端坐在芭蕉树下修行静坐的景象。一九三四年的《弃民图》为其代表作,表达他对抗日期间“东北事件”的关怀。画作描绘一名老者拄着拐杖,双臂各挂有盛装食物的竹篮,画幅上方以毛笔写下“弃民图”三个字,如同水墨画的题跋,直指东北弃民,也暗喻故乡台湾。
另一幅《台湾遗民图》采用佛画西方三圣的形式,油画绘于细致绢布上,三位穿着几何纹饰旗袍的赤足女子,两侧女子双手合十,中央女子一手捧着地球模型,另一手下垂,手心向外,绘有一只眼睛。画作上方钤以“台湾遗民”四字之方形印章,颇富宗教象征意涵,王悦之将对台湾的祝福化为宗教性的冥想。综观王悦之毕生创作,已显露出他思考如何将东西绘画特质融为一炉,徐悲鸿学生、评论家安敦礼形容他是“中国西画民族化的第一人”。
郭柏川也致力将中国传统媒材与西画结合。郭柏川出生台南,一九三三年自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毕业,一九三七年前往中国东北,一年后到北京开启创作生涯,并获得北平国立艺专(今中央美术学院)教职,生活安定,与黄宾虹等人熟识。一九四二年应聘私立京华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任训导主任,期间,日本画家梅原龙三郎数次到北京写生,均由郭柏川担任翻译与向导。梅原画紫禁城的红墙黄瓦,追求西方油彩的东方色调,尝试油渍晕染宣纸的效果,画出西洋画的东方风格,这对郭柏川有深远的启发。
一九四三年,郭柏川开始尝试纸上油画,试图在宣纸上做出具有中国透明色彩特质的油画效果,从中国北方建筑的彩绘获取灵感,也从宋代的陶釉吸取技巧与效果,强调线性笔触的同时,提炼出中国文人式的油画创作,代表作如《北京故宫》等。
一九四八年郭柏川举家从天津搭船回到台湾,一九五〇年应聘台南工学院(今成功大学)建筑系教授。一九五二年他组织“台南美术研究会”(简称“南美会”),举办“南美展”,发挥在南台湾画坛的影响力。
小结
综观台湾美术史犹如一部台湾政权交替史,随着外来政权产生艺术的变种。日治时期,日人透过近代化教育培养出台籍菁英,就读台北国语学校的学生,多数是家境贫苦、但资质优异的年轻学子,透过近代化知识教育过程和稳定的教职工作,宣扬日本殖民母国的深厚文化。在这场由日本人启发的台湾新美术运动当中,充分反映出殖民母国与殖民地子民之间的微妙情结。
相较于同时期的台湾文学带有强烈抗日、宣扬民族意识的氛围,台湾新美术的培植主要操之在殖民政权手上,如帝展、台展,其品味也受到日人的左右,由于美展的规定是日人所制定,台湾艺术家只能被动配合,迎合殖民母国的风格喜好,也因此,即使日治时期台湾新美术运动风起云涌,相较于台湾文学,对于殖民政权的杀伤力也没有那么强烈。即使如此,台湾新美术运动让台湾人首次接触、见识西方艺术的内涵,透过留学方式打开台湾人的视野,让台湾逐步和国际艺术思潮接轨;此外,这一代台湾艺术家也藉由画笔记录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以及形色人物,展现艺术的社会关怀,这样的行动与创作自由,在国民党政府来台之后,曾因政治箝制一度被打压,直到一九七〇年代“乡土运动”崛起,才又有台湾艺术家背着画具走入乡间,描绘工业化底下没落颓圮的农村风景,但这已是怀旧情绪胜于社会写实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