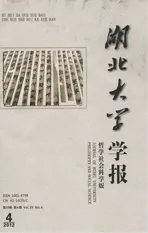中共“二大”历史疑点考证述析
2012-04-09王志明
王志明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上海200041)
中共“二大”历史疑点考证述析
王志明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上海200041)
中共“二大”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但由于历史原因,留下了一些历史疑点:(一)会期问题。基本上存在三种说法:一是大多数人认为的1922年7月份,二是毛泽东回忆的同年冬天,还有一说即是瞿秋白所说的同年5月。根据原始档案和多数当事人的回忆,可以确定为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二)会址问题。根据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的调查研究以及李达、王会悟夫妇等人的回忆,第一天的大会是在上海市南成都路辅德里六二五号(今“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举行的;(三)与会代表问题。根据现有资料,与会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1人,此外,张太雷、陈望道、高君宇、项英、邓恩铭、邓中夏、向警予等7人完全有可能参加了一次或几次党的“二大”的全体会议或小组会议。与会代表的最终确认有待进一步研究。
中共“二大”;历史地位;会期;会址;与会代表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与中共“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中共“二大”的原始资料至今存留不多,加之年代久远,当事人的回忆相互或前后不尽一致,这给党史研究留下来了不少难解之迷。
一、会期问题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或者回忆录中查寻,关于中共“二大”召开时间的会议材料并不多。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1922年7月16日—23日,这一时间的确定几经考证。
1921年11月,中央局向各地党组织发布了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签署的《中央局通告》,《通告》宣布“明年七月召开大会”。这里就明确提出1922年7月召开中共“二大”的设想。从“二大”的几位当事人的回忆中,我们也可以对中共“二大”召开的时间有个大致的把握。毛泽东虽然没有能够参加会议,但在他的记忆中谈及“二大”是1922年的冬天召开的。与会者张国焘回忆说:“中共第二次大会终于七月十日左右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央所租的房子里正式开幕了。”[1]235李达回忆中谈到:“党就在七月间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2]17蔡和森撰文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22年7月”[3]479召开的。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写到中共“二大”是在1922年5月召开的。
共产国际相关代表也对中共“二大”召开的时间做了记载,米夫1936年撰写的《英勇奋斗十五年》记录“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于一九二二年七月”[3]419。葛萨廖夫1926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初期革命活动》认为,“远东会议开过不久,一九二二年六月(也许是七月)里,(中国共产党)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3]466。C.A达林的《中国回忆录(1921—1927)》也记载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举行。
从上述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共“二大”召开于1922年,没有异议。问题的焦点在于具体的时间段。基本上存在三种说法:一是大多数人认为的7月份,二是毛泽东回忆的冬天,还有一说即是瞿秋白所说的5月。《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是瞿秋白1929—1930年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发表的报告。他所依据的材料是莫斯科档案馆保存的俄文版的“二大”文件。这个文件在1926年5月1日印刷时,不知何故,对《二大宣言》发表的时间1922年7月,特意做了声明更正:“本是1922年5月,误排7月。”瞿很有可能就是根据这个“更正”,将“二大”召开的时间定为5月。
中共“二大”召开时间的原始根据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22年7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的文件,从这些原始的档案资料中,我们可以找到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其中的最后一条——第六章第二十九条明白无误写着“本章程由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二十三日)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4]64。这是关于党的“二大”召开日期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从这里,我们可以确定党的“二大”应该是1922年7月16日—23日召开的。这一结论与当事者的回忆基本上是一致的。
二、会址问题
关于党的“二大”的开会地点。张国焘的回忆中提及是“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央所租的房子里”召开的。1951年,胡乔木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所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提到,“1922年5月,党在杭州西湖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会”[5]8。当时,胡乔木可能是把党的“二大”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西湖会议)误以为是党的“二大”了。这一说法引来了李达所说的“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地点问题。我曾经对胡乔木同志说过,开会的地点是在上海,不是在西湖”,“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十五、六人)一共开了三天大会,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附近的几个地方举行的。第一天的大会是在南成都路辅德里六二五号举行的,第二、第三两天的大会是分别在一个地方举行的,里街和门牌号码我不记得了,但都在英租界,这是千真万确的”[3]582。
1954年2月,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的同志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开始对党的“二大”会址进行寻找和踏勘。他们根据李达、王会悟夫妇的回忆,找到了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并进行了调查了解。他们访问了辅德里的老居民,去上海市档案馆查阅工部局历史档案,核对门牌号码今昔变更情况。上海档案馆保存的公共租界工部局英文档案表明:辅德里南成都路625号,属联排式石库门旧式里弄建筑。
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的同志把老成都北路辅德里7弄30号和7弄42号的房子拍了照片,寄给了李达、王会悟夫妇,请他们帮助辨认。1958年12月6日,李达给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的同志回信,确认“辅德里30号(旧625号),和42、44号(旧632号A)正是当年我的寓所和平民女校校址。……30号楼下是客堂,有方桌一张和四个椅子,几个凳子。楼上是我的卧房兼书房”。并且李达还详细回忆了当年室内的家具摆放情况。
王会悟看了照片“感到非常亲切”,“引起了许多宝贵的回忆”。她也确认“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是当年李达的寓所,正是中共“二大”会址和第一个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为了说明情况,她还专门“请人描了两张草图,并画了湖南篾篓子、自转椅、书架、床铺等图样,随信附上”①参见王会悟1958年12月11日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的信;1960年2月5日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的信。。
不久以后,李达来到上海,亲自前往老成都北路辅德里7弄30号和7弄42号勘认,确认无误。以后,当年曾在平民女校读书的钱希钧(毛泽民的夫人),她到上海时也前往勘认,并且做了回忆。
1959年5月26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把中共“二大”会址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77年12月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重新予以公布。2002年6月30日,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含平民女校陈列)建成并于次日正式对外开放。
三、与会代表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记载,参加党的“二大”的有中央局的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广州(广东)代表谭平山、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施存统等11人,尚有一人无法确定。这个代表的名单源于《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1922年12月9日)和中共“六大”《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3]16~21。《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6]57是1922年12月9日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记载,1922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七个地区(上海、北京、山东、湖北、湖南、广州)七个代表,每个地区各一人”[2]128。《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是1928年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整理出的一份关于“一大”至“五大”的代表名单。根据这份名单的记载,出席党的“二大”的代表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共12人。”这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时间最接近于党的“二大”,了解有关党的“二大”代表情况的两份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资料,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确定参加党的“二大”代表的原始依据。
看了这两份材料,我们产生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说党的“二大”的代表来自7个地区的7名代表,但是文中只列出了6个地区,这第7个是哪个地区?代表是谁?二是《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中,“二大”代表有毛泽东,毛泽东究竟是否参加党的“二大”?三是党的“二大”有没有列席代表?
目前,关于参加“二大”代表的名单,基本上是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而定的。关于中央局的代表如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地区的代表如王尽美、蔡和森,青年团的代表施存统等6人,已经是没有什么争议了。问题在于7个地区的代表究竟是谁?张太雷、陈望道、高君宇、项英、邓恩铭、邓中夏、向警予是否参加了“二大”?党史界尚有不同意见。
从理论上分析,参加“二大”的各地代表,除了另有原因,应该是各地党组织的负责人。虽然李达说,“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指定从莫斯科(参加远东会议后)回国的是那省的人就作为那省的代表”[7]17。这与各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并不矛盾。因为1921年11月中央局已通知各地党组织,明年7月召开党的“二大”,各地党组织都应该有所准备的。
当时,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是张太雷或陈望道,不是杨明斋。1921年底,上海党组织根据中央局通告的要求,建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由陈望道任书记;1922年6月,陈望道辞职,由张太雷任负责人[8]。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党的“二大”,会议应该由上海党组织负责人张太雷参加,张太雷不能参加的话才会委托陈望道或其他人参加。目前为止,没有找到张太雷或陈望道因故不能参加会议而委托他人参加的资料。反而是张国焘回忆说,参加会议的有张太雷。
高君宇是北京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参加“二大”的可能性比罗章龙的更大些。因为高君宇参加了远东会议,符合李达所说参加“二大”的“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指定从莫斯科(参加远东会议后)回国的是那省的人就作为那省的代表。”同时,根据高君宇在“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情况,他是应该参加“二大”的。而罗章龙在1981年回忆说,自己曾经参加党的“二大”。但是,有关文献和他较早期的回忆《椿园载记》里,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记载的只是他当时正忙于领导安源工人罢工。
湖北党组织的负责人是包惠僧。对于自己为什么没有参加会议的原因,在他的《包惠僧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他说:“我本人极力反对张国焘在党内进行‘小组织’活动,与张国焘的摩擦很厉害。‘二大’召开以前,中央局署名‘钟英’(中央局当时的化名)写信给我说,‘武汉工作重要,叫我不要离开,出席代表可另派一位同志。’我接到信以后,联想到张国焘的‘小组织’会在‘二大’上‘捣鬼’,于是决定:‘我不能争着要去出席,我也不能让张国焘小组织分子去出席。’我就提了项英,多数同志同意,其实,项英此时入党还不到一年。”[9]10~11言之凿凿,是项英参加“二大”的有力佐证。
山东党组织负责人是王尽美,关于王尽美参加了党的“二大”基本上没有异议。问题是,参加了会议的是王尽美和邓恩铭两人,还是仅为王尽美一人?王、邓两人都参加了远东会议,两人都参加也不是没有可能。
广州党组织的负责人是谭平山,目前,没有资料表明谭平山没有出席会议。
湖南党组织的负责人是毛泽东。《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关于“二大”代表名单中有毛泽东。作为湖南党组织的书记,毛泽东是完全有资格作为代表参加会议的,而且毛泽东也是准备参加党的“二大”的。问题是,毛泽东自己说,没有参加“二大”。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明确说,“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冬天(引者注:应该是7月、夏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10]118。李达在1955年8月的回忆中也确定“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2]17。
邓中夏时为中国劳动书记部主任,李达在回忆中也提到:参加“二大”的“有邓中夏”。因此,他作为中国劳动书记部代表的可能性比李震瀛更大。1922年12月9日《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报告中提及来自七个地区(上海、北京、山东、湖北、湖南、广州)的七个代表。那么,除了上述6个地区以外,第7个地区是什么地方,谁是代表?根据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这第7个地区应该是郑州。因为除上述地区外,当时党员人数最多的是郑州,有党员8人。于1922年4月成立的中共郑州支部的书记李震灜应该是代表郑州参加“二大”的代表。
党的“二大”有没有列席代表?张太雷和向警予是不是代表或列席代表?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为什么会记得张太雷和向警予是列席代表?李达在回忆中也提到参加“二大”的“有向警予”。而且,陈独秀在1921年11月签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明确提出:在明年七月召开大会前,“请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及妇女运动”。在党的“二大”上也专门研究了妇女问题,可见中央局对妇女运动与青年运动是同样重视,作为妇女运动领袖的向警予是完全有可能参加会议的。
所以说,张太雷、陈望道、高君宇、项英、邓恩铭、邓中夏、向警予等人是很有可能参加党的“二大”的,但是目前也没有确凿的资料能够否定杨明斋、罗章龙、许白昊、李震瀛参加了党的“二大”。
大胆地假设一下,有没有可能参加会议的代表不止12人?
李达的回忆说是“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十五、六人)”[3]3。张国焘回忆“这次到会的正式代表却只有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张太雷、向警予等人”[1]214。共产国际米夫认为“参加大会的代表共二十人”。
总之,关于参加党的“二大”的代表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在没有直接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的情况下,中共六大关于《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提出的参加党的“二大”的代表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无法确定”。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时间最早的关于党的“二大”代表的原始文献资料,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应该受到重视。同时,当时的会议观念没有像今天这般有组织的程式化,也没有专门严格的代表资格审查之类的要求,更谈不上有任何规格上的考虑。所以参加党的“二大”的代表除了上述11人外,张太雷、陈望道、高君宇、项英、邓恩铭、邓中夏、向警予等7人完全有可能参加了一次或几次党的“二大”的全体会议或小组会议。
[参与本文写作的还有:倪娜(1985-),女,上海人,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助理馆员;丁宁(1981-),女,上海人,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助理馆员。]
[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0.
[2]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一大”前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时光,周承思.“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第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5]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7]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8]肖甡.访问建党时期的知情人[J].百年潮,2001,(5).
[9]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0]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D23
A
1001-4799(2012)04-0045-04
2012-03-25
王志明(1950-),男,上海人,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学术顾问,主要从事中共创建史研究。
邓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