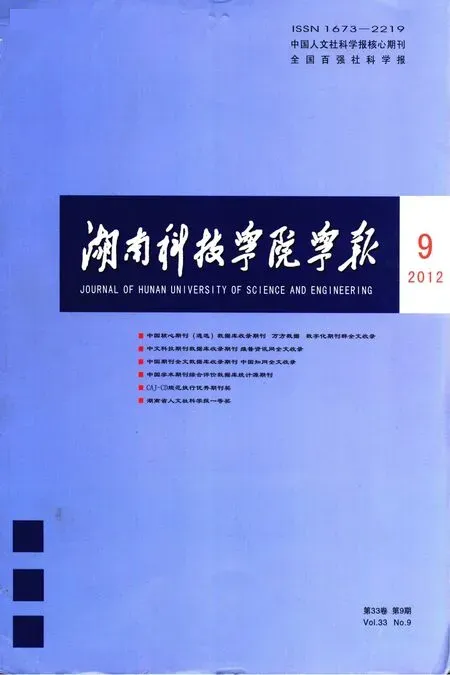身份认同与夏衍电影艺术创作
2012-04-09刘骋
刘 骋
(中国计量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身份认同与夏衍电影艺术创作
刘 骋
(中国计量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作为左翼革命知识分子和党的文化领导人,夏衍的电影创作承担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重任。这种身份要求其电影创作必然蕴涵强烈的意识形态诉求,同时艺术家的身份使他注重电影艺术的审美特性。该文从文化身份的视角指出夏衍电影创作和理论的核心是力求在意识形态和审美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并探求由于其身份内在的困境导致主观的平衡诉求与艺术实践的裂隙。
文化身份;意识形态;审美;文化领导权
一 革命身份认同与意识形态书写
夏衍与那些将艺术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文学艺术家不同,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和那些同时代从艺术走向革命并与他站在同一阵营的革命艺术家也并不能完全等 同,这一类文学家革命的冲动生长在艺术的土壤里,以艺术个体的反叛情结与革命激情达成同谋,因此他们生命的底色依然是艺术;如果说前者是以艺术家的身份从事革命工作,夏衍则是以革命者的身份从事艺术工作,且艺术工作不过是他所从事多种工作的一部分。夏衍是作为职业革命者,受党组织的安排秘密进入电影圈开始艺术实践的。他在回忆自己的电影生涯时说:“我对电影是外行,只因当时为了革命,为了提高左翼文化运动,为了要让一些文艺工作者打进电影界去,运用电影来为斗争服务,才逼着我们去学习一些业务,去摸索和探求。”[1]他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逐渐成为知名的电影剧作家、戏剧家、杂文家,但他的艺术书写生长在革命的土壤里,几乎全部沾染着政治的风尘。坚定的政治信仰和贯穿一生的革命追求是夏衍生命的底色,因此他对革命者身份的认同高于一切。选择和确定革命者的身份意味着以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方式看待世界,也意味着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承诺: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服务。
文化领导权的核心是意识形态领导权。某一集团(阶级)获得文化领导权意味着该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精神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观、道德观,其支配性地位可以整合其他非本阶级的思想,从精神领域实现对个体的控制。意识形态通过对精神领域的控制,不仅可以使本阶级成员结成自身利益一致的统一体,而且可以将个体建构成适合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主体,并进一步用普通民众的“同意”牢固本阶级统治的历史合法性。因此,一个正在夺取政权或已经夺取政权的政党都将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中承担举足轻重的责任。虽然知识分子自己不掌握任何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但是他们作为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承担者,可以通过哲学能动性,文学艺术作品等手段再生产信仰体系,夏衍这样党的知识分子所承担正是生产信仰体系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任务。反观中国20世纪文化历程,20年代的“革命文学”、30年代“左联”运动、40年代延安“讲话”都是中国共产党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标志性运动。接受党的派遣的夏衍打入被资产阶级垄断的电影领域无疑是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争夺的一个步骤。中国共产党将文化争夺的目光投注到电影这一新兴的艺术领域,是敏锐意识到这一大众传媒所具有的大众化形象化特质,并由此具备使意识形态迅速社会化、常识化的功能。对此夏衍有深刻的认识并多次强调:“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最富于群众性的艺术,它是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最有利的武器。”[1]可见夏衍介入电影主要的任务就是运用审美化革命话语生产与再生产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同时颠覆和解构官方国民党意识形态,从而达到鼓动与组织群众的目的。无论客观工作要求还是主观的自我认同,革命知识分子身份规范着夏衍的创作姿态和价值取向:电影叙事中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夏衍对其创作的意识形态性有相当清醒和自觉的追求:“这些影片可以说都是为政治服务,从属于当时党领导的政治的”,[1]“我们当时就是想通过艺术形式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说实话,当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艺术是谈不上的”。[1]具体文本运作中,以人物的对白,具有政治信息的背景等直接进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宣谕,“无论是自己编写剧本还是帮助别人修改剧本,都要千方百计地将进步的爱国思想掺进去,在他们的艺术片中加进一些革命的对白,在无声片里加上这种内容的字幕”[1]。例如《春蚕》中的序曲,以新闻报纸的大标题,数字统计表的形式直接表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使民族经济濒临崩溃的主题;《时代的儿女》中随着“狂风暴雨般划时代的血”字幕后“五卅”惨案的血腥场景;《自由神》中穿插的歌曲;《风云儿女》中被压迫人民发出的“团结起来”“杀尽敌人”的喊声;《女儿经》中几个女学生各自回忆自己的不同的人生道路后校长所做的总结性发言等等。从严格的审美角度看,这种的手法显然很粗糙幼稚,但这种明朗的意识形态宣谕恰与当时文化语境下观众的政治期待心理相吻合,他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可以使他们的政治焦虑得以宣泄并受到人生指导的“行动的诗”,因此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
夏衍电影艺术创作的意识形态特点集中体现于作品的叙述人身份中。细读夏衍一九四九以前的电影脚本,我们可以发现文本中叙述人的革命启蒙身份角色,叙述人身份与作者真实的文化身份同一。列宁谈到革命必须由先获得真理的知识分子从外部进行教育和启蒙。因此象夏衍这样的有机知识分子要做一名革命的播火者、启蒙者、“雄辩者”、“坚持不懈的劝说者”。革命者身份化为叙述人,使夏衍剧本叙述视角采用先知先觉的位置自上而下进行革命的启蒙和指导,教育观众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他的电影文学剧本也就因此承担形象化意识形态教科书的任务。在剧本的叙述模式上,夏衍采用阶级对比的方式向观众展示路有冻死骨,朱门酒肉臭的图景,这种对比有着相当的视觉和情感冲击力,从而激发观众的阶级意识,暗示必须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有出路,例如《狂流》、《上海二十四小时》、《压岁钱》等电影;在《女儿经》、《时代的儿女》、《自由神》、《风云儿女》等作品中,夏衍采用如何选择正确人生道路的“问题”模式。作者提出青年人在人生旅途中面临个人/国家、奉献/索取究竟如何抉择的问题,在结尾给出答案,指出在风云际会,国难危亡之时只有投身革命才是正确的选择。
由于受到当时国民党文化审查和文化围剿,解放前夏衍的剧本中革命启蒙者叙述人角色是隐蔽的。夏衍解放后的电影剧本中叙述人角色则由革命启蒙者转变为阐释者和立法者,并由隐蔽走向前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并相应获得了文化领导权,夏衍这样党的知识分子成为国家领导机关行政当局的文化领导权的代表,他们的任务就是通过制定和传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来整合其他各个阶级以及知识分子,保证社会各种组织与群众“同意”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与规则,维护社会稳定。一言以蔽之:以文艺的方式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立法和阐释,确立全民对这种合法性的信仰。这种身份角色影响了他在建国后的系列电影作品。例如《人民的巨掌》,作品的意识形态相当明朗,夏衍把毛泽东在人民政协开幕词的一段话以字幕的方式直接展现在电影的开始:“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我们务必不要放松自己的警惕性。”在电影结束时又打出字幕:“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保卫新中国经济建设。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如果说开始的政治方针是全剧的中心和论点,结尾是对论点的重申和呼应,那么中间的人物和故事就是剧作者提供的形象化的论据,对论点进行阐释和论证。这里作者明确地展示了自身作为意识形态阐释者的角色。
又如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祝福》,夏衍在保持原作的故事框架基础上将其进行了全新意识形态的阐述。夏衍在谈改编作品时说:“每个改编者必然有他自己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管有意无意,它总是要反映到改编的作品中去的”。[1]原著作品中鲁迅借助一个回到故乡的知识分子视角以第一人称叙述发生在鲁镇的一个妇女的人生悲剧,作品深厚的内蕴不仅仅源于从文化视角延续着鲁迅对中国国民性和中国封建文化的批判性思考,而且由于祥林嫂命运所隐含的人本困境,尤其她发出的“人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追问使作品具有形而上高度。夏衍在电影《祝福》中将原著知识分子叙述人改为意识形态阐释者,叙述人隐退在幕后由画外音承担。电影一开始一个“低沉但苍劲”的男声讲起(这个男声是意识形态霸权话语的隐喻):“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这已经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大约四十年以前,辛亥革命前后,在浙东的一个偏僻的山村里。”电影的结尾男声画外音再次响起:“――对,这是过去了的时代的事情。应该庆幸的,是这样的时代,终于过去了,终于一去不复返了。”这个画外音是解读整部电影的核心,它的目的不仅是故事背景的客观陈述,而是通过一个时间的向度表明导致祥林嫂苦难的那个旧社会终于被消灭了,现在的人民在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过上了好日子。对旧社会的揭露就是对新社会的赞扬,教育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这是主流意识形态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进行阐述。由于作者有意运用了第三人称(原著第一人称)显得阐释具有“客观性”,阐释的意识形态便相应具有了真理的意味。作者自身文化身份决定他对鲁迅原著的文化视角转变为政治视角,由原著的形而上追问转为形而下的注视,因此他注重的是祥林嫂的阶级社会属性,添加引起后来争议的祥林嫂“砍门槛”的情节,是合乎逻辑的必然,进而电影《祝福》对小说完成了一次重新阐释,借此完成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构。
二 意识形态劝说宣传方式的寻觅
革命者身份的工具化思维、“元话语”诉说冲动和迫切的政治任务遮蔽艺术的感性、非理性和想象的翅膀。艺术成为政治的工具,艺术直接机械地反映着意识形态。由此造成的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裂痕成为横亘在左翼文学艺术家面前挥之不去的梦魇。与艺术无法融合只是包裹在外面的那些政治符号和激动的号呼,不论思想如何正确但是远不如艺术本身内在的倾覆性持久且深入人心,因此弥合艺术裂隙寻求艺术的平衡成为摆在大部分左翼艺术家面前的任务。
对于革命作品普遍的艺术裂隙夏衍是警惕的并且有着对于艺术本体规律认知的自觉,这应当归功于他阅读与翻译文学作品带来的良好的艺术积淀。他很早就提出艺术创作作为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同,并强调电影创作,不但“要符合一般艺术创作的规律,同时它还有自己特殊的规律”[1],学习和认知艺术规律,使之更好地为革命工作是夏衍毕生的艺术信条,他把这种弥和归结为思想和艺术,政治与业务的统一。
夏衍之所以能够在艺术行程中较为自如的穿行并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笔者认为很大程度由于萦绕他心中的平民情结。这种情结成为他寻找艺术平衡的支点。与当时左翼极力倡导描写激进的革命斗争不同,平民的情结使他电影叙述之始就将视角更多地投注到自己熟悉的,生活在生活底层的小商人、小知识分子、保姆、舞女等等小人物的生存状态,通过小人物的跌宕命运来展示他所要表达的时代精神。他在《题材与出路》一文里说:“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描,穷人与富人生活的映照,在教育的意味上固然重要,但活泼的、更阔大的,向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摄取有关于社会问题的题材,给观众一种启示,一样是不可少。任何方面的题材,只要编剧人的观点正确,在教育意义上是同样的。”这种题材的多样拓展了左翼文学的题材范围。更重要的是平民情结赋予夏衍对小人物的真诚情感,化为内趋力在一定程度上柔化坚硬的政治理性。对小人物的善良无奈、懦弱卑微的人性描画客观上有助于突破机械的阶级情感。
夏衍在30年代的作品中善于以曲折的情节来包裹意识形态,力图用这种方式达到意识形态与审美之间的平衡。他在回顾30年代左翼电影时耐人寻味地谈到,当时的电影是理论上学苏联,技术上学美国。他将美国“好莱坞”的通俗情节剧的表现手法移植到左翼电影中,比如《白云故乡》融入美人计、间谍戏,《狂流》、《自由神》、《同仇》等影片中的多角恋爱情感纠葛,《风云儿女》《压岁钱》等影片中的情节巧合,作品人物的大喜大悲,黑白、善恶泾渭分明的斗争故事与中国传统审美习惯暗合,很吸引观众。显而易见,夏衍将审美当作一种包裹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形式,就象药片外面的那层糖衣。这种对艺术规律的理解有着一定的局限,因此在实践中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他所追求的平衡状态。
对于夏衍来说这种平衡追求真正取得效果是1937年话剧《上海屋檐下》的完成。该作品是作者对艺术规律真正理解和尊重的分界,也是他作为艺术家身份成熟的标志。伴随着艺术家身份的自觉和对艺术本体理解的深入,在其后的电影创作中夏衍从狭隘的政治窠臼中走出来,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进入审美创作的核心领域。他意识到审美不仅仅是外在于意识形态的包装,而是和意识形态血肉相连的生命体。因此夏衍寻求平衡的方法开始变化,他的注意力从外在的故事情节转入人物性格的刻画,他把人物沉浮在现实生活河流中,力图通过成熟丰满的艺术形象血肉一般包裹住意识形态骨骼,达到他追求的平衡状态。他选择那些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创作比较成功的《祝福》和《林家铺子》背景都是他的家乡江南水乡,江南的房屋小桥、流水、树木,人物的服饰屋内陈设这些细节的真实营造出浓郁的现实生活氛围。作者从容自如地描写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物,《祝福》中的祥林嫂,作者予以其较多的内心展示,尤其她与贺老六之间的情感从冲突到认同,相濡以沫,描绘得丝丝入扣,人物丰满充实。《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是夏衍电影人物刻画最为成功的形象。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多重矛盾纠葛中描绘这个人物内心的挣扎、痛苦、无奈和善良的天性。整部作品叙述流畅,结构严谨,充盈着朴素、隽永的夏衍特有的风格。这部作品成为他电影创作的最高峰,并且真正达到了他所追求的意识形态与审美之间的平衡。
三 身份困境与弥合裂隙的失败
客观地讲,象许多左翼作家一样,夏衍的电影留给我们的恐怕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印痕,这些印痕渐渐消隐于历史的风尘中,可见作者弥合艺术裂隙的努力并不完全成功。大部分作品从概念出发,即使夏衍凭借生活和艺术的积累,尽量避免因此而造成的人物形象的干瘪及作品的概念化,但作品中意识形态的诉求压迫遮蔽审美因素成为常态,少有能够立得起来的人物。多数人物缺乏丰富的内心世界的挖掘,原本无限宽广复杂的人的心灵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人本身多方位的情感的裂隙、扭合以及产生的张力让位于外在的阶级冲突,人物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变得透明和单维等。这里我并不想脱离具体的政治文化语境对历史人物进行简单的审美价值判断达,我想探讨的是:如果说意识形态与审美的分裂状态在30年代是由于作者尚属于艺术青春期,需要一个在创作实践中逐渐掌握艺术规律的成熟过程;那么在创作出《上海屋檐下》、《芳草天涯》,已经成为一名成熟的艺术家的夏衍,在自己艺术创作巅峰状态,理应有更多的优秀电影作品出现的时候,为何艺术实践与作者主观平衡的诉求之间依然存在如此的裂隙,而且这种情况在左翼文学中有着普遍性。
悬置众所周知的政治文化语境,以及官方意识形态部门对电影特有的文化政策这些外在因素,作为主体的身份是探求疑问的一个角度。我以为夏衍革命艺术家这个身份本身就是一个可怀疑的角色定位。革命者与艺术家两个角色无法达成同一,即使艺术家怀着对现实的不满、对更合乎人性的美好乌托邦社会的寻求而显现的革命反抗性和政治敏感,这与某一时段革命者的政治诉求可以交融,但是基于自由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和普遍质疑(包括元话语)的批判精神、以及相应的个体自由书写的要求,这种交融就是暂时的,与革命角色之间有着本质的悖离是长久的。因为作为被特定意识形态建构的革命者(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必须以政治、政党利益为出发点,以既定的思想观点乃至政策作为评判和思考事物的唯一标准。党的文艺工作者作为革命事业的螺丝钉必须服从整体的革命事业,当自己的思想和感受与政党的要求相悖时,他们会自觉地放弃属于个人的独立思考,自动寻求与政党意识形态的同一。意识形态的束缚使他们很难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精神高度,个体消融在集体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艺术家应当是体制外的,被体制收编就必须同他的自由精神和无偏见的总揽能力告别。当时被自由派知识分子讥讽为“两栖人”的革命艺术家遇到的悖离与分裂的身份问题恐怕冷暖自知。如这些左翼文化人批判第三条道路行不同一样,在艺术家与革命者之间同样无法寻找两头兼顾的中间地带。革命艺术家身份最终只能意味着革命者身份对艺术家身份的压抑,权利总是要渗透和解构艺术,艺术家身份成为易受威胁的“他者”。夏衍《芳草天涯》的际遇就是最好的例子:该作品体现出真正艺术家的人生感悟,因其超越性的视角赋予了作品深厚人性的内涵乃至对存在意义的形而上探询。但艺术家的个体言说,意味着知识分子个体精神的凸现,在当时语境中这恰是需要抛弃和改造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由此,在夏衍的身上体现出一种真正的二律背反:一、接受意识形态的询唤,艺术家的身份需要抛弃;二、艺术家的身份需要保留,这不仅出于知识分子的潜意识情感,更出于艺术家(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这种背反式的身份困境折射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人的内在危机。沈芸曾谈到夏衍在电影创作中属于艺术家个体原创力的淡化,作者创作的愉悦感时时会被政治的需求所替代。并指出在“夹缝”中进行电影创作的心态。[2]这种焦虑心态恰恰表达出作者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夏衍在艺术实践中试图弥和这种分裂的主体性。比如建国后以改编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著作的方式寻找作为艺术家的书写空间。在《林家铺子》中,作者一方面突出林老板的阶级性,描写其欺凌比自己弱小的人以转嫁经济困顿,以表现鲜明的意识形态定位,另一方面给人物以人性化处理,描写人物的善良和无奈。作者的这种调和身份矛盾的努力反映到林老板身上,客观表现出人性的复杂并因此显得丰满厚重。但归根结底身份的内在困境是无法调和的,因此平衡的探求并不都能象《林家铺子》这样成功,审美最后总是被遮蔽,比如《革命家庭》中的母亲《烈火中永生》的江姐等人物都可以看出作者努力平衡的痕迹,但真正人性的光辉都淹没在所谓英雄形象的伟大之中。夏衍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他坦言在他二十余部电影剧作中较满意的只有《春蚕》《林家铺子》《祝福》和《憩园》。
陈荒煤对这种身份定位作过恰如其分的描述:没有把自己看作什么左翼戏剧家、左翼作家。不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是把这些活动当作革命工作,当作一个严肃的政治斗争。[3]可见身份天平自然地向革命倾斜,其作家的生涯只是革命生涯的一种补充,文学活动是革命存在形式之一种。革命与文学之间,意识形态与审美之间,前者是第一位的。这就不难理解理论上尽可能纠正唯政治化的非艺术性的倾向,但实践中对口号式作品的宽容。周作人所说的“赋得的文学”可谓一针见血。
这里我们不得不谈到夏衍身份带来的理论局限。基于革命功利仅仅将文学艺术看作载道的工具,造成的只能是审美一翼的缺失。作者将艺术创作的首要目的放在“道”上,文学用来传达“道”,并以此作为入世,实现政治报负的途径。这种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使其无法以纯粹的“求真”“求美”为目的进行艺术本体的探求,从而造成对艺术本身及审美现代性的弱视。萨特说:“文学当它未能明确意识到自身的自主性,当它屈服于世俗权利或某一意识形态,总之当它把自己看作手段而不是不受制约的目的时,这个时代的文学就是异化的。”[4]文学的社会功用是通过意识形态来实现的,如果过分夸大其社会功用,就很容易将文学等同意识形态。在文学为人生,为现实,为政治为政策之间有着一种逻辑推进的必然关系,不经意间造成审美诉求的断裂。
正是功利理论和身份的双重困境使夏衍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很难平衡。即使在新时期,历经坎坷的老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扭转中国电影纯粹意识形态化作出杰出的贡献,但依然无法摆脱由于这种困境带来的局限。他无法意识到站在功利的一端是很难达到他毕生追求的这种艺术平衡的。马尔库塞说:“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在于它自身的审美之维”,[5]这恰恰道出艺术的功利性在于其非功利的追求中这一有趣的艺术悖论。事物的辨证法告诉我们,惟有当手段本身升华为目的,它才能最有效地发挥手段的功能。这种身份困境及理论局限带来的创作得失在中国20世纪左翼文化中带有普遍性,故回顾夏衍就具有审视历史的意味,其实对历史的审视也是对自我的审视。
[1]夏衍.夏衍电影文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2]沈芸.史料、回忆与研究[A].夏衍论[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3]陈荒煤.伟大的历程和片段的回忆[J].人民文学,1980,(3).
[4]萨特.什么是文学[A].萨特文学论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5]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北京:三联书店,1989.
(责任编校:王晚霞)
I235.1
A
1673-2219(2012)09-0188-04
2012-07-10
刘骋(1971-)男,河北涿鹿人,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影视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