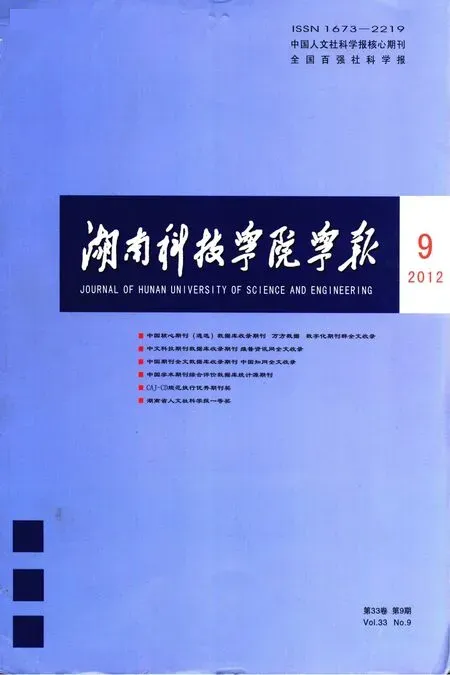弥漫着土地芳香的两位女性
——《飘》与《一千英亩》人物形象之比较
2012-04-09廖海燕潘利锋
廖海燕 潘利锋
(湖南科技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系,湖南 永州 425100)
弥漫着土地芳香的两位女性
——《飘》与《一千英亩》人物形象之比较
廖海燕 潘利锋
(湖南科技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系,湖南 永州 425100)
美国现代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在《飘》(1936)中塑造了一位敢说敢做的新女性形象——郝思嘉,而美国当代女作家简·斯迈利在《一千英亩》(1991)中塑造了一位从“失语”走向“抗争”的新女性形象吉妮。论文拟从两位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觉醒过程和其土地情结作一番比较与分析。两位女性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但同为农场主的女儿,她们都与土地有着十分亲密的联系,都为她们所生活的土地做过努力抗争,在觉醒过后完成了对自我身份的构建,散发出迷人的芳香,成为了文学史上经典的女性人物形象。
《飘》;《一千英亩》;郝思嘉;吉妮;比较;土地情结
引 言
根据美国现代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Margaret Mitchell)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1939)获得了当年包括最佳女主角、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在内的多 项奥斯卡奖。1997年,导演Jocelyn Moorhouse也根据美国当代女作家简·斯迈利的《一千英亩》改编了电影《陌上伊人》,两位美国女作家的代表作都被搬上了银幕。郝思嘉是玛格丽特·米歇尔在《飘》中塑造的一位十分叛逆坚强的新女性形象,而吉妮是简·斯迈利在《一千英亩》中塑造的一位性格懦弱的新女性形象。米歇尔和斯迈利都对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作品比较钟爱;她们都受其母亲影响,内心有着强烈的女权意识;都经历过两次婚姻。两位作家都以女性的生活为题材,通过对人类与自然,尤其是女性与自然之间亲密关系的探索,塑造了两位独自主的新女性形象,展现了女性的生态智慧。同为新女性,《飘》和《一千英亩》中的女主人公个性迥异,自我追寻的过程不一,最终她们对于土地的选择也是截然不同的,本文拟从两位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觉醒过程和其土地情结作一番比较与分析。
一
《飘》中的郝思嘉有着叛逆、独特的个性,她在交友、恋爱以至婚姻问题上蔑视父辈的传统,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完全我行我事,整个儿背离了父亲的意愿。首先,她不顾一切地向艾希礼求爱,而当艾希礼与媚兰的婚姻成为事实,她又咄咄逼人地提出与艾希礼私奔。当此事未能如愿,她就要报复艾希礼,其招数是与媚兰弟弟查理结婚。可是婚后的查理在军中病死,她又蔑视祖辈一直遵循的服丧制度,早早地将衣服脱去,毫无顾忌地在社交场合出头露面,恣意享受少女少妇们正常的生活乐趣。
郝思嘉这一叛逆性格后来更加变本加厉。战后,为了控制丈夫的财产和保住种植园,她与她妹妹的未婚夫弗兰克结了婚。这一切,都是从一己的私心出发,我行我素,任何家庭的意见都一概置之度外,表现了她反抗叛逆、骄傲自信的性格特征。除此之外,上一辈的爱尔兰人的富于挑战的性格像肥水一样流进了干涸的田里,需要吸收的思嘉将其点点滴滴都吸收了。
而《一千英亩》中的吉妮,却在无意识中吸收了忍耐和佛学中安于天命的观念。下面是吉妮和杰斯就父亲的农场合营一事所作的对话:
杰斯:“反正我觉得事情该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每件事在它的内因外因作用之下,结局是不可改变的。佛学里说,安于天命,你就会找到美,找到宁静祥和。如果你担心,事情只会越来越糟。”
吉妮:“龙卷风来的时候,我母亲也是这么说的”(张冲21)。
应该说,吉妮在潜意识里就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对牧师的布道顶礼膜拜,并用以观照家族的一切。“我们的教区牧师亨利·道奇做了年度布道,说人世间任何的财富都来自耕种土地。这句话肯定会引起农民们的自尊心……。因此我觉得,和马弗一起坐在后排座位上的爸爸此刻的心情一定挺好”(同上 33)。吉妮对此深感欣慰,也想借此调和父亲与作为律师身份的妹妹凯洛琳的关系。因此,从教堂出来后,吉妮劝凯洛琳说:“去吧,圆滑一点。吻吻他的脸,拥抱他一下,然后说:‘对不起,爸爸。’就万事大吉了。你能办得到的……”(同上33)。
可以看出,不但是吉妮自己,她还要让妹妹凯洛琳去接受父亲的圣旨,希望她听从父亲关于一千英亩土地的安排,不要因厌恶农村生活而拒绝父亲。吉妮的母亲早死,她认为作为家中老大,自己有责任担当母亲的角色,去管住自己的妹妹。实质上她不仅将自己作为父权制的奴隶,也要让妹妹们成为其奴隶。在父权制的泽布伦县,父亲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女儿像土地一样是农庄的私有财产,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女人们难有作为,只能像自然一样被当作物用,像她妹妹罗丝对吉妮所说的,“我们是他(父亲)的,他对我们就像对池塘、房屋、猪和庄稼一样,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同上 207)。女性所受的压迫迫使他们长期处于被支配的地带。想不到对这样一位乱伦的父亲,吉妮还对他保持着一丝敬意,这一切都说明了她忍气吞声的懦弱性格,而吉妮服赝于成功的父亲及其这块富于生机的土地,也是她的性格使然。
二
除了性格不一,在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父权制的反抗方面,郝思嘉和吉妮的觉醒过程和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在《飘》中,从小说一开始,郝思嘉就颠覆了男权话语中心对女性的扼制,表现出咄咄逼人之势。郝思嘉对男权的挑战,不仅体现在她对丈夫的态度上,也包括对待她的父亲。有一次,她只因同瑞德跳舞而惹怒了她的父亲,因而父亲执意要接她回家,可女儿别出心裁,要以状告父亲喝酒一事相威胁,在女儿的要挟之下,父亲只好屈从于她,将她继续留在舞场。《飘》的女主人公郝思嘉显然是一位理想的生态女权主义者,她蔑视男权,我行我素,最后成为土地、工厂和生态的主人(潘利锋,廖海燕,2009:85)。
在与弗兰克的婚姻中,她也完全占据着女性话语权,以女强人的姿态俯视一切和指挥一切,这使得弗兰克完全被架空而无所适从。“弗兰克和他认识的所有男人一样,觉得妻子就必须由学识更深的丈夫来引导。必须全盘接受丈夫的意见而没有自己的意见”(李美华,759)。弗兰克这一传统之见,完全被思嘉打破,他不能在妻子面前有任何作为。就这样,思嘉在锯木厂和生意场上独往独来,且游刃有余,大赚其钱。这确实使弗兰克如丧考妣,没有脸面,因为一个女人“在这么一项男性化的活动中取得成功,没有一个男人会感觉对劲的”(同上761)。要知道,亚特兰大从来没有女人像郝思嘉一样做生意。
在亚特兰大人眼里,思嘉简直就是异类。她不仅以横空出世的能耐经营好锯木厂,还用卖不出的下等木材盖酒馆,以便赚了钱买下更多的锯木厂。“她的声音尖刻辛辣,坚定果断,转瞬间就可拿定主意,没有一点女孩子的优柔寡断”(同上 762)。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比男人还会走捷径。比如雇用廉价的犯人,经销时以次充好,做事不择手段,但又善于伪装,常以鬼魅的伎俩击败竞争对手。她的行事方式和称霸异性的行为,招致了全城的非议。
同是对待父亲和父命,《一千英亩》中的女主人公吉妮与郝思嘉有着天渊之别。吉妮是一个丧失了女性身份的“失语者”,一直生活在父亲的阴影里。吉妮容忍着一切,在吉妮看来,父亲的话就是圣旨,他要女儿做什么,女儿不敢越雷池一步,哪怕他实施罪恶的乱伦,女儿也只能忍气吞声。父亲是权威的象征,她对他充满了畏惧。
“我对父亲的最初记忆就是害怕看他的眼睛,我根本就不敢看他。他身材那样高大,声音那样低沉,如果我必须和他交谈的话,我只敢盯着他的外套,他的衬衫,或是他的靴子说话。如果他把我拖到他的脸边,我会极力向后缩;如果他亲我,我会忍着痛苦让他亲,然后轻轻拥抱他一下作为回报”(张冲18)。
父亲的眼睛,折射出父亲的威严,这是男权制下至高无上的威严。吉妮的观念和意识在父权制面前完全消失,完全被男性世界所吞没。吉妮的一生是悲惨的,在新婚之夜,她反复擦洗自己的身体,想洗出父亲在身上留下的肮脏,但她与丈夫在一起的时候,仍然厌恶自己的身体没有丝毫快乐。由于化肥农药渗入地下水,她六次流产,不能有自己的孩子。她没有婚姻的幸福,她与泰伊仅是名义上的夫妻,泰伊缺乏情趣,和她的父亲一样,满脑子都是农场。他一心支持吉妮的父亲,目的就是从老丈人那里得到更多的土地,因此他在诉讼案之后出卖了吉妮,迫使吉妮最终决然离开了他。
值得指出的是,吉妮在长时期内尽量忍受着这一切的一切,对丈夫,她是贤妻;对父亲,她是孝女;对妹妹,她能忍让,既不能像罗丝一样蛮横任性,也不能像凯洛琳一样选择自己的生活。随着吉妮女性意识的觉醒,她逐渐地成为了一位能发出自己声音的勇敢女性。虽然比起《飘》中的郝思嘉——那个敢做敢为并完全占据着女性话语霸权的勇敢叛逆者,那个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生态智慧成为了土地的主人的郝思嘉,吉妮与她当有着天渊之别,由于受父权制思想压制之深,吉妮这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过程太漫长太艰难,但是,正因于此,她的成功更显不易。
三
《飘》和《一千英亩》中的女主人公都跟土地有着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可是同样作为农场主的女儿,她们对待土地却有着完全相反的态度。在《飘》中,小说的开始,郝思嘉对土地不屑一顾,甚至讨厌自己的土地,当父亲对她说:“我可以把塔拉留给你们。郝思嘉的回答却是“够了,谁稀罕你的农场!”,父亲说:“我可告诉你,土地是我们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来源于土地,它是惟一值得我们用生命的代价来换取的东西啊!”郝思嘉根本就没觉得土地对于她有什么意义,这时的她对父亲说:“真是个爱尔兰人!”(李美华26)
离开农场,来到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突飞猛进的亚特兰大之后,她马上又惊奇地发现自己才离开塔拉农场几天就经常想念起那个地方来了,对那块养育她的土地的怀念之情油然而生。之后,随着塔拉庄园受到战争的迫害,亚特兰大受到沦陷后,郝思嘉逐渐意识到了塔拉对于她的重要性及意义。她想回到塔拉农场去,回到那安全又宁静的家去(同上 285)。而且,她开始为塔拉农场担心起来,在得知北军到了琼斯博罗,而琼斯博罗离农场很近时,她为农场忧心忡忡。那时的她懂得了:对她来说,家是她生命的源泉,家是她永远的精神家园(同上 301)。迫切想回家的她甚至对瑞德说:“你再不让我回家,我就杀了你!”(同上326)
郝思嘉在战争中完成了一次痛苦的蜕变,她从少女变成了女人,成为了一个有着顽强意志、不屈精神的女人。塔拉农场是她生命的源泉,红色的土地离不开她,她更离不开红色的土地,它和她唇亡齿寒,生死相依(同上 358)。重建时期郝思嘉在农场向艾希礼表白的对话中,艾希礼说了一句:“有一样东西,你爱它超过爱我,你没意识到,它就是塔拉”(同上46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郝思嘉对土地的爱是发端于无意识的。
在经历了厌家、离家、回家、保家的过程之后,她表现出了浓浓的家园意识。危难时刻,她总是从塔拉这片土地上寻找养料和力量,而不是从男人那里寻找帮助,因为她坚信,她所需要的东西是土地恰恰所能给予而男性不能给与的。因此,在小说的结局,我们看到:当郝思嘉真正爱上瑞德,而他却离她而去时,她充满信心地说:“毕竟,明天又将是新的一天。”她的脑海里出现的是塔拉的画面。这时的塔拉不仅仅是给她温暖,让她疲惫的身心得以休憩的地方,而且也是激励她继续战斗下去的力量之源。郝思嘉选择了回到给予她精神力量的塔拉,在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实现了自我价值,完成了对女性自我身份的构建。
《飘》中的郝思嘉对土地的爱是从无意识到有意识,而《一千英亩》中的吉妮对土地却是有意识的一种爱。小说的开始我们就了解到她想用心经营好这片土地,她对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表现出了喜爱之情,吉妮还跟父辈们回忆起了土地的历史与它所受到的改变及人类对土地的征服过程。在吉妮的眼中,土地就是财富,是一切的源泉,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在这一千英亩土地上有所作为。可是,随着一件件历史事件的真相浮出水面,吉妮的女性意识逐渐苏醒之后,她了解到在这块土地上死于乳腺癌的多位女性和自己五次流产的根源都与地上的井水有关,吉妮最终逃离了那片被污染了的土地,离开了农场开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吉妮在一家餐馆当上了女招待,干起了自己最喜欢的工作。她已找到了自己真正理想的世界,在这里精神充实、生活愉悦。罗丝死后,吉妮得到了罗丝两个孩子的监护权,在还完了农场所欠下的税单之后,吉妮让两个孩子远离了农场的负担,也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至此,吉妮完成了自己的全部蜕变,从一个受压抑受迫害的家庭妇女转变为一个可以把握自己把握未来的独立女性。
郝思嘉和吉妮的新生活预示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女性的解放。在小说的结尾,虽然两位女主人公选择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可实质都是一种精神上的回归,其目的都是为了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郝思嘉对土地的依恋和回归体现了她对塔拉农场的爱,而吉妮最终选择离开农场,也是对土地的一种爱护。比较两部小说中女性对土地的最终选择我们就会发现:随着美国农业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人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处于转型期的郝思嘉在征服土地、利用土地的过程中成为了土地的主人,而处于美国农业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把追求最大利润作为奋斗目标,把土地当作一种财富。农药化肥的过多使用,机械化程度的加深,给现代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吉妮便在改造土地的过程中沦为了土地的奴隶。
结 语
米歇尔和斯迈利用自己细腻的笔触为世人塑造了两位永恒的文学经典形象——郝思嘉和吉妮。郝思嘉对土地的回归和吉妮对土地的逃离都是自我身份构建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同的是,《飘》在创造和维持生命方面,自然过程遵循的是女性的创造性,能动性原则,而《一千英亩》中,自然界和女性都被物化,人类对土地的贪婪和化肥农药对环境的破坏,预示着生态环境的危机和女性原则的毁灭。鲁艾克特在《文学与生态:一个生态批评的实验》一文中说:“我们处在环境危机之中,因为我们在使用生态圈创造财富的方法破坏生态系统本身。”(转引自张瑛,2005:75)这种破坏的极致,也许不仅仅是女性原则的毁灭,还可能是整个人类生存原则的丧失。这也是《一千英亩》给我们提供的一个警示。
当今人类面临着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如何处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了一个日益重要的课题。美国两位不同时代的女性作家米歇尔和斯迈利所塑造的两位女性人物向读者揭示了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关注女性与自然,关注生态危机,建构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社会。笔者期望通过这一比较为读者提供一种新的对比的角度,以号召人们关爱女性与自然,关注女性生存状况,提升现代人们对于自然和女性这一永恒的文学主题的认识。
[1]Carden,Mary Paniccia.Remembering/Engendering the Heartland:Sexed Languages, Embokied Space,and Ameirca’s Foundational Fictions in Jane Smiley’s A Thousand Acres[J].Frontiers,1997,18.(2):181-202.
[2]Edwards,Anne.Road to Tara:The Life of Margaret Mitchell [M].New York:Dell.1983.
[3]Gaard,Greta.Ecofeminism:Women,Animals,Nature.Philadel phia Temple[M].UP,1993.
[4]Griffin,Susan.Woman and Nature:The Roaring Inside Her [M].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8.
[5]Faber,Becky.Women Writing about Farm Women[J]. Great Plains Quarterly 1998,18(2)(Spring):113-26.
[6]Merchant,Carolyn.Earthcare:Women and the Environment [M].New York:Routledge,1996.
[7]Spretnak,Charlene. Critical and Constructive Contributions of Ecofeminism[A].Ed. Peter Tucker and Evelyn Grim. Worldviews and Ecology Philadelphia[C].Bucknell Press, 1993:181- 89.
[8]戴桂玉.生态女性主义:超越后现代主义[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4):16-21.
[9]关春玲.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 1996,(2):25-30.
[10]简·斯迈利(张冲等译).一千英亩[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1]金莉.生态女权主义[J].外国文学,2004,(5):57.
[12]玛格丽特·米歇尔(李美华译).飘[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
[13]孟鑫.国内学者对西方女权主义七个流派的评价[J].教学与研究,2001,(3):58-62.
[14]潘利锋,廖海燕.生态女权主义的两个文本——《飘》和《一千英亩》之比较[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3):82-85.
[15]张瑛.土地·女性·绿色阅读[J].当代外国文学,2005, (3):72-77.
[16]左金梅.《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J].当代外国文学,2004,(3):99-103.
(责任编校:张京华)
I106.4
A
1673-2219(2012)09-0059-03
2012-06-13
湖南科技学院2010年校级课题“《一千英亩》的存在主义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0XKYTC007)。
廖海燕(1977-),女,湖南新田人,湖南科技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潘利锋(1955-),男,湖南汨罗人,湖南科技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