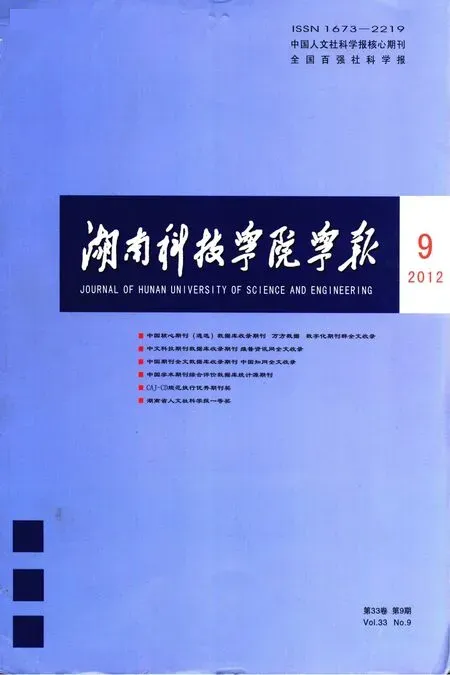一部女性成长小说
——邝丽莎的《雪花与秘密的扇子》
2012-04-09冯玥
冯 玥
(南京晓庄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一部女性成长小说
——邝丽莎的《雪花与秘密的扇子》
冯 玥
(南京晓庄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作为拥有中国血统的美国作家,邝丽莎的写作特色是书写华人故事。《雪花与秘密的扇子》是这位女作家写的一部女性成长小说。女性成长小说强调女主人公从青年到成年的心理和道德成长,并且关注这一过程中由于经历磨练和考验而引起的性格特征的变化。《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主要描述了女主人公在父权文化中、父权意识形态下成长的困境以及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艰难过程。女主人公百合一生经历了隔离、创伤、成长仪式的考验,从童年到暮年她逐渐丧失自我意识、处于被动受支配地位。
女性成长小说;隔离;创伤;仪式
邝丽莎是一位有1/8中国血统,生于巴黎的美籍作家。对于她来说,研究中国、写华人故事是她一生感兴趣的事。邝丽莎笔下的人物描述得栩栩如生,她善于生动地展现古老的中国文化,笔触细腻。出版于2005年的《雪花与秘密的 扇子》是这位女作家以中国文化为题材写的一部优秀小说。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湖南省瑶族聚居地江永县。小说围绕百合和雪花展开,以她们之间的交流媒介——写在扇面上的女书为线索,讲述了一个关于悲与喜、爱与痛、欺骗与遗憾、背叛与救赎的故事。故事的讲述者是百合,她回顾了她八十年的人生经历,倾诉了她以及她周围的人或悲伤、或哀怨、或幸运、或不公的境遇,读者透过她的视角看到了一位 19世纪中国女性的成长故事。
成长小说最早追溯到18世纪末出版的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此后,首先是在欧洲,之后在全世界,这种文学类型产生广泛影响。中外学者对于成长小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进而对其进行解释、定义。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对成长小说进行了梳理,认为“它塑造的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建构,时间进入了人内部,进入了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的涵义上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1]。总的来说,对成长小说的阐释强调主人公从青年到成年的心理和道德成长,并且关注这一过程中由于经历磨练和考验而引起的性格特征的变化。成长小说不局限于关注主人公的青春期成长,时间跨度可以从出生持续到婚后整个认知世界、认知自我的过程。关于成长小说的研究存在的问题是过于关注男性的主体成长,所以女性文学研究必须首先对“女性成长小说”作出解释。虽然无法找到对其严格的理论和概念界定,但这类小说主要描述女性主体作为“他者”在父权文化中、父权意识形态下成长的困境,经历创伤、考验来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艰难过程。
小说《雪花与秘密的扇子》的女主人公百合主要生活在19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小说的作者利用前人从未挖掘的新颖题材,通过真实表述各种成长仪式,深化隔离、创伤等成长小说普遍涉及的主题撰写了一部典型的女性成长小说。
一
《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中女主人公百合在结婚前经历了成长小说中典型的各隔离与考验仪式。婚前是百合由女孩蜕变成女人的阶段,她被隔绝在闺房,经历了情感和身体创伤,懂得了主宰女人一生的儒家条例:三从四德。
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世纪的父权制中国社会。“在父权文化中,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永远是男主外、女主内。世代相传的性别角色强调女性在私人领域(家庭)的责任,社会化过程使人们相信妇女更适合呆在家里相夫教子。”[2]当时的女性绝大部分足不出户,生活内容局限于家庭范围内。女性在成长过程中被限定在封闭性的环境中可以更好地接受传统文化的教化,这是成长过程中隔离的作用。百合家当地典型的建筑有两层,楼上的屋子供女性使用,是女人们聚会的地方以及姑娘们的闺房。歌德在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里虚构了一个“教育省”,主人公在那儿接受强化教育。对于百合来说,楼上的闺房就是她从六岁缠足开始直到出嫁怀孕去夫家居住之前的学习基地。她学习女工、女书,提高将来打理家务的能力。在闺房里,百合意识到“男主外女主内,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无论你是贫穷或富有,为王或为奴,女人总该呆在家里,外面的世界是男人的。女人无论是在行为上还是思想上都不能超越这条界限。”[3]P20被隔离在闺房,她从此明白了自己的女性社会角色和女性从属的性别境遇。
百合对世界和自我的进一步认知还来自于情感、身体创伤带来的心理体验。这些创伤是女性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考验。
封建社会中,由于受社会性别角色和经济条件限制,女性活动范围局限于家庭,她们的个性和气质的形成受制于家庭关系状况。女性在成长过程中体现出对爱的强烈渴望,尤其是来自于家庭成员的爱。同为女性的母女之间可能由于相互之间的理解而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同时母亲是女儿的理想楷模、模仿对象。女儿渴望被母亲欣赏,从母亲那里得到关注和温情。百合从五岁开始就感受到母亲对她存在的漠视。母亲从未表扬过她。当百合看到母亲疲劳想用双手环抱她给她慰籍时,她的母亲却缓缓把她推开。“我突然惊恐地意识到她在那些恐怖的岁月里并没有给过我任何一个母亲应有的疼爱。而她当年施加在我身上的种种痛苦只是为了满足她自私的愿望罢了。”[3]P125百合虽然和大姐同睡一张床,但并不了解她;小妹是和她争夺父母的关爱的竞争对手;父亲和哥哥忙于干活养家也无法给她渴望的疼爱。“我的整个一生都在渴望爱。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不管是作为一个女孩还是后来为人妻,但是我却依然执著地坚持着这份对于爱不合情理的渴望,而它却成了我一生中种种遭遇的根源。”[3]P1与她感情最好的表妹美月意外被蜜蜂蜇到,在她面前痛苦地死去,百合在家里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孤独。死亡成为百合经历的最严酷的创伤考验。渴望爱却在缺乏爱的环境中成长,百合对家人产生强烈的疏离感。出嫁入住夫家后,她并不愿意常回娘家。对作为成长初始环境的家在情感上和空间上的自然疏离是女性成长的重要标志。
具有强制性且附带极大痛苦的创伤考验是缠足。缠足是百合经历的肉体创伤。“缠足改变了我的双足,也改变了我的性格,我总是有种奇怪的感觉,曾经的那段经历似乎贯穿了我整个一生,把我从一个温顺的小孩变成了意志坚定的女孩,又从一个对婆家提出的任何要求都千依百顺的少妇蜕变成一个本县地位最高的女人,村里法规习俗的执行者。”[3]P2父权制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可能制造出拥护者和背叛者。由奶奶、母亲、婶婶、姐姐等周围女性言传身教,百合在阁楼上不但学习了各种生活技艺,更重要的是认同了文化灌输给她的各种“被动”和“服从”为特征女性自我概念。她成长的初始环境通过压制渗透促使她完全接受缠足仪式。她愿意按照男性理想的女性形象塑造自己的言语、行为和身体。在这个过程中,心甘情愿遏制了自己的本性,按照周围的女性模范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肉体。“考验本身都有明确目的,主要是为了发掘和验证成长的潜力,而这种潜力最终需要投入和应用于婚姻为开端的成年生活。”[4]缠足这种考验仪式最彻底地验证了中国封建社会女性投入婚姻的成长潜力。缠足可以使她们在未来丈夫面前显得更有吸引力,完美的小脚是嫁得好的基本保证。缠足意味着女性正式从女孩过渡到女人,所以对于生养女孩的家庭是非常郑重的大事件。传统习俗通过繁复的仪式强化对接受者的教化作用,身体上的疼痛加强了仪式的效用从生理转化到心理的渗透。百合七岁正式开始缠足。首先卦师根据八字测算出适合绑脚的日子,然后吃红豆汤圆希冀绑好的脚如同汤圆一样娇小,村里的女孩带来礼物并唱女歌表示祝贺。在选定绑脚的日子,用米团祭拜了小脚姑娘,把小鞋供放在观音像前。绑带要浆洗过,用浸泡了杏仁、草根、桑树根等植物的沸水洗净双脚,由母亲用十米长的裹脚布紧紧缠绕女孩还在发育的双脚。足有四年,百合忍受双脚变形带来的疼痛,直到十一岁才完全愈合。被动地承受肉体创伤带来痛苦考验了百合的勇敢和耐性,她拥有了一双理想长度七厘米的完美小脚,证明了自己进入婚姻的成长潜力。
二
《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中百合的再生是指她婚后社会身份的定型以及身份的变化给她心智、个性上带来的转变。再生的结局未必是光明美好的,相反,女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又增添了新的痛苦与磨难,这是由天真向经验状态的变化付出的成长代价。
在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结婚是女性人生重要的分水岭,出嫁入夫家也意味着女性成长的重大转折,是女性成长小说中女主人公再生的标志。在成年仪式前,百合觉得“隐藏在长着心灵深处的传统既令人捉摸不透,又使人无所适从”[5]。但十五岁之后,百合的凤凰发髻改成了龙形发髻,准备嫁衣,婆家送来布匹、糯米、猪肉还有钱款,与老同雪花坐歌堂,与母亲、父亲、叔叔、婶婶记两个兄弟依次互相哭诉吟唱,一切都标志着百合仪式性的再生体验。出嫁前,母亲给她婚前教育的话,“我和你说过,一个真正优秀的女人不会允许任何不完美进入到她的生活中去,只有吃足了苦头才能领会到真正的快乐。……言行举止都要符合自己今后的身份”[3]P96。这些封建社会的成年仪式提供了丰富的传统经验来处理女性成长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成功地向女性灌输了融合意识。
婚后百合经历的深度隔离一是来自出嫁的女儿必然要经历的疏离娘家人的失落感,二是由于未怀孕前夫家并没有真正接纳她。女儿被视作家中得一个匆匆过客,在她们嫁人之前只不过是家里寄养的一张嘴。婚后回到娘家时,百合在情感上和生活中实行一些小小的反叛,尽可能悄悄疏离她的家人。家人对待百合的态度是客气的。百合未生育前,夫家不会正式允许她进门,也不会供养她。在百合的家乡的方言里,妻子和客人是同一个词,这说明在女性出嫁后的日子里,会一直被视为丈夫家中的一个客人,但绝不是被盛情款待的上宾,而是一个永远的外人,始终被用隔阂和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的人。结婚后几个月没能怀孕,周围的人们已经开始给她不好的眼色看了。她深刻意识到她更深层次的职责,也就是女人真正的职责:传宗接代、开枝散叶。怀孕后,百合的夫家特地准备了顶轿子接她正式进门。百合感受到了有无子嗣在夫家地位的差异,“我的孩子很快就会出世了,我真正的人生才刚刚展开”[3]P134。
百合婚后经历的最大情感创伤莫过于与老同雪花间关系的破裂。自七岁起,两人结为老同,成为彼此情感的伴侣,发誓永远忠于对方。两个同龄女孩通过写在折扇上得女书分享彼此的心事,并一起学习新的事物,互相鼓励度过生活中得困苦时刻。但由于误解,两人由失信导致最终决裂。为此,百合痛苦、失望、甚至用最为公开的斥责歌来报复雪花。直到雪花临死前,两个人才化解误会。百合用人生的后四十年来弥补她对老同的亏欠。百合一生都在渴求爱——父母的爱,丈夫的爱,以及老同之爱。她没能真正珍惜那份最珍贵的老同之爱,因为对她而言,爱是至高无上的感情,她无法与任何人分享。为了维护县里大户人家的儿媳妇“卢夫人”的荣耀,保持自己“卢夫人”的良好形象,百合伤害了雪花。她已经被男权文化所同化,放弃了最珍贵的老同之爱。婚后的各种创伤、考验证明了百合的成长体现了父权社会女性的生活经历的典型特点,她一直扮演着一个对婆家提出的要求都千依百顺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努力实现了社会赋予她的女性角色、身份。
三
《雪花与秘密的扇子》叙述了女主人公百合一生的生活经历。她的一生与其他同时代的女性毫无异样——从闺中少女到为人妻母,到子孙满堂,再到静坐的暮年。出嫁前经历的各种成长仪式,缠足造成的身心创伤把百合从一个温顺的小孩变成了意志坚定地女孩;结婚时以及结婚后各种洗礼和创伤考验把她驯化成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角色,固守着导致所有不合理和悲痛的父权制社会堡垒。正如西蒙波伏娃指出的那样,“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6]。百合的生理和心理体验突显了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成长的困境,她的成长经历代表了父权制社会压制下女性艰辛的成长过程,她的人生道路体现的是丧失自我意识、处于被动受支配地位女性的命运。
[1][苏]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30.
[2]魏国英.女性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7.
[3][美]邝丽莎.雪花与秘密的扇子[M].元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4]徐丹.倾空的器皿[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68.
[5][美]玛格丽特·米德.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M].宋践,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85.
[6][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24.
(责任编校:周欣)
I246
A
1673-2219(2012)09-0052-03
2012―05―12
冯玥(1973-),女,江苏连云港人,南京晓庄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