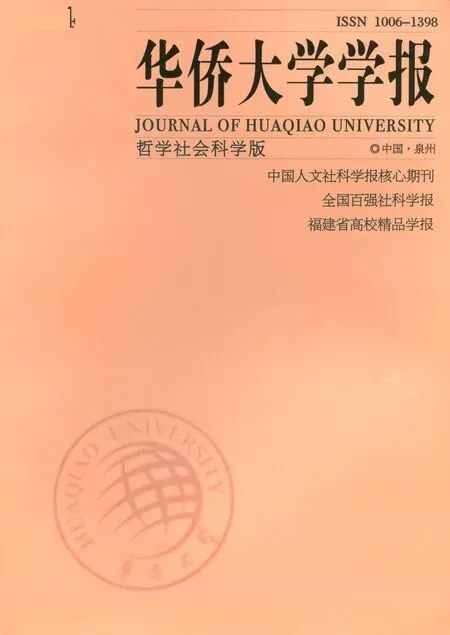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澳美欧华文文学比较
2012-04-08庄伟杰
○[澳]庄伟杰
(华侨大学 华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在大陆境外华文文学版图上,目前被学术界由近及远划分为四大版块:台港澳文学为第一大版块,东南亚诸国华文文学为第二大版块,澳洲(纽)华文文学为第三大版块,美国(加)华文文学为第四大版块。其实,应再加上欧洲华文文学这一版块。无庸置疑,东南亚华文文学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如果用一个蹩脚的比喻来形容,海外华文文学的生成和变奏而组合的形象,仿如文学世界中一个有着三头六臂的奇人异物,那么东南亚华文文学起码占有一头两臂。不言而喻,它与中国本土文学及文化环境的确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同时也与澳洲华文文学及美欧华文文学等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把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澳美欧华文文学这两者笼统地放置于特定的华文生态中进行比较分析,似乎尚无人涉及。尽管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可比性,但真正梳理谈论起来却有相当的难度。当然这种比较对照自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素和探讨价值。如果我们从历史文化背景和地缘因素,从作家身份意识与知识结构、从地域经验与文本书写形态等方面来加以观察,便可发现两者之间潜藏着诸多耐人寻味的话题。爰作此文,其实就是试图把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两大主要部分来略作分析比较。因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在亚洲语境中,即在“蕉风椰雨”中发展壮大,而澳美欧华文文学是在西方语境下,即在“欧风美雨”中自由生长。
谈论这个话题,即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澳美欧华文文学的区别时,必须表明,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澳美欧华文文学有许多共同的所在,譬如它们同是在非母语的国度用母(汉)语张扬的话语空间来表达自身的渴望和诉求,共同推进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对此,笔者称之为“第三文化空间”,其意是指既不愿丢弃自身的文化意识或中国形象,又必须想方设法去适应居住国主流文化的现实,这便是“第三文化”产生的主要根源。更确切地说,如果自身的文化浸润并用母语书写的原在性是“第一文化”,而移植于异质土壤、受到他种文化气候熏染的潜化性是“第二文化”,那么,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碰撞交融之中派生营造的文化景观或空间,即为“第三文化”。它们皆是作为一种独立自在的文化形态或生命方式产生着、存在着、生长着,都处在一种不确定性的流动状态中。它们同是置身于异质文化语境中,将对母语和华族文化的怀念化为文学写作的原动力,在文本母题及变奏方面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时在人文精神方面,相对享有心灵的自由,不断而自觉地寻求和表达个体的生命价值观念等等。从作为后殖民文化理论建构起来的流散研究(Diaspora Studies)的视角观照,它们两者则共同支撑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天空。因为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和体验,流散经验在文化身份的形成中具有深长的意味。究其源在于流散者离开家园土地(homeland)之后,迁徙于异质的空间,无论如何得想方设法去贴近和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但对于原来(母国)的记忆总是无法忘怀。华人的这种散居或离散,驱使了生活于海外的华文作家,用20世纪之初(五四)以来形成的现代文学传统来唤醒自己的创造力,无论是在东南亚还是澳美欧的“旅行”中,都企冀再造了(re-in-vented)一个和居住国紧密相连的“文化中国”,即再造了一个自己心目中向往的精神家园。当然,海外华文作家文本书写中所呈现的“文化中国”,在严格意义上说,既非纯属意义上的他国文化,也非纯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这个所谓的“文化中国”,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文化空间”。具体地说,海外华人作家由于身处中国语境之外,置身在异域文化背景下,穿行在跨文化语境中,往往有着不同文化社会的经历、感受和体验,这种双重的跨域经验和身份角色在有意或无意中影响着他们的创作,而在流散之中更能体悟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等因素带来的种种思考。可以说,华文书写不仅充实了海外华人的生活,也为东西文化和不同文化的比较提供了一个相对理想的具体参照。[1]
一 历史境遇和文化背景迥然有异
所谓东南亚华文文学,应是指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尼、汶莱乃至印支(越棉寮)及缅甸等国的华文文学。首先,从发生的历史背景来加以观察,这些国家的华文文学历史相当悠久。华文文学在东南亚的诞生和崛起,同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密切相关。早在唐代,中国与外国的交通就相当发达,通商贸易比较频繁,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有不少中国人移居海外。鸦片战争以后,移居海外的中国人逐渐增多,尤其是闽粤沿海一带,地少人多,水旱频仍,每年都有大批破产农民离乡背井远赴南洋谋生,在东南亚形成独特的华人社会。但是,那时飘洋过海到东南亚的华人先决条件是谋求生存。由于绝大多数是缺衣少食、无田可耕的贫苦农民,最初在国外旅居,干的也是最底层的体力劳动,根本没有从事华文文学活动的基础和条件。“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的出现,是在华文报纸创办之后。早期刊登在华文报纸上的华文作品,都是旧体诗词和文言小说,数量不多。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诞生,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2]114因此,在全球华文文学的大格局中,它是令人瞩目而独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从身份意识观察,东南亚华文文学经历了由华侨文学到华文文学的转变。按王列耀先生的看法说来,东南亚华文文学所呈现的族群身份意识,是经历了由华侨意识到华人意识再到华族意识这样一个由“三段式”体现的发展过程;而且作为“三段式”的华族意识,现在依然在转换、成长和壮大之中。[3]此外,“东南亚大多的国家是多元种族、各种语言的国家,有些国家标榜着各种宗教信仰,但也有对一种宗教极为虔诚的。”[4]由此可见,从历史文化背景来看,东南亚华文文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并且走过了自己的风风雨雨和逶迤曲折的道路。可以肯定地说,华文文学在东南亚的生发、形成和发展,乃是华人南迁之后落地扎根而后成长的果实。没有华人移民的流动和散居,自然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也因此,它是跟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族群的变迁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华文作家个体生命体验等诸多因素紧密相关的,从而恒定为特定的时代生活和历史风情的真实写照和缩影。在很大程度上,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生命流程或者说发展史,就是华人在东南亚的移民史、创业史和命运史。
澳美欧华文文学则不同,它们的发展历史不太长,或者可以说很短暂,甚至无从查考。譬如只有两百余年历史的澳大利亚,因为年轻,本身积淀的文化显得单薄和稚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澳洲华文文学便可想而知。尽管澳华文学的形成轨迹,同样走过一段曲曲折折的、来之不易而令人难忘的里程,但真正属于澳华文学时代的到来,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事实,即大批中国留学生/新移民涌入澳洲之后,因逐渐意识到生活在不同文明的夹缝中有一种不中不西的生存尴尬。在这种独特的历史境遇中,澳洲的华文文学才开始真正热闹起来,从混沌初开到无序单薄到初具形态,逐步形成自身的格局闪烁于南十字星空下。应该说,它刚刚浮出水面,刚刚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期待。诚然,作为海外华文文学大潮中的一脉激流或一道景观,澳华文学正积蓄着自己的生命活泉向新的世纪奔涌。有学者认为,这是文化认同危机的关切使然。其实,这种说法同样适合生长于美加和欧洲的华文文学。
从上述的阐明中可以窥见: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生、发展流程较长,庶几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相去不远;而远在西方现实时空中横冲直撞的澳美欧华文文学崛起的历史相对较短,抑或说,一切才刚刚开始,未来前景尚是一个未知数,或有待观望。况且前者主要处在亚太文化语境即东方文化语境中,而后者完全置身于西方语境中,尽管各自都在不同程度上甚至几乎接受所在国的文化影响,在所在国的文化土壤中萌发、生根、成长和壮大,并且亦已形成各自相对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特质。
二 作家类型及知识结构差异互见
从某种意义加以观照,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前期即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作家,由于所受的教育大多是中国传统文化,其文化知识与心理结构跟中国本土的作家颇为相似。加之他们大多是飘洋过海谋生或被当作“猪崽”被逼出去逃生的,几乎是挣扎在动荡不安和多事之秋错综复杂的处境之中。于是它们所刊发的作品,几乎与报纸的取向相似。或者说,早期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甚至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在东南亚的自然延伸,“其文化心理是和中国文学一样的。凡是中国文学有过的艺术形式、表现手法、文学风格,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全部有或多或少的重现。”[5]之后,到第二代、第三代作家的出现时,华文学校的创办和兴起成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首要支柱,开始培养出大批能够掌握华文并以汉语书写的写作者(群体),尽管对华语的掌握程度参差不齐,文学薪火的承传在无形中可能已经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但毕竟是支撑起东南亚华文文学长盛不衰的缘由和重要命脉。东南亚华文作家群还有别于其他如澳美欧等地的华家,他们大都是亦文亦商,以商养文的写作群体。是故,江山代有人才辈出,各领风骚于东南亚。如马华的云里风、庄延波、韦晕、曾沛、郑宪文;新华的骆明、黄孟文、周颖南、流军、李龙;泰华的司马攻、梦莉、岭南人、曾心、方思若、姚宗伟;菲华的林健民、云鹤、吴新钿等等。他(她)们大多是儒商型的文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处境的改变,族群的凝聚力和文化的亲和力,驱动着中华文化的世代相传和不断延展,从而在东南亚这片南洋土地上,产生了不少拥有相当实力且硕果盈芳而蜚声于海内外的华文诗人、作家和学者,他们在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上成就斐然,不仅在当地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引起整个华文世界的广泛注目,其影响力堪称是国际性的。如新加坡的尤今、蓉子、王润华、陈瑞献、淡莹、原甸;马来西亚的戴小华、吴岸、朵拉;菲律宾的云鹤、吴新钿、施柳莺;泰国的司马攻、梦莉、岭南人等诗人作家;新生代作家群中如马华的黄锦树、林幸谦、陈大为、黎紫书,新华的希尼尔、许福吉,菲华的王勇等。
返观澳美欧的华文作家,在知识结构上最显著的特点是,留学生身份或技术移民身份居多,文化程度高,有一定的外语水平。例如,从入选《澳华文学丛书》的100多位诗人作家中,95%以上获得大学或大专以上学历,有的甚至获得博士、硕士或双学位,他们一般能通晓或多少掌握除母语以外的一门外语即英语等。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海外华文作家,乃是既不愿放弃所热爱和熟练的母语,又不得不尽可能地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一方面是永远保持自身文化的优势,又被动或主动地接受并溶汇到主流社会中去。他们是一群被澳洲人、美国人和欧洲人视为外来者(他者)的文化中国人,被中国人视为绿卡族或华侨,而在华侨中又分别被视为香港人、台湾人、上海人、北京人、广东人、福建人……,似乎拥有着多重“角色”的莫名其妙的“边缘人类”,或称“边缘文化人”。由于他们自从踏足异邦他乡之后,大多散居在遥远的海外各地,有的已是第二、第三代,更多的是第一代的留学生∕新移民。如果说东南亚华文作家是一群“南洋客”(或称“番客”)的话,那么,用“外来客”(在澳洲称“澳洲客”、在美国称“美国客”、在欧洲称“欧洲客”)来称呼他(她)们可能更为合适。
限于篇幅,这里以作为“澳洲客”的华文诗人作家为例说明。
在老中青三代相结合的澳华作家群体中,有像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移民澳洲之后自称已封笔,但依然通过各种文学活动促进和推动澳华文学的前辈。著名艺术家黄苗子和郁风,老而弥坚,双双齐飞并书写了不少散篇佳作;作为学者型作家的刘渭平、陈耀南和南澳的徐家祯等老一代,仍热心华文,耕耘不辍,且精通英语。一般情况下,凡是大学时代就读中文专业的,外语程度相对次之;凡就读外语专业的或中学时代即赴澳留学的,生活空间相对游刃有余,也较易与主流社会接轨。例如,学建筑工程设计的李润辉、以西洋音乐为专业的江静枝,以文学研究和文化教育为职业的张典姊,他(她)们早年便留学澳洲,本身不仅掌握英文,还能摸透澳洲人的生活习俗和欣赏习惯。诚然,作为用母语表达和写作的华文作家,重要的还是要深入到母语中去,并寻找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才是至为关键的。倘若英文程度本身有限,硬拉胡扯地打着融入主流的旗号,搞不好会人仰马翻,甚至适得其反。不可否定的事实是,文化程度高、外语掌握好,更能拓宽作家的视野,更新其知识及思想素质,更有利于提高自身的写作水准。
有趣的是,澳华作家知识结构上呈现多元化的色彩,文化的、新闻的、艺术的、历史的、社会的、教育的、科学的、商业的专业人士比比皆是。澳华作家自从登陆澳洲之后,原有的身份往往出现一种“立竿见影”的转型,并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的文转商文商结合,有的理转文文理兼顾,有的交叉并重、左右驰骤,有的见机行事、说转就转,以谋取生存之道。话虽如此,就读大学中文系出身的诗人作家依然占大多数,如留学生∕新移民中的张奥列、庄伟杰、千波、毕熙燕、小溪、王世彦、施国英、如冰、林茂生、许耀林、张劲帆、刘放、陈积民等,他们出国前已是此道中人。艺术类出身的也不在少数,如吴棣、沈嘉蔚、塞禹、胡涛、苏珊娜等,前四人是颇负盛名的画家,后者原为舞蹈演员。罗宁、微风、吴景亮、桑妮、辛夷楣等是从事新闻的,林达、蔡子轩、舒欣、王云梅等是学外语出身的,西贝、未来、沈志敏、田地、林木、干旻辉、雪阳、璇子等是学理工科的,萧蔚、黄平等是从医的,凌之、莫梦、曼嘉、柴惠庭等分别就读哲学、经济、教育、历史。澳华诗人作家中由于前后经历的变化迥异,尤其是个人的禀赋和爱好使然,个别诗人作家乃属“多栖人”。回眸巡视,来自大陆、港台和东南亚文化背景的众多老一辈或早期的诗人作家,知识结构和层次不尽相同,大多高学历,文化修养深,心理素质高,视野眼界宽,他们以历炼的人生经验,严谨踏实的写作参与澳华文学的开创进程。此外,还有一个早年居澳或土生的华裔学者群,大多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并任职澳洲著名大学,如陈顺妍、萧虹、刘渭平,南澳的徐家祯等。
由于专业知识的积淀和所从事的职业不尽相同,形成了各自相对较为稳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造就了他们在知识结构上的宽泛性和现代性。然而, 由于知识结构的先入为主或浸染,也直接影响到澳华作家的艺术想象力和思维方式,乃至影响到他们的创作意象、创作构成和艺术表达力。譬如,学理工科出身的作家,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的基础训练可能较为扎实,作品里更注重写实的成分,观察和思维趋于细密精确。学文史科出身的作家,作品里更偏重于自我意识、内心世界和历史感等方面的开拓,形象思维和虚构想象的能力相对突出。学者型出身的作家,在文化趣味、文化底蕴、文化品位上也有明显的优势。这一情景,在美加和欧洲也大致如此。
三 地域经验与文化书写各具特色
对东南亚华文文学而言,如果说以儒释道为文化背景是其源流之所在、庞大的华人群落是其产生的缘由,而多重的生活体验乃是华文创作主体的内驱力的话,那么,被称为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即华文报刊、华文教育、华人社团则是其走向发展和繁荣赖以生存的根基。
由于来自诸多方面的种种原因,东南亚华文文学有其明显的共同特征,都在蕉风椰雨中生长起来,自然带有浓郁的南洋人文风情特色,但这只是调色,其底色依然是华夏文化,二重色调加之作家的生命本色,这“三大原色”共同交互协奏成其独具风格和色彩的韵味。但作为一个离散族群,文学书写不仅只是个人化创造也是社会化的行为,加上文学跟所处的地域空间、文化背景、生存状态等无法分开,因而不同地域不同生存经验的华文写作所体现的历史意味、美学特色、文化品位和价值取向不尽相同。这些,只要从其文本、文存、文情、文风等方面加以考察,便可发现其中的差异,也因为存在的差异性而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化生态链。因此,不同地区的华文文学自有其独特的性格、色泽和风貌。发展态势较为乐观的马华文学、新华文学、菲华文学、泰华文学如此,整体格局较为薄弱的印(尼)华文学、文(莱)华文学及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亦然。它们不仅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文学与文化价值和意义,而且具有迥异于母体文化(中国文化)的独特风韵和气质。
不言而喻,在华文文学世界的整体格局里,东南亚华文文学首当其冲地扮演着一个接受着多种文化浸染的文化角色,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值得探讨研究的意义。相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它应是一种变了形的“文化输出”所生成的开放性文化,它独处于地球的东南一隅,在异质土壤上、在自己的领地内尽显风光,仿如其它地区(海外)的华文文学一样,依仗着同一种语言符号,闪烁缤纷于每一个特定的地域时空,其历史地位和产生的意义与作用固然有轻有重,却同样存在着一种不尴不尬的境况,似乎是个十足的异类。
文化输出的同时,伴之而来的必然是不同文化的冲突,其结果可能产生一种怪胎,也可能产生一个崭新的优良品种,或诞生一个美丽的宁馨儿。诚然,东南亚的华人自从踏足这片热土之后,其身份指认可能已随之发生变化,而且已逐渐成为所在国(地缘)的国民(公民),我们通常称之为“南洋人”或“华侨”或“海外华人”等,但是无论如何,本质上(血缘)依然是黑眼睛黄皮肤龙的传人,依然保持着华族文化固有的主要特点,尽管游荡在中国文化大地的边缘。因此,当代东南亚华文文学作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南洋文化现象,既不能说已全盘洋化,也不能仅仅定位于传统中华文化层面上,而是一种文化杂交的典型,即已经受了蕉风椰雨的浸染和侵袭,经历了“南洋化”的过滤和融合过程。所谓东南亚华文文学(或称之为南洋文学或亚细安文学),从时空两个方面来加以定位,大体都可以成立。基于以上认识,我们不妨从野生植物、杂交品种、南洋特产这三种不同主要表现形态,来观察一下东南亚华文文学在殖民语境和后殖民语境中,如何从文化失根的跋涉到文化杂交品种的生成、乃至走上文化整合的转向的曲折发展过程,加以一番勾勒:野生植物——流散族群在语言与文化上所面临的一种危机意识和失根状态(边缘性形态);杂交品种——南洋风味、中华文明、西方色彩、商业文化等相揉互混生成的杂交文化品种(混杂性形态);南洋特产——具有地域色彩或南洋本土特色,甚而转向文化整合的文学图景的建构与形成(本土性形态)。这三种主要形态的展现及其嬗变过程,或许可以为我们理解、感知和把握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存在方式和特色提供有益的思考和阐释可能。当然,要从总体上去把握其人文精神、内在特质和来龙去脉,还得深入到具体个案、文本和不同时期的文学现象中作深入的探析。
对于当代东南亚华文文学而言,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在全球化语境中,作为一种文学存在,可以说是既面临着新的机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这种挑战更多的是来自于文学本身,即文学的内部空间结构上,其指向明显的是需要创新和突破,才能更好地发展。譬如应如何处理、对待和协调中国(文化)性因素、本土性特色和人类性关怀等几个方面的关系,在不断反思中重新思考和酝酿新的文学生长空间,等等。如是,华文文学的东南亚就有可能在新世纪里迎来更为理想的新收获。
如果说地理学视野中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由于所处的是东方文化区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华文化的辐射影响,包括当地的土著文化,均呈强势之态,以至于当地华人在与他族社会平等相处中也不乏“同化”他族的心态;那么,澳美欧华文文学则完全处于西方强势文化语境下,俨然处于边缘地带生长的一种少数民族(裔)文学,虽不被完全同化,却呈现出明显的文化交融性和混杂性。因此,漂泊感、无根感、历史感和乡愁情绪在以新移民为主体的华文作家笔下,成为文本叙事的主线和基调。至于那些土生土长的海外华人作家,由于从小浸染在西方文化氛围中,社会环境和接受教育的西化色彩使然,他(她)们的观念意识和思维方式已不同于第一代移民,于是面对父辈文化传统和异域文化形态,驱使他们必须做出艰难选择和文化心理调整,其呈现的文本书写形态更多地趋向于跨域性、异质性和流散性,作品大多表现异质文化语境中华人社区的生活场景和心态,且包孕丰富的中华文化底蕴。甚或通过对海外华人众生相的文化书写,从中揭示人们普遍关注的族裔、文化和人性问题,等等。譬如,以美国为代表的澳美欧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典型的移植文学,在空间位移上具有远离中国大陆的地域优势,而置身于多元文化的宽容氛围里,使得华文作家总是立足于跨文化视野,书写想象中的故国家园和异域风情。同时,更加冷静、客观地看待大陆文化机制及其中华文化。这些在华裔美国文学谱系中尤为清晰可辨,而且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风貌庶几可以窥见。据不完全统计,迄至为止起码有20多部华裔文学作品,要么获得美国重要奖项,包括美国图书奖、美国诗人学会奖、美国书籍评论界作品奖、百老汇剧本奖等;要么位居美国畅销书榜,受到美国评论界好评。可以说,无论是从地域经验出发,还是从文化书写形态的展现,华裔美国文学已逐渐被美国主流社会所认同和接受。当这些被译为中文,“重返”华文世界,有人认为,这是延续了当年林语堂作品在两大世界(英语世界和华文世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探索之路。透过华人作家作品,我们发现,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这种流散写作,从上世纪之初开始,就依次在东南亚和美欧澳这两个区域形成高峰,并彼此表现为“潜性互动”。
由于同属于海外华文文学的这两大区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上存在很大差异,体现在地域经验和文化书写上同样迥然有别,泾渭分明。东南华文文学渐进的单一文化身份,以一种“只要是落地生根的地方,便是自己的家园”的心态,去寻求跟居住国文化的认同,从而形成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移民文学那种“落叶归根”式的书写形态,从无根到寻根再到恋根,然后走向“落地生根”的文学书写。相比之下,散居美欧澳各地的华人在数量上较为稀少,其华文文学无论是发端、基础和氛围,还是积累和辐射面都相对薄弱,即先天条件有所欠缺。然而,这些地区的华文作者中留学生众多,技术移民不断递增。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是从大陆、香港和台湾直接移居而来的。在某种程度上,美欧澳新移民文学似乎更接近于纯粹的中国文学。如果我们称东南亚华文文学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一个重镇,那么,美欧澳则可看成是21世纪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心。它的兴起,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富创造性的探讨对象和新的学术空间,而且“有可能为比较文学提供一系列新的视域、新的对话模式、新的融合和超越的机缘。”因为“海外华文文学在各国‘旅行’、‘居住’,开花结果,生成、发育、发展的条件、土壤很不一样,对它在各个国家、地域的起点、传播、中介、影响、融合、变形等等的追问,就极具比较文学的价值和意义。”[6]4
四 余论或新的思考
将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澳美欧华文文学在比较诗学层面上的考量,有助于我们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整体性视野的拓展。
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特别重视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语境,考辨诸多因素的相互影响及其转换过程,以融通开阔的视野对研究对象进行还原整合及价值判断,这种突破局部性的分析而走向整体性通观的治学精神颇具启示意义。或许我们需要回到整体文学场,回到文学场的整体上来。从第一层面看,应对华文文学和现状有一个全面、清晰、准确的认识与判断;从另一层面看,研究者应对自己的研究和所论述的问题及使用方法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把握。如果畸重畸轻而导致生态失衡,对推进学术研究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
长期以来,国内的学者与海外的学者在文学研究方面存在一定的分野,前者强调板块结构式的区别,后者注重打通空间式的融合。譬如对世界文学的研究,我们有中外区别;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我们有中国大陆文学、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区分。这种规定的主要依据是研究对象的身份不同。即便是研究同一语种的海外华文文学同样如此。如果我们从双向互动的角度,重新审视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与世界性,就可能有助于我们疏通文学研究的空间分隔,淡化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分界。其实,包括东南亚华文文学和澳美欧华文文学创作在内的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在中国学者的眼中都常常被中国化,并在有意无意间,可能已受到国外学者和西方理论思潮带有他们各自独特的背景和观点的影响,加上中国学者多从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和视角去分析、鉴赏和评述,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对整体的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在某些方面的先入为主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探讨能放置于一个多元化研究的系统坐标上,那么,对作家和文学文本的解读,就能在“世界性”的系统中加以实现。因为,一个作家的世界观、一种文学的世界性,恰恰在于能够为包括该民族在内的全人类提供值得共同关注的文学创作特征。一个伟大作家首先是属于本民族的,但又是具有世界意义或属于世界性的。尤其在全球性多元文化语境中,对于文学研究的世界性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如是,我们的研究才能从多样共生的思维方式出发,并在双向或多向的互动中加以透视和立体展开。这对于包括海外华文文学在内的文学研究同样是适合的。
参考文献:
[1] [澳]庄伟杰.流散写作、华人散居和华文文学[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3).
[2] 饶芃子,费 勇.东南亚华文文学简论[M]∥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 王列耀.东南亚华文文学:华族身份意识的转型[J].文学评论,2003,(5).
[4] 骆 明.在世界格局中的东南亚华文文学[M]∥期望超越——第十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讨论暨第二届海内外潮人作家作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5] 陈 辽.略谈东南亚华文文学[M]∥公仲,江冰.走向新世纪——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6] 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新视点——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M]∥刘中树.世界华文文学的新世纪——第十四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选.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