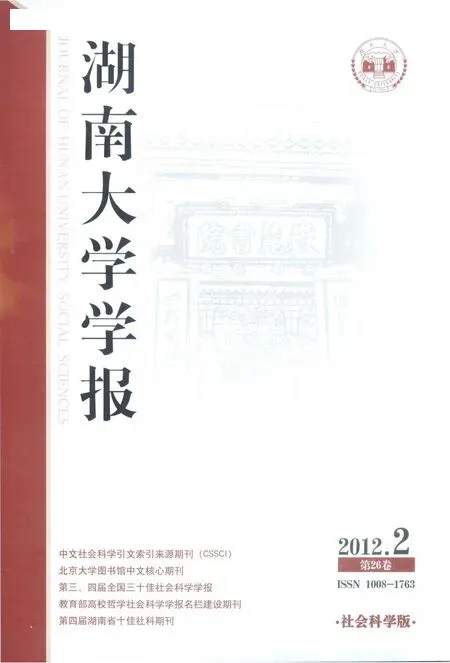王一庵平民儒学思想析论*
2012-04-08贾乾初陈寒鸣
贾乾初,陈寒鸣
(1.山东大学 威海分校 法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2.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天津 300170)
王一庵平民儒学思想析论*
贾乾初1,陈寒鸣2
(1.山东大学 威海分校 法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2.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天津 300170)
王一庵尽管晚年做过低微的下级教育官员,但就其一生行谊来看,仍属泰州学派平民学者。他继承了心斋之学,并在诚意慎独方面有自己的新发展。一庵的诚意慎独之学是他平民儒学思想的理论依托,“自强”“法天”观念彰显了一庵平民儒学思想的主体意识,“随分而成功业”体现了一庵平民儒学思想的事功观。一庵以讲学集会为实现其平民政治理想的主要手段。这种手段的苍白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觉民行道”的“外王”取向,始终徘徊于“内圣”内涵的边缘上,难以真正向外拓展。
王一庵;诚意慎独;主体意识;平民儒学;觉民行道
王一庵(1503—1581),名栋,字隆吉,号一庵,泰州姜堰人。他以族弟的身份师事王心斋(艮),是泰州学派的第一代嫡传弟子,后来学者将之与王心斋、王东厓(襞)父子并称为“淮南王氏三贤”或迳称为“淮南三王”。亦有将之与王阳明、王心斋并称为“越中淮南三王夫子”①《王一庵先生遗集》卷首《年谱纪略》(附出处事迹),东台袁氏编校本。者,有《一庵王先生遗集》传世。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一庵之学概括为主要两端:“一则禀师门格物之旨而洗发之”,“一则不以意为心之所发”。②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第7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意谓一庵认同了心斋之学的“格物”说并有发展,且一庵在“诚意”方面有新创造。黄氏所勾勒出的一庵之学总体面貌,为学界基本认同。总体而言,一庵充分继承了心斋之学,但同时又有自己的新发展,如吴震研究一庵思想后指明,一庵之于心斋的思想关系,大略可用“受格物之旨”、“得家学之传”二语来定格,然而一庵在“从格物认取良知”方面、尤其是诚意慎独方面,都有着自己的创新和贡献。③吴震:《泰州学派研究》,第247页,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因之,他将一庵之学直接定位为诚意慎独之学,无疑是精准的。我们这里主要立足于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主流,据此来讨论一庵的平民儒学思想,希图藉之深化对一庵思想价值的认识。
一 游走于士绅与平民之间的王一庵
余英时先生曾说,王阳明“龙场悟道”所暗示的理学内在转捩,从政治文化角度探析,暗示出阳明由“得君行道”向“觉民行道”的路向转移。“明代理学一方面阻于政治生态,‘外王’之路已断,只能在‘内圣’领域中愈转愈深。另一方面,新出现的民间社会则引诱它掉转方向,在‘愚夫愚妇’的‘日用常行’中发挥力量。王阳明便抓住了这一契机而使得理学获得了新生命。”①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第196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不可否认,此时的王阳明作为遭贬的官员,这一转移有其不能“得君行道”的外在政治环境触发的原因——“良知”学说的出现当然与王阳明的个人政治际遇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觉民行道”或“以道觉民”路向一开,且这路向又恰开启于中古社会晚期母体内部商品经济孕生,及新兴市民阶层跃登社会历史舞台之时,遂使得阳明学于明代思想史上独放异彩,培育出诸多“躬行实践”、“英雄莫比”的思想人物。
一庵的老师王心斋,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由心斋本其一介布衣身份而开创的泰州学派,在“愚夫愚妇”的“日用常行”中所做“以道觉民”的工作,在实践中极大地推展了阳明学的这种转向。由士绅儒学到平民儒学,王心斋和他创立的泰州学派,凸显了强烈的个性特征。“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泰州以外的王学,都是一个近乎封闭的士大夫群体,他们并不热衷于向平民宣教。”②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第22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因之,泰州学派立足“百姓日用”的平民儒学指向,在阳明后学中,特色鲜明,且形了自身的传统。这一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其一,传道对象大众化;其二,儒学理论简易化与儒学经典通俗化;其三,心性自然化;其四,传道活动神秘化;其五,社会理想道德化。③陈寒鸣:《论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河北学刊》1993年第5期。一庵作为心斋的第一代嫡传弟子,很好地继承了上述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传统。
与阳明、心斋坎坷的人生遭际不同,一庵的生平没有极端的波动。他既不像阳明那样由仕宦生涯而事功显著,也不像心斋那样将布衣身份保持终生。而是游走于士绅与平民之间。
一庵父名王赞,号伯林,业医。一庵七岁时受父命“习举子业”,但“时年十有一岁,遇瘟疫流行,奉先公命,备药材,施救村镇。一日行至沙村庄,遇马噬啮,几为所伤,仍命业儒。”④《王一庵先生遗集》卷首《年谱纪略》(附出处事迹),东台袁氏编校本。经过这番曲折,一庵回归业儒的正途。据《年谱纪略》载,嘉靖五年(1526),一庵24岁时,补郡庠生,师事阳明弟子泰州知州王瑶湖(名臣,字公弼,号瑶湖,生卒年不详);嘉靖六年(1527),一庵食廪饩,与林东城(名春,字子仁,号东城,1498—1541)一同师事其族兄王心斋,“受格物之学,躬行实践,久遂有所得”⑤《王一庵先生遗集》卷首《年谱纪略》(附出处事迹),东台袁氏编校本。。自嘉靖三十七年(1558)56岁至隆庆六年(1572)70岁致仕回到泰州,一庵作基层教育官员有14年之久。先后任江西建昌南城训导、山东泰安州训导、江西南丰教谕、北直隶深州学正等职。任职期间,一庵以主持书院事务、大开讲会为主要活动。他先后主讲白鹿洞书院、正学书院,创太平乡讲会、水东大会等讲会,“集布衣为会”、“名动当道”,产生了极大影响。“致仕归里,清贫如洗。乐学不倦,开门受徒,远近信从日众。创归裁草堂,著《会语续集》行於世。创《族谱遗稿》以睦族人。”“主会泰山安定书院,朝夕与士民论学,四方向风”。⑥《王一庵先生遗集》卷首《年谱纪略》(附出处事迹),东台袁氏编校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庵讲会论学以“布衣”即平民为主要对象。他逝世前对后人嘱咐,也仍然是“会学一事”而已。可见,平民教育信念在一庵心目中所占地位。
《年谱纪略》所谓“志切高尚”、“清介”、“贫穷如洗”、“乐学不倦”诸语,大略勾勒出了一庵的人格风范。其中所记述的事迹数则,尤可见一庵对所受心斋格物之学,在百姓日用中的“躬行实践”之处:
先生事亲最孝,先公性刚直,一日与内不合即外居,先生废寝食,泣拜三日劝归,使父母欢悦。每事几谏,不听则拜,务谕亲于道乃止。⑦《王一庵先生遗集》卷首《年谱纪略》(附出处事迹),“嘉靖十九年”条,东台袁氏编校本。
时署县事,有胡姓兄弟告争家财,先生谕以难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土,动以一本至情,胡感悟,兄弟泣拜,归复共曩,终身永翕,俨然苏公下泪,殊有感谕之风焉。⑧《王一庵先生遗集》卷首《年谱纪略》(附出处事迹),“嘉靖三十七年”条,东台袁氏编校本。
时置丰事,有一寡妇子某,太学生,罪诬大辟。先生感渠寡母曲全之,私报数百金,概置不顾。⑨《王一庵先生遗集》卷首《年谱纪略》(附出处事迹),“嘉靖四十五年”条,东台袁氏编校本。
初擢深州,接邸报,丰有乡达某嘱先生曰:某向知深州积金一罂,忘持归,如署州事可取之。后先生果署州事,竟不理,及老归田里,终身不齿其事。(10)《王一庵先生遗集》卷首《年谱纪略》(附出处事迹),“隆庆五年”条,东台袁氏编校本。
一庵于孝道,可谓煞费苦心,模范践行。除如《礼记》所教“几谏”的办法之外,他还要“谕亲于道”才算到位。心斋之学尤重践履,对“孝弟”的高度重视是泰州学派、尤其是心斋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心斋看来,“孝弟”绝非只基于伦理学的考量,故其“以孝弟为教”实彰显了他所认可的“外王”取向,此确如吴震所说,“心斋有关孝弟的思考不仅有伦理学的解释方法,更有社会学、政治学的分析视野”(11)吴震:《泰州学派研究》,第183页,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而一庵恪遵古礼,事亲至孝,“谕亲于道”的切己践行,非惟是对心斋“格物之旨”、“孝弟之实”有深切领会,更重要的应该是他能领会心斋重视“孝弟之教”的社会、政治意涵或曰“外王”取向。如此,则一庵处理胡姓兄弟争家财之事,以兄弟至情“感谕”教化之的做法,其高度认同“孝弟之教”的切实思想根源便可明了于心了。至若视金银如无物,就更能说明一庵在“修身立本”方面践行得非常之好。如他申述自己的理解说:“先师原初主张格物宗旨,只是要人知得吾身是本,专务修身立本,而不责人之意,非欲其零零碎碎於事物上作商量也。”①《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续集》,东台袁氏编校本。如此“修身立本”,正是践行心斋的“格物之旨”。
王一庵与林东城同时投师心斋,属心斋第一代弟子中及门时间较长者,但二者的人生取向却不很相同。东城嘉靖十一年(1532)举会试第一后,大部分时间在京为官,直至卒于吏部文选司任上,所交游者率皆士绅名流。就心斋开创的泰州学派平民儒学主流而言,林东城显然背离了这个传统,完全成长为士绅之儒。一庵则与之不同。尽管他晚年亦走上仕宦之途,但据年谱所记,一庵与士绅名流的交游寥若晨星,语焉不详,惟“集布衣为会,兴起益众”、“开门受徒,远近信者日众”②《王一庵先生遗集》卷首《年谱纪略》(附出处事迹),东台袁氏编校本。的记录清晰可见。如上文所言,一庵的教育对象主体是“布衣”即平民,显然他是十分认同心斋教化“鄙夫俗子”的平民教育路径的。如他说:
自古士农工商,业虽不同,然人人皆共此学。……天生我先师,崛起海滨,慨然独悟,直超孔子,直指入心,然后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灵、自完自足,不假闻见、不烦口耳,而二千年不传之之消息一朝复明,先师之功可谓天高而地厚矣!③《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正集》,东台袁氏编校本。
故而,一庵虽然游走于士绅与平民之间,却未可遽以“士绅之儒”目之。邓志峰认为,“王栋的一生,是一个有恒心而无恒产的士,为了自己的道德理想,步履维艰的一部辛酸实录。”④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第21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栋是那个朝代从事讲学活动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⑤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第21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可以想见,王一庵长期但任基层教育官员,并且“清贫如洗”,在士绅圈子当中,不会有很大市场的。大约这也是《年谱纪略》对于他与士绅名流交往记述阙如的原因之一。一方面,享年79岁的一庵,一生只有14年担任基层官职低微的教育官员;另一方面,他的讲学活动的主要对象又以“布衣”为主;再加上他继承了心斋的平民儒学思想,就此而言,我们认为一庵堪称继心斋杰出的“平民儒者”。
二 “诚意”、“慎独”之学与一庵的平民儒学思想
(一)“诚意”、“慎独”说:一庵平民儒学思想的理论依托
王一庵在心学理论上的新创造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诚意”、“慎独”说方面。他对《大学》、《中庸》中的“诚意”、“慎独”进行了富有个性特征的新解释:
诚意工夫在慎独。独即意之别名,慎则诚之用力者耳。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动之处,单单有个不虑而知之灵体,自做主张,自裁生化,故举而名之曰独。少间才以见闻才识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则是有所商量倚靠,不得谓之独矣。世云独知,此中固是离知不得,然谓此个独处,自然有知,则可谓独我自知、而人不及知,则独字虚而知字实,恐非圣贤立言之精义也,知诚意之为慎独,则知用力於动念之后者,悉无及矣。故独在《中庸》谓之不睹不闻;慎在《中庸》谓之戒慎恐惧,故慎本严敬、而不懈怠之谓,非察私而防欲者也。⑥《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正集》,东台袁氏编校本。
依据这种新解释,“慎独”体现的是“诚意”工夫。因为“意是心的主宰”,而“独”却是“意之别名”,换言之,“慎独”正是体现的“诚意工夫”。一庵将“诚意”与“慎独”做此种打通解释,显然是沿着心学主体意识的高扬与标举道路,予以进一步的推展。他强调“有所商量倚靠,不得谓之独”,本体有“意”作“心之主宰”,“自作主张”、“自裁生化”,焉用“商量依靠”!这是一庵平民儒学思想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依托。
对这个理论依托,一庵论列颇多。除重点指出“诚意工夫在慎独”之外,尚有如下数端。
1.诚意是立本工夫
一庵强调“诚意二字,正吾人切实下手立本工夫”,他分析说:“格物知至,方才知本在我,本犹未立也,故学者既知吾身是本,却须执定这立本主意,而真真实实,反求诸身,强恕行仁,自修自尽,如此诚意做去,方是立得这本。若只口说知本在我,而於独知之处尚有些须姑息、自诿、尤人、责人意念,便是虚假,便是自欺。自欺於中,必形於外,安得慊足於己而取信於人乎?故诚意二字,正吾人切实下手立本工夫,方得心正身修,本可立而末可从也。”⑦《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续集》,东台袁氏编校本。
2.诚意立本则心有所主
“诚意”既然是“修身立本”的大节目,然而“诚意”作为“切实下手立本工夫”,其“切实”处何在呢?一庵联系“正心”指出,诚意立本则心有所主。他在答人问“诚意既足以立本矣,何复有正心工夫”时,指出:“这却只是一串道理,意是心之主,立本之意既诚,则心有主,故不妄动,而本可立、身可修。若自家不曾诚意立本,而望施之於人,侥声感应,皆是妄想,皆是邪心,皆是中无所主,憧憧往来病痛。故意诚而后心正,非於诚后复加一段正心工夫也。”⑧《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续集》,东台袁氏编校本。
3.敬在诚意中
一庵在答人“主敬不如主诚乎”的疑问时说,“今只泛言敬则中心有主,不知主个甚么?将以为主个敬字,毕竟悬空无所附着,何以应变而不动心乎?吾辈今日格物之学,分明是主修身体,诚意是所以立之之功,不说敬而敬在其中。盖自其真实不妄之谓诚,自其戒慎不怠之谓敬。诚则敬,敬则诚,其功一也。”①《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续集》,东台袁氏编校本。
由上可知,一庵将诚意工夫解释得相当浃洽,这些解释显然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吴震指明,在一庵这里,“诚意工夫可以一揽子解决身心问题、本末问题(包含家国天下)。格物问题也自然可以由诚意工夫来解决,也就是说,反身立本的格物工夫有赖于诚意工夫,而诚意工夫又必须首先立定一个吾身是本的‘主意’,因此‘意’就成了所有问题的关键。”②吴震:《泰州学派研究》,第250页,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在我们看来,一庵高度重视“意”的理论阐释,除彰显了他在心学理论上的新发展外,以此为机窍,强化主体意识,强调主体的把捉,透显出了一庵平民儒学思想的立脚之处。换言之,一庵的诚意慎独之学是奠定了他平民意识的理论基础。
(二)“自强”“法天”:一庵平民儒学思想的主体意识
一庵的时代是儒学日趋世俗化的时代,人们的正常欲望被逐渐肯定,心学的发展亦体现此时代脉搏,而又不断发展变化。③所以如此,显然与其时商品经济的孕生及与之相适应的新兴市民阶层跃登社会历史舞台密切相关。明乎此,才能埋解阳明“四民并业而同道”之言及由此而开启出的儒学世俗化、大众化的发展新路向。而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则是这路向上必然会有的思想成果。立基于普通百姓立场而倡发平民儒学的泰州学派,更充分肯认人们的合理欲望,反对一味的“灭人欲”说教。这使其与处于官学地位的程朱理学迥然有别。一庵于此亦多有阐发。如谓:
孟子言:“养心莫善於寡欲。”荀子却言:“养心莫善於诚。”非但不识诚,亦不识养字之意。人心一觉便是真体,不善养之则有牿亡之害。故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所必不能无者,一切寡少,则心无所累,得有所养,而清明湛一矣。此非教人於遏人欲上用功,但要声色臭味处知所节约耳。④《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正集》,东台袁氏编校本。
他认为,“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作为“人所不能无者”,是人的基本生理欲望,只要“一切寡少”“心无所累”“得有所养”,最后达于“清明湛一”便好。所以,于“人欲”上,关键不是在“遏”,而是在“节约”,或者是言“寡”。一庵又借辨明孟子、周子所言“欲”含义的分别而阐述道:
孟子止言寡欲,周子遂说寡焉以至於无,此非其养心者有疏密之异,特二公所指欲字之意不同。周子以心之情私感物而动者为欲,故不得不谓之无;孟子以身之形气应迹而迷者为欲,故不得不谓之寡。读者不以辞害义可也。⑤《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正集》,东台袁氏编校本。
因之,一庵旗帜鲜明地指出:“察私防欲,圣门从来无此教法。”⑥《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正集》,东台袁氏编校本。既然“圣门从来无此教法”,何以先儒们都从“察私防欲”这个从来没有的教法上用功呢?问题出在大家对于“克己”的理解存在问题。一庵说:“先儒莫不从此进修,只缘解克已为克去已私,遂漫衍分疏,而有去人欲、遏邪念、绝私意、审恶几,以及省防察检纷纷之说,而学者用功,始不胜其繁且难矣。”⑦《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正集》,东台袁氏编校本。那么,圣人所讲的“克己”究竟应如何理解呢?念庵指明,这里的“己”是指的“身”,而不是“身之私欲”。他说:
然而夫子所谓克已,本即为仁由已之己,即谓身也,而非身之私欲也;克者力胜之辞,谓自胜也。有敬慎修治而不懈怠之义,《易》所谓自强不息是也。一息有懈,则焰然而馁矣。夫天,阳也,刚也。《易》之乾卦,著阳刚之德也。故乾以自强言之,示天下以法天之学也。告颜子而以克已言之,示颜子以体乾之道也。⑧《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正集》,东台袁氏编校本。
这样一来,“克己”被一庵解释为“自强”“法天”的积极行动,而不是“察私防欲”那样的消极作为。显然,一庵对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将“己”理解为“身之私欲”的观点,是持明确的批判态度的。
在“克己”的理解上,从朱子等人“察私防欲”的消极作为,转变为一庵解释的“自强”“法天”的积极行动,是否显示出士绅之儒与平民儒者思维方式上的某种差异?无论如何,藉此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确存在着宋明理学从“得君行道”的期许,到“觉民行道”的担当之间的变化消息。人的基本生理欲望是“人所不能无者”,与其纠结于此,何如一意担当而“法天”“自强”?这里无疑再次显示了平民儒者无所倚待的主体意识。个人主体意识的不断成长与发展,的确是心学发展的重要枢机。
在此种理解的基础上,王一庵充分继承了泰州学派平民儒学的宗旨。
(三)随分而成功业:王一庵平民儒学思想的事功观
一庵明言:
吾人为学不屑与乡里庸众之人共为之,终是自小。⑨《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正集》,东台袁氏编校本。
他举例认为,“大舜之所以为大”,是因为舜“善与人同”,“不独自为善”,故而“与会为善,而使人人同得乎善,乃见其为善之大,正与天下化于孝,此之谓大孝一例。”(10)《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正集》,东台袁氏编校本。这里,举大舜为例,一庵表明了泰州平民儒学的一个重要立场:
虽耕稼陶渔之人,凡有向上之志、可接引者,皆可取也。(11)《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正集》,东台袁氏编校本。
心斋泰州学派门下正是如此,如农人夏廷美、樵夫朱恕、陶工韩贞诸人出身为“耕稼渔樵”的平民儒者,并皆传世,可称卓荦。一庵更强调说:“鄙夫虽气质凡庸,而良知本性未尝不与贤知者等,故圣人必竭两端而告之,非但良知人人自明,抑道本愚夫愚妇可以与知。举其至近而远者,自寓乎其中耳。”(12)《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正集》,东台袁氏编校本。他在此指出了两点:一是就良知本性上来说,鄙夫与贤者同;二是道(即良知)本来就是愚夫愚妇可以与知的。换言之,在良知本性面前,贤者与鄙夫平等,前者不存在什么先在的优越性。
反观孔门,一庵认为平民教育本是孔门传统,只不过是被秦汉以还的经生文士们给破坏了。在他看来,孔门教法是兼收并蓄,且各就学生材质大小,“造就曲成”之。此教法需要“有道君子”的担当与包容。一庵道:
孔子欲得中道,而狂狷亦在;所思乐育英才,而鄙夫亦堪叩教。故包蒙藏疾,不弃一人;庸众三千,兼收并蓄。夫然后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造就曲成之盛,乃至七十余士,如造化之生物不息,而品物成章也。有道君子欲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则必有包容荒秽之量,然后可以收董陶长育之功。①《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续集》,东台袁氏编校本。
也正是在恢复孔门平民教育传统的立场,慨然以师道自任上,一庵高度评价了其师心斋的崇高地位,认为心斋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使“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灵、自完自足”的平民教育功绩。宜乎邓志峰将一庵判作继承心斋泰州“以师道为己任”主脉的“师道派”嫡传②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第21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按:邓志峰认为,王东厓(襞)虽承心斋家学,但仔细体认,东厓无论在思想还是行动上,都与乃父心斋相去悬绝。东厓实则受王龙溪(畿)影响甚大。邓著第284—292页。。
尽管一庵在实际行动方面无法与其师心斋相比,但他由是而形成了自己的“事功观”:
圣人经世之功,不以时位为轻重。今虽匹夫之贱,不得行道济时,但各随地位为之,亦自随分而成功业。苟移风易俗,化及一邑一乡,虽成功不多,却原是圣贤经世家法,原是天地生物之心。③《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续集》,东台袁氏编校本。
他认为,作为一个“虽匹夫之贱”的平民儒者,在“不得行道济时”的情况下,只须“各随地位为之”,便也可“随分而成功业”。扎扎实实地以自己的努力,使“一邑一乡”移风易俗,即便成功不多,也是体现了“圣贤经世家法”,尽了“天地生物之心”。
由此来看,一庵这种“事功观”所表明的平民儒者扎实的践履,一方面沿着王阳明以来心学“觉民行道”的转向,继承了王心斋的平民儒学传统,称其为贯通二王并不为过;但另一方面,相比于其师王心斋周流天下,赤身担当,慨然以师道为己任的宏大气象,一庵这里无疑显得有些无奈和无力。事实上,尽管一庵大兴布衣集会,讲学不已,但其身后再传无闻,连他自己和学行思想也险些被历史的尘霾所淹没。如此状况,实乃专制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必然结果。反观近世,梁漱溟诸先辈倾心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不也无果而终吗?古今同然,个中消息,实堪体味。
三 王一庵的平民政治理想
一庵平生学行,以集结同志、开门受徒、兴办讲会的平民教育活动为首要,以至临殁遗言,也念念不忘“会学”。盖以“布衣”为对象的讲学集会为实践其平民政治理想的主要手段而已。这一点与其师心斋一脉相承。
检一庵所著《会语正集》与《会语续集》,他于讲学过程中大力发挥了心斋的“淮南格物”与“安身立本”之学。
一庵概括心斋之学说:“先师《乐学歌》,诚意正心之功也;《勉仁方》,格物致知之要也;《明哲保身论》,修身止至善之则也;《大成学歌》,孔子贤於尧舜之旨也。学者理会此四篇文字,然后知先师之学,而孔孟之统灿然以明。”④《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正集》,东台袁氏编校本。他以《乐学歌》、《勉仁方》、《明哲保身论》、《大成学歌》四篇作为心斋之学的代表作品,认为心斋之学继承了“孔孟之统”,并且有力地发挥了“孔孟之统”。一庵为心斋的嫡传高弟庶几不谬。
对心斋的“淮南格物”说,一庵予以大力阐明:
先师之学,主于格物。故其言曰:格物是“止至善”工夫。“格”字不单训“正”,“格”如格式,有比则、推度之义,物之所取正者也。“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谓吾身与天下国家之人。“格物”云者,以身为格,而格度天下国家之人,则所以处之之道,反诸和身而自足矣。⑤《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正集》,东台袁氏编校本。
格物原是致知工夫,作两件拆开不得。故明翁曰致知实在格物,格物乃所以致知,可谓明矣。且先师说物有本末,言吾身是本,天下国家为末,可见平居未与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即是未应时之良知。至於事至之物来,推吾身之矩,而顺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即便是既应时之良知。致知格物可分拆乎?况先师原初主张格物宗旨,只是要人知得吾身是本,专务修身立本,而不责人之意,非欲其零零碎碎於事物上作商量也。⑥《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续集》,东台袁氏编校本。
他复通过解释《大学》三纲领中的“止于至善”来发挥心斋的“安身立本”之学说:
先师谓止吾身於至善之地,使身安而不危,则能妙出处而动合时宜,制经权而行无辙迹,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然后保家保国天下,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而非断港绝河之学矣。⑦《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正集》,东台袁氏编校本。
又云:
先师以“安身”释“止至善”,谓天下国家之本在身,必知止吾身於至善之地,然后身安而天下国家可保,故“止至善”者,安其身之谓也。欲安其身,则不得不自正其身。其有未正,又不容不反求诸身,能反身则身无不正,身无不正则处无不安,而至善在我矣。古今有志於明德亲民,而出处失道,身且不保者,不明止至善之学故也。⑧《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正集》,东台袁氏编校本。
可见,一庵充分继承了心斋平民儒学的特质。侯外庐等先生所主编的《宋明理学史》深刻指出,心斋奠基于“淮南格物”基础上的“安身之本”之学,“在古旧的语言形式下,蕴含了争取人的生存权利和维护人的尊严的思想”,并且从中“推度出人己平等和爱人思想”。①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册,第439—4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我们之所以称一庵的政治理想为“平民政治理想”,正是由此出发的。
王一庵极为认同心斋以师道自任,“随处觉人”的“大成之学”。他说:“今学者苟知随处觉人,不徒善一身而已,虽不能为大成之圣,是亦大成之学也。此先师扩孟子所未发处。”②《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续集》,东台袁氏编校本。在他看来,在“君、师之职”已相违离的当下,毅然以师道自任,拿起被帝王抛弃的师教大权,奉行平民教育,乃是造成安定平和理想社会的根本手段。他说:
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师。自古帝王君天下,皆只师天下也。后世人主不知修身慎德,为生民立极,而君师之职离矣。孔子悯天下之不治皆缘天下之无师,故遂毅然自任,无位而擅帝王师教之大权,与作《春秋》同一不得巳之志。况不俟时位,随人接引,则杷柄在手,而在在成能,此其所以贤尧舜而集大成者,凡以任师道故也。观其汲汲周流,无非欲与斯人共明斯道,或上而君卿大夫、下而士农工贾,苟可以得其人,斯足以慰其望矣。孔,孟既没,世鲜能师。至宋周子曰“师道立而善人多”,程子曰“以兴起斯文为已任”,真得孔、孟任师家法,但不力主其说,以为运世承统第一事功。吾先师所以不得不自任也,而亦岂所得已哉?③《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续集》,东台袁氏编校本。
如此践行,则建立在血缘宗族之上的和谐社会政治局面是不难实现的。
那么,一庵认为如何实现他的平民政治理想呢?
首先,改善王政的四大方面:“井田”、“封建”、“肉刑”、“里选”。一庵指出,“王政之大端,莫要於井田、封建、肉刑、里选四者,今皆变坏而不可复矣。然限田可以救不井田之失,久任可以救不封建之失,严生刑而宽死则可以救不肉刑之失,先德行而后文艺可以救不里选之失。”④《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正集》,东台袁氏编校本。这显然深受其师王心斋在《王道论》中阐述的政治理想的影响。
其次,立师道,“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而“熔铸天下”。一庵在回答“使子为政亦能熔铸乎?”之问时说:“熔铸天下,必君相同德同心,方可整顿。此孟子所以不得行其志者也。若使得宰一邑而熔铸一邑,理亦有之,但恐监司者掣其手足、与迁转之速,则不能耳。然终是田制之偏、赋役之重,刑统滥於罚赎、学校弊於文辞,凡此皆关大政。熔铸,夫岂易!然古人之学不袭时位,吾将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使师道立,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此吾所以熔铸天下之一大炉冶,而非时位所能限也。”⑤《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续集》,东台袁氏编校本。简而言之,一庵认为以师道自任大兴斯文,是“熔铸天下”,实现理想政治局面的关键。
复次,从家庭、宗族的“劝善”入手,实行教化。一庵说:“吾人诚欲以善善世,必自有蔼然亲爱实意,先得其心,然后言易入而善易从也。如欲善父母,必亲爱父母,而得父母之心;欲善兄弟妻子,亦必亲之爱之,而各得其心。以至於宗族亲戚、朋友乡党,获上获下,莫不皆然。未有情意不孚,而教化可行者也。故君子亲得天下人,然后教得天下人。”⑥《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会语续集》,东台袁氏编校本。无疑,在一庵这里,由血亲情感出以发,以情感人,是“劝善”施教的教化工作取得理想效果的起点。一庵由是还写了不少浅白顺口的诗歌,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如他作诗劝人“尊敬长上”云:“天地生人必有先,但逢长上要谦谦。鞠躬施礼宜从后,缓步前行莫僭前。庸敬在兄天所叙,一乡称弟士之贤。古今指傲为凶德,莫学轻狂恶少年。”⑦《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二《乡约谕俗诗六首》,东台袁氏编校本。又劝人“教训子孙”云:“子孙有教是诒谋,失教还为祖父忧。不独义方昭训迪,更寻师友择交游。才须学也夸贤嗣,爱勿劳乎等下流。骄惰养成为不肖,败家荡产是谁尤?”⑧《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二《乡约谕俗诗六首》,东台袁氏编校本。
问题在于,尽管一庵继承了其师心斋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特质,作为一个平民儒者有区别于士绅之儒之处,然而,就其平民政治理想来看,仍无法跳出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桎梏,只能在小生产的生产生活条件下,做一厢情愿的空想和苍白无力的说教。此确如龚杰所指出的,王一庵“设想的‘士农工贾’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以‘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父慈子孝’、尊兄爱弟为‘乡约’,而达到‘邦家其昌’的‘安乐’景象,能否实现呢?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成功不多’,对此没有信心,说明他与泰州学派的许多学者一样,洞察明王朝所面临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教育上的严重危机,但又找不到出路,不得不在旧制度的深沟高垒中四处碰壁,辗转彷徨。这就是泰州学派基本的政治特征。”⑨龚杰:《王艮评传》,第228—229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毋庸讳言,从对王道大政的热切关注,到不无尴尬的试图以师道自任而“兴起斯文”,再到苍白的劝善诗,一庵的平民政治理想,与其师心斋一样,“百姓日用”推展开来的“觉民行道”激情,亦止于“百姓日用”所限定的底层精神格局。况且,一庵游走于士绅与平民之间,既无其师心斋的超凡魄力,更无同为泰州后学的颜山农、何心隐辈“异端”诸人的狂侠气象。概而言之,王一庵的平民政治理想乃至泰州学派“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王道政治理想,亦不过止于道德理想主义的空想而已。“以道觉民”的“外王”取向,始终徘徊于“内圣”的内涵边缘,难以真正向外拓展。它的宝贵思想内核和重要价值,还要到了小生产方式的“硬核桃”被彻底砸开之后,才能为我们所充分认识与分享。
On the Thought of Wang Yi-an’s Popular Confucianism
JIA Qian-chu1,CHEN Han-ming2
(1.Law School,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Weihai 264209,China;2.College of Tianjin Trade Union Administrators,Tianjin 300170,China)
According to his whole life,Wang Yi-an was a scholar of common people,although he once was a junior educational officer in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He inherited the thoughts of Wang Xin-zhai thoroughly and made new development in positive heart and restraining in privacy which was the base of his Confucianism of the popularity.The idea of self-renewal and according to the Heaven revealed his subject awareness.To establish accomplishments within fate was his view of achievement.Giving lectures and gathering adherents was the main way of achieving his political idea.The pale of this way show the fragility of external strength and internal holiness under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 in that time.
Wang Yi-an;positive heart and restraining in privacy;the subject awareness;Confucianism;fragility
B222
A
1008—1763(2012)02—0020—06
2011-05-10
贾乾初(1971—),男,河北沧县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山东大学政治学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