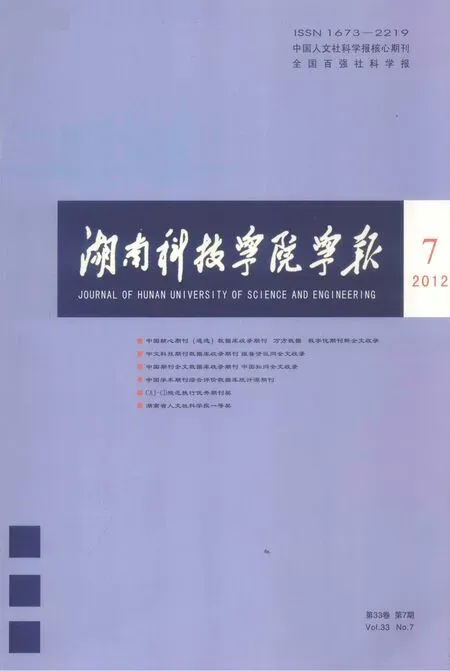灵魂的荒凉与拯救:杜拉斯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
2012-04-07黄雪莹姚锦莲
黄雪莹 姚锦莲
(钦州学院 中文与传媒学院,广西 钦州 535000)
灵魂的荒凉与拯救:杜拉斯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
黄雪莹 姚锦莲
(钦州学院 中文与传媒学院,广西 钦州 535000)
杜拉斯与张爱玲虽然是不同国家的作家,但是她们的作品却都关注人类的生存处境,揭示了人类灵魂的荒凉、道德的缺失、生命的无耐等主题,她们企图通过创作对人性的失落进行反思,探寻拯救日益堕落的人类灵魂的途径。
杜拉斯;张爱玲;荒凉;拯救;女性文学
一 引 言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和中国女作家张爱玲(1920-1995)属于同时代的作家,在20世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他们在不同的国度里走着相似的道 路。她们同样经历过痛苦的童年、漂泊的生活和创作的狂热,她们在缺失亲情的童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中真情写作。面对生命的无奈、命运的漂泊,她们最终都用自己珍爱的文学为自己构筑了灵魂的居所。
相似的人生经历使杜拉斯和张爱玲在创作中都不约而同地关注人类生存的处境,揭示人类灵魂的荒凉、道德的缺失、生命的无耐等主题。他们用心灵去写作,去揭示人性的丑恶,去拯救道德荒野中的人类灵魂。
二 灵魂的荒凉与绝望
杜拉斯与张爱玲的小说大都带有一些荒凉的背景、苍凉的色彩,以此衬托出他们笔下人物的痛苦与欲望,揭示出人物灵魂深处的绝望。
张爱玲的小说有一种“苍凉”的情调,她喜欢用意象,文笔细腻,语言清新干净而又透着沉寂、苍凉的意味。在张爱玲笔下的环境总是阴暗、灰色、荒凉的,如“灰色的破烂洋房”、“灰色的老式洋房”、“堂屋里暗着”、“阴森森高敞的餐室”、“弄堂里黑沉沉的”、“穿堂里空荡荡的”等等。有这些阴暗灰色、荒凉的空间还不够,张爱玲还在其间加了一些道具,如屏风、旧照片、胡琴(有时是口琴或长笛)、镜子等,造成一种新旧重叠的效果,使人似乎能从中感到时光的流逝,历史的变迁,但它们又分明并置在现代生活环境里,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股荒凉之气,云消雾散一般地在作品里弥漫开来。在这个荒凉的背景之上,她通过对人物中畸形病态的描写,深刻反映了人性的“荒凉”,灵魂的“荒凉”。
张爱玲生在乱世,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张爱玲自己生活在一个破落的封建贵族家庭中,饱受父亲与后母的虐待。童年时期爱的缺失造成张爱玲对人的怀疑和对人性的悲观,逐渐长大后张爱玲早熟敏感、内心阴郁,对时代的悲观和对人的悲观自然而然地融注到了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加之青年时代又在香港体验到战争的恐怖,张爱玲形成了对人生较为悲观的看法。她通过一种近乎残酷的笔法,揭示了当时中国都市生活的阴暗、灰色,表现的是人性中自私、虚伪、贪婪、纵欲等“恶”的部分。我们在她的作品中很难见到阳光的一面,有的只是无尽休止的心灵创伤和心灵荒芜。
杜拉斯的小说则充满一种绝望感,喜欢描写汹涌欲望的海潮与急流,灼热的阳光与荒漠,她的语言狂热而灵动,风格洒脱。身为法国人的杜拉斯出生于殖民地越南嘉定,童年的生活艰苦而无助,直到十八岁才回到巴黎求学。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动荡与漂泊给了她创作的灵感源泉,她的作品中有不少是以印度支那的社会现实为题材的,通常描写一些试图逃脱孤独的人物,她在作品中描绘贫富对立和人的欲望,是在以独特的方式揭露社会现实。她的作品力求以平淡的风格,更直观、直接地发掘人们心理的变化。《长离别》就讲述了一个绝望的故事:一个失去记忆的、生活在情感世界之外的流浪汉,却深深地震撼着黛蕾丝的心灵,黛蕾丝努力想得到爱情,却永远是孤独徒劳的等待,希望最终走向绝望,孤独无限延伸。杜拉斯笔下的人物总是在绝望无助的性爱中悲怆地离别,孤独地痛苦,他们总是爱得轰轰烈烈、爱得死去活来,最终却曲终人散,走向更深的孤独与绝望,一如《情人》里的简和东尼。
对比张爱玲与杜拉斯的作品,虽然都以一种绝望、荒凉的笔调去感悟人生、拷问灵魂深处的欲望的气息,但是在表达这种痛苦与荒凉的方式上却有不同之处,张爱玲总在回顾中绝望,杜拉斯更多是在痛苦中逃离。
张爱玲的童年经历了暴力、软禁、重病甚至几近死亡,那样的生活痛苦而沉重,留在记忆中的是永远无法抹去的难堪的重负,这种一辈子都无法忘怀的记忆让张爱玲以后的生活总是走不出残酷、冰冷、感伤的过去,因此张爱玲的绝望是对现实无奈的绝望。《半生缘》中曼桢面对无法改变的痛苦现实凄惶地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 这句话表面了张爱玲总是走不出回忆,在现实中痛苦不堪又无可奈何的绝望。
杜拉斯则不能接受“走回去”的人生,她总是力图以最快的速度走出过去。杜拉斯曾这样谈过她的童年:“它(童年)太痛苦了。我完全处于黑暗之中。我在一生中飘泊不定”。[1]她对自己也说过:“我没有故乡。”[1]这些表现于杜拉斯的作品中,就是那无处不在的漂泊感,孤独感和绝望感。她又说:“我是一个不会再回到故乡去的人了。因为与一定自然环境、气候有关,对小孩来说,那就是既成事实。这是无疑的。人一经长大,那一切就成为身外之物,不必让种种记忆永远和自己同在,就让它留在它所形成的地方吧。我本来就诞生在无所有之地。”[1]令杜拉斯最向往的生活就是不断地逃离过去、找寻激情的生活。杜拉斯从来不会把情感钉在一点上,她不断地逃离过去,不断寻找新的情感寄托,在她古稀之年,与比自己年轻40多岁的情人——扬·安德烈亚在一起时,还坦率地说不一定是最后一次爱情。杜拉斯笔下的人物同样没有永恒永远,没有地老天荒,他们总是相遇、相爱又复归于绝望,然后走向新的漂泊与流浪。《情人》的女主人公明知道没有爱情,却沉迷于情人的金钱与欲望中。《蓝眼睛黑头发》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绝望中缠绵却竟然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和过去。杜拉斯的人物总是喜欢逃离过去,去寻找一份又一份新的情感经历。
处于灵魂的荒凉与绝望中,张爱玲用追寻过去的敏感、脆弱与悲悯的方式表达荒凉,杜拉斯以烈火般焚毁过去的方式留下空洞与绝望,这或许是她们最大的区别了。
三 写作之为拯救
张爱玲与杜拉斯在现实中挣扎,在困境中创作,她们都描写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从而揭示了人类灵魂的荒凉,但她们的创作并不是要将人类导向绝望,而是要藉此对人性进行反思,探寻拯救日益堕落的人类灵魂的途径,启示人们如何走向健全的人生。
张爱玲在她的散文《自己的文章》中一再强调,“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2]P172。“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2]P172,这说明拥有安稳的家,尤其是拥有能寄托心灵的精神家园是人类心灵深处普遍的愿望和追寻。然而,喧噪浮华的都市里,战争和现代文明的异常膨胀,这种热望和追寻变得遥不可及。因此,张爱玲在书写这种热望和追寻的时候就必然带有一种深深的绝望和无以名状的苍凉。然而,张爱玲的创作并不是要将人们导向虚无、厌世和弃世,而是希望通过这些苍凉的故事,对人们有所启示,启示人们如何去追寻美好人性,如何拯救现代人荒凉的灵魂。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大约可以看到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要真正尊重生命。尽管张爱玲笔下的 “人”大多是凡人、普通人,而非超人和英雄,但他们的是活生生的生命,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和乔琪乔也有真情流露、人性复苏的美好瞬间;《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半夜醒来与柳原拥抱的一瞬间,便是男女的真情流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虽风流无情,但在多年后见到王娇蕊也还是会莫名流泪;《金锁记》中歹毒母亲的曹七巧,也在岁月的侵蚀下辛酸痛苦。……在小说里,在冷静的叙述和苍凉气氛的渲染中,张爱玲把自己的理解、同情和关怀以及救赎给了她笔下这些不完美、甚至丑陋的小人物,使那些小人物们在小说里获得了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让我们看到了张爱玲对人性的博大的关怀。人类唯有真正尊重每一个生命,让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自在的生存空间,每一个生命才可以寻找到可以安放自己灵魂的美好家园,不再压抑、焦灼和恐慌。
其次是要执着追求真爱。张爱玲的小说表现人生的苦难与毁灭通常是为了突出对真、善、美的肯定,从而呼唤人的正常生活和正当权利,呼唤人间真爱,呼唤美好人性。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她虽然是张爱玲笔下人性恶体现“最彻底的人物”,但张爱玲也并未完全否定她。年轻的七巧原本也是一个热情开朗、渴求友谊与温暖、追求美好情感的人。是姜季泽的卑劣彻底扼杀了她追求爱情的美好梦想。《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范柳原不过是一对自私的男女,但他们都渴望真爱。《茉莉香片》中,作者写了聂传庆无爱的家庭带给他的人性的畸变。但就是人性畸变的聂传庆,在心灵深处渴望的却也是真诚的爱。聂传庆这种对人间挚爱的渴望,不正是作者的心声吗?只要人间有真爱,我们的灵魂就有了依归。
再次是要回归“佛”之善。张爱玲是运用意象的高手,“佛”意象在其作品中出现多达14项。张爱玲描写战乱时代人类的生存状态以及人性趋恶的作品中出现的 “佛”意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她是在用“佛”之善来对抗“佛”的反面——人性的欲望与险恶。更值得注意的还是张爱玲的小说《心经》中富有“佛”意味的许太太这一形象。而小说中具有坚忍、包容和悲悯情怀的许太太就极富“佛”的意味。她是张爱玲笔下难得的一位拥有伟大母性和高尚人格的母亲。当女儿和丈夫陷入不伦之恋时,出于对女儿和丈夫的爱,她一直不愿相信那是真的,宁愿相信他们仅是父女情深。当事实逼着她不得不相信时,她毅然担负起了斩断这段不伦之恋,维护女儿幸福的责任。从许太太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希望。至此,张爱玲告诉我们,人类唯有回归“佛”之善,才能摆脱人之恶,人类的灵魂才能寻找到永恒的归宿。
如果说张爱玲写作为了拯救挣扎于乱世的人民,那么杜拉斯创作首先拯救的却是自己。杜拉斯说:“我不是有所为而写。我也不为女人写。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写那个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我自己。”[3]P53杜拉早就把自己看成了历史长河中无数孤独、寂寞的女子中那个共同的“我”。杜拉斯在《酗酒》一文中坦白承认,人们的灵魂是荒凉的,因为他们缺少一个上帝,所以她酗酒,虽然知道“酒不可能提供什么慰藉,它不能充实个体心理空间,它只能顶替上帝的缺失”。[3]P22杜拉斯和她笔下的人物一样,由于在现实中没有安全感,于是总是在精神的沙漠中漂泊、绝望追求。杜拉斯在《写作》中告诉我们,“我现在才明白在房间里呆上十年,独自一人,是什么滋味,我明白在写作时我是一个远离一切的孤独的人。有时候,我关上门,切断电话,闭上嘴。”“身处一个洞穴之中,身处一个洞穴之底,身处几乎完全的孤独之中,这时,你会发现写作会拯救你。”[4]P78这是晚年的杜拉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是她在经历了沧桑、孤独与无助之后的唯一生存动力,她为自己的绝望找到了唯一的拯救方式——写作。虽然杜拉斯自己并不承认是女性主义者,但实质上杜拉斯用她的创作表现了女性的主题,她拯救自己的同时也在拯救“杜拉斯式”人物们。在《情人》中,杜拉斯就颠覆了传统的两性关系,让一个富有的、年长的中国情人成为一个卑微的求爱者,让一个贫穷的、年轻的法国姑娘成为一个高傲自信的女孩。她石破天惊地喊出了“我想”“我要”这样的话,在十分微妙的两性关系中,她将自己置身主动索取的位置,而让“中国情人”成为受动者,这是典型的女性宣言,是女性拯救自我的一种力量的体现。杜拉斯是一位以生命和真情写作的作家,不管我们是否认可她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方式,她的艺术魅力仍然是独特而深邃的。
[1][法]玛·杜拉.房屋[A]玛·杜拉.物质生活[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2]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3][法]玛·杜拉.菲贡·乔治[A].玛·杜拉.物质生活[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4][法]杜拉斯.写作[M].桂裕芳,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
(责任编校:王晚霞)
I106
A
1673-2219(2012)07-0019-03
2012-05-06
黄雪莹(1974-),女,广西钦州人,讲师,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姚锦莲(1974-),女,广西钦州人,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