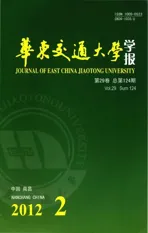论唐婚恋传奇中的理想女性及其文化内涵
2012-04-07高翠元高丹卡
高翠元,高丹卡
(华东交通大学1.教务处;2.科研处,江西南昌330013)
唐传奇是中国文言小说的成熟阶段,题材甚多,涉及婚恋、神仙、豪侠、政治诸多方面,而其中之翘楚当为婚恋传奇。唐代文士用清丽、奇幻的文笔书写了许多哀婉传神的婚恋故事,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逾越前代。郭箴一先生指出:“在唐以前中国无专写恋爱的小说,有之,始自唐传奇。就是唐人所作的传奇也要算这一类最优秀。”[1]的确,唐传奇中许多名篇皆以塑造具富文学价值的女性而载入文学史册。而深为唐婚恋传奇塑造的女性形象是饶有意味的:这些女性容貌出众、才华卓越,能跨越礼教藩篱主动追求爱情,同时又是遵守礼教规范,柔弱卑顺、相夫教子、恪守职份的贤妻良母。从当时唐代婚恋传奇的创作群来看,都是男性作家,这为创作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性别色彩。事实上,“唐代社会话语权力一直都为男性所把握,那么作为话语之一的唐传奇,实际上多是那个时代男性意愿的表达,文本承载的多为男性之意愿。”[2]丹纳指出“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解释它,那么我们在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种种族的心理”。[3]笔者认为,在男性叙事的唐婚恋传奇中,理想女性形象是被建构和生产的,她们的性别特征和角色功能都是迎合男性的需求尺度而塑造的,是在男权文化下男性对女性幻想和期盼的结果。但是处在相对开放、进步的唐代文明中,作为当时文化精英的文士又在理想女性的塑造中流露出不少进步的情爱心理和性别观念,这也是不应忽视的。
1 唐婚恋传奇中理想女性类型
1.1 名妓型的“理想”女性
唐婚恋传奇初步构筑了才子佳人模式,在这里男女钟情的基础是一种典型的男为“色”倒,女为“才”慕的才子佳人模式。《霍小玉》[4]4006-4011中的男主角李益就宣言:“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站在男性角度而言,女性首先是作为一个给男性带来感官愉悦和快感的角色存在的。在描绘女性时唐文士有意或无意地突出女性性吸引的特征,使得这些女性个个美艳绝伦,秀色可餐。《裴航》[4]313-315中的裴航惊于云英“脸欺腻玉,鬓若浓云”的美色而“惊怛植足,而不能去”。《莺莺传》[4]4012-4017“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的莺莺使张生相思陷入“行忘止,食忘饱”的境地。《任氏传》[4]2021-2023中颜色姝丽的任氏竟致使富公子韦崟初次会面便不顾朋友道义,企图凌辱……在对女性的审视中,男权文化定义女性个体价值第一位的便是美色,这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价值观,并成为一种常规文化心理沉淀下来。翻开文学史可以发现女性的美首先都是以容貌呈现的,“由于唐传奇的男性体验——男性创作——男性消费的特点”[5]使之在描绘女性时传承了这种“色”的标准,女性的美在一定程度上被物化、庸俗化了。
唐婚恋传奇中爱情的演绎往往由美色开始,由于美色和欲望的紧密联系,顺理成章这类故事通常贯穿着性的色彩。从因为从本质来说,“爱情的动力和内在本质是男子和女子的性欲,是延续种属的本能。”[6]唐传奇中的女性如同美丽饰物般光彩耀人,她们更是满足男性情爱欲望的尤物。这些女性无论是不染尘俗的异类女性还是礼教氛围中的俗世女子,在恋爱时都将贞节规范弃置不顾,沦为一种包含妓女原型因素的女性。织女牛郎的坚贞爱情一向被奉为典范,可在《郭翰》[4]2425-2427篇中织女寂寞难耐,背着丈夫来凡世偷情,男方尚怀忧虑,织女无所畏惧:“河汉隔绝,无可复知,纵使知之,不足为虑。”;《虬髯客传》[4]1445-1448中红拂本是司空杨素的侍妾,但是看中李靖是一位胸怀大志的英雄便毅然奔就;名门望族崔莺莺“贞慎自保”,却被张生几首春词逗乱芳心而自荐枕席……在古代,传统女性在婚恋上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从四德”等礼教规范,但是这些女性却丝毫不为礼教所束,她们写诗自媒、深夜叩门、自荐枕席,行为举止颇为出格,而面对女性的轻薄狂放之举男性却是坦然接受,尽享枕席之欢。女性的放浪轻浮恰满足了他们的色欲之心,使得他们长期被儒家文化压抑的身心在这种非正常的情感中得以放松,女性的放纵举止正迎合了他们心灵深处的越轨倾向。
在唐传奇才子佳人式的婚恋模式中,女性才华横溢也是非常显著的现象。霍小玉“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非烟传》[4]2831-2832中非烟“善琴声,好文墨,尤工击瓯,其韵与丝竹和”……在对女性的刻画中,唐代“文人才子在欣赏女性色艺之美、修饰之艳的同时,又融进了对女性才情的赞叹和钦佩”[5],唐文士这种对象诉求相对于那种只关注女性色相、剥离女性情感,定位女性为赏玩戏乐角色的女性观,显然是一种进步。但实际上这些女性的满腹才华是迎合了文士作诗吟赋、自矜风调的习性而创造的,在双方诗词酬唱、调侃赏乐的交流中,唐文士的才华素质和情感体验得到了真正的关注和赏识,而女性的情感却往往是被淡化和忽略的。《霍小玉传》中霍小玉与李益虽曾未谋面前早已闻知李益诗才,并终日念想,初次会面霍小玉有所遗憾“见面不如闻名。才子岂能无貌”,但却很快托付终身还定下八年盟约,这不得不归功于李益的才华魅力;《柳氏传》[4]3995-3997中李生赏识韩翊的才华便将自己姬妾柳氏赐给韩翊,天宝之乱韩柳两人失散,韩翊写诗寻找“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流落在外的柳氏也做诗回应“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如此描写其实更多注重是男士失去附属之物的心理感受而非女性动荡中不能自保的悲惨命运,如杨义先生所言:“寻人变成了诗人的寻诗”[7]。《广异记·李元恭》中博学多智的狐精惑崔氏,他以丈夫的身份对崔氏曰:“人生不可不学”,于是引一老人授崔经史,后又引一人教之书,崔氏终于以工书著称。这时他又说:“妇人何不会音声?”又引一人授教弹琴,于是崔氏“悉教诸曲,备尽其妙。”[4]3671-3672故事中崔氏的才艺是迎合男人的需求而不断增加,这正说明女性才情是唐代文士对理想情爱对象的一种期盼,女性的才华很多时候是迎合男性、服务男性,并不是女性真实的性别内涵。
1.2 贤妻良母型的理想女性
唐婚恋传奇中,恋爱中的女性极富“名妓”的特征,任情放诞,而在刻画家庭中的女性时唐文士又往往强调“贞洁”、“贤德”,突出女性的女德塑造。最显著者,《李娃传》中的李娃在青楼时举止轻佻,初见情郎就主动勾引“回眸凝睇,情甚相慕”,再见情郎大胆邀其留宿,而在萦阳生最终耗尽资财的时候却与鸨母设计赶走萦阳生,使之沦为挽郎乞丐,陷入“枯瘠疥疠,殆非人状”的悲惨境地。可以说无甚妇德、妇道可言,然而这个娼荡之姬被纳入了封建正统家庭之后,却从此变成了固守伦常孝道的“汧国夫人”,她“妇道甚修,治家严整,极为亲所眷尚”,生的4个儿子,也都做了大官,成为贤妻良母的典型,以至于文人为其“操烈之品格”击节称赞[4]3985-3991。又如《任氏传》的狐妖任氏,她不拘人间礼法,充满野性,与本有家室的郑生厮混。但是情许郑生后却对其忠贞不二,郑生表兄韦崟闻她美色,一路寻来,一见便“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但是任氏拼死反抗,打消了韦崟的淫念,最后她还为郑生殉情至死。作者对其贞洁给予了高度评价:“遇暴不失节,殉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李娃和任氏虽身份有异,但她们这种集荡女和贤妇的角色显然是合乎唐代士子的心理需求的,从作者对她们的高度褒扬中投射出唐代文士希望女性在家庭中严守妇道、妇德,在妻妾位置上各守其分,以维护男权社会家庭秩序的心态。与对贞洁品质的高度标举相反,唐传奇不少篇章对女性违背贞节的行为给予了谴责。如《非烟传》与《冯燕传》[4]1463-1464。故事中的两个女性都是个性粗鄙的武将之妻,两人都背着丈夫与人私通,最终都受到了男权社会的严厉惩戒,一个被丈夫鞭挞致死,一个反被情夫杀死,维护了男权社会所谓的正义和秩序。文末作者的点评也是异曲同工,《非烟传》作者虽对非烟抱以同情但坚持非烟之罪“不可逭”。《冯燕传》作者则视不守妇道的女性“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贞节实质是男人对女人单方面的期望和控制,这种女性角色特征也是历来被强调的。在唐代贞节观念虽然较之别的朝代相对淡漠,但是“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在社会上还是有一定的地位,贞节的行为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提倡。”[8]它依然是女性性别内容的一部分。
除了强调女性贞节,唐婚恋传奇对女性在婚姻中柔弱卑顺、恪尽职份等角色功能也是极力强调的。在唐婚恋传奇中,女性进入家庭后几乎都是柔弱服从,相夫教子、持家理财的贤妻良母。如《韦安道》[4]2375中的女神后世夫人在武则天面前可以发号施令,但是在公婆面前却恭谨异常,送上丰厚的赠礼。《申屠澄》[4]3486中的虎女知书达理,却认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规范,其夫要她写诗,她则说“为妇之道,不可不知书,倘更作诗反似妪妾耳。”她将承担全部家庭职作为自己的本职,在丈夫俸禄微薄的情况下,“力成其家”,结交宾客“大获名誉”,所教育的子女“亦甚明慧”;异类女性如此,俗世的女子同样全心奉献。《唐暄》[4]2635-2638中的张氏死后在阴曹仍然忠于阳间的丈夫,不但立志不嫁还对丈夫迎娶新妇不怀嫉妒,尽心侍奉阴间的公婆,抚养幼女,维持着阴间家庭的和谐。对于这类彻底奉献的女子,文士都是给予了高度评价的。在描绘女性尽力承担为人妻、人妇的职责时候,唐传奇有时更是将女性提升到母亲的地位,从女性给予男性种种慰藉,拯救人生困厄、实现人生价值等角度来塑造女性。在唐传奇中女神女仙用超常神力给文士裕产殖财,女妖女鬼为男性解除心灵寂寞,青楼妓女又与他们琴瑟和鸣,充当知音。女性对男性的爱护从物质到精神无微不至,她们不求回报,甚至不惜牺牲一切。这些女性实质上被赋予了母亲的色彩,这也是文士心底潜藏的母亲情结。在悲喜殊味的士妓恋爱小说《李娃传》和《霍小玉传》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女性是否能从情人身份上升或转换到“母亲”,具有母亲那种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特征是被男性认可的条件。故事中的两个娼门女性皆与门第清贵的少年欢好,她们都知晓娼门游戏规则,但是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李娃在萦阳生资财耗尽的时候设计赶走萦阳生,也放弃了情人的身份。而在萦阳生被逐出家门、陷入挽郎乞丐的困境时,她由往日的情人转而成为引导萦阳生健康和地位恢复的母亲,她用母亲般的呵护和教诲引导萦阳生,使之从“不齿人伦”的境地上升到“科举及第”、“争霸群英”、“策名第一”的显赫声名,而她自己也被文人誉为“节行瑰奇”的汧国夫人。而相较李娃的身份转变,霍小玉想长久维持情人身份,最终成为死后仍纠缠李益的女鬼,命运迥异可见一斑。从中可见,唐代士子理想的女性还应具有“母亲”似的奉献精神和引导功能,拯救陷入困境的男性,帮助其实现人生理想追求,这是对女性的更高期盼。
2 理想女性隐含的文化内涵
综上,唐婚恋传奇中的理想女性是集情人、知己、贤妻和慈母于一身的形象。这种理想的女性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应文士的需要而存在的,这种显著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意识,不但体现了唐代文士的情爱心理,其实更隐含着一定的文化内涵。
2.1 名妓情节:浪漫情爱的追求
古代婚姻被父母乃至家族主宰,唐代婚姻尤其讲究门第,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耻。”[9]当时婚姻主要是两个家族之间地位和权势的结合,不顾男女双方的感情意愿。《柳毅传》[4]3410-2638与《离魂记》[4]4033-4036就是迫于父母之命、家族意愿的悲剧婚姻代表。《柳毅传》中的龙女先被父亲洞庭龙君命嫁于门当户对的泾川小龙,倍受夫家凌辱却无力反抗,后被义士柳毅搭救,遂芳心暗许。在遭到柳毅拒婚后,其父又欲将她许配濯锦小儿,深受不幸婚姻煎熬的龙女,以“闭户剪发,以明无意”的反抗才最终争取到了幸福。《离魂记》中王宙与表妹倩娘自幼相爱,倩娘之父张镒却悔婚将倩娘许配与“有宾寮之选者”(吏部官吏)。在爱情受阻却不敢违抗父命的情形下,倩娘其魂魄脱离肉体跟着情人私奔了。然而他们的婚姻却并不幸福,违背父母意志和社会礼教的倩女魂魄一直为自己行为深感羞愧,另一方面倩女躯体始终沉疴在床,奄奄一息。此外《霍小玉传》、《莺莺传》等篇章都蕴含着门第婚姻悲剧的影子。
唐代科举制度使得自东汉以来沉沦下僚的庶族文人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上层阶级的一部分。科举制度带来的巨大地位变迁使得唐文士精神昂扬。“这些士人的创造欲得到了满足或拥有满足可能性的同时或稍后,他们要求甚至迫切要求情爱欲的满足”[10]。唐文士不满足夫妻间枯燥的同居,追求情趣投合的爱情,而“唐人传奇作者都是受封建礼教束缚较大的士人举子,与娼妓的交流几乎是他们有可能产生爱情关系的唯一社会活动。”[11]据陶慕宁考定,中国青楼业形成全国范围规模化的经营也正在唐代。它是应唐代全社会对新兴士子的尊崇而产生的新的文化消费场所[12]。《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了当时文士与妓女交流的盛况:“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13]1725青楼成了实践士人恋爱憧憬最便捷的场所,而妓女的容貌才情、谈吐举止又恰与士人理想的伴侣标准暗合。唐《北里志·序》记载:“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语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是非,良不可及。”[13]1403观看名妓型的女性,她们姿色出众、伎艺超群、且风流放诞,而实际上古代的一般女子,由于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卑下,加之“三从四德”等道德礼教束缚,大都缺乏文化教养,呆板乏味。很显然名妓型女性很大程度上是以青楼女子为模型塑造的。无庸讳言,在刻画名妓型的女性时文士流露出对美色、情欲的感性欲望渴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女性精神面貌、气质修养也是极为关注的,男性对女性美丽的欣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狎玩意味,几乎所有传奇在描写女性美时都没有明清小说中那种色情猥亵,而是上升到诗的境界,呈现出精神上的强烈渴求。如《霍小玉传》中称霍小玉“若琼林玉树,互相照耀,转盼精彩射人。”写尽女性超凡脱俗的瑰姿美态和气质风韵的高雅不凡,又如《绿翘》[4]922-923描写鱼玄机:“色既倾国,思乃入神。喜读书属文,尤致意一吟一咏”,对其内外俱美的不凡风度赞赏不已。可见,作为当时文化精英的唐文士在情爱中一定程度上挣脱了单纯的欲望束缚,将女性的才艺、气质等也纳入了男性的审美范畴中。用一种相对自由的审美情感来审视和塑造情爱对象。揆之当时文人与妓女的交往状况也可发现,“唐代女性以自己的才情赢得了正直文士骚客的尊重和敬慕,这在中国女性生活史和妇女观念史上都是值得注目的现象。”[14]当时的文章魁首皆与青楼妓女有密切来往,如元稹,白居易等与歌妓薛涛唱酬交往,诗人陆羽,刘长卿等与女道士李冶(唐代女道士犹如娼妓)交往颇深。在和妓女的交往中,士人感受到了情人的风情、知己的赏识,尝到了心灵契合的浪漫爱情滋味,唐代文士塑造的理想女性,这种名妓情结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2.2 贤妻良母:狂热之后的理性回归
唐代特殊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造就了文士自矜风流,在传奇中书写着对爱情的追求。但是人是社会的人,“爱情把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联结在一起。它是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综合体。是物质和意识多面的、深刻的、有生命力的辩证体。”[6]332因此,唐代士子在对爱情执着追求的同时不可能沉溺于一种只追求两性爱慕而不受社会法则、道德评判、以及各种理性观念影响的爱情。当爱情最初的狂热平静下来后,便需要考虑前程仕途、面对婚姻生活了。如程国赋先生所言“唐代理想的文士一般要经过这样的人生历程:年少风流,眠花枕柳,而后科举中第,娶高门女,出将入相。”[8]142名妓型女性虽是唐代文士追求的情爱对象,但是面对“合两性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事也。”(《礼记·婚义》)的婚姻唐文士又是谨慎的。如《北里志》的“王团儿”,进士孙棨很欣赏妓女宜之的谈吐风度,多次赠诗歌给她。宜之芳心暗许,呈诗询问爱情前景:“日日悲伤未有图,懒将心事话凡夫。非同覆水应收得,只问仙郎有意无。”孙棨虽“甚知幽旨”却答曰“非举子所宜”,并申明“泥中莲子虽无染,移入家园未得无。”[13]1411朱光潜先生论言:“西方人重视恋爱,有‘爱情最上’的标语。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真正的爱情往往见于‘桑间濮上’……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15]这也正是崔莺莺与霍小玉被张生和李益始乱终弃的原因。尽管张生始终对莺莺有缱绻之情,纵使李益与霍小玉感情“婉娈相得”,两人在面对仕途前程、门第差距、等级区别、道德伦理等现实问题时,理性地选择了仕途和豪门女,他们的行为在当时却是被认同的,时人称张生为“善补过者”。
唐文士渴求情趣投合的爱情,然而面对现实的仕途、门第的荣耀、家族的压力以及社会的价值评判等等社会理性,他们又都会走向理的回归。“中国人在两难的冲突中,最后总是一己的欲望服从按天的法则而设的‘礼’,消灭动乱因素,走向安定大局。在礼与非礼之间是非礼服从礼,在大礼与小礼之间,是小礼服从大礼。”[16]唐文士清楚与高门联姻才是他们的最好选择,因为一旦与豪门甲族结亲,就能扯着裙带获得厚禄显爵。然而豪门中的贵族女性并不如妓女那样柔弱顺从,易于控制,恰恰相反,唐代贵族妇女地位较高,在感情上放纵胡为,个性强悍善妒。唐代贵族女性改嫁、偷情、私奔的事情比较常见,“《新唐书·诸公主传》、《唐会要》卷六《公主》记载,唐代公主改嫁的就达三十人,有些公主更是三嫁。”[8]153而武则天、韦后、太平公主、襄阳公主等贵族女性都有风流韵事流传。此外,在唐代,贵族女性多妒悍,这在唐五代笔记小说中有大量的记载。上至中宗畏韦后、宰相房玄龄的妻子宁妒而死[13]34,下至中宗御史大夫裴谈对妻“谈畏之如严君”[13]1253,不胜枚举,如此居高临下、放纵任性的女性自然不能为唐文士接受。弗洛伊德认为“艺术作品在排斥其欲望的现实界与实现其欲望的幻想界之间,争得一席之地”。[17]因此唐传奇则表现了他们在心理上一个反拨:无论是地位显赫的神女还是卑贱的婢妾、妓女,这些女性进入家庭中被规范到男权社会的主流意识中,都具备贞节柔顺、恪尽职守等普遍的形象特征。地位显赫的仙女进入人间屈从人间礼法,侍奉翁姑,曲意奉承,养育后代,不遗余力,还利用神力让文士穷尽享受;妖魅妓女们则积极改造自己,消除自身野性变得贞节自持、卑顺服从,苦心奉献让男性过得舒心如意。而且这些女性基本没有自主意识和独立意志,即使被抛弃或放逐她们只能接受现实,黯然离去。如《韦安道》中的后士夫人、《崔书生》中玉卮娘子、《焦封》中的王茂之妻、《莺莺传》的莺莺等等。
当然,贤妻良母型的理想女性也与唐文士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相关。唐传奇的作者都是儒家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才子,“虽然他们不拘小节,崇尚风流,对自身的道德修养不够重视,但是在心理上,受儒家思想浸染的痕迹还是非常深的。”[8]215儒家给中国士人设计了一条理想的人生道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家国同构的封建社会中,男人的一生是试图在天下与家庭中寻求共同发展的过程。建立一个典范的家庭是男性社会价值的初步体现。这种价值实现不仅需要贤妻的支持,而且贤妻本身就是典范家庭的一个必要角色(典范家庭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顺,)所以对于唐文士而言贞节、柔顺、贤德等品质仍是唐文士所认同的,女性侍奉公婆,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料理家事等职责也是他们着力颂扬的。而在家国同构的社会中,封建社会的男子自觉承担了建构国家的角色。他需要成为一个强者,但是男人总有软弱的时候,“如人疾苦,必呼父母”这时,具有温柔和善、不求回报的妻子成为替代母亲的人。在传统的观念中,母亲身份还有教育子女职能。“孟母三迁”、“岳母刻字”、“画荻教子”便是流芳百世的教子例证。联系唐代科举制度盛行的背景,母亲的含义还表现为女性对文士科举功名的支持。在唐婚恋传奇中也不乏妻子劝夫自励,助丈夫蟾宫择桂的佳事。
3 结语
唐代虽然是个文化开明、女性地位比较高的时代,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以及许多参政的女性,如长孙皇后、韦后、太平公主等等,也出现了薛涛、鱼玄机等优秀的女性作家,她们进行了较多的创造,但是她们的声音不足以对男性话语造成冲击,而且男权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唐婚恋传奇对理想女性的书写中流露出不少进步的性别观念,但是无论是挚友、贤妻或是良母,女性的美貌、才智、贤惠和奉献等美德都是男性对女性幻想和期盼的结果,她们的角色内涵也是被建构和被生产的。
[1]郭箴一.中国小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37.
[2]蒋愿望.性别、权利与话语[J].北方文学,2011(2):24-25.
[3]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58.
[4]李旷,扈蒙,李穆,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5]白军芳.唐传奇中的女性美[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3):69-71.
[6]瓦西列夫.情爱论[M].赵永穆,范国恩,陈行惠,译.上海:三联书店,1984:1.
[7]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63.
[8]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58.
[9]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16.
[10]林明华.唐传奇表现的士人心态[J].中国文化研究,2001(2):115-119.
[11]李宗为.唐人小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5:84.
[12]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102.
[13]丁如明,李宗为,李学颖,等校.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403.
[14]杜芳琴.女性观念的衍变[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93.
[15]朱光潜.朱光潜全集[M].3卷.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82:75.
[16]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50.
[17]张隆溪.比较文学论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