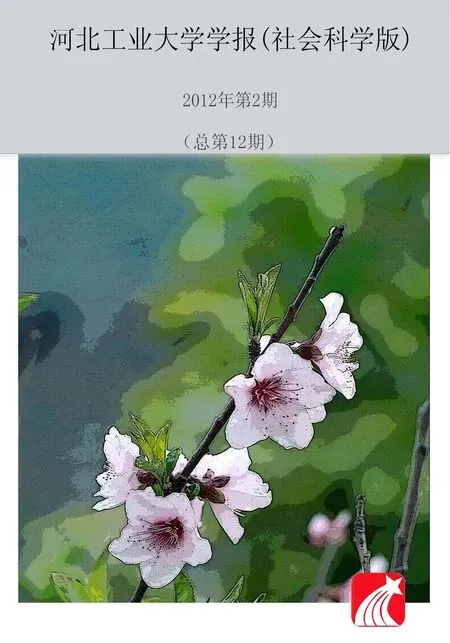审判与救赎——反启蒙及其论域中的《美丽新世界》
2012-04-07张秋子
张秋子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审判与救赎
——反启蒙及其论域中的《美丽新世界》
张秋子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展现了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世界,科技与暴政结盟,对人性与社会都产生了毁灭性影响。面对启蒙理性过度膨胀的恶果,赫胥黎站在反启蒙的立场上,通过审判科技与政治暴政结盟的罪行,揭示了技术统治与极权主义的直接引语关系,即极权主义正是通过对技术统治下既定的社会人类模式不断引用,演变成其暴行,从而他提出异化艺术形象的双重概念,在探讨启蒙与反启蒙的辩证关系中,寻找救赎之路。
《美丽新世界》;反启蒙;技术统治;极权主义;救赎
一、反启蒙与《美丽新世界》
英国小说家阿道斯·赫胥黎的著名小说《美丽新世界》初版于1932年,再版于1947年,一经问世,各种评论纷至沓来。然而,中外评论界对《美丽新世界》的批评多把它作为某种理论流派的试验场,从女性主义到精神分析批评不一而足,研究结果异彩纷呈,而另一些阐释则大量集中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辩证中,即使对本书中唯科学主义与极权主义的警告有所察觉,也并没有把二者联系起来。因此,从反启蒙角度对《美丽新世界》进行再次阐释,不仅可以探索这部经典焕发的新意,更能使其实现当下的批判性意义。
把《美丽新世界》置于反启蒙的视域下时,我们发现这部幻想小说蕴含着严肃深刻的时代隐忧。可以说,赫胥黎手执反启蒙之枪,通过对未来世界的展望,向当下人类的文明状况猛烈开火,引出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渗透着《启示录》气质的《美丽新世界》,沉痛预言着技术统治与极权主义结合下产生的所多玛之恶。在反启蒙视域的审视下,这预言无疑具有超前性,赫胥黎在谈及本书创作时就说道:“我们在沮丧岁月里的噩梦与将来发生的噩梦迥然不同,我们是匮于规约的噩梦,他们则是充斥着太多规约的噩梦,”且“我于1931年作出的预言实现之快超乎我的预期……在西方,个体男女享受着很大程度的自由,然而即使在这些拥有民主传统的国家,这种自由、哪怕是对自由的追求都日趋萎靡。”[1]这并非杞人忧天,回顾二十世纪世界历史,法西斯主义与反犹主义硝烟散尽,我们担心的也许不再是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否野蛮,而是改头换面之后的技术与暴政联盟向人们施压时,人们能否抵抗。
那么首先要厘清的问题,就是何谓反启蒙,它为什么成为赫胥黎批判技术统治与极权主义结合的武器?若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反启蒙似乎意味着对抗启蒙带来的福祉,重返愚昧、迷信、昏聩的状态。如果这样,它当下的救世功能何为?它与流行的反智主义之说又有何分别?应该说,反启蒙的涵义呈历时性嬗变,早在西方文明的两希源头,确实酝酿着一股反对知识智慧的潮流。
可以理解,《圣经》中人被逐出伊甸园和巴别塔的故事都有着深一层阐释的可能性。建立巴别塔正是僭越了上帝的权威,“它从神学上嘲讽了人类意图建立‘自己的名’的冲动,意味着宗教对文化的批判,它与伊甸园的人因知识而被逐出伊甸园有着同样的意义”。[2]一旦对上帝的权威加以亵渎,就将要受到责罚,以示话语权力的不容侵犯。《圣经》中的智慧文学,更是对所谓的智慧有所质疑、反思与提问。譬如《传道书》就是持一种约伯式的口吻自问:“我为什么有智慧呢?那我有什么长处呢?”既然智慧人与愚顽人并无不同,那么智慧本身的意义何在?在此宗教视域内,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即仅为满足求知欲的东西,也只能占据次要地位。对于属于更早时代的圣奥古斯丁来说,追求知识的好奇几乎成了一种冒犯的罪过。为何随着人知识的不断增加,带来的不是祝福而是失序与冒犯?基督教思想传统认为,人的智慧有限,唯独上帝的智慧无穷尽且完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上帝以一种看似反智的方式阻止人类获得知识,实则是在强调上帝与人关系的本质:绝对的虔敬——这是上帝在狂风中对约伯言说的目的,也是亚伯拉罕杀子献祭的意义。
从西方文明的另一源头中,我们也可以嗅到反智的踪迹。不妨把古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王视为一个反智原型,他正是因为掌握了杀父娶母的秘密——隐喻意义上的智慧——而难逃自刺双目的命运。学者施密特认为,“索福克勒斯在他的《俄狄浦斯王》中展现了启蒙这一新问题在历史中的现实意义,而他同时又认为这一问题来自于人性本质,并且必然产生于这一本质,他描绘了相信自己的知识和自己力量的人如何在存在意义上的失败。”[3]俄狄浦斯王所体现出的反智意味正是由于作者意识到了人类知识的有限易朽,而渴望挽回宗教机构、神谕体系衰落的颓势。以此类推,在古希腊戏剧文化中,俄狄浦斯是求得知识的殉难者、卡珊德拉是占有知识的殉难者,普罗米修斯则是追求知识的殉难者,他们或拥有不吉预言的先知能力而遭到众人记恨嘲笑,或因盗取火种而遭到众神迫害——无论是杀父娶母的秘密、不吉预言的能力还是盗取的火种,在反启蒙的论域中,都可被视为知识、智慧的隐喻,而追求它的后果就是无法摆脱命运之轮的残害。
近代,反智主义一词爆得大名是来自于美国史学家霍夫斯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该书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艾森豪威尔时期共和党的统治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大亲企业,嘲笑满脑子道理的读书人是“鸡蛋脑袋”,这对新政后得势的知识分子是个不小的冒犯。其间麦卡锡主义崛起,对知识阶层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甚至迫害。因而,霍夫斯塔特对美国社会存在的反智主义思潮的梳理,根本出发点是深切的当代政治关怀。他认为,美国反智主义的源流部分来自于清教信仰,部分来自于拓荒精神。前者怀疑掌握文字的牧师对神意的转达,更愿意听任前经验的心灵寻找神迹,后者则将知识视作扩荒过程中的阻碍,相比于书本的教条律令,直接亲近大自然劳作更为实用。[4]在当代反智主义的侵袭之下,宗教与世俗实践力结合的反智情结为右翼政府利用,遗患无穷。
然而,反启蒙并不就此等于由古典思想发源而来、于今颇盛的反智主义。后现代语境里的反启蒙与原始意义上的反智已大相径庭。在某种程度上它与反智主义同源,随着历时的发展,它衍生出了新的意义,即从对知识及其特权消极的拒斥上升到后启蒙时代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的自我反思之上。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乃是借心智之光以驱散思维的昏暗,达到思想解放,智性昌明。但在当代,人类看到的更多的是对理性的不合理地利用,由于科技单向度发展带来的异化与宰治,人类不仅没有掌握自我的持存性,反而在对世界过度的探索中失落了主体。这就是霍克海默所谓的“启蒙的悖谬”。针对于此,反启蒙思潮清洗掉反智主义的消极色彩,留下了对理性、技术等启蒙硕果审慎的持疑态度。可见,反启蒙是后启蒙时代由反智主义升华蜕变出的一股批判思潮,它促使人们追问后现代多元话语的语境中启蒙是否就是铁板一块的事实?启蒙的发展与其初衷是否悖谬?现代主义理性具有致命的自负,同时也包含着自我怀疑与反思,因而反启蒙绝非作为启蒙的二元对立面出现,毋宁说它吸收了现代性与启蒙对自我深刻的批判精神,可以确信,它是启蒙自我意识的改造,是启蒙的反思性延续,而“追求建构性社会目标和伦理目标必然需要一种反启蒙姿态。”[5]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启蒙思潮涌动的文本,在谈及创作时他所使用的“噩梦”一词正是反启蒙对过度启蒙理性的批判性描绘。以敏锐的洞见,他从过度启蒙的唯科学主义中观察到其走向极权主义的危险性,并以反启蒙思潮独有的建设力量展开审判与救赎。这无疑是一场启蒙辩证法的角逐,也是人性的辩证法的角逐,是人在求存的指引下,于自然欲求和道德律令间的来来往往。当压倒性的工具理性演变为普世的技术统治,反启蒙,作为满含着否定性力量的批判利器,审判着文化、制度乃至人性。
二、审判:技术统治作为极权主义的引语
1947年《美丽新世界》再版时,赫胥黎在补写的序言中提出了此书的思路:“原子能的释放标志着人类历史第一次了不起的革命,却不是影响最深远的终极革命……真正革命性的革命不应该在外部世界进行,而应该在人类的灵魂和肉体上进行。”于是,《美丽新世界》成为一种历史决定论的试验场。在卡尔·波普尔那里,历史决定论意味着无视个人对人类发展的作用,而力图寻找某种预见未来的历史规律,它“强调某个集团和集体的重要性——例如,某个阶级——没有它,个人微不足道。”[6]这种一元的历史决定论顺利转化成美丽新世界中世界国的格言:“社会,本分,稳定”。绝对的本分不逾矩,使人成为历史决定论的试验品。
在人类灵魂和身体上进行的实验,无不来自技术统治时代里登峰造极的启蒙成果,其背后,却埋伏着极权主义的影子,包藏着专制统治的祸心。启蒙赋予科技自明的合理性转化成支配社会的合理性,当这一“合理性”所铸成的人性与社会形态顺延至极权主义统治中时,科技必然与暴政狼狈为奸、相辅相成。反启蒙所批判的,正是极权主义对技术统治的不断引用。反启蒙视技术统治为极权主义统治术的直接引语,两者结合产生的恶劣影响,不仅是启蒙之病,也是反启蒙之痛。
首先,从人的外部性考察,是极权主义对“个性与私人性丧失”的引用。
美丽新世界中,实施严格的人工种姓制度。小说的开篇就以参观的学生这一视角对这种人工种姓制度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取消了正常的胎生过程,从受精到至胎儿教育,都受到严格的技术控制,由此发展出等级各异的种姓。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的主任宣称:“‘社会,本分,稳定’这是了不起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无穷无尽地波坎诺夫斯基化,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7]种姓制下,哪怕连高种姓等级的人也只有贫乏的思维。小说女主人公,高种姓的列宁娜对“大家都属于彼此”教诲牢记于心,充满色情意味的合成音乐里也在不断传道:“让我们十二人融为一体\犹如注入社会洪流的涓涓水滴\让我们现在就汇聚到一起\犹如您的闪光轿车一样迅疾。”[8]在此,集体高于一切,人从一出生就注定了与别人的复制般的命运,千人一面,个性泯灭,社会的马车单向度地平稳前驱。
个体的消失不仅显示在个性的消失,也显示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传统区分被打破后,前者对后者的侵犯与渗透,也即个性与私人性一并消失。从教导婴儿们弃绝美丽花草的育婴房到提供大量麻醉人药品的弥留医院,一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构成为对个人进行体制规训与曝光的领地。人们满怀着“创伤性的空虚”,纵情享乐,分享共同的趣味,没有任何私密性可言。列宁娜“聪明”地领悟到,极端唯科学主义与后工业时代的文化产业中,拥有私人秘密只会与社会格格不入,伯纳不愿在公开场合谈他俩之间最秘密的私事,使她觉得好笑。人们都对伯纳“爱做私事”的作风感到不解,认为“他那老干私事的怪癖,实际上就是游手好闲。一个人私下能够有什么可干?”[9]个人隐私被极大程度曝光的结果就是公共领域的控制全面渗透个人领域,蛮横地为个人提供了生存与行事的内在准则,所有人必须整齐划一地分摊为均质的见解与趣味。
这样的人格特征被极权主义相中并加以利用,成为其统治术的直接引语。
在极权主义中,最显著的主体间际关系正是这样:个人消融于集体,似乎没有了隔膜,但实则却愈发陷入无物之阵,孤独隔绝的无以复加,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称之为“沟通带来的隔音”。《启蒙辩证法》描绘出一种个体依附于集体的倾向,依附到“客观化的,集体的,而且已经是确定了的欺骗形式上去,正是由于他们在服从团体的过程中产生了恐惧和空虚,他们紧密的结合为一体,并被赋予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10]这种倾向,在雷达里赫那里是“积极的不自由”的命题,在美国曼哈顿计划中是“幸福问题”的命题——换句话说,叫人热爱奴役。人民,这群本来最具有革命因素的酵母,却被驯化成巩固统治的基础,当科技的操纵与管理达到最全面状态时,打破奴役状态与获得自由的手段根本无法想象。赫胥黎在书中描绘了一种甜蜜的幸福剂:嗦麻。一经服用,再无忧愁。嗦麻正是对人们作为奴隶而习焉不察的状况的隐喻。舒舒服服的不自由,一如马尔库塞指出,是极权主义工业社会的一大特点。不难理解,热爱奴役来自于技术统治后自我持存的孤独与焦虑感。人与原始的自然世界关系一一断裂,存在于意义的天空与虚无的大地之间命悬一线。在绝焦虑孤独感的威逼下,人选择了弃绝自身的独立性和超越性,宁可舍己,也要归化,极权的集体就成了唯一可以信托者。这一状况,与科技宰治下的状况没有区别。
其次,从人的内部性考察,是极权主义对宣传手段的引用。
美丽新世界中的孩子们接受的是睡眠教育。批量生产的男女幼儿在睡梦中舒坦地躺着接受喇叭广播的社会条理与人生准则。主任介绍道:“在醒来之前这些话还要为他们重复四十到五十遍;星期四、星期六还要重复。三十个月,每周三次,每次一百二十遍。然后接受高一级课程”,[11]他将睡眠教育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道德教育和社会教化力量。通过不断暗示宣传,社会所要求的律令成为人们终生而唯一的心灵内容。列宁娜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公民,她恪守睡眠教育中所潜移默化接受的一切,自主的思想已被律令取代,张口就是堂而皇之的道德规范。新世界相信一种理论:“道德教育是不能诉诸理智的”,单向度的思想由政策制定者和宣传机器共同推进,在潜意识中得到不断的强化。
睡眠教育作为一种宣传,也意味着聚合成一个封闭的话语领域。“儿童穿咔叽。穿的更差些。们太笨,学不会读书写字;他们穿黑色,那是很粗陋的颜色。”话筒的里的语句以陈述句的方式表达,内涵判断,有着不证自明的合理性,如同巫术的仪式。卡尔·克劳斯早已指出,言谈、写作、标点符号乃至排印的方式都有可能揭示一个完整的道德或政治系统,马尔库塞进而补充道:“由于不断被强行嵌入接受者的大脑,它们产生了把意义封闭在规则所给出的条件范围内的效果”。[12]一如美丽新世界毫不避讳展现出的:宣传教诲中的字词句用看似无意识的、隐蔽的方式巧妙地遮盖了意识形态目标。它不仅有着如同嗦麻般的催眠特征,还带有伪善的劝谕意味。世世代代成长起来新世界公民生活在必然领域,也从不期待可然领域,先入为主的秩序看似成了唯一的秩序,必然构成话语霸权独白。从宣传受众的角度看,放弃怀疑与批判也是人自我保护的手段。那些先入为主的看法,那些成见与教条,“也许是我们个人传统的核心,是对我们社会地位的保护。在充满惰性与自我逃遁的心理定势下,顺从宣传是如同一双旧鞋子那样令人舒适”[13]。
技术对宣传的控制与利用最明显地表现在文化工业领域。随着电报把信息变成了商品,摄影术把世界切割的支离破碎,无数密集如雨点的信息涌入大脑,人们根本无暇进行反思与消化,连求得不知情权都是困难,久而久之,“人们不仅失去了真实信息,也失去了判断信息的能力。”[14]密集的意识形态宣传遮蔽了选择的可能性,展现出的只有一副美丽新世界歌舞升平的图谱,而人在接受电信化宣传的同时,就把自我托付给没有生命的媒介,宣传通过伪造和替代人对世界的实际经验,进而操纵了主体的意识形态,继而丧失了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
由此产生的,就是马尔库塞所谓的著名的单向度人,这一宣传特性,同样成为极权主义统治术的直接引语,为其提供了现成的技术与理论资源。
作为美丽新世界中的头目,世界国总统穆斯塔法·蒙德实际上对局面了如指掌,他通晓莎士比亚,通晓人的困境与麻木的幸福,并明确指出科技带来的恶果。但身在极权主义金字塔的顶端,他的“特点正是不受他们自己意识形态的束缚。这些人根据组织来思考一切事物和一切人。”[15]他利用已经被技术统治削掉思想与质疑的大众思维,通过在孵化和条件设置中心的各种安排而运筹帷幄。穆斯塔法·蒙德总统这样对野蛮人约翰炫耀着宣传终稳定世界:“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要什么有什么,得不到的东西他们绝对不会要”。与纯粹暴力相关联的极权已经是过去式,就像嗜血的罗伯斯庇尔最后只感到虚无,与幸福相关联的说教成为新的手段,因为暴力至多达到恐吓民众的目的,重复的、常态的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才直抵毫无防备的人心。
极权主义对技术理性最直接的借鉴莫过于“它的宣传非常强调其论点的科学性质”,阿伦特指出,这一点常被人用来比较某些在群众面前做自我表演的技巧。当领袖或者政治家在电视、广播、舞台上大谈科学与自由时,他们就是在做自我表演,其言论只是无意义的声音。在丧失了判断能力的群众面前,穆斯塔法·蒙德对民众进行各种蒙昧训话,他举了大量科学的分析与例证,对于受众而言,这些科学式的言说具有精密化与理性化,使得宣传极有说服力。缜密的逻辑推演背后暗藏着专横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逻辑暴政的必然迫使人们驯顺地表示赞同。
正是通过以上两点,以反启蒙的审判为镜,我们看到在美丽新世界中极权主义继承了技术统治下形成的人与社会模式,对人达成全面的操纵,这是启蒙开出的最恶之花:技术与暴政的结缔。赫胥黎的预言有着启示录一般的沉痛性与现实意义。但不应忘记,人作为实存,有向下堕落的魔性,也有向上飞升的神性,反启蒙对向下堕落的魔性进行审判后,寄希望于向上飞升的神性,赫胥黎在书中赋予这种飞升以审美信仰的品格,期待否定之否定背后的肯定。
三、救赎:诗与思
反启蒙论域中,赫胥黎所诉求的,是人性和信仰的复返。不可否认,历代学人对科技与理性过度发展的抨击无不来自于反理性等精神性论域,对物理世界科技奇迹板上钉钉的现象却缺乏有力解释。然而,正如当年卡尔·波普尔提出证伪主义学说,一反学界流行的实证主义,用“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了“归纳-实证”的实证机制,艺术领域中的文学想象所诉求的也并非直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这是启蒙霸权所惯用的手法——而是“猜想与反驳”社会机制的不合理性,在“试错”了启蒙理性后,间接表明“社会的不合理性愈明显,艺术领域的合理性就愈大”。[16]正是文学与艺术想象提醒着人们精神性的崇高,《美丽新世界》一书的书名就意味深长地借用了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的台词,从而表达出救世希望。该剧第五幕第一场中,被父亲带至荒岛的米兰达公主第一次见到由父亲魔法作用下,遭遇风暴,狼狈登陆的人类,不禁兴奋的欢呼:“神奇呀,这里有多少美好的人!人是多么美丽!啊,美丽新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通过两个“美丽新世界”的对比,赫胥黎期待真正的艺术化新世界的到来。
在这一点上,赫胥黎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思想汇流,他们共同痴迷于对真正艺术的捍卫,对诗的坚守。当技术手段成为一种存在方式时,与之抗衡的不朽的诗歌精神则期待着灵性的复苏。马尔库塞对艺术寄予深情,他提出了艺术异化的概念,“艺术的异化即是升华,在此过程中,艺术创造的种种生活形象与既定现实原则不可调和。”[17]在美丽新世界中,这一异化艺术形象就是印第安保留地的野蛮人约翰。他作为文明人在野蛮地出生的孩子,遭受排斥,天生就具备某种耶和华式的苦难意识。当来自文明世界的伯纳问起他的秘密,他说道:“我做了一件别人从没有做过的事,夏天的正午,我双臂伸开靠在一块岩石上,好像十字架上的耶稣。”[18]此时,赫胥黎明白无误地表达了野蛮人作为弥赛亚的化身,作为诗的化身。做为反启蒙的异化艺术形象,他勇敢正视野蛮人保留地里荒淫作乐的恶习,更力图为文明世界去除阴霾。
莎士比亚的诗是约翰生命体验的重要支点。当母亲琳达强迫他看那些文明世界的书时,他哭着把书扔到地上:“讨厌,讨厌的书。”在他十二岁接触到了一本“书脊叫耗子咬了;有些书页散了,皱了”的书:《威廉·莎士比亚全集》,阅读之后,“那些奇怪的话在他的心里翻腾,犹如滚滚雷霆说的话,犹如夏令舞会上的大鼓敲击声——若是鼓声也能表达意思的话;犹如唱玉米之歌的男声,很美,很美,美的叫你想哭……”[19]莎士比亚表达的是一种诗性经验,在前技术时代,人们有能力去冥想与沉思,有权利去体验与讲述。约翰正是把莎士比亚的诗句当做审美救赎的手段,循着这一脉熠熠发光的矿藏,勇敢进入苍白贫困、已入夜的半世界之夜。以高扬诗之精神的反启蒙精神,约翰叩响启蒙的自省之门。他这一努力指向人类的终极关怀、存在依据的诉求、神圣秩序的重构乃至意义系统的命名。他不断救赎,最终舍弃肉身。
首先,是诗对爱欲的救赎。
美丽新世界风行无限制的性交,丝毫不受道德伦理约束。不难理解,在极权主义社会,放纵的性欲是为了补偿受奴役的政治经济情况。为了促使人迅速成熟,新世界从幼儿时就进行各种性游戏,但人与人之间无感情可言,过分亲密或持久的感情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母子、情侣、家庭这些纲常伦理观都被纯粹的性欲冲垮。但爱欲毕竟不等同于性欲,性欲仅指两性间的欲望,爱欲却广阔的包含着饮食,休息,乃至各种人伦亲情的生物欲望。弗洛伊德提出爱欲本质论,认为生命的本能就是爱欲,性欲总是被看做向爱欲无限的无限渴慕和升华,马尔库塞更认为人的解放绝不是不受限制的性欲的允许,毕竟性欲只是个人的、局部的、有时甚或伴随着痛苦经验。不幸的是,随着文明的过度发展,充满建设力量的正常爱欲被暗中偷换成了纯粹的性欲,“文明要求不断的升华,从而削弱了爱欲这个文化的建设者”。[20]
文明升华,琳达对母亲身份表现出极度厌恶。她肆意打骂自己在保留地出生的儿子约翰,拒绝承担母亲的义务更认为生下孩子是对自己文明人身份的玷污,她只贪享与保留地的男人们纵欲的肉体之乐,这一点刺激了约翰,他想起《哈姆雷特》里的诗句:“不,而是生活\在油迹斑斑臭汗熏人的床上。\浸渍在腐败、调情和做爱里,\下面是恶心的猪圈”。他期待母爱,期待一个贞洁的母亲形象,但琳达使他幻灭。与性欲相比,爱欲是全面持久的,它建构真正社会文明,也使人寻得存在意义的情感。琳达给予约翰爱欲的一无所有,他们之间仍维系着不可抹杀的血缘亲情。当琳达病危,约翰不计前嫌,驻守在病榻边,不离不弃,挑战文明人的刻板伦理。他在她脸上读到回忆,读到母子俩在一起的经历,那些如莎士比亚戏剧般美丽的“关于天堂的故事,关于善与美的乐园的故事,并没有让它因为跟真正的伦敦和事实上的文明男女的接触而遭到玷污。”他保持着精神的灵性,把爱欲作为人类生存的答案,在幻灭的废墟里建构着爱的世界,以期对抗文明的压迫。
同样,在男女之爱上,他也保持着诗般的纯洁性。他深为高种姓妇女列宁娜迷惑。在他的印象中,列宁娜是丰腴美艳的天使。他并不知道,在爱欲溃散的文明世界,列宁娜只是丧失自主思维的浅薄交际花。在电梯里见到的人都喜欢跟她打招呼,因为她与他们都有过正常不过的肉体关系。在列宁娜外表美丽的感染下,他甚至一度眼中噙满泪水。但当他来到文明世界,连列宁娜都自愿献身想尝尝与野蛮人的性欲快感滋味时,他再一次对爱感幻灭了。他不能再爱这团没有灵魂失去生命的肉。他痛苦的拒绝着,“好像驱赶闯进来的毒蛇猛兽”,莎士比亚的诗句再次给予他救赎的灵光:“她们上半身虽是女人,下半身却是淫荡的妖怪;腰带以上虽为天神占有,腰带以下全归一群魔鬼……”(《李尔王》)。他认识到,这种只强调肉体感觉的性欲之爱没有任何创造意义,而真正的爱是具有创造性的一种表现,它包含了关心,尊敬,责任感和了解。约翰只能主动舍弃这个爱欲溃散的世界,以此来恢复对已被技术与暴政结合的世界所扑灭的超越性,虽然他的“这儿有多少美好的人”的赞语历经变调,但他的立场始终未变,诗歌的精神塑形着他的思维,打造着他选择评判世界的标准,那就是在不断幻灭之中坚守诗对爱欲的救赎。
其次,是诗对真理与信仰的救赎。
穆斯塔法·蒙德提倡廉价麻木的幸福,他自言曾为追求真理而付出代价,遂将幸福感贬低为欲望的满足于现实的安稳,受苦受难的代价太高。约翰却对麻木舒适中那些高科技替代劳力的东西弃之如敝屣:“有一类卑微的工作实用艰苦卓绝的精神忍受的,最低贱的事往往指向最崇高的目标。我想用艰苦卓绝的精神忍受一些压力。”真理自痛苦出,这往往是因为,在击碎梦想的事实面前,人先验的构想与判断已破灭,极端的悲剧感使人告别了先前一切先验判断,一切由观念构造的普遍性、必然性和稳定性以及一切由此产生的或遭遇的必然处境。当世间的希望破灭后,人们才会重新考量真理的意义与路径。
约翰在文明世界里对母亲和列宁娜爱欲的追求失败后,他更明了信仰的真谛,那就是通过受苦来获得真理的昭明。他主动请缨受苦来换取那些带上点眼泪的东西,在每个处于廉价幸福中做奴役而不察的人对苦难唯恐避之而不及时,约翰却说:“我现在就要求受苦难的权利。”他要求被孤立、被放逐。而支撑他的诗之精神正是不甘于生命幻象的冒险力:“勃勃的雄心振起了他的精神,使他蔑视不可知的结果,为了区区弹丸之地,拼着血肉之躯向命运、死亡和危险挑战。”(《哈姆雷特》)。对苦难而非幸福的诉求犹如惰性思维的马刺,刺激着人们趋向于真理的境界。
在忍受苦难的真理之旅中,约翰发掘了信仰,坚守着信仰。他被放逐到远离文明的地区隐居。为了弥补在闻名世界沾染的罪恶,他熬夜祈祷,乃至实施自鞭苦行。“他不时地伸平双臂,好像上了十字架,许久不动,伸得胳膊生疼,越来越疼,疼得发抖,难以忍受。”赫胥黎再一次把约翰比作基督。高度工业化的极权主义社会把真与美的合理性嫁接到舒适和幸福中而抛弃了上帝——认为他表现为一种虚无的存在,仿佛根本不存在。在丧失上帝规约的世界中,丧失信仰人进一步深深走入失落,约翰却坚信“上帝十之八九是存在的”。耶稣是人神二性的存在,因而每个人人性中也留存神性的萌芽,一如舍斯托夫指出:“人身上尚有永恒的,珍贵的东西,这就是上帝赋予每一个人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精神位格。其核心乃是人自身内具有的最高价值,无穷无尽地促使人向基督看齐的挚爱的意向。”[21]他于隐居地独自谋生,崇尚精神生活,向基督看齐,拒绝文明世界的一切,在园子挖地时,诗歌的精神依然临在于他精神维度的天空,他苦苦挖地,苦苦翻掘自己思想的实质,批判着启蒙对人性的鲸吞蚕食,“一铲又一铲,我们所有的昨天,不是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麦克白》)就这样,吟唱着莎士比亚走向死亡,约翰以圣徒的风度完成了舍弃肉身与精神上升的统一。
在此生死一线中,赫胥黎借野蛮人言说出最大的生存之秘,那就是《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五节里所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约翰以死来提醒每一个目睹这一死亡事件的文明人,何谓真与善,何谓存在之意义。把现世的存在投射到未来无限可能性之中,他启迪着众人反思自己人性中积淀的神性与罪恶的对抗。他的死亡是圣徒的死亡,他受的过也是代人受过,为救赎众人的存在,他以西绪弗死式的方式对启蒙的恶之花实施了重重一击。
就这样,以诗歌的精神,约翰完成了对堕落文明世界的双重救赎。在反启蒙的论域中,他的存在是赫胥黎救世的希望所在,也是我们重新思索启蒙、延续启蒙、建构启蒙的所在。
[1]AldousHuxley.BraveNewWorldRevisited[M].New York:Rosetta Books,2000:10.
[2]满斌.希伯来圣经的历史文本思想世界[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185.
[3]刘小枫.经典与阐释: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7
[4]Richard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inAmericanLife[M].New York:ALFRED A.KNOPF,1963:253.
[5]安东尼·J·卡斯卡迪.启蒙的结果[M].严忠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7.
[6]卡尔波·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M].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9.
[7][8][9][11][18][19]阿道斯·伦纳德·赫胥黎.美妙的新世界[M].孙法理,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0:5,73,186,35,30,111.
[10]马克思·霍克海默.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82.
[12][16][17]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80,214,66.
[13]沃尔特·李普曼.大众舆论[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7
[14]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39.
[15]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49.
[20]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M].黄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58.
[21]刘小枫.走向十字架的真:20世纪基督教神学引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77.
Trial and Redemption——Anti-enlightenment and Brave New World
ZHANG Qiu-zi
(School of Literature,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701,China)
Aldous Huxley's Brave New World presents reader a future world with develop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wever,thecombinationoftechnology andtyranny bringhuman beings adevastating impact.Facingthe excessive reason of enlightenment,Aldous Huxley,standing on anti-enlightenment position,judges the criminals brought by the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yranny.At the end of the essay,the writer analyzes the double concept of alienation of artistic image,and makes effort to discover a way of salvation from the discussion of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enlightenment and anti-enlightenment.
Brave New World;anti-enlightenment;technocracy;totalitarianism;redemption
I106.4
A
1674-7356(2012)02-0021-08
2012-03-30
张秋子(1988-),女,云南个旧人。南开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主攻欧美文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