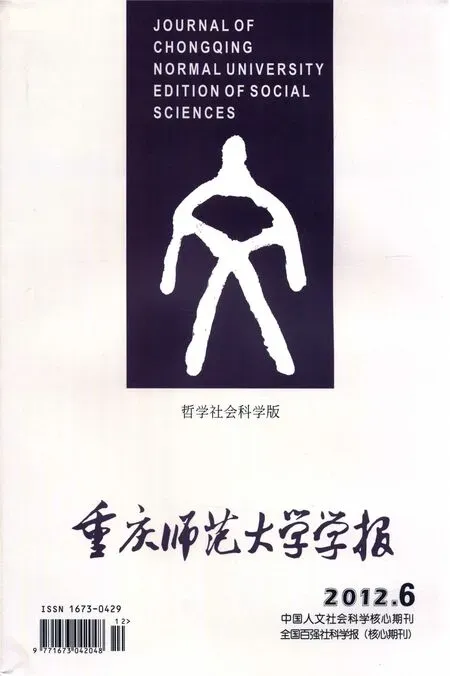叶嘉莹“兴发感动”理论对王国维“境界”的体系化及反思
2012-04-02朱维
朱 维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24)
叶嘉莹在诗词鉴赏和诗词研究方面均有极深造诣。在众多诗人、词人、词学研究者中,她唯独对王国维心冥神合,这主要是因为王国维形诸于笔端的生命感悟特别是王国维对自我、对他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的真诚态度深深震撼了她的心灵;更因二人相似的生活阅历在各自的生命体验中烙上相似的印痕。叶嘉莹透过王国维看到了曾经和自己一样挣扎的灵魂,这个灵魂在寻求种种安抚的过程中虽然创下了形式各异、贡献极大的学术实绩,最终却只能在死亡中求得真正的宁静,令人唏嘘感慨。从某种意义上讲,叶嘉莹的“王国维情结”正是因为王国维于她而言具有某种接受的合形式性:内心相通,使叶嘉莹能深入王国维的精神世界,对其学术人生的理解多了一份切肤之感和知己之音;感受敏锐,使叶嘉莹能在准确鉴赏诗词的基础上对《人间词话》进行研究,真正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这两点成就了叶嘉莹的王国维研究,使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成为王国维文学批评学术研究史上的一座高峰。笔者以为,叶嘉莹最大的贡献在于,在港台词坛对王国维的研究还停留在对个别概念的理解和论争上时,她已有意识地运用“兴发感动”理论使“境界”体系化,并使其在动态系统中获得自身内涵。
一、港台词坛关于王国维“境界”研究的问题之争
俞平伯曾总结了“词”自诞生之日起的发展道路,认为词本来有两种发展方向:一种是“广而且深(广深)”,一种是“深而不广(狭深)”,限于社会环境,经过文士的改造,词最终走上了“狭深”的发展道路。[1](8)词的风格和题材的狭深,也使词学呈现“狭深”的局面。晚清民初的词学基本“围绕着词的意格问题向纵深方向掘进”[2](7)。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港台词坛,在《人间词话》的研究上延续了晚清民初的词学本体传统,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彼此商榷和讨论,提出了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对以“境界”为核心的诸概念的理解问题。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其词学的核心和理解《人间词话》的关键。但他并没有对“境界”及围绕“境界”的诸多概念做明确具体的界说,因而造成诸多论争。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关于“境界”的来源问题。研究者指出“境界”非王国维首创,主要有两大源头:一是古代文论,二是佛学思想。关于古代文论的源头,争议不大:叶鼎彝认为,“境界”可以向上追溯到严羽、王士祯、司空图、刘勰、陆机、孔子,他们的理论都是对客观存在的“境界”的不同表述[3](51);饶宗颐认为“境界”本佛家语,在王国维之前,司空图、苦瓜和尚、王士祯、袁枚、刘体仁、江顺诒、陈廷焯等人即用“境界”论诗词[4](85);劳干认为境界说“实从沧浪渔洋的理论转变而来”[5](172-173)。但佛学博大精深,具体来源于佛学的哪一方面,研究者的意见分歧很大:蒋英豪认为源自佛家《翻译名义集》中的“尔焰”一词,意为由能知之智照开所知之境[6](100),强调的是“境界”的理性层面;王宗乐则认为境界一词出于《无量义经》,“一般皆作修学所造诣之境解”[7](60),偏重的是创作主体的素养。
“境界”理论源远流长,王国维的“境界”理论是从他的诗词创作中提炼出来的,同时也是对之前“境界”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既有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含义,又有自身特定的内涵。梳理其来源,不能只强调某一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尤其不应忽略把“境界”放回王国维的诗词创作中和文学批评的总体中加以探讨。片面强调王国维的“境界”来源于古代文论或来源于佛学,虽然反映了这个概念的丰富性,但也使“境界”研究陷入片面的学术论争。
第二,关于“境界”的含义问题。关于“境界”的含义,有如下几种解释角度:一是从训诂学角度解释。萧遥天认为:“‘境’的本字作‘竟’,说文:‘竟,乐曲尽为竟,从音,后人,会意’,引而申之凡是终极的都可称‘竟’。”由此境界即是“文学的终极现象”。[8](4)二是从作家修养的角度解释。徐复观指出境界指“人的精神生活所能达到的界域”,是修养的到达或造诣[9](160);柯庆明提出境界是“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之中,为某种洞察感悟所统一了的完整自足的生活世界”[10](224)。三是从读者欣赏的角度解释。吴宏一认为境界即是要将作品的“自然”和“真”传达给读者,“引起读者共鸣”[11](194;186)。四是从主客关系的角度解释。此种解释角度最为流行,有两种类型,第一种认为“境界”即是“写景”,“境”与“景”可以互换[12](187);第二种认为“境界”即情景交融:叶鼎彝指出做到“心物交会,情景融合,如水乳交融,结成一体而不可分,情即是物,物即是情”即是有境界[3](52-53);劳干认为境界包含“物态”和“气象”或“神”的两个层面[5](177);吴宏一认为境界是“统意与境二者而言的。境界也就是情趣和意象”[11](194,182);蒋英豪认为王国维的“境界”经历了由“情景”到“意境”再到“境界”的过程,情景的界限越来越彼此不分[6](101-102)。
这几种解释角度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训诂学的解释角度固然不错,但无视王国维“境界”概念的特殊性,而将其与一般意义上的“境界”等量齐观;从作家修养的角度解释“境界”只看到了“境界”创造主体的“能感之”的因素而忽略了技巧传达层面的“能写之”的因素;从读者欣赏的角度理解“境界”,使“境界”的评判标准主观化,偏离了王国维对“境界”的客观评判标准;从主客二分的角度理解“境界”,虽然客观上有助于分析“境界”的构成部分,但却使“境界”研究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此种二分模式,延迟了从总体上理解“境界”的进程。
第三,关于“造境”与“写境”的含义问题。研究者主要用创作方式的不同来解释“造境”与“写境”。蒋英豪认为“写境”偏重写景,强调写实,“造境”偏重抒情,强调理想。[6](109)徐复观认为写境是“写由关照所得之境”,“此时是触景生情”,造境是“写由想象而出之境”,“此时是因情铸景”。[12](189)
这种理解比较贴近王国维的原意。王国维这样论述“造境”和“写境”:“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理想家亦写实家也。”[13](191;192)王国维认为“造境”和“写境”的分别是“理想”和“写实”的分别,所谓“造境”即是用虚构之法创造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之境,因此“理想”的成分更多些;所谓“写境”即是用写实之法向自然中取得材料加以临摹,因此“写实”的成分更多些。然而“理想”成分再多的“造境”仍来源于现实,“写实”成分再多的“写境”仍有诗人主观的创造,所以二者很难分别。对于这二者的关系,王国维本人讲得十分清楚,所以并无太多论争。
第四,关于何为“有我之境”、何为“无我之境”的问题。一是用“移情作用”解释。姚一苇认为有我之境是“从自我出发”,使世界都染上我的色彩,无我之境则是尽可能摆脱自我的影响。[14](310-311)徐复观认为有我之境是“将自己的感情移出于景物之上”,无我之境是“将自己化为景物”。[12](190)二是用作品创作的不同方式来解释。柯庆明认为有我无我不同于主观客观,主观客观是指“表现时所取的立场,创作时处理的态度”,有我无我则是指“作品的内容,所塑造表现生活世界的性质”。[10](224-225)三是用叔本华的“意志”来解释。蒋英豪认为“无我之境”是“直观的对象与人完全无利害关系”的境界;“有我之境”是直观的对象与人的意志冲突,人只好放弃意志而直观对象的境界。[6](111)周策纵认为“有我之境”和优美密切相关,指对象之形式无关吾人之利害,“无我之境”和壮美密切相关,指对象之形式不利于吾人,吾人保存本能以超乎利害关系。[15](22)
“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理解问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王国维在探讨这两个概念时并未明言二者之间到底有何不同,只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13](191;192)正如“造境”和“写境”在具体的诗词语境中颇难分辨一样,“有我”和“无我”具体到某首诗词中也很难绝然分开,王国维所举的例子并不能清晰区分这两个概念的本质差异,尤其是又使用了不知所指的“动”和“静”二词,使如何理解“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困难重重。
笔者认为,理解“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动”和“静”。王国维将“静”与“优美”联系起来,将“动”与“宏壮”联系起来,而“优美”和“宏壮”是叔本华哲学体系中的概念。在叔本华看来,“优美”和“壮美”在客体上没有差异,因为二者都要在事物中展示“理念”。不同的是,优美是指“客体使理念的认识更为容易的那种本性,无阻碍地,因而不动声色地就把意志和为意志服役的,对于关系的认识推出意识之外了”,而壮美是指“纯粹认识的状况要先通过有意地,强力地挣脱该客体对意志的那些被认为不利的关系……才能获得。这种超脱不仅必须以意识获得,而且要以意识来保存”。[16](282)由此看来,“人惟于静中得之”是指“无我之境”不需要刻意让意志去认识其中存在的艺术之美,意志与艺术之美自然合一;“于由动之静得之”是指意志要刻意去除不利于认识艺术之美的关系,而后才能达到对其认识的目的。因此,笔者认为,由于上述研究或者没有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理解问题与叔本华的优美和壮美理论紧密联系起来,或者即使联系起来了但又没有领会其中的含义,所以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还有关于“气象”、“游”、“天才”、“真”、境界的大小高低等问题,也有少数学者提出来加以探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与如何理解《人间词话》紧密相关,是研究者无法绕过的问题。
二、叶嘉莹“兴发感动”理论对王国维“境界”的体系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港台词坛在王国维的“境界”研究中由于解释立场相差悬殊,结论差异很大,且多停留在个别问题的争议上,需要重新整合,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正是在此背景中应运而生。
其实,对以上所有问题的争论是对一个最根本问题的争论:何为“境界”?不难看出,港台学者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有些共同倾向:在认识论的范围之内谈论境界,把境界视为主观和客观或感情和景物的交融;在文本范围之内谈境界,忽视了境界形成过程中作家、社会、读者等参与进来而形成的合力作用;在理论范围之内谈理论,割断了“境界”理论和用“境界”理论指导诗词鉴赏的实践之间的关系;在特定的某一个问题范围之内谈某个问题,忽略了此问题和彼问题之间的关联,这是争议不断的主要根源。
叶嘉莹以“兴发感动”理论为基点,阐明了“境界”的内涵及与之相关的概念,对以上诸多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何谓“兴发感动”?叶嘉莹认为它是“诗歌之基本生命力”,“诗人之心理、直觉、意识、联想等,则均可视为‘心’与‘物’产生感发作用时足以影响诗人之感受的种种因素,而字质、结构、意象、张力等,则均可视为将此种感受予以表达时足以影响表达之效果的种种因素。如果用《人间词话》中静安先生的话来说,则前者应该乃是属于‘能写之’的种种因素,后者则是属于‘能感之’的种种因素”[17](339-340)。我们可以视“兴发感动”为“兴”、“发”、“感”、“动”四个要素,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的因果承续,分别对应于“外物”、“作者”、“创作”、“读者”,它们彼此互动而形成的丰富内涵,对“境界”阐释的体系化做出了贡献。
首先,“兴发感动”理论使“境界”的内涵形成彼此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层次。叶嘉莹认为诗词的功用在于唤醒人内心的生命,因而十分重视诗词的感发因素。这个立场,让她对境界的来源有不一样的看法:“‘境界’之梵语应为Visaya,意谓‘自家势力所及之境土’”,这里的“势力”是指“吾人各种感受的‘势力’”,“唯有由眼、耳、鼻、舌、身、意所具备的六识之功能而感知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六种感受,才能被称为‘境界’。由此可知,所谓‘境界’实在乃是专以感觉经验之特质为主的”。[17](220)另外,《人间词话》多处提到“境界”,但是在不同层次的意义上使用,既包含传统的几种不同的含义,又有以西学为背景的新义,因此不容易被准确把握。叶嘉莹指出《人间词话》中“境界”一词除具有本体意义外,还有另外四个层次的意义:一是“指一种现实之界域而言者”,二是“指作品内容所表现的一种抽象之界域而言者”,三是“指作品中所表现之修养造诣而言者”,四是“指作品上所写之情意及景物而言者”。[17](223—224)这四个层次意义的仔细厘定,将含混的“境界”之义做了精微的分别,包括了从创作到鉴赏的各个层次,是对境界极为科学的解释,也使叶嘉莹成为境界含义研究的集大成者。80年代之后,仍有为数不少的论文探讨境界的内涵,但很多都是低水平的重复。
其次,“兴发感动”理论使“境界”包含作家——作品——读者的完整动态体系,并使围绕“境界”的其他概念也融入这个动态体系之中。叶嘉莹认为:“凡作者能把自己所感知之‘境界’,在作品中作鲜明真切的表现,使读者也可得到同样鲜明真切之感受者,如此才是‘有境界’的作品。”[17](221)因而,“境界”有三个必备要素:作家有鲜明真切之感受,作品有鲜明真切之表现,读者有鲜明真切之体会。而作为创作主体的词人和作为审美主体的读者,通过不同的兴发感动之作用,使作为审美对象的词完成了从创作到鉴赏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兴”的作用是由物到心,“发”的作用是由心到物,这两个因素突出了外物和创作者之间的互相作用;“感”的作用是由心到文,“动”的作用是由文到心,这两个因素突出了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互相作用。比起其他的研究,这个理解更加综合和全面,而且由于强调了作为接受者的“读者”在“境界”形成中的参与作用,使“境界”具有更开放的品格。
在此基础上,叶嘉莹将与“境界”相关的概念也一并纳入由“兴发感动”贯穿的创作到鉴赏的过程之中:“造境和写境”是在境界创造过程中,对内容所取材料之不同的划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是物我关系不同的划分;“境界之大小”是对作品中取景之巨细及视野之广狭的划分;“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是对写作的叙写态度的划分;“真景物真感情”是强调感受的真切和表达的真切;“隔与不隔”是就作品是否有真切之感受并是否真切表达出来而言;“代字、隶事”是就作品表现时使用的文字而言;“游”是就词的口吻和表现态度而言;“文学之历史演进观”的得出是因为一种文体越发展到后来,就越因为追求技巧而丧失了真切之感受;用名词一类的印象式批评术语,主要强调作品本身的素质,形容词一类则是强调对读者造成的感受;“三境”说也是因了兴发感动的联想作用而来。可以看出,围绕着“境界”概念的其他概念和观点,基本以“兴发感动”为中心,成为一个自足的“体系”。这个体系纠正了前人研究一个极大的误区:把作为核心的“境界”和其他概念割裂开来分别探讨,使此概念的解释和彼概念的解释彼此冲突。叶嘉莹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她始终把各个概念的解释放到王国维的批评实践之中检验,使结论不再流于空头理论。
最后,“兴发感动”理论使“兴趣说”和“神韵说”与“境界”一脉相承,在这个线性发展脉络中“境界”获得了更深厚的层叠意义。叶嘉莹以心物交感理解王国维的“境界”,并认为它与严羽的兴趣说、王士祯的神韵说具有承续关系,因为三者都“重视心与物相感后所引起的一种感受之作用”,不同之处在于:“沧浪之所谓‘兴趣’,似偏重在感受作用本身之感发的活动;阮亭之所谓‘神韵’,似偏重在由感兴所引起的言外情趣;至于王静安之所谓‘境界’,则似偏重在所引发之感受在作品中具体之呈现。沧浪与阮亭所见者较为空灵;静安先生所见者较为质实。”[17](333)叶嘉莹用“兴发感动”激发“兴趣说”、“神韵说”与“境界”的相关因素,使之成为前后关联的系统。
三、“兴发感动”理论对传统文论的继承和发展
叶嘉莹在其论著中没有专门对“兴发感动”下过定义,但曾多次对其界定和论述。“兴发感动”理论实则是生命诗学和接受美学高度融合的产物。生命诗学以个体生命为关注中心,以生命体验为辅助手段,追问生命存在的超越性意义。接受美学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之维探讨作品的意义。叶嘉莹的“兴发感动”理论将二者进行融合,形成了自身的特色。缪钺曾这样总结叶嘉莹的“兴发感动”理论:“叶君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心物相接,感受颇繁,真情激动于中,而言辞表达于外,又借助辞采、意象以兴发读者,使其能得相同之感受,如饮醇醪,不觉自醉,是之谓诗。故诗之最重要之质素即在其兴发感动之作用。”[18]此种概括十分精准。“兴发感动”的起点在心物互感,在作者心中酝酿真情之后,经由文字传达给读者,并使读者也深刻体会到作者的感情。因此,“兴发感动”将情之萌生、情之酝酿、情之表达、情之体验四个环节一并串起,虽无宏大的理论规模和体系,实已具备较完整的理论雏形。笔者拟从理论来源和理论特点两方面来分析“兴发感动”理论对传统文论的继承和发展。
一,从理论来源看,“兴发感动”虽是叶嘉莹独创的一个概念,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兴”的诗学传统。“兴”强调心与物的交感作用,《礼记·乐记》最早提出心物交感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19](2527)这一思想在陆机的《文赋》中继续发展:“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20](14)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全面地总结了心物感应理论,“确立了心物互感交融乃是兴的美学结构的基本特点,并初步将它视为文学艺术的生命本体”[21](329)。叶嘉莹的“兴发感动”以心物交感为最基本的动力,指出心物交感的方式有二:一是得之于“自然界节气景物”之变化的感发,二是得之于“人事界之生活际遇”,表现的方式和途径是传统作诗的比、兴和赋三种方法。[17](321)这其实是站在生命诗学的立场,从表现形式到表现内容两方面对古代诗词做了一个极为全面的总结。叶嘉莹借用王国维的话,将心物交感的作用成为“能感之”的因素,具备敏锐的感受力,是诗人之成为诗人的先决条件。除此之外,诗人还须熟练掌握字质、结构、意象、张力等形式技巧,将种种感受生动地传达出来,具备“能写之”的禀赋。“兴发感动”理论的最大特点是感发生命。
二,从理论特点来看,叶嘉莹引入生命诗学理论,强调“兴发感动”的最大特点是“感发生命”。她说“兴发感动之作用,实为诗歌之基本生命力。”[17](339)又说:“对诗歌之衡量,当以其所传达之感发生命之有无多少为基本标准。”[22](19-20)笔者认为,“兴发感动”理论的提出与叶嘉莹的个人际遇密切相关。叶嘉莹十三岁即从伯父学习古典诗文,入台湾辅仁大学后又从顾随学习诗歌和词曲,顾随“一向推重王静安先生,无论其理论亦或词作”[23](178),他的鉴赏能力“感锐而思深”[24](1),给了叶嘉莹不少启发。诗词研究在她的人生经历中,与其说是文化修养的增强剂,不如说是生命苦痛的安慰剂:她幼年丧母;中年饱受时局动荡之苦;壮年丧女,很长一段时间独自承担全家的生活。政局变迁、失亲之痛、生活之累在她的人生经历中层层累积,最终成为她生命体验的基本结构。在众多词人和词学批评家中,她独钟情于王国维,是因为王国维和她一样酷爱诗词,也一样在动荡的时局中饱受丧妻丧子之哀和精神无所归依之痛。叶嘉莹参透了王国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生命体验和以诗词为慰藉的无奈,同时也和王国维一样借助诗词来抒发生命,并提炼出带有强烈的生命诗学色彩的“兴发感动”理论。
四、“兴发感动”理论解读王国维“境界”存在的问题
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兴发感动”确有其适用性。但是,“兴发感动”理论在叶嘉莹的诗学体系内圆融自得,并不等于在王国维文学批评体系内同样游刃有余。“兴发感动”理论仍存在着盲视之处。事实上,“兴发感动”不仅是叶嘉莹接受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基点,也是叶嘉莹诗学体系的基点。叶嘉莹对“境界”的理解在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领域里极具影响力,暂且探讨用“兴发感动”解读“境界”所存在的问题。
叶嘉莹以其高度的鉴赏力,运用“兴发感动”理论重建“境界”理论体系,虽功不可没,但有削足适履之嫌。叶嘉莹认为“境界”是“特指在小词中所呈现的一种富于兴发感动之作用的作品中之世界”[25](66)。但王国维的“境界”意蕴丰富,具有词之本体的地位,而且“兴发感动”只是境界之成为境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徐复观在反驳学界流行的“境界即是能表现具体而真切的意象”的观点时曾指出:“表现一种具体而真切的意象,乃是诗词之所以成为诗词的基本条件。不具备此种基本条件,不然不成为诗词。但具备了此种基本条件,未必便是‘最上’的作品。”[9](150-160)同样的道理,“兴发感动”是“境界”的基本条件,但具备了此种基本条件未必就是有“境界”的作品。
作为具有形而上色彩的“境界”,笔者以为“境界”作为词的根本包括三种必备之品质:一是词要有区别于其他文体的“要眇宜修”之美感特质,这是就词的独特性而言;二是所抒发之情和所描绘之景须“真”,这是就词的内容而言;三是应该“忧生忧世”和“担荷人类罪恶”,这是就词的价值指向而言。叶嘉莹强调了词的“要眇宜修”之美感特质,但是忽略了景物之“真”而一味强调感情之“真”,尤其是没有体味到王国维已使“境界”一词超越了词的局限,扩展成一种至高的人文理想。总结起来,“兴发感动”理论的盲视之处主要有二:
一、“兴发感动”理论强调主观感受之真而忽略了客观景物之真。王国维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13](193)他是从两方面强调境界之“真”的,一是从主观上讲,要有“真感情”;二是从客观上讲,要有“真景物”。二者水乳交融,不可分割,同时兼备,才是有境界。叶嘉莹也认识到“真”在境界中的重要地位:“无论是写景、叙事或抒情,也无论是比体、兴体或赋体,总之,都需要诗人内心中先有一种由真切之感受所生发出来的感动的力量,才能够写出有生命的诗篇来,而如此的作品也才可以称之为‘有境界’。”[17](334)但是,她把具有兴发感动作用的“真感情”作为境界的核心要素,忽视了王国维同样也注重“真景物”的本来意图,不免有失偏颇。事实上,王国维不仅提出了境界中的景物之真,而且还讲到了如何实现的途径:与自然融为一体。他极力推荐纳兰容若词,认为其“以自然之眼观物”[13](217),深得自然之神髓,是北宋以来唯一的词人。景物之真是感情之真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因为词人“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13](220)。因此一味强调主观感受之真,忽略了客观景物之真,与王国维的“境界”还是有距离的。
二、“兴发感动”理论忽略了境界理论中蕴含词中应蕴含“忧生忧世”和“担荷人类罪恶”的精神指向。王国维对李后主词尤为厚爱,在《人间词话》的64则定稿中,涉及李煜的词话有6则之多,在王国维具体评赏的所有词人中居第一位。王国维分几个层次高度评价了李煜词:一是李煜对词进行了开创性的改造,“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将家国之恨融入词中,使词逐渐摆脱香丽浓艳而具有深邃的意境;二是李煜词没有局限在形式技巧的层面,具有“神秀”的品格;三是李煜用“赤子之心”创作的词性情极真;四是李煜词具有“担荷人类罪恶”的悲情,将个人的渺小与历史的恢弘、个人的短暂与自然的永恒、个人的痛苦和人类全体的悲苦书写得淋漓尽致,最终超脱了个体而将大关怀指向人类,这才是李煜词的真正意义。
叶嘉莹的“兴发感动”理论忽略了王国维强调的景物之真,并且将“境界”的创作视野囿于词的生命感发力而没有体会到其中熔铸的人文理想,虽然她独创一家,理论特色鲜明,但最终还是与王国维的“境界”擦肩而过。
[1]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前言[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方智范,邓乔彬,周圣伟,高建中.《中国词学批评史》前言[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叶鼎彝.广境界论[A].何志韶.《人间词话》研究汇编[C].台北巨浪出版社,1975.
[4]饶宗颐.《人间词话》平议[A].何志韶.《人间词话》研究汇编[C].台北巨浪出版社,1975.
[5]劳干.论神韵说与境界说[A].何志韶.《人间词话》研究汇编[C].台北巨浪出版社,1975.
[6]蒋英豪.王国维文学及文学批评[M].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国学会,1974.
[7]王宗乐.苕华词与人间词话述评[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
[8]萧遥天.语文小论[C].槟城友联印刷厂,1956.
[9]徐复观.诗词的创造过程及其表现效果[A].何志韶.《人间词话》研究汇编[C].台北巨浪出版社,1975.
[10]柯庆明.论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境界[A].何志韶.《人间词话》研究汇编[C].台北巨浪出版社,1975.
[11]吴宏一.王静安的境界说[A].何志韶.《人间词话》研究汇编[C].台北巨浪出版社,1975.
[12]徐复观.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说”试评[A].香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粹·文学评论篇(1950—2000)[C].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
[13]况周颐,王国维.蕙风词话·人间词话[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14]姚一苇.论境界[A].艺术的奥秘[C].漓江出版社,1987年.最初由台湾开明书店于1968年出版.
[15]周策纵.论王国维人间词话[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1.最初由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972年出版.
[16]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M].商务印书馆,2007.
[17]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18]缪钺.迦陵论诗丛稿·题记[C].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1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中华书局,1980.
[20]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1]刘怀荣.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7.
[22]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例说[A].迦陵论诗丛稿[C].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23]顾之京.《论王静安》整理后记[A].施蛰存等主编.词学(第四卷第十辑)[C].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4]叶嘉莹.早年学诗经历[A].迦陵文集(第十卷·我的诗词道路)[C].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25]叶嘉莹.中国词学的现代观[M].岳麓书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