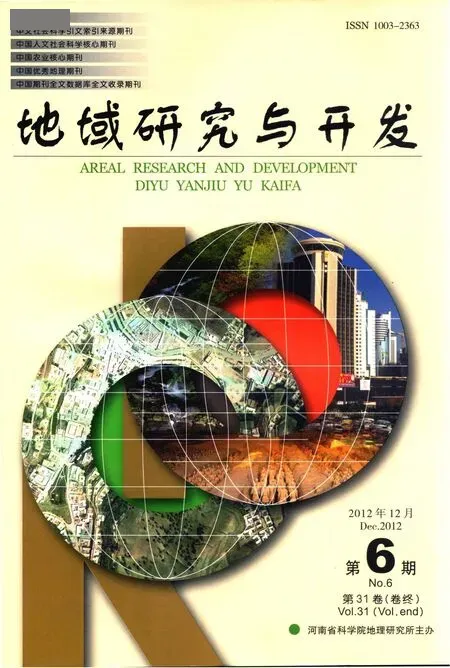耕地保护主体的行为方式及其特征分析
2012-04-02张凤荣
李 灿,张凤荣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193)
0 引言
耕地的资源利用价值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市扩张、土地生态保育的需求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和稀缺性;与此同时,在新一轮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耕地加速流失的形势日益严峻。长期以来的实践证明[1-2],耕地保护的效果离政策设计目标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并且这种差距有愈加严重的趋势。国际上的经验说明,当经济驱动力与政策相左时,实际的结果往往是受经济动力左右,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经济驱动的作用尤为明显[3]。目前,对于因逐利行为造成耕地转移的主要动因已为许多学者所共识,不同学者从经济驱动机制、耕地保护的经济学行为、耕地补偿机制、耕地价值以及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4-9]。在当前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下,耕地保护主要是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的方式自上而下地进行指标的分解下达,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法规予以保障实行,耕地保护责任的主体角色由经济上相对弱势的农民群体来承担,由于耕地保护的成果被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因而存在着制度设计上的不公平性,耕地保护效果往往是低效的[3,10-12]。本研究通过分析耕地保护的主体行为特征和现行制度框架下的耕地保护运行机理,认清耕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为探寻并建立耕地保护的长效机制提供参考。
1 耕地保护主体的行为选择
1.1 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行为选择
为保护耕地,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措施,并把保护耕地、实现粮食安全列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之一。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如制定了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实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用途管制、农地征用管制等等,但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应该说当前中央政府实行的是积极的耕地保护政策,并且是一种在强势行政体制下的目标管理制度,但由于地方政府的灵活变通性以及在市场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过程中,致使中央政府耕地保护的初衷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地方政府所化解和消融,结果是中央政府处于被动地位,地方政府成为土地支配实际主体,掌握了资源的分配权。
在中央政府下达耕地保护指标后,地方政府拥有了足够的话语权左右耕地的规划布局,特别是对基本农田的空间划定。地方政府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主体,负有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职责和义务,当前经济发展的效果又与主政地方官员的政绩直接相关,因此,在利益驱动机制下,地方政府过于追求经济产值和发展速度,并以消耗耕地资源为代价。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负有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保护耕地任务的责任,需严格执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因此,实际上地方政府处于一种发展与保护的“两难”境地。然而,当经济发展政策与资源利用的目标发生矛盾时,地方政府政策的理性选择必然是“利大取重,害中取轻”,选择保护让路于发展的策略。因而,就会出现目前常见的耕地破碎分散、基本农田“上山下滩”的现象。
1.2 农民保护耕地的行为选择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地区的农户是“穷而有效率的”,其农业生产的行为也是“理性的”[13],也就是说在没有外在比较利益驱动和刺激下,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户往往能够有效地保护好耕地,究其原因是在该地区转用耕地获利的机会相对较少,或者农户预期的机会成本损失很低或者不存在。国内学者高明认为农户对耕地的投入取决于对耕地投资回报预期,如果耕地收益预期较大,农户就会采取保护耕地的使用方式[14]。陈美球等通过对不同农户群体对待耕地流失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高龄农户对耕地保护的积极性较年轻农户要高,但是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更愿意从耕地里面抽身出来从事非农产业[15]。从比较利益和市场价值机制的导向来看,农民的选择完全是理性化的,因为农民具有摆脱贫困和提高收入的潜在动力。
另一方面,农民缘于世代流传下来的“土地等于饭碗”的传统意识,不愿放弃耕地,认为耕地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对耕地不断投入以保证耕地的生产能力,但在面对农地转用的利益激励时,农民就有不愿保护的潜在心理,盼望通过农地非农化过程获得利益,然而在实际中,通过农地非农化过程农民预期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完全实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对于耕地保护处于一种“生活保障vs获取利益”的观望心态。
2 现行制度框架下耕地保护的特征
2.1 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耕地保护
当前,我国耕地保护是通过“委托-代理”机制实现的[16],其特点是通过法规和政策约束机制以及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管体系,借助于土地规划载体,把耕地保护的责任层层分解下达,其实质是政府(中央政府)委托给耕地保护实际执行者(地方政府及农民),其中的委托-代理链条就构成了耕地保护的相关利益主体。在此过程的传递下,各级地方政府只作为耕地保护的名义主体,而实际委托人为农村集体组织,并通过承包方式,最终委托给耕种土地的农民,即农民作为耕地保护的直接执行主体。然而,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农民之间,必然会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目标激励的偏差引起管理制度的低效行使[17],其根源在于此种体制下中央政府与耕地保护主体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
基于理性经济人的行为选择理论,委托-代理双方都在关心自己效用的最大化,为顺利实现耕地保护的目标,需要使两者的目标函数趋向一致,然而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逐渐出现了与中央政府不完全相同的利益追求曲线,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出现了利益上的差别[18],加上信息不对称,就会使得在两者之间的代理关系中产生一种非协作、非效率的问题,即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问题[19-20]。因此,在面临委托-代理双方目标效应函数不一致的情况下,就需要引入新的激励机制,最大化委托人的目标函数。
2.2 基于公平偏好视角下的耕地保护
首先,实行统一的耕地保护政策未把区域间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实际等因素有效地考虑进来,政策设计注重过程的公平性,全国各地按照统一的政策和规则管理,忽视形式公平掩盖下的效率差异,其结果常常是耕地保护的步调不一致,效果相差大。由于耕地保护指标的分配存在不科学性,发达地区因经济发展的压力往往突破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而欠发达地区却因用不完占地指标而连年结转[21]。
其次,耕地所产生的环境生态、粮食安全、社会保障等外部效益被政府简单地视为一种“公共利益”,并理所当然地归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利益倾斜,导致耕地保护主体感受到不对等的权利与义务。并且农民在保护耕地过程中所丧失的“机会成本”得不到补偿,极大地影响了耕地保护的积极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原本脆弱的耕地保护激励被逐步提升的公共意识所抵消。
第三,耕地保护是政府基于公共目的所设定目标基础上的强制性行为。换言之,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为保障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对耕地转为其他用途采取极为严格的限制措施,农民只能被动地接受和执行耕地保护的政策。《土地管理法》明文规定,耕地征转流程只能是由政府部门来主导,并且极力限制各种经济主体自主介入的市场行为;而在耕地的经营方式上,囿于“农地农管”的思维方式,也并不鼓励引入市场化的经营管理模式。在这种以政府主导的耕地保护政策背景下,农民的发展诉求常常被忽视,所产生的后果,一是剥夺了农民的农地发展权,抑制了农民保护耕地的内在动力;二是限制了耕地资产功能的发挥,使农民背负机会成本,耕地保护的社会意愿与农民个人意愿的矛盾在此凸显出来;三是难以形成市场化的耕地规模化经营方式,阻碍耕地生产效率的提高。
2.3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耕地保护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集体”这种层级管理体制对于委托-代理方式下的耕地保护关系而言,必然会由于代理人的目标与委托人的目标不一致,导致管理与执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出现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农民耕地保护的要求不一致的现象。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包含有两个管理层面上的信息反馈偏离。
第一个层面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最高土地行政审批部门,把握一定时期内耕地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政策走向,主要对规划期内耕地保护的数量和质量提出要求,其管理决策所依赖的信息绝大多数由地方政府提供,信息质量具有被打折扣的嫌疑,所制定的目标与地方实际产生一定偏离。作为委托方的中央政府由于难以准确观察到目标偏离,因而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第二个层面就是地方政府与耕地保护直接执行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是耕地保护政策执行的主导方,由于接近信息源,因而比中央政府更能控制信息的流量和真实程度,但是地方政府更倾向于管理的技术层面,偏好规划控制和数量管理,而对农民利用耕地的实际情况,以及把耕地擅作他用的现象不能实行有效的监管,难以及时纠正土地违法行为。与此同时,农民处于耕地保护政策与管理的被动执行地位,直接形成了耕地保护执行过程中的信息来源,熟悉耕地的地力条件和生产功能,却由于信息反馈机制的缺乏,不能把有效信息及时传递给决策者,致使农地的管理和规划与农民对耕地投入和维护的实际意愿不相吻合,造成政府土地管理与农民农业生产行为上的信息不对称。
2.4 投入产出不对等下的耕地保护
耕地不仅具有稳定社会、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而且承担有提供生态保育空间、净化环境的外部性功能,因而耕地保护的社会成本应由全社会共同承担。农民对农业生产进行投入后,只能从耕地中获取单纯的农产品经济价值,耕地的生态和社会价值却不能在市场交易中得到体现,而这部分外溢价值来自耕地保护主体所提供的效用输出,其他社会成员却免费享有,从而造成耕地保护成本与收益分配的不一致,严重损害了耕地保护主体的利益。
对地方政府而言,保护耕地意味着为中央政府承担了由于资源禀赋差异而导致的区域间耕地保护的外部性成本,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机会,因为农地征转可获取大量土地出让金,为地方经济发展创造条件[22]。对此,地方政府出于全局的粮食安全和公共利益考虑,必然会牺牲因区位差异而背负的成本去“顾全大局”。对于农民而言,却是既承担了耕地的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成本,又背负了巨大的耕地转用机会成本。由于国家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外部性忽视,没有形成对农户耕地保护的社会化补偿机制[23],因此,如果农民不能就其提供的环境生态、粮食安全等外部性效益获得合理的补偿,农民就会逐渐失去对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正如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指出的,农民是否珍惜土地在于他们对于经济收益的考虑[24],当耕地转用有利可图时,市场经济行为会推动耕地向获益更高的用途转变。
2.5 利益干扰下的耕地保护
耕地保护不仅在地区间存在“诸侯经济”的问题,而且在政府部门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割据”现象。按理说保护耕地是政府为代表公共利益而实行的监管行为,应该得到政府公共部门的支持和贯彻落实,但由于公共部门利益的异质性使得政策难以执行[25]。在对待耕地征转问题上,随着土地收益在政府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在对待耕地保护监管方面也存在着意见冲突,地方政府中公共支出部门倾向于松弛的耕地保护政策,而农林、水利、环保部门则与之相反。具体而言,比如规划部门试图通过规划的方法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和集约度以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建设扩展问题,而土地管理部门则努力通过严格的用途管制以防止耕地的流失;经济发展部门想利用低地价扩大招商引资规模;农业部门希望通过耕地保护措施获取更多的财政补贴;交通部门想优化本部门的规划体系等等,各部门基于本位利益考虑的做法极大地弱化了政府防止耕地流失的努力。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耕地保护博弈过程中也不断在调整各自的策略。中央政府在对待耕地保护方面态度一直都很坚定,政策设计极为严格,特别是在耕地流失问题显化后,必然会针对耕地流向建设用地的行为采取更为严格的限制性政策。然而,地方政府在面对巨大的发展诱惑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多数是与中央的要求相违背的。有数据显示,2007—2010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比例从0.31:1迅速上升至0.75:1,而与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的比例由0.18:1上升到0.41:1,土地出让收入(未扣除成本)和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几乎相当,因此土地财政又有“第二财政”之称[26]。由此可见,在当前所谓“经营土地”来推动“经营城市”的发展思路下,地方政府在面对巨大经济利益时的政策选择倾向必然会导致耕地流失的进一步失控。
3 思考与对策
现行的农用地管理制度具有明显的城市偏向性[27],耕地保护的主要挑战来自于应对城市空间扩张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当前我国处于城乡发展转型和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耕地保护力度不容放松,同时经济和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土地供给也需要有相应程度的保证,因此,应当正视耕地一定程度上的减少。但是,基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和粮食安全考虑,严厉的耕地保护政策和监管措施仍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3.1 完善经济补偿和激励机制
在市场化日益深入发展的环境下,政府应该为农民保护耕地所背负的机会成本和耕地功能的外溢效益”埋单”。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背景和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下,农民是在政府设定的耕地保护目标下的政策执行主体,被理所当然地认为负有保护耕地的责任。就市场经济行为而言,政府剥夺了农户对承包地经营的选择权,农户为了国家的粮食战略目标牺牲了某些潜在的经济利益;同时伴随耕地保护所产生的生态、社会效益价值并没有体现在农民耕地保护的行为上,因此,有必要对耕地保护功能的外溢效益进行评估,将耕地保护损失的外部成本“内化”,提高耕地保护的收益和占用耕地的成本,从经济激励上调动农民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和抑制耕地的非农化驱动。
由于存在明显的政府委托代理下的激励扭曲问题,因此,有必要建立激励相容的绩效考核制度,采取诸如修正耕地保护政策目标、强化耕地保护政策执行力度、转变政府官员的考评方式等措施,构建一套合理可行的激励机制,由政府正面激励农民保护耕地的行为,提高农民耕地保护的积极性。
3.2 构建畅通的信息反馈机制
在委托-代理方式的耕地保护机制下,存在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间的信息交换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以及双方利益诉求的差异,具有较高的效率损失风险。而且在当前缺乏健全的社会参与机制下,必然产生严重的管理反馈链条上的阻塞,导致政府的政策意图不为农民所理解,农民的意见也难以参与到政策的修改完善当中,以致出现管理过程的滞后性问题。因此,应当构建畅通的信息反馈渠道,让农民在执行耕地保护政策当中产生的问题能够如实迅速地反馈到政策制定者当中,以利于政府实时调整监管措施,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同时,在当前新农村建设和法治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建立公众参与机制,让农民获得参与权和自主权,及时有效地表达耕地保护过程中的利益诉求,真正体现耕地保护的主体地位,显得极为必要。
3.3 创新土地产权体系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土地的产权制度变革处在不断的探索当中,可借鉴国外土地发展权的思想,引入土地发展权制度设计,平衡土地保护、金融补偿、经济激励、区域发展战略和发展等之间的关系[3]。通过增设农地发展权,使耕地的资产价值在市场中得以体现,而让农民参与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土地增值分配,有利于消除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为中央政府有效地管理和保护耕地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农地发展权能够有效地应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压力,要实行符合当地实际的耕地保护监管措施,不断深化国家土地管理的宏观调控。
[1]毕于运,郑振源.建国以来中国实有耕地面积增减变化分析[J].资源科学,2000,22(2):8-12.
[2]封志明,刘宝勤,杨艳昭.中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趋势分析与数据重建:1949—2003[J].自然资源学报,2005,20(1):35-43.
[3]丁成日.美国土地开发权转让制度及其对中国耕地保护的启示[J].中国土地科学,2008,22(3):74-80.
[4]曲福田,陈江龙,陈雯.农地非农化经济驱动机制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05,20(2):231-241.
[5]钱忠好.耕地保护的行动逻辑及其经济分析[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1):32-37.
[6]张吉献,秦明周,张启珍,等.我国耕地保护制度的经济学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0,29(2):99-103.
[7]周小平,柴铎,宋丽洁.“双纵双横”:耕地保护补偿模式创新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3):50-56.
[8]蔡运龙,霍雅勤.中国耕地价值重建方法与案例研究[J].地理学报,2006,61(10):1084-1092.
[9]蔡运龙.中国农村转型与耕地保护机制[J].地理科学,2001,21(1):1-6.
[10]谭述魁,张红霞.基于数量视角的耕地保护政策绩效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4):153-158.
[11]朱红波.我国耕地保护政策运行效果与效率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7,23(6):50-53.
[12]纪昌品,汤江龙,陈荣清.耕地保护政策的内涵及其公平与效率分析[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5,22(3):28-32.
[13]毕继业,朱道林,王秀芬.耕地保护中农户行为国内研究综述[J].中国土地科学,2010,24(11):77-80.
[14]高明.现阶段农户对耕地投入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5,26(2):43-47.
[15]陈美球,邓爱珍,周丙娟,等.不同群体农民耕地保护心态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5(9):16-22.
[16]朱道林.土地资源利用与政府调控[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1.
[17]曲福田,冯淑怡,诸培新,等.制度安排、价格机制与农地非农化研究[J].经济学,2004,4(1):229-248.
[18]黄少安.产权·人权·制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19]陈志刚,曲福田,黄贤金.转型期中国农地最适所有权安排:一个制度经济分析视角[J].管理世界,2007(7):57-65,74.
[20]郭贯成,吴群.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析中国耕地保护体制障碍[J].中国土地科学,2008,22(4):49-55.
[21]张效军,欧名豪,李景刚.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变迁及其绩效分析[J].社会科学,2007(8):13-20.
[22]姜广辉,孔祥斌,张凤荣,等.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2009,23(7):24-27.
[23]陈美球,周丙娟,邓爱珍,等.当前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现状分析与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7(1):114-118.
[24]张五常.佃农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5]黄征学.我国耕地流失中的政府行为研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29-35,77.
[26]贾康,刘微.“土地财政”:分析及出路——在深化财税改革中构建合理、规范、可持续的地方“土地生财”机制[J].财政研究,2012(1):2-9.
[27]王淑莉,张换兆,李洁松.中国农地宏观管理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博弈分析[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9,27(3):5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