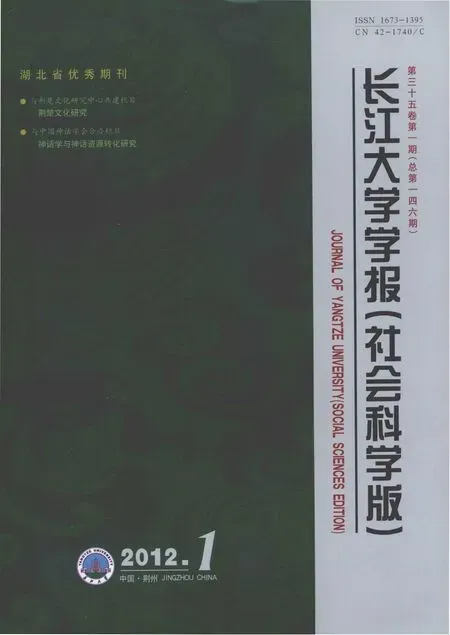媒体、通俗文化与社会关系话语权①
——以《哈利·波特》为例
2012-03-31廖建乐王宁川
廖建乐王宁川
(1.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中心,广东 广州 510260;2.华南农业大学 珠江学院,广东 广州 510900)
媒体、通俗文化与社会关系话语权①
——以《哈利·波特》为例
廖建乐1王宁川2
(1.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中心,广东 广州 510260;2.华南农业大学 珠江学院,广东 广州 510900)
政治、媒体与通俗文化,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文性的共生关系。媒体与文化交织在一起,不断地对现存文化素材进行梳理与整合,从而在经验和环境中塑造出特殊代表,并使其看似与现实意义之间有着必然的、准确的,甚至是与生俱来的联系。
媒体;通俗文化;话语权;哈利·波特;社会关系
通俗文化和大众传媒,一直是传播意识形态、政治论辩、构建社会概念和意义的重要阵地。只要有话题出现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日程上,媒体就会对公众的态度和行为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向导作用,“各种政治概念和社会价值被大众传媒及其中所传递的信息所塑造”。同时,通俗文化又是大众媒体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少学者认为通俗文化仅是供人娱乐的“草根文化,大众文化,公民文化”,是一种空洞、主观、武断、以态度为基础的认知,不足以成为衡量社会政治活动的理论标准。
一
通俗文化之所以能与大众传媒融为一体,成为政治的表达工具,并在全球范围内对精英文化形成一种淹没性的浪潮,是因为与死板的说教方式相比,大多数人更乐于在娱乐中接受信息的传播或理念的传递。而娱乐功能恰恰又是通俗文化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娱乐媒体生存在大众之中,“大部分媒体,特别是电影和电视,都能强化政治象征主义,处理各种象征符号和令人似是而非的东西”。[1](P445)而通俗文化在传播娱乐的同时,对传统道德的影响也具有侵蚀力。因此,二者才有机会成为一种传播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美国可以说是最早意识到“娱乐功能”在意识形态传播和国际政治博弈中的作用的国家之一,自觉用文化来传播政治,用文化政治来影响世界政治进程,使其话语权在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中充分发挥作用。好莱坞电影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为什么美国的文化输出能得到相应的政治回报?这其实是以礼物为基础的政治交换,即礼物交换经济,但所回报的内容并非是单纯的物质,而是某种道德义务和意识形态上的认可,“需要对其整套的原则和惯例进行普遍承诺,认为它们是处理各种关系的最佳法则”[2](P161)。与传统的军事占领和其他政治介入相比,这种交换方式更具隐蔽性、不可防范性,因为这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利益交换纽带(包括未来自我利益的实现和认可),但首先本着让朋友高兴的原则;其次,它象征着一种博爱文化,在引发情感和关系上的亲近感的同时,也使人类陷入道德枷锁的捆绑状态。
此外,二者都具有“镜像”功能。镜像不仅能折射各种政治现象,同时也能与国际政治产生互文性(inter-textual)的关联。“镜像”作为媒体元语言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概念,学者们都纷纷用其“具有反射功能的类比”来解释各种媒质的特性。阿尔都塞认为,报纸、电视、文学、艺术、体育,等等,都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国家工具”,通过它们的狂轰滥炸,既可以用来约束管理者(舆论监督),也可用来约束大众群体(舆论监控),同时也强迫主体认可其中的“意向文本”(imagetext),并通过想象力与他们所生存的现实世界产生联系。尽管它们可能会被夸大、缩小或扭曲变形,但通过象征、互文等具有隐喻性的多重手段,不仅能反映或影射国际政治中的历史事件、人物形象和政治关系,使主体在其中发现与现实世界的同位对应物,同时还能“建构意识形态,并确保其功能的施行,将所有个体转化为被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主体,并使后者受控于这个无形的,却又普遍存在的社会法则之下”[3](P134~135)。
二
以《哈利·波特》为例,它是一个涵盖“社会学概念,其中包括文化、社会化、等级化、社会不公、社会制度和社会理论”的范例。若将《哈利·波特》中的政治经济模式聚焦于现实世界的国际关系,人们会发现其中有许多相似之处。
例如,《哈利·波特》中的反面人物伏地魔嗜杀成性,其人物性格兼有暴君、独裁者、种族主义者、极端主义者和舆论控制者等特性。他坚持主张,巫师的血统必须纯正,对混血巫师和普通人肆意地杀害,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种族歧视的印记。
另外,伏地魔派遣其党羽破坏公共设施,谋杀无辜平民,强迫党徒自残、儿童弑父等行为,也与当今国际恐怖主义者的行为有异曲同工之处。而这种联系也许并非单纯巧合,人类和巫师世界所受到的伏地魔的恐怖威胁程度,恰恰正是随着现实世界中全球恐怖主义阴霾的扩张进程的时间顺序而不断展开的。在巫师世界中,作者也描述过一个类似现实世界中炭疽综合热恐怖事件,黑巫师用施了魔法的邮件来误导魔法部的警员故意去逮捕无辜的民众,从而在平民中造成恐慌。从互文性的角度讲,黑暗魔法师隐藏在飞机场、汽车站、火车上,伺机进行破坏,与现实世界中2001年美国恐怖袭击,2004年马德里火车事件,以及2005年伦敦双层公交车爆炸案,都有诸多相似之处。
尽管这些情节都是源自文学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篆仿(imitation),不过,若将这些正义与邪恶斗争的故事植入现实,人们会发现哈利·波特虽然是个英雄,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是魔法学校校长邓布利多和伏地魔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邓布利多的掌控之中,并无真正意义的活动自由,且和伏地魔一样,时常变得偏执、疯狂,充满幻觉。但有趣的是,这却都是他成功的关键性要素。因此,对于这种为了信仰而牺牲的做法,马克·布斯科特(Marc Bousquet)幽默地认为:基于当前人们对政治文化戏剧性跌宕起伏的期望值或依存度不断上升……无论是否读过这部文化作品,都会去帮助国家政权和媒体,组织各种为了统治需要的民族牺牲感。[4](P177~178)
三
从文化政治学角度对《哈利·波特》进行分析,不仅印证了媒体、政治与通俗文化的共生关系,同时也发现:基于新媒体的发展、全球化意识的提高、对文化多样性的认知与接受、商业的需要,以及通俗文化自身所具备的“高度媒介性”,通俗文化已对当代国际政治的研究与发展形成一股强势的冲击力。也就是说,大众文化与其他严肃文艺作品一样,对社会具有批判功能。尽管这对传统的社会话语权研究模式极具颠覆性色彩,但却足以显示通俗文化在现代社会关系中的话语权重,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视域下对“巴赫金狂欢诗学中话语权角色转换”的诠释与范式表现。正当现代主义思想感慨事物发展缺失确定性,并试图用严格、理性和经验研究来克服这种不确定性的时候,后现代思维已沉浸在自由的喜悦中,并欢快地在互文的领域大展身手。
[1]Jerel A.Rosati,James M.Scott.The Politics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M].Cengage Learning,2010.
[2]Gerald A.Cory.The Consilient Brain:the Bioneurological Basis of Economics,Society and Politics[J].Springer,2004(28).
[3]Louis Althusser.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Notes Toward an Investigation)[J].Mapping Ideology,1994(1969).
[4]Elizabeth E.Heilman.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Harry Potter[M].Taylor &Francis,2008.
G206
A
1673-1395(2012)01-0161-02
2011 10 10
廖建乐(1984—),男,海南儋州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大学英语教学研究。① 本文属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校级重点科研课题(HZJK201015)产出论文。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