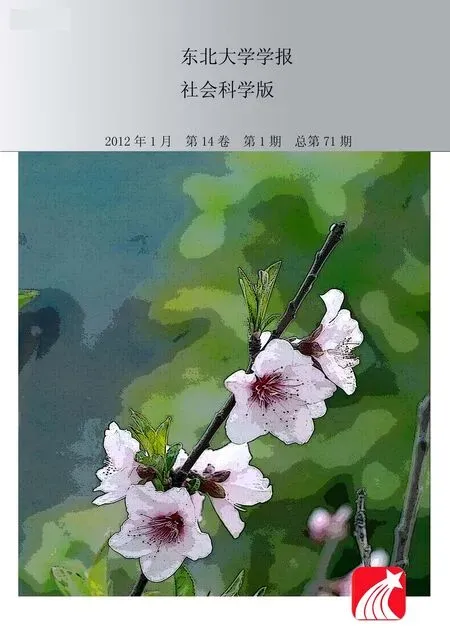文学与日常生活的辩证想象
----论鲁迅小说对日常生活的书写
2012-03-28张慧敏
张慧敏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
即使是最为普通、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是对更为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
----格奥尔格·齐美尔
在“五四”文学中,贯穿着一条强大的、作为现代性冲动的启蒙理性线索。伴随着这种现代性冲动,日常生活作为一个范畴开始出现在“五四”作家的文学书写中。他们笔下的日常生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而是作为现代性表征之一的“现代日常生活”。从陈独秀提出建设 “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1],到周作人要求作家以严肃的态度去反映底层社会的“非人生活”,用普通的文体写大众生活的真情实状,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2],文学在对现代日常生活进行观察与思考时,已经展开了与现代性话语或顺从或反抗的对话。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对现代性的思考与回应,还是对现代日常生活的批判与拯救,文学都以一种独特的话语彰显出日常生活的辩证蕴涵。因此,从文学形象的角度对“五四”文学与中国现代日常生活的关系进行探讨是有意义的。本文以鲁迅的《端午节》(1922)、《幸福的家庭》(1924)和《伤逝》(1925)为例考察文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探讨他在对现代日常生活的书写中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立场与态度。
一、 深陷囹圄:三个为柴米油盐所困的新知识分子
在鲁迅为数不多的小说中,与围绕《伤逝》讨论的多达上千篇文章的壮观景象*在中国CNKI学术总库中输入“《伤逝》”,可检索到相关的记录共有1037条,可见其受重视程度之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端午节》和《幸福的家庭》这两篇小说却几乎是被忽略、遗忘的。然而,把这三个文本并置时,就会发现鲁迅对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细腻呈现中隐含着深刻犀利的批判。
在鲁迅的这三篇小说中所呈现的日常生活,不同于前现代农耕社会人与自然、工作与休闲、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都高度地统一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常生活。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并不是非日常生活的对立面,而是一个整合未分的概念。资本主义出现后,越来越多的分化出现在社会各领域中,不仅劳动出现了分工和专门化,而且家庭生活及闲暇也与劳动相分离,受制于生产和市场的要求,社会关系趋向纯粹的实用主义,导致日常生活必然处于总体统治和商品化之中。“日常生活,既是前现代社会性形式丧失的牺牲品,又是那种逝去了的统一性的残余承载者。”[3]列斐伏尔将这种社会称为“消费受控制的科层制社会”,因为“商品、市场和货币,以及它们无可代替的逻辑紧紧抓住了日常生活。资本主义的扩张无所不用其极地触伸到日常生活中哪怕是最微细的角落”[4]193。在各种知识话语中,特别是在科学和哲学中,日常生活逐渐变为一个被讽刺的对象:一方面日常生活和其他活动分离了,另一方面日常生活自身又逐渐被贬低了。鲁迅所描绘的就是这种中国社会现代性原初语境中的城市日常生活,其基本特征就是“它的整齐划一,它的沉闷无聊,也许与它特征相同而又最为常见的东西就是流水线”[4]12,“重复性思维典型地代表了日常生活内在的一般的对象化图式,……日常生活是重复性思维(实践)占主导地位的领域”[5]8。这种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日常生活,使人变得刻板机械,极大地减少了生活的情趣。
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大都抱着启蒙的目的写小说,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意”[6]。启蒙是现代性的一个表征,而日常生活是启蒙运动的产物,“由于启蒙运动,知识和哲学思考被突出地强调出来,人类活动根据古典的区分,被区分为‘高级’和‘低级’两个部分。理性代表了人类的高级机能或能力,它属于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而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是不值得关*的,它与人的感性等低级机能有关”[7]。《端午节》作为鲁迅第一篇以现代家庭生活为背景,以新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充分展现了他们在现代城市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困境。这里的“新知识分子”,或如爱罗先珂所谓的“知识阶级”,是指不同于传统士大夫而以自己的专门性知识为手段来取得薪水以作为谋生资本的现代文化人。教育、知识是他们最大的财产,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无论是《端午节》里的方玄绰、《幸福的家庭》里的“他”,还是《伤逝》中的涓生,都可归入这一类。方家的家庭经济是依靠官方和学校所发的工资,虽然多半是欠着的;“他”是靠自由撰稿而“捞几文稿费维持生活”[8]35;涓生起初是一个负责抄写的小职员,失业后也是靠翻译、撰稿来维持生活的。对于他们,物质的欲求、日常生活的沉闷,无疑就是欲罢不能的重负,就是永远看不到希望的“铁笼子”。这个“铁笼子”如韦伯所言:“就是日常的现代性,亦即机器般的和官僚制度般的。它就是禁欲主义所控制的日常生活。”[4]19而方玄绰、“他”和涓生都是一些为柴米油盐所困的新知识分子。
按照赫勒的界定,日常生活是“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而没有自我再生产,任何个体都无法存在”[5]3,就是说,日常生活是每一个个体最直接的生存境况。那么方玄绰们的生存境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方玄绰在小说中的身份是政府官员兼学校教员,但这“官”其实只是类似于公务员的小职员,是没什么特权的,不仅教员的薪水积欠大半年,连官饷也得不到手,乃至造成家中拮据,陷入困境。不仅如此,连一向对他尊重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太太也开始对他连连抱怨,再加之因怯懦退缩,不敢挺身参加索薪的抗争以致最后陷入过不了端午佳节的窘境。《幸福的家庭》中的“他”,自己身居陋室,书架旁边是白菜堆,床底下是乱糟糟的劈柴,外面是妻子和卖柴的小贩斤斤计较的嚷声、三岁的女儿被妻子责打的哭声,然而他却还要在这样的环境中为了“捞几文稿费维持生活”而饥肠辘辘地去构思那“幸福的家庭”:“幸福的家庭的房子要宽绰。有一间堆积房,白菜之类都到那边去。主人的书房另一间,靠壁满排着书架,那旁边自然决没有什么白菜堆;架上满是中国书,外国书,《理想之良人》自然也在内----一共有两部。卧室又一间,黄铜床,或者质朴点,第一监狱工场做的榆木床也就够,床底下很干净”[8]39。这样的构想不禁使人想起《伤逝》中的涓生,鲁迅对子君和涓生日常生活的讲述,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住宅问题展开的。住宅缺乏在当时已经是一个明显的社会问题,这自然与现代化进程是息息相关的。在《伤逝》的开头,便提到涓生的住所是“会馆里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和板床”[9]113,这一切无不表明涓生的现实处境,他作为小职员的所得也只是“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绝不会肥胖”[9]121。即使后来迁到吉兆胡同,和子君一起租了一间自己的屋子,但与《幸福的家庭》中的“他”类似的是,身处陋室的涓生深感自己工作的不便,他抱怨道:“可惜的是我没有一间静室,……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但是这自然还只能怨我自己无力置一间书斋”[9]121。毋宁说,“他”就是结婚生子的涓生的翻版,以至于涓生最后得出结论“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而决绝地离弃了子君。
这一切就是方玄绰、“他”和涓生们作为从属地位社会群体的日常文化实践表征的“现代文化事实”(托尼·贝内特语)。正是在对这些文化事实的呈现中,通过对新知识分子在现代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困境的深描,体现出鲁迅对日常生活之异化的批判:作为启蒙产物的琐碎而困窘的日常生活深深地禁锢了怀抱启蒙理想的新知识分子的行动。
二、 超越之径:三个弱者不同的抵抗方式
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本身具有压抑和颠覆的双重性,因为无论现代日常生活是多么单调乏味,总是有改变它自身的可能性。有论者指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把当代的日常生活看做是开采滥用型的、压制型的以及残酷控制型的。而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他又企图在日常生活内部寻求能用来改变它的各种能量。”[4]189就是说,“日常生活”并非一个简单的同质性的概念,一方面它指日复一日的最为稀松平常的家常和栖居空间中的衣食住行等各种司空见惯的行为;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又具有一种足以超越它自身的可能性。米歇尔·德·塞尔托与居伊·德波等在列斐伏尔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日常生活本身蕴涵着一系列有效的抵抗策略。日常生活中的弱势群体表面上公开接受统治者们为他们描述的合理现实,然而这并不等于他们就成为丧失了能动主体意识的傻瓜,而“把日常生活当做一个抵制的领域(既是实质意义上的,又是实际意义上的)。但是这种‘抵制’并不是反对的同义语,……它就是阻碍主要的能量流并且使之消散的东西,它就是抵制表象的东西”[4]251。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实践或曰“抵抗”并不必然是公开的反抗、起义、造反甚至革命,相反,那些抵抗的“日常形式”也许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
鲁迅在小说中不仅对日常生活的异化展开批判,而且同时寻求一种以弱者的抵抗来超越日常平庸的救赎。仅将方玄绰、“他”和涓生们视为是逆来顺受的为柴米油盐所困的知识分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鲁迅在描写这类知识分子时对他们的态度是极其复杂的,是批判中又带有同情和理解的。他们既不是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那样有改革理想、进步的新知识分子,但也绝不是四铭(《肥皂》)、高尔础(《高老夫子》)那样的保守虚伪、貌新实旧的传统文人。在《端午节》中,方玄绰面对现实的困境与经济的压迫,虽有很多不平之鸣,也不敢奋起反抗加入索薪的队伍,但他自有一套策略或曰“战术”(德·塞尔托语),那就是他的“差不多说”。有论者认为方玄绰的“差不多说”“其实是另一种自我麻痹的阿Q精神,鲁迅将阿Q精神移植到方玄绰这位当代知识分子身上,加深刻画他个人内在外在的落差与冲突”[10]。其实鲁迅笔下的“差不多说”毋宁说是主人公的一种“口头文化”,“口头文化的主要形式是市井流传的笑话、传言、歌谣、顺口溜。下层文化的递送人一般是处于权力体制边缘的市井小民、贩夫走卒,也包括一般市民社会的成员。口头文化是德赛都(M.De Certean)所说的那种寄生性日常大众文化的典型形式,它利用现有的公开语本,在其夹缝中寻求自己的声音”[11]231。方玄绰们没有自己的空间,他们不得不在现存权势的控制下活动,他们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让世界不至于太不能忍受,以此“来保存一点起码的自我感觉”[11]232。其实,方玄绰完全不同于没有灵魂的阿Q,而是有着很强的自省意识的,他深知自己的懦弱。鲁迅描写方玄绰发明“差不多说”之后的自我分析:“他自己虽然不知道是因为懒,还是因为无用,总之觉得是一个不肯运动,十分安分守己的人。”[12]561鲁迅一面刻画方玄绰为自己的怯懦来辩解,一面又指出他为这种怯懦而苦恼,如此反反复复,将这位知识分子矛盾挣扎的灵魂揭示得一览无余,也逐步地逼使他去正视自己苦恼的根源。
而《幸福的家庭》中的“他”也并非以往论者所说:“是一个沉浸在资产阶级恋爱观、幸福观和文艺观中的‘文学家’。他在用恋爱、家庭之类的‘丝’作茧自缚,饿着肚子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却自不量力地又要在这些自己也被缠得狼狈不堪的问题上作‘牧师式的说教’。”[13]鲁迅在对“他”含泪的讽刺中更多透露出的是辛酸与无奈。这位曾经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初的抵抗行动就是曾经为爱情付出代价,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她听得他说决计反抗一切阻碍,为她牺牲的时候,也就这样笑眯眯的挂着眼泪对着他看”[8]41。然而,在日常生活的销蚀之下,“他”的锋芒渐渐萎缩了,不得不靠“捞几文稿费以维持生活”,他的写作很显然是实用主义的,投其所好的,虽然与现实生活是背离的,却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抵抗的“策略”。
詹姆斯·斯考特在论述下层群体对抗官方权力的“隐蔽语本”中第一种关系就是迎合权力精英自我形象要求的下层话语,这是最安全的,同时也是一种彻底接受控制的下层话语。“例如权力精英要营造一种极具关怀的父母权威形象,下层话语就将它歌颂的比爹娘还要亲。”[11]229“尽管公开的顺从是权力演示追求的效果,但它毕竟和心悦诚服的积极认同有所不同。……奴隶对自己和别的奴隶的恭敬顺从后面藏着什么,多少是知道的。”[11]227“他”很清楚自己的写作性质,“那作品,像太阳的光一样,从无量的光源中涌出来,不像石火,用铁和石敲出来,这才是真艺术。那作者,也才是真的艺术家。----而我……,这算是什么?”[8]35“他”的写作行为并非要主动地粉饰现实,而是迫不得已的下策。“他”极力地要通过艺术创作超脱出他的日常生活,然而却不断地被生活所干扰,最终只好放弃了,“粗暴的抓起那写着一行题目和一堆算草的绿格纸来,揉了几揉,又展开来给她拭去了眼泪和鼻涕,……将纸团用力地掷在纸篓里”[8]42。“他”当然不明白这个道理:“艺术”和“日常生活”本不是完全对立的。“‘艺术’远非自由漂浮在日常事务之上的某一天国领域里,它一直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并与人们在日常基础上的所作所为相联系。”[14]115只是在19世纪才出现了称之为“艺术世界”的独特文化领域,它从此就被定义为独立于日常事务并优越于日常事务。“而后者(日常事务)的特点是缺乏精神性并由诸如赚钱之类的‘粗俗’事物所主导。阿诺德将‘高雅文化’定义为高于世俗生活,反映了‘艺术’这一新的社会领域的建立,感觉上是远离于人类日常事务。艺术与艺术家的世界被视为与‘日常生活’(ordinary living)并无联系,并且要优越于日常生活。”[14]118“他”的悲剧就在于不仅无法超越出自己的“日常生活”,就连“他”的作为抵抗之“下策”的写作也一起失败了。
在某种程度上,《幸福的家庭》可以看做是《伤逝》的一个*脚,“他”一天的日常也许就是涓生一天的日常。所不同的只是,涓生经历了一场“对生活充满希望----希望破灭----重新燃起希望”的情感波折。“他”为了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超脱出来也付出了很多行动与代价。与《幸福的家庭》中的“他”相似,涓生冲破封建束缚和子君自由结合,“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9]117,之后“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然而,日常生活毕竟是单调乏味的,它暗示的是普通、平庸,蕴涵的是连续的重现,持续的重复。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这个术语,“至关重要的正是它的重复:每日的家庭杂务和那些意味着对单调乏味的工作进行补偿的已经固定化的快感”[4]211。对此,涓生像“他”一样求助于艺术,“默默地相视片刻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9]114。看到自己的小品文发表,涓生感觉到“一惊,仿佛得了一点生气。我想,生活的路还很多”[9]127。而实际上他的所得也不过两张两角和三角的书券,为此还多付了九分的邮票。以致子君在离去之时,给他留下的那些物品,读来是如此地触目惊心:“我转念寻信或她留下的字迹,也没有。只是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却聚集在一处了,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这是我们两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现在她就郑重地将这留给我一个人, 在不言中,教我借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9]129。联想到在创建小家庭时子君卖掉自己唯一的金戒指和金耳环,我们就可推断涓生在维持家庭日常生活上的乏力。再加上失业,无异于雪上加霜。然而涓生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他掌握着事态发展的主动权,“他通过爱情来逃避无聊与乏味,而一旦生活变得艰难,他又从爱情中逃离”[15]。韦伯曾指出,现代文化首先是一种理性的和阶层制的文化,抑或他所谓的“法理权威(legal-rational)”,也就是说,“人们的思想及行为不再受到专制君主及暴君独裁专断地使用和滥用权力的限制以及管制,而是受制于对规则与程序的体制化应用。这种统治的典型形式是阶层制(bureaucracy)”[14]51。韦伯坚信,这种控制类型就是现代性的典型特点,日常生活的广阔领域已经被官僚结构的原则殖民化了。“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而去。”[9]126可悲的是,涓生最后的反抗就是在这样的规则控制之下为了自己所谓的新生而离弃了子君并直接造成了她的灭亡。
三、 无法言说:三个作为日常生活“傀儡”的女性
对于《伤逝》,论者多认为鲁迅是为了回答“娜拉走后怎样”,主张女性的解放必须首先获得经济上的独立。然而,在《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这样反诘:“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16]。在他看来,处于现代日常生活中的男男女女,都是互为“傀儡”的。因为男性尚可以用语言或书写来表达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困境,方玄绰的“差不多”、“他”的构思以及涓生的“手记”等皆如是,而女性则似乎永远是一个无法言说自己的“傀儡”。
由于妇女不仅承受着日常的负担,而且最容易受到日常需求的影响,同时也对日常的需求最缺乏抵抗力。因此,对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感受最深切的就是女性。列斐伏尔指出,妇女既承载着日常中最沉重的负担,但又是最没有能力认识到这是一种异化的形式,她们处在一种模棱两可的位置上,“一方面,她是商品的消费者,另一方面,她又是商品的象征”,因此,在他看来,妇女“不能够理解”日常,妇女抗争的基本特征是“各种表述笨拙、无的放矢的要求”[4]208。或许这一观点会受到当今形形色色的女权主义者的批评。然而,在“五四”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费瑟斯通所谓的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的大众文化还没有大规模兴起,该文化“二战”后在西方兴起,在中国则从20世纪90年代后才开始。因此,在当时的中国,女性表述自身的途径是极其有限的。方玄绰的夫人方太太,一个“没有受过新教育的”女性,方玄绰甚至都不称呼她“太太”,又因为没有“学名或雅号”,生活中就被称为“喂”。而方太太则连这个“喂”的表述能力也没有,“只要脸向着她说话,依据习惯法,她就知道这话是对她而发的”[12]562。方太太负担着全部的家务,每当由于方玄绰无能导致生活困顿时,她的表述或反抗最终都变得苍白而又无力,“方太太……,愕然了,但也就沉静下来”,“见他强横到出乎情理之外了,也暂时开不得口”,“料想他是在恼着伊的无教育,便赶紧退开,没有说完话”[12]567。最讽刺的是,当方太太因生活拮据而提出买一张彩票却受到丈夫厉声斥责的时候,她绝不会想到这种“笨拙、无的放矢的想法”也曾在他的脑海中出现过。
在《幸福的家庭》中,“他”的太太的处境与方太太毫无二致。她虽然也曾有过“可爱的嘴唇”,然而现在只剩“阴凄凄的眼睛”了,她的日常生活只有斤斤计较每一个铜元,买柴、买白菜,唯一发泄不满的途径就是责打三岁的女儿。除此之外,我们再也看不到她的任何一点抵抗。她彻底地沦为日常生活的“傀儡”,被生活所摆布。然而和子君比较起来,方太太们还是幸运的。面对生活,子君做出了最决绝的抵抗却陷入了最悲惨的境地。她高喊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口号却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所指的空洞能指。她为了享受与维持小家庭的日常生活,不惜“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金耳环”,包括“喂阿随,伺油鸡”。即使在被父亲带走时她想到的还是如何维持涓生的生活,从作品中看不到她像涓生那样对生活抱怨和不满。因为她没有任何言说与反抗的的空间,而只能成为被书写的对象和日常生活的牺牲品,连像方太太们那样的“傀儡”的资格也丧失了,这正是子君的悲剧。唯其如此,才能真正理解列斐伏尔那看似自相矛盾的观点,“妇女在同一时刻既是‘异化’最为深重的个体,又是这种异化最积极的‘抵制者’”[4]209。
总之,鲁迅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构成了一个栩栩如生的辩证形式,这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的辩证法一致:一方面是现代性的各种表征、日常生活的异化、现代知识分子深陷其中的种种困境;另一方面则是他们试图围绕现代日常生活展开的种种抵抗与超越。鲁迅并非一味地怀疑、贬损甚至否定日常生活,比如在《朝花夕拾》中就能看到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各种抵抗与诗意的一面。他之所以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而否定“为艺术而艺术”,正表明他希求借助于文学的眷顾来超越日常生活刻板机械的平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他对现代日常生活批判与超越的辩证法正表明:“鲁迅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性人物,或者说,一个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17]。
参考文献:
[1] 陈独秀. 文学革命论[M]∥胡适.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44.
[2] 周作人. 平民文学[M]∥胡适.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211.
[3] 托尼·贝内特. 现代文化事实的发明[M]∥陶东风,周宪. 文化研究:第六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256.
[4] 本·海默尔. 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5] 阿格妮丝·赫勒. 日常生活[M].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6] 鲁迅.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全集:第4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526.
[7] 周宪. 日常生活批判的两种路径[J]. 社会科学战线, 2005(1):114.
[8] 鲁迅. 幸福的家庭[M]∥鲁迅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9] 鲁迅. 伤逝[M]∥鲁迅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0] 彭明伟. 爱罗先珂与鲁迅1922年的思想转变----兼论《端午节》及其他作品[J]. 鲁迅研究月刊, 2008(2):32.
[11] 徐贲. 弱者的抵抗:詹姆斯·斯考特的弱者抵抗理论[M]∥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 文化研究:第三辑.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12] 鲁迅. 端午节[M]∥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3] 曾华鹏,范伯群. 论《幸福的家庭》----鲁迅小说研究之一[J]. 扬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6(3):3.
[14] 戴维·英格利斯. 文化与日常生活[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15] 刘禾.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M]. 北京:三联书店, 2008:237.
[16] 鲁迅. 娜拉走后怎样[M]∥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70.
[17] 汪晖. 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