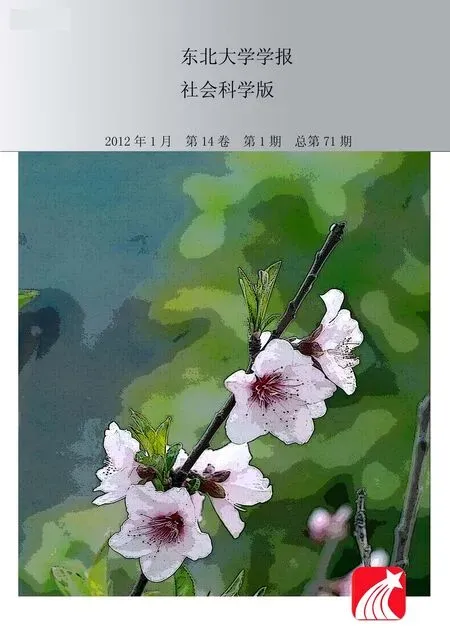信息哲学作为元哲学何以可能
2012-03-28李武装刘曙光
李武装,刘曙光
(1.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 710049;2.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政法与经济管理系,甘肃合作 747000)
信息哲学(information philosophy 或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后者简称PI)这一新生的“哲学门”究竟应该作为“元哲学”看待,还是理应视为目前流行的“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例如有论者[1]认为信息哲学是科技哲学的新“范式”)?如果是前者,那么,信息哲学作为“元哲学”何以可能?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展开学术探讨,希冀引起学界争鸣。
一、 何谓“元哲学”
对metaphysics一词所作的“形而上学”、“后物理学”的译介,造成人们对“上”、“后”和“元(meta)”的诸多误解和歧义。实际上,“上”、“后”和“元”在这里并不是真正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先与后、上与下,而特指逻辑意义。或者说,“上”、“后”和“元”不是发生学的考察,而是一种功能性的规定。这种逻辑意义或功能性的规定至少包含两重含义:一是超越,二是反思(包括批判)。前者相当于英文中的“transcendence”、“going beyond”,主要指称前提、条件和根据;后者相当于英文中的“contemplation”和德文中的“nachdenken”,主要指反身自认。
西方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业已表明或证成了这种超越和反思的基本理路。因为在从西方古代哲学到中世纪哲学关于“一般与个别”的争论中,按照阿奎那的定论,“一般”只有三种存在形式:作为上帝创造世界的理念,它存在于事物之先;作为事物的形式,它存在于事物之中;作为事物的概念,它存在于事物之后。也就是说,在结构与发生学意义上的“一般”考察已走到了尽头。而对“被证明了的真的信念”的不懈追求,导致人们必须思考:作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有效性品格的“一般知识”从何而来?即认识如何发生?在思考探究这一问题时,西方近代的哲人们大多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康德式问题,即“某某何以可能”的追问与求解路向。譬如,西方近代哲学中的“实体”概念、康德的“物自体”概念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范式,都是一种基于“何以可能”(对条件、限度、前提等的发问)的逻辑设定。实际上,这就是哲学式的“元理论”追问与求解方式:对前提、根据、限度、条件的自我认识。
沿循上述理论,我们必然陷入“元元哲学”的“恶无限”困境。而问题在于“元哲学”自身的特殊性。我们知道,前提预设是无限的,但其层次不然。如果预设的层次达到了循环,那就意味着已经进入了最高层次,即循环的出现或者最高层次的呈现是以预设已经“适用于说明所可能知的一切”为临界点的。这也就是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指出的,任何理解中都包含的承诺或约定。“解释学循环”的合法性就在于求得一个合理的“阿基米德点”,而开创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的“超循环理论”,其依据就在于“自组织系统”逻辑的推演。“元哲学”自身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本身就是这个“阿基米德点”;“元哲学”作为对“所可能知的一切归根到底只能如何的形式化思辨考察”,再也无法超越,达到了最高的层次,自主、自因且自明,即达到了对哲学最基础理论的把握。这就相当于塔斯基对真理的语义学定义:“X为真,当且仅当P”。缘于此,西安交通大学已故的刘永富教授强调,“元哲学”更应该被合理地称作“哲学基础理论”;而陕西师范大学的金延教授则认为哲学的功能是“考察人的认识和人的行为的逻辑基础”[2]。后者抨击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不是“物理学,警惕形而上学”,而是“哲学(形而上学),警惕物理学”,认为西方近代哲学实质是考察“科学知识的逻辑条件”;他揶揄中国哲学“安身立命”的回答方式可能把形而上学(哲学)变成一个道德问题。金教授的“逻辑基础”(“逻辑条件”)完全可以理解为哲学的“元”追问,即“元哲学”问题。
那么,“元哲学”或者“哲学基础理论”一般包含或指谓哪些内容?或者说,成为“元哲学”的参照系或标尺何在?遵从刘永富教授的论述,就是对于以下问题的解答:“哲学所特有的主题;哲学问题的本性、分类以及处理哲学问题的方法;哲学所特有的价值与目的;哲学批判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哲学能否像自然科学那样取得进步”[3]。也就是说,能圆满回答或者至少致力于解答这些问题的学问,一定属于“元哲学”。
从抽象的可能性着眼,运用与时俱进的话语逻辑,“元哲学”之谓“元哲学”,首先得从众所周知的“哲学基本问题”入手,致力于回答世界以及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系列视点、视界、方式的“范式性革命”主题。其次,要着力考察世界“主题转化”的质态及其意义:是否在“时代性”上置换或更新了人们的视阈?是否真正推进了人类把握世界的世界观面相以及方法论全面创新?再次,关*“生活世界”、现实问题从而对哲学本身进行“建设性向度”的系统重建或解释(用解释一词主要为了彰显哲学的“解释力”),而不是着眼于个别问题的澄明和释义。
从具体的可能性而言,“元哲学”之谓“元哲学”,主要立足于对以“现代科技革命”、“社会整体转型”和“全球思维”为旨趣的当代世界是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构与重构,从而彰显和昭示一种人类全新的、辐射“理论、体系、方法”三维度的哲学批判逻辑、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超越模式。因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二、 作为元哲学的信息哲学
就当代日益勃兴的信息哲学而言,无论如何,都应该在“元哲学”层面去深度理解并规范定位之。其中缘由,我们可以从哲学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和哲学价值论几个方面得以把握。
1. 在本体论和“哲学基本问题”上
按照邬 教授富有哲学意蕴的信息定义----“信息是表示间接存在的哲学范畴,它是物质(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4],以及他对“存在领域的分割”论证,我们看到存在(世界)由“物质(质量和能量)和意识”的旧二分演变成“物质和信息(包括信息的最高形态----精神)”的新二分。即存在是由“直接存在”(物质)和“间接存在”(信息以及信息的最高形态----精神)构成。在信息的世界观意义上,世界被二重化为物质世界和信息世界。相应地,“哲学基本问题”就成了物质和信息的关系问题。
姑且不论这种新二分的合理性限度和合法化根据,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信息确实成为当代人类不可或缺的、最普遍的从而不能不关*的存在“样法”。进而,当我们考察“哲学基本问题”时,对“信息”的归属问题以及信息与物质、信息与意识、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关系的思考,本身就触及到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重新理解和审视。这样,就有可能建立起关于“信息一般”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从而建立起全新的系统的形而上学,即“元哲学”层面的信息哲学。邬 教授对这一理解是坚定而明确的,其论述是充分的,而其批判亦是尖锐的、有针对性的。
事实上,对信息定义的考察是信息哲学出场的前提。虽然关于信息的本质目前还是聚讼纷纭,但讨论本身就孕育和澄明着信息哲学因子。因此,不能像有的学者认为的因为信息的定义还没达到“共识”或者对“哲学基本问题”还没给予信息视阈的架构就否认信息哲学的出场或对信息哲学产生怀疑,而且,“哲学基本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不断澄明的问题。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明确指出,对它的使用要有限度。
一个显见的结论是,对信息的哲学本体论反思,等于试图确证了一种关于信息的本体论观念。一般认为,“本体论承诺”有三种方式(二元论本质上依附或归化为一个本体):宇宙的(或自然的)、物质的和意识的。以“间接存在”定义的信息概念,其承诺的本体论显然是属于宇宙本体或自然本体。因而,信息的世界观意义乃至哲学主题和存在域界的转换,足以把信息哲学定位在“元哲学”层面。
2. 在“哲学认识论”上[*]在“哲学认识论”和“哲学价值论”这两部分的论述,得益于西安交通大学国际信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邬 的研究和赐教,在此向邬老师致谢。这两部分相关深入的论述,请参阅邬 :《信息哲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
人们把握、认知世界的方式,在现时代已经很少去直接体验了,而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们借助于网络等现代传媒去“间接”认识我们的现存世界。传统认知的主体、客体以及主客体直接互化模式,随着计算机网络等“虚拟世界”的出现,更多地依赖“信息中介”。“信息场”、“负熵”、“微观量子”等概念的出现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实际上,作为现代认识过程基本要素或环节的信息,对认识的一次完成主要依赖以下“发现”:“信息凝结”产生认识主体;“信息场”沟通认识主体与客体;客体被信息中介的多级建构进入主体;信息中介建构和“虚拟”认识。
按照传统哲学认识论定义----认识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我们指出,基于“主体—客体”模式的传统认识路径在“信息时代”已完全置换为“主体—信息—客体”或者“主体—信息”模式,将来还有可能完全进化为“信息—信息”模式,即人类把握和认识世界完全成了“信息的时空对话与交流”。要指出的是,这并不否定作为终极主体的人的作用。人永远承担“分析综合”和最终驾驭信息的职能。问题是,信息时代莅临从而人类认识视阈的“越界”或“移情”,确实打破了原来认知之“主体—客体”的宁静,带来了“信息革命”意义上的认识论新图式,从而滋生出认识论领域中一系列新问题,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真理问题”,一如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
基于此,可以说,信息完全改变或更新了人们的认识视阈和思维模式。以信息掌握量和信息控制力为竞争力的“信息大战”从个人、民族、国家到全球,已植入我们思想的最深层。这不仅改变着我们的世界观,更缔造着我们全新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从而确证着作为“元哲学”的信息哲学。
3. 在“哲学价值论”上
哲学价值论对于价值的界定一般集中在以下三种学说:关系论、实体论和综合论。关系论主要基于主体客体的关系,包括属性说、好恶关系说、需求完成说、效应说、兴趣说和意义说等;实体论认为价值具有自身独立存在的东西(如摩尔关于“善”的不可定义论和高清海与韩东屏的“人”论);综合论基于层次、结构等方法来诠释(如张世英基于对张岱年的“表象分析法”和牟宗山“实质研究法”的辨析)。但无论怎么说,价值之“自然本体”并没有得以彻底澄明,即是说价值仍然是一种主观认识领域的东西。
信息的横空出世,打破了这一限制。以前,人们往往认为价值评价就是价值本身,而从逻辑上讲,评价过程怎么等于评价对象?作为最一般意义上的价值怎么可以忽视那个“自在世界”?此一“自在世界”难道对“人类世界”以及人类进化没有价值作用吗?等等。而按照事物(物质和信息)相互作用(包括内部和外部)所实现的效应来界定价值,则可以化解上述困惑。
首先,事物的相互作用所实现的效应可以分为直接存在变化的效应和间接存在变化的效应两种。两种效应分别对应于物质价值和信息价值。事物(物质和信息)的存在就体现在“双重效应”之中。从而,价值有了最高层级的基础和根据,即“自然本体”意义上的“价值一般”。
其次,对“是”与“应该”的困惑可以用自存事实与效应事实来化解:自存事实指忽略事物内外相互作用关系的事物的存在事实,效应事实则反之。前者是非价值事实,后者是价值事实。价值事实执着于价值现象本身就是“是”,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此,可以统一“是”与“应该”,即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从而避免陷入“是”与“价值”是否可推论以及二元论等质疑和迷茫。
第三,一个价值过程“相互作用→对象化→效应(价值)”在信息视阈中可以转化为“相互作用(信息交换)→对象化(信息变换)→价值效应(信息建构)”。
第四,社会价值是物质价值、信息价值(包括精神价值)的综合。
可见,信息视阈中的价值已经超越了实在论的价值预设,完全拥有了自己“自然本体”意义,从而繁衍出“一般价值哲学”。
按照刘钢研究员的论述,信息哲学“首先关心信息世界、计算和信息社会所呈现出的一阶现象的整个领域。但是,之于其自身资源的方法论批判方面,它更倾向于一种元理论的方法,也就是说,它在现象学和元理论之间保持着一种必要的张力”[5]。所谓“元理论的方法”,就是“所探讨的话题是有组织的知识体系”。简而言之,信息哲学的研究对象既是信息本身(信息科学),更是全新领域的、独立的、自主的“新领域研究”。因此,信息哲学既然“代表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能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一种创新的方法”、“能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那么,信息哲学对于前文罗列的刘永富教授关于“元哲学”成立标准的问题,都可以一一作出合理的解释,从而,作为一种“元哲学”理解的信息哲学,就得以正名。
三、 信息哲学作为元哲学的现实条件及路径依赖
考察信息哲学作为一种元哲学的现实条件,即是对“信息哲学作为元哲学何以可能”的现实求解。对此问题的解答虽然目前尚乏定论,但笔者以为,在达致这一“共识”或路径依赖上,我们更应该或者至少应该关*以下几点。对这些关*点的挖掘、研究本身具有方法论的启示。
1. 关*信息哲学的“公共性本质”
信息本身是一个“公共性”存在。信息哲学的旨趣就是对作为“公共性”存在的信息作出最高层面的哲学透视,形成关于信息的“元理论”。面对21世纪“现代性”、“全球化”以及“现代科技革命”在全世界范围的渗透,我们确实处在“地球村”或者“全球邻居关系”状态。因此,以人类“公共生活”的确立为核心的“公共性”生存理想不再是“博物馆神话”。有学者断言:公共性已经成为后现代性之后的现代性主题[6]。对“公共性”的关*,就是对现代公共传媒、公共舆论、公共产品、公共需求、公共权力、公共构造等现代“公共领域”的关*,而对公共性的领悟与把握,事实上就是对现代信息科学、现代信息技术、现代信息理论的恰当运用。其实,“信息时代”和“公共性生存”只是对当代世界不同的表达范式,在一个向未来敞开的世界中,其本质是相通的,都是“元”层面的考量。在这个意义上,信息哲学的建构还需要借助“公共性”研究中的许多有机养料。譬如,新兴的信息哲学可以借鉴公共哲学研究中相对比较成熟的理论。
2. 关*哲学自身的危机从而实现哲学的“信息转向”
哲学危机预示着哲学的“转向”。哲学已经实现了的“认识论转向”以及张再林教授所说的“现代西方哲学理论的四大转向”[7],特别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语言学转向”,都是哲学每一次经历危机后的自救。当代信息技术、信息科学和信息理论在全球范围各个层面的侵入,使哲学从“语言分析”、“逻辑分析”中不得不转向对信息的观照和透视。从“意义”转向“信息”,是当代哲学义不容辞的历史境遇,也是哲学自身回应“哲学终结”从而走出“贫困”的新的范式性革命。这一点是许多论者的“共识”。正如邬 教授所说的信息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全新的哲学范式”。
当今世界,信息中介普遍联系着整个世界,哲学理应建构崭新的最一般、最高层次的信息反思和信息批判理论。
3. 关*信息哲学的“符号论”迷茫
信息哲学的“符号论”迷茫,要求我们积极投身于信息的有效沟通与信息符号的合理转化机制研究。这个问题是建造“巴别塔”问题,实质是信息的“语言基础”问题。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家族相似性”的指认,以及库恩关于科学“范式”和“不可通约”的理解,取的就是此一路向。因为作为沟通、交流之另一现代普遍存在的信息,不但要面对此类问题,而且,较之于语言,信息更复杂从而更难以翻译、买卖和交流:不仅需要跨时空,而且需要跨话语界限、跨学科、跨文化、跨物种甚至需要跨星球等等,一如“基因转移”、“移情”等范式所指。
信息哲学要想成为“元哲学”,没有对作为现代科学语言(比如计算机语言)以及与信息相关的诸学科领域的符号、图表、公式、代码及其相互转化机制等的全面系统掌握,对于信息哲学的研究一定是肤浅的,属于“无根的浮萍”。
4. 关*信息哲学的“整体性思维”逻辑
关*与信息紧密联系的计算机科学、通信工程、图书情报学、心理学、伦理学、语言学,包括新兴的生命科学等学科或专业的概念、方法和理论并进行系统梳理,致力于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于一炉的“整体性思维”的锤炼,为信息哲学提供“元理论”的建模、阐释和分析的框架。
传统理性的根基是自然科学。对于理性向“合理性”的反思,使人们渐次吁求理性的本体论意蕴。因为理性不只是“reason”(理由、终极原因),理性还是“rationality”(原理、“第一原理”、“合理性”)。“理性的德性并非只是要实现人类生活的一个半圆,而是应当能支配自己给人类打开的整个生活空间,也能支配我们的一切科学能力和我们的一切行动。”[8]
人类生活的“另一个半圆”就是“精神科学”(人文科学)。因此,要理解整个信息世界,人类理性就不能囿于自然科学,更不能偏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应在“大科学”视野里把握世界,一如信息之作为“一般”。譬如,如何避免“单向度”的人,如何化解信息时代的认同危机等问题也是信息哲学必须警惕和深度关切的领域,而对于信息与信仰关系等问题的思考事实上成为反信息哲学论者抛给作为元哲学的信息论者的未来问题之一。
信息时代“交叉性学科”的不断涌现,既是对作为科学的“信息学”发挥作用的契机,更是对作为“元哲学”的信息哲学应该掌控的“飞地”(enclave)。飞速发展的信息以及“信息学”从而不断呈现的新的哲学问题,迫使信息哲学不断作出新的解释。因此,不断关*和了解与信息“联姻”的诸学科,信息哲学才能真正掌握“第一手资料”并成为信息时代的精华,信息哲学也才能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哲学”。
最后要强调的是,作为元哲学的信息哲学,重在建设;走出“领域哲学”的藩篱,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程现昆,王续琨. 信息哲学:从历史走向现实[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26(3):1-5.
[2] 金延. 论哲学的功能[J]. 人文杂志, 1999(3):1-6.
[3] 刘永富. 元哲学自身的两个元问题:“怎么才算”与“何以可能”[J]. 学术月刊, 2009(2):37-45.
[4] 邬 . 信息哲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45-46.
[5] 刘钢. 当代信息哲学的背景、内容与研究纲领[J]. 哲学动态, 2002(9):17-21.
[6] 沈湘平. 公共性:后现代性之后的现代性主题[J]. 江海学刊, 2008(4):28-32.
[7] 张再林. 现代西方哲学理论的四大转向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J]. 教学与研究, 2004(3):47-51.
[8] 伽达默尔. 作者自序[M]∥科学时代的理性.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