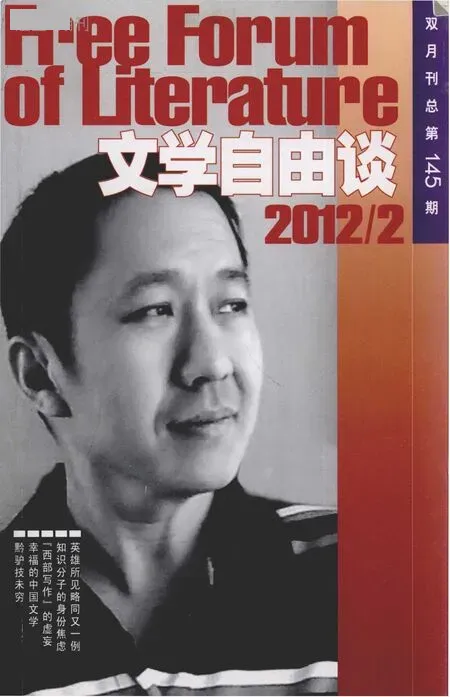搬 家只带一本书
2012-03-20熊万里
●文 熊万里
双胞胎女儿出生以后,我忙于家务,远离了阅读。其实,又没有停止阅读。抱着孩子,我一直在读一本280页的《新千家诗》(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2月第一版)。确切地说,我只读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古诗”,只读“古诗”中的几十首。这几十首诗大部分被选入中小学课本。
很多诗人似乎只留下了几十个字。骆宾王的《咏鹅》、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王翰的《凉州词》、卢纶的《塞下曲》、孟郊的《游子吟》等等,加上标题也就二三十字,却让无数后人记住了,反复吟咏。我们现在写文章,稍长的一句话可能就有百把字。
经常抱孩子在书房行走。有两堵墙排满了书柜,那些花花绿绿的书脊构成了特殊的壁画。我想让她们从小熟悉“坐拥书城”的氛围。她们长大了,肯定不满足于这本《新千家诗》。但是,值得读第二遍、第三遍的一定有这本《新千家诗》。等她们将来教孩子说话时,肯定也会反复朗诵那几十首古诗。
如果现在搬家,如果只能带一本书,我一定会带上这本《新千家诗》。
这只是假设。如果变成现实呢?我果真舍得下那些辛辛苦苦码放起来的“砖头”吗?我开始把假设当做迫在眉睫的现实,逐一浏览书柜,权衡一下,到底应随身带上哪些书籍?
打开一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扉页之后便是作者简介。作者已斩获国内所有官方文学大奖,多次获得国外文学奖,作品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出版。可惜,这部数十万字的长篇是我头脑发热而买的,一直读不进去。我觉得从《新千家诗》中随便撕下一页贴身存放,重量都远远超过这部长篇。它只是一坨装帧漂亮的纸浆,连同作者显赫的声名。
我又打开一本《1978—2008中国诗典》。冠之以“典”,即使不是经典,也应该离经典不远吧?在三十年里选了三百多位诗人的诗歌,沉甸甸的五百多个页码。一只手托着吃力,必须正襟危坐,双手“捧读”。每个作者都附有简介。几乎每个作者都出版有多部诗集。而且相当一部分作者出版有几千行的长诗,也就是说一首诗一本书!可是,我怎么没有记下一句“经典”?我每读完一本书,喜欢在扉页写几句感想。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我留下的“墨宝”是:“泥沙俱下的选本。惟一的亮点大约是新颖的序。蜻蜓点水地翻过,倒有催眠的功效。”我笑了,之所以让它挤占空间,是因为自己掏了五十元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当时夸奖了序言新颖,于是重读一遍主编写的序言,读到一句“你们挑出来的却是人名而不是诗啊知道不!可悲啊……”这主编倒不打自招地说了一句大实话,可惜我买书不慎,只看书名威风凛凛,就冲动地一点鼠标,从网上邮购回家了。
除了掏钱买的书,还有朋友送的书。一本诗集,勒口有作者简介:“发表诗歌1000余首,出版诗集40多本。”一本小说集,封底彩照配简介:“当代著名作家,发表300多万字,结集20余种,获奖30余次。”我感觉脑门一阵痒,伸手一摸,原来是汗珠滚过。汗后,一个激灵。我不是为朋友打冷颤,而是为自己。因为十几年前,少不更事的我,不知天高地厚,也经常写类似的简介。
前不久,有一个外国老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获得201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据说他只写了一百六十多首诗歌。他的文字很短,写的速度也很慢,四到五年出一本诗集,每本诗集一般不超过二十首诗,平均一年写两到三首。我们身边的作家呢?出国旅游一次,就能出版一本诗集、散文集。文章的长短与分量无关,书的厚薄与生命力更不沾边。我想起臧克家的一句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如果一个作者不靠写字换钱,最好三思而后书。有的文章虽然印成为书,却已经被遗忘。有的文章即使不印成书,也会代代相传。想到这里,我得匆匆收笔。没有含金量的长篇大论统统是废话。得益于高科技,生活垃圾尚可发电、再生能源,文字垃圾如果印刷出来除了浪费,还有何用?
再给女儿读古诗,一字一句,愈加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