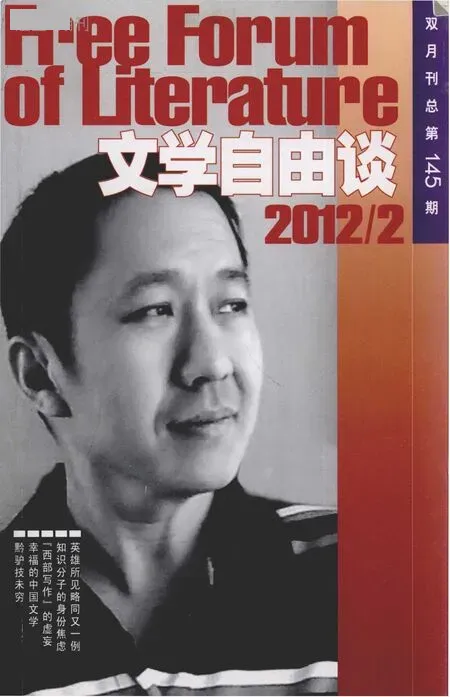纯批评:是什么?要什么?
2012-03-20李建军
●文 李建军
苏格拉底说,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我很喜欢这句话,喜欢的程度,与讨厌“难得糊涂”的程度相埒。根据我的观察,许多好事情,都是勇于思考而且善于思考的结果,而许多灾难性的后果,都是不许思考或者不会思考造成的。
思考意味着对生活的质疑和批评,而批评则意味着发现残缺和揭示问题。如果限制、剥夺人类思考和批评的权利,如果人类因此而丧失了思考和批评的能力,那么,人类的生活将陷入可怕的愚昧状态和严重的混乱状态。
文学就是人类思考和批评生活的一种方式。一切伟大的文学,无论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其本质,都是反思性和批评性的。文学创作是对生活的反思和批评,文学批评则是对文本以及它所叙述的生活内容的反思和批评。面对作家和作品,文学批评必须具备一种自由而平等的精神,必须摆脱内心的顾虑和恐惧,把“说真话”当做绝对的原则。就此而言,真正的文学批评,都有一种纯粹的品质,——虽然我一向对“纯文学”理论不以为然,但是,我很愿意仿照“纯文学”这一术语,把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命名为“纯批评”。
其实,所谓“纯批评”,也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几十年前,一个叫瑞恰慈的英国批评家,早就用过一回了。只是,“新批评”理论里的“纯批评”,把文学作品当做文学批评的“本体”和“客观”对象,排除包括读者、作者、社会内容和历史背景以及“意图”在内的一切非文学因素,这与我所说的“纯批评”,显然是大不相同的。在我看来,将作品当做批评解剖的主要对象,无疑是对的,但是,如果忽略甚至排除包括读者、作者以及社会背景在内的关联性因素,那么,文本批评的有效性,就要大受影响。所以,我的“纯批评”观,在方法上,固然也吸纳“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和修辞分析的经验,接受它对语言的“咬文嚼字”的认真态度,但却主要是一种针对当下文学批评的庸俗化而提出来的主张,意在强调求真精神和专业精神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
纯批评把文学当做一个高贵的生命体,对它充满爱的情感。这不是一般性质的爱,而是一种近乎宗教情感的爱。一个批评家倘若不能将他对文学的情感,升华到这种纯粹而热烈的高度,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批评家。正像普希金在《论批评》中所说的:“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对艺术的纯洁的爱,那么,不管他在批评中奉行什么样的原则,他就必然会沦入被卑鄙、自私的动机所任意摆布的人群中去。”
“纯批评”相信文学具有解放人和升华人的力量,相信文学是与人的教养、尊严、自由和幸福密切相关的事情。它认同人类已经确立的高贵的精神法则和崇高的文化理念。它评价一个作家成就大小的尺度,评价一部作品价值高低的标准,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精神性的;不是市场性的,而是真理性的。它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文学有着不可被“产业化”的品质,有着非商品化的特殊性。所以,一个社会越是将金钱和市场的成功当作追求的最高目标,那么,它的精神生活就有可能越贫乏,它在文学方面的创造能力也就越低下。“纯批评”完全接受格奥尔格·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对金钱与那些伟大价值之间对立关系的描述:“金钱被重视的程度越深,真、善、美、荣誉、才能、健康的思想就越市场化,人们对它们的态度就越嘲弄、轻佻、玩世不恭。它们的价值被看作与路边小摊叫卖的杂货没什么区别。将高尚的价值转化为肮脏的交易,金钱的这一讽刺性的功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纯批评”从不根据一部作品的印数和码洋,来确认它的价值,也从不根据一个作家获奖的次数、级别以及奖金的多少,来评价他的成就。《哈利·波特》第五部在出版的第一天,就卖了五百万本,成为人类出版史上从未有过的疯狂现象。此时此刻,批评《哈利·波特》,就需要极大的勇气,其难度,按照布鲁姆的形容,“比哈姆雷特面对一片汪洋的困顿还要棘手”。然而,哈罗德·布鲁姆、威廉·萨菲尔和英国女作家拜厄特却尖锐地表达了他们对这部作品的质疑和不满,拜厄特甚至发出了“谴责”的声音,认为那些沉迷于《哈利·波特》的人,“都是些心智未开的,且从无阅读习惯的幼稚人士”(苏友贞:《小哈利·波特所不能承受的重》)。我们应该向这三位捍卫“纯批评”立场的知识分子致敬。他们不仅没有接受《哈利·波特》中的那些“像旧鞋一样让人舒服的陈词滥调”,而且,还在这部作品引发的海啸席卷而来的时候,镇定而勇敢地向人们发出了安全撤离的警报。
是的,“纯批评”不是作家的亦步亦趋的应声虫,不是他们的随叫随到的按摩师。它的任务,是准确地描述一个作家的风格特点,是合乎事实地揭示他的写作的成败得失。它不屑于为了照顾作者的情绪,而说一大堆违心的好听话。这样,尺度和标准的严苛,态度的尖锐性和彻底性,就成了“纯批评”的重要特点。诗人哲学家张中晓在《无梦楼随笔》中谈到“有所创见的思想体系”的时候说:“彻底性,正如独创性和尖锐性,永远使思想产生吸引力。永远反对冗长、平庸、枯燥、无味和空洞。反对思想的模糊,模棱两可。”纯粹的文学批评,就是严格而尖锐的批评,而不是温温吞吞、模棱两可的批评。别林斯基曾经在《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批评及其文学意见》中区别过“对读书的爱好”和“对文学的要求”之间的不同,在他看来,尺度严格的要求,乃是文学产生的前提条件:“只有等到我们的读书界变得人数众多起来,求全责备和严厉苛刻起来的时候,文学才会出现。”的确,没有严格的批评,就不会有良好的文学环境,文学就很难自觉和成熟起来,真正的文学就很难出现。
严格,越是面对“有影响力的作家”,“纯批评”的尺度就越是严格。屠格涅夫在《回忆别林斯基》中说:“别林斯基以和蔼的谦虚和同情的温暖来鼓励他认为有才能的新进作家,扶助他们最初的进展;可是,对他们往后的创作他就严格起来,无情地指出他们的缺点,以一视同仁的公正态度驳斥或者赞扬。”这样的不讲情面的严格,常常会使那些被批评的作家怏怏不快、恼羞成怒,甚至会使他们对批评家产生严重的误解甚至敌意,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和精神伤害。除了第三厅厅长本肯多夫,对别林斯基心怀不满甚至敌意的作家,不乏其人。1837年,别林斯基在给克拉耶夫斯基的信中说:“……在我看来,说你不想说的话,用自己的信念投机,这不仅不如沉默和忍受贫困,甚至不如干干净净地死掉。”正因为有这样的信念,所以,面对别人的误解和伤害,别林斯基从来就不曾畏惧过。
“纯批评”不是在形式上大做文章的技术主义批评,也不是只关注自我的个人主义批评,而是充满理想激情的人文主义批评。它追求的愿景是“大文学”。这种文学,就像俄罗斯杰出的女作家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在评价《古拉格群岛》时所说的那样:“这是奇迹,这奇迹可以使人复苏、改变血液构造并制造新的心灵。”(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大文学”是扎米亚金在《目的》一文中提出的重要概念。他根据目的和“任务”的大小,将文学分为“大文学”和“小文学”。他说:“应该清楚,文学与科学一样,可分出大文学和小文学,二者均有各自的任务。外科学也可分出‘大外科’与‘小外科’:‘大外科’推动该学科前进,‘小外科’完成每天例行的工作;‘大外科’可以进行卡莱尔和沃罗诺夫的实验,‘小外科’为手包扎绷带;天文学也有大小之分:大天文学推断出太阳系的运动轨迹,小天文学为轮船在海中航行建议采用确定方向的方法。如果我们让卡莱尔去缠绷带,结果就是又多了一位医士;当然这也有好处,但是很愚蠢,因为人们虽多了一位医士,却失去了一位天才的科学家。”他对当时的俄罗斯批评家深置不满,认为他们忽略了“大文学”,只看得见“小文学”:“评论界将俄罗斯文学引向医士之途,医士主义就是俄罗斯文学病症的名称。”他认为,“大文学”有着伟大的“目的”,有着规划和变革生活的抱负,要对整个人类生活发生巨大的影响。为此,他提倡有理想的“一千米的文学”,而反对无目标的“一粒米的文学”。对于文学批评来讲,“大文学”有着背景和坐标的意义,——没有“大文学”的参照,任何文学批评都将是缺乏方向感的,甚至是无效和无意义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需要文学来记录和见证的时代。人们需要能给自己的内心带来勇气和力量的文学,需要能使自己更优雅、更有教养的文学。然而,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市场化”笼罩一切的时代,这样的文学还能产生出来吗?我们的文学还有希望变得更好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