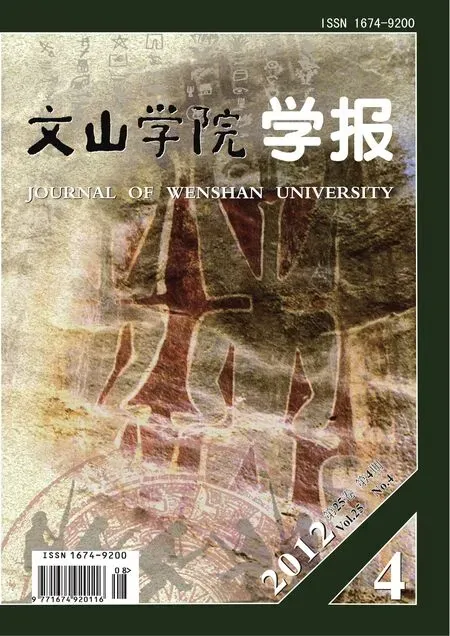儒学对晚清礼法之争的影响——以伍廷芳和张之洞为考察对象
2012-03-20张丹露
张丹露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089)
晚清“礼法之争”是指在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和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围绕《大清新刑律》等新式法典的修订而产生的理论争执。一般认为法理派是主张大量吸收和运用西方的法律原理改造中国传统法律,而礼教派则是主张改革不应偏离数千年相传的“礼教民情”。法理派侧重吸收西方的法律原理代表着先进,礼教派侧重坚守中国传统礼教文化则代表保守,甚至是落后。公元2000年前后,学界掀起了一股“翻案风”,对包括张之洞、劳乃宣、沈家本等礼法之争中的代表人物进行了重新评价,但评价标准依然没有离开上述所说的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这一评价维度。笔者认为无论是礼教派亦或是法理派的修律思想实践都存在继承、运用传统文化的内容,尤其是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对儒学文化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促成了修律主张之不同。张之洞和伍廷芳分别是礼教派和法理派的代表人物之一①。本文拟以此二人为代表来分析儒学对礼法之争的影响。
一、伍、张二人对儒学的不同理解
伍廷芳和张之洞对儒学都非常推崇,但他们对儒学的理解不同。
在外交活动及外交活动之外的许多言辞中,伍廷芳的言辞都表达其对儒学的尊崇。他曾提到“道教和佛教只是在儒学所未触及的领域和人们中间发挥作用”,而儒学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政治、国民生活的基础”,走遍中国的东南西北,“无论政治家、农民、商人、学童(生员)都羞于把自己归入儒学之外的其它任何一种学说的信奉者之列”。[1](P112-113)他甚至认为,儒学在中国的地位正如基督教在美国的地位。伍廷芳的儒学思想具有以下特点:其一,他反对将儒学宗教化,将孔子神圣化。在伍廷芳看来,“孔子之道,不尚神奇”。“孔子持躬谦逊,未尝自诩以生知胜人”,“敬鬼神而远之”,且“不以神明自居”,这是“见于记载”,可以考证的事。后人“尊敬之,崇拜之”也是应该之事。但是“若尊之若神,则意虽甚崇重,窃谓孔子必不受此谀词也。”[1](P618)其二,强调儒学经世致用的社会责任感。在否定了儒学的宗教性之后,伍廷芳进一步指出孔子之学只于伦常日用之中,其言“曰忠恕,曰仁,日用伦常”。他反对八股文,认为八股“只知猎取功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无丝毫之补”。[1](P618)伍廷芳也倡导“五伦”之说。他认为所谓“五伦”是“一个人置身社会的地位和各种生活态度”,“每一种地位和态度都联系着特定的职责,履行这些职责就可以造就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1](P115)他的“五伦”更强调的是社会中每个人“各司其职”的社会责任以及由此建立的社会秩序。他所提倡的这种“五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纲常道德的政教性。其三,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兼容精神。伍廷芳的儒学并不仅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是具有了一定的“全球性”。伍廷芳曾不只一次地批判过美国人的那种“时间即是金钱”的生活原则。在这种生活原则的指导下,美国人面临着生活紧张、压力大、健康水平下降、人际关系冷漠等一系列的问题。而儒家的生活原则却可以缓解这些问题。他提到有一个本来在中国工作的美国汉学家,回到美国后却难以适应美国的生活,又回到了中国工作、生活。另外,伍廷芳也指出“竞争是激烈的和具有破坏性的”,提议用儒家的和平精神解决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这些也体现了伍对和平、和谐精神的追求。
相较于伍廷芳来说,张之洞的儒学思想则有很大不同。对于张之洞的儒学特点,前辈学者已经有了很多具体且深入的探讨。本文仅在概括的基础上做一些补充。其一,张之洞将儒学视为儒教。《劝学篇》开篇中,张之洞即指出“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2](P51)因此,其主张“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 若“中士而不通中学,此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无舵之舟,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虽有博物多能之士,国家亦安得而用哉!”[2](P90-91)其二,强调三纲五常的政治性。张之洞提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2](P70)其三,主张经世致用。张之洞提出“读书期于明理,明理期于致用”。龚书铎和王兴涛教授则进一步指出张之洞的思想是通经致用,而不仅仅是“经世致用”。“通经致用”与“经世致用”的区别在于“后者主要强调致用,而前者则将‘通经’和‘致用’两者并举,甚至视‘通经’为‘致用’的前提条件。”二人认为“张之洞提倡西学归根结底不过是手段而已,一旦他意识到西学直接威胁于儒学名教,便要起而捍卫。”[3]有学者注意到张之洞的经世致用具有双重性。在社会危机下,匡扶救拯使命感促发的经世思想,打破了传统的‘本末’、‘夷夏’观念”,提供了张之洞汲纳新知、采补西学的思想动力,另一方面,这种以‘切用’、‘致用’为旨趣的学术追求和致思路径,农业——宗法社会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实用理性,又不得不服务于至高无上的道德伦理。当‘经世致用’的张力危机社会道德主体的生命时,它必然会转向自救,捍卫‘中学为体’不可动摇的地位,‘经世致用’又称为保守思想的摇篮、卫道的工具,变成近代化的障碍。”[4]
综而言之,张之洞和伍廷芳虽然都表现出了对儒学的尊崇之情,但是伍廷芳则更侧重于把握住儒学中重视社会责任感、注重个人修养等精神层面的内容,而弱化了其中三纲五常的政治化内容,更偏向于文化方面的意义。经过这样的处理,伍廷芳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应对和处理危机,也可以更灵活地融合其他文明。而张之洞则更侧重于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秩序。他用儒家的纲常伦理维护封建道统,用封建道统来维护纲常名教的合法性。因而,虽然张之洞有改革之主张,也只是在传统政治秩序和文化系统内部的循环。
二、伍、张二人在修律问题上的争论
伍廷芳和张之洞的争论主要围绕着1906年《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和1907年上奏的《大清新刑律草案》的内容。
关于诉讼法。1906年4月25日,伍廷芳、沈家本等上了《奏诉讼法请先试办摺》,提出了两条具体建议:设陪审团和用律师。光绪帝对该奏折做了如下批示:“法律关系重要,该大臣所纂各条究竟于现在民情风俗能否通行,着该将军、督抚、都统等体察情形,悉心研究其中有无扞格之处。”[5](P5506)该谕旨下发后,遭到各将军、督抚和都统的反对,其中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反对尤烈。有学者认为张的意见集中代表了这些封建官僚的思想。1907年七月二十六日,张之洞上了《遵旨核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称伍廷芳等所拟之诉讼法于“中法本原似有乖违,中国情形亦未尽合”。具体而言,在第五十条中,伍廷芳等人建议,“凡公堂审案令原告亲身到堂”。张之洞认为“原告到堂,自是正办,然职官、命妇、举贡、生员例得遣抱”,“以全体面而是优异”,“例应遣抱者令抱告到堂”又如,第一百三十条建议,“本人妻所有之物”、“本人父母兄弟姊妹及各戚属家人之物”、“本人子孙所自得之物”,“不在查封备抵之列”。而张之洞则以“今以查封备抵之故,而强为分析财产,则必父子异宅,兄弟分炊,骨肉乖离,悖理甚矣”否定了这一提案再如,第两百四十二条,“凡职官命妇均可由公堂知会到堂供证”。但是,张之洞认为“妇女到堂供证,为万不可行之事”,“此为名教所关”,“如实系案内紧要人证,尽可令其子侄兄弟到堂”,“以养廉耻全名节”从以上的辩论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伍廷芳等人是按照公平、平等的原则来拟定法案,而张之洞主要是以名教纲常为原则来评判伍等人所拟之法案。他认为“盖法律之设,所以纳民于轨物之中,而法律本原实与经术相表里,其最著者为亲亲之义,男女之别,天经地义,万古不刊。乃阅本法所纂,父子必异财,兄弟必析产,夫妇必分资,甚至妇人女子责令到堂作证,袭西俗财产之制,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教,纲沦法斁,隐患实深”,而列强能否归还法权不在中国法律是否完善,而在于“国家兵力之强弱,战守之成效”[6](P1772)。1910 年 12 月,修订法律馆起草完成《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因清廷被推翻,未及核议颁行,但成为后期北洋政府立法的蓝本。
关于《新刑律》的讨论。伍廷芳在修订刑律方面的主张概括言之就是废除笞杖、缘坐、刺身以及主张死刑唯一等。具体而言,他主张用斩决、绞决、监候代替凌迟、枭首、戮尸。至于缘坐,除了“知情者仍治罪外。其不知情者,悉予宽免。”刺字一条,概行删除,“凡窃盗皆令收所习艺,按罪名轻重定以年限”。[5](P5325-5327)另外,笞杖用罚金代替。[5](P5329)这一草案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经宪政编查馆奏交部、院及疆臣核议,签驳者众”。[7](志一P4190)法律上呈后,受到张之洞、劳乃宣为首的“礼教派”的强烈反对。1908年5月,张之洞上奏对《新刑律》进行了反驳,“新订刑律草案与现行律例大相谬刺者”如下:其一,“旧律于谋反大逆者,不问首从,凌迟处死”,而新律草案则于“颠覆政府僭窃土地者,虽为首魁或不处以死刑”,“凡侵入太庙宫殿等处射箭防弹者,或科以一百元以上之罚金”。“此皆罪重法轻,与君为臣纲之义大相刺缪者也。”其二, “旧律凡殴祖父母父母者死,殴杀子孙者杖。”而新律草案则“凡伤害尊亲属,因而致死者或笃疾者,或不科以死刑”。这样的做法“视父母与路人无异”,“与父为子纲之义大相谬刺也。”其三,“旧律妻殴夫者杖,夫殴妻者非折伤勿论。妻殴杀夫者斩,夫殴杀妻者绞”。而新律中,“妇人有犯罪坐夫男者独多,是责备男子之意尤重于妇人,法意极为精微”。并且新律草案“并无妻妾殴夫之条,等之以凡人之例”。“是与夫为妻纲大相刺缪者也。”其四,“旧律犯奸者杖,行强者死”。新律草案则“对于未满十二岁以下之男女为猥亵之行为者,或处以三十元以上之罚金。行强者或处以二等以下有期徒刑”。“亲属相奸与平人无别”,“是足以破坏男女之别而有余也。”其五, “旧律凡殴尊长者,加凡人一等或数等。殴杀卑幼者,减凡人一等或数等。干名犯义诸条,立法尤为严密。”新刑律草案则并无尊长殴杀卑幼之条,等之于凡人之例,是足以破坏尊卑长幼之序而有余也。”其六,流刑可除,“而笞杖则有不能尽废”,罚金则“不尽可行”。新律草案“凡因过失致危害于乘輿车驾者,凡侵入太庙宫殿者等处射箭防弹者,凡因过失致尊亲属于死或笃疾者,亦以罚金之例行之。则饶于赀者必轻于法。此在重货财而轻礼义相习成风者,或可行之。要非所论于我彝伦攸敍之中国也,此刑名之未可全改者也。”其七,“酌减死罪一条,有万不可减者”,如谋反者,卑幼殴杀尊长者,强奸妇女者,强盗于盗所强奸者,发塚见尸者,发尊亲属塚见尸者,放火决水者,“皆属殊等,不置之死,何以戢暴。”其八,“新律草案称死刑仅用绞刑一种,大逆逆伦重案俱用斩刑。然现当斩刑未废,如一律用斩,是等君父如路人,破忠孝之大义。将来流弊之所极,有非臣子所忍言者”。其九,“原奏删除比附一条,尤为矛盾。但由审判官临时判断,独不虞其意为轻重耶。引律比附,尚有依据。临时判断,直无限制。即如罚金一项,多或数千元,少或数十元,上下更易,出入必多。且所定各条,多有同一罪而定三种之刑,悉任裁判官订拟。范围太广,流弊甚大。”其十,惩治教育“可以仿行”,但“尚须酌定年限”。“凡犯罪在十六岁以下,不论大小轻重,皆无刑事上之一切责任,一以惩治教育处之。限年太宽,恐滋流弊”。[5](P5909-5910)1909年,清廷谕令修律大臣:“凡旧律关乎伦常者,不可轻率变更”,要求秉此宗旨从速编订刑律,“请旨颁行,以示朝廷变通法律,循序渐进之至意”。修订法律馆不得不将此草案收回,并重新草拟刑法。直到1911年1月25日,政府才正式公布经过多次修改的《大清新刑律》和《暂行章程》五条。《大清新刑律》分总则和分则两编共411条,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新式刑法典,无论体例还是内容均与中国传统刑律大不相同。清政府本预定在宣统五年正式施行。但由于在此法典公布后不久,清王朝即告覆亡,故《大清新刑律》并未正式施行。
三、儒学的影响:融合与固守
龚自珍有言,“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8](P4)笔者认为,对儒学的认识和理解之不同影响了两人在法律中的思想和实践。
在法律改革中,张之洞的思想资源和动力主要是儒家经世致用的社会责任感、“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以及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在经世致用和“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的双重作用下,张之洞积极主张变法。1901年,慈禧借光绪之名发布上谕“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可变者令甲令乙,不防如琴瑟之改弦……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至富强。”[5](P4601)之后,张之洞、刘坤一上呈了《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中提出了诸多变法主张,包括“恤刑狱”一条,主要内容为:“禁讼累”,革除差役,消除讼累;“省文法”,减省诉讼中的繁文缛节;“省刑责”,禁止刑讯逼供,“重众证”,改革苛酷刑罚;“修监羁”,完善监狱制度,改良监狱管理以及“教工艺”、“恤相验”、“改罚锾赎罚之刑”、“派专官”等。1902年2月,光绪又发布上谕“著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著责成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候简派,开馆编纂。”[5](P4833)在张之洞等的保荐下,伍廷芳被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
但是,我们观察到在法律改革过程中,一旦涉及到纲常伦理的内容时,张之洞就会变得敏感而严厉。不论是在刑法改革亦或是在诉讼法改革中,张之洞所反对的都是伍廷芳等提出的关于与“亲亲”、“尊尊”、“父父”、“子子”、男女有别等伦常相违之处。在第一部分中,我们提到张之洞的经世致用精神具有双重性,而且其对纲常伦理具有执着的坚持。因而,张之洞虽然赞同法律可变并且积极参与,但是始终都不会破坏君臣父子夫妇的纲常伦理②,跳不出“中体西用”的范围。当时袁世凯、刘坤一曾举荐何启为法律人才,遭到了张之洞的反对。张认为何启“前三年曾作《驳〈劝学篇〉》一卷,句句皆驳。……其尤力驳者,教宗、明纲、正权、宗经数篇。谓鄙人教宗篇称本朝十五仁政条条皆非……谓君臣父子三纲之说为非古……谓只当有民权,无当有君权……谓中国经书不当信从……此人此书,可谓丧心病狂无忌惮……万不可举”。[9](P727)同样,在诉讼法和刑法的改革中,张之洞和伍廷芳的争论其实主要就是针对是否要维持等级秩序,儒学的秩序是否一定是法律的秩序、政治的秩序。张之洞坚持将保国与保教视为紧密联系着的两个概念。他的修律逻辑亦为要保国就要进行法律改革,而为了保教,又不能使改革的范围超出儒教的范围。法律成了他维护儒学的一个工具。有学者指出,张之洞的法律变革主张是在对中国“政治、宗教、风俗、习惯、历史、地理”等情况加以考证的情况下所做的选择。他所走的改革道路是“渐进”的。但是,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张之洞的法律改革永远都不可能实现从传统的伦理法向现代法律的转变,而只能是在传统伦理法内部调整。
伍廷芳的法律改革资源和动力除了儒家的经世致用和“仁政”的思想外,还添加了一部分反应西方法律原理的内容。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倾向于肯定伍廷芳对西方法律原理的追求和应用[10],甚至有学者认为伍廷芳是资产阶级的法学家。笔者认为促使伍廷芳修律的动因主要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精神以及“以民为本”的“仁爱”思想。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已经注意到了中国需要改革,即“欲救国厄,非赴欧美精究法学,举吾国典章制度之不适者,非改弦而更张之不可。”[11](P24)抱着这样的志向,伍廷芳于1874年赴英国自费留学法律,并成为第一个取得大律师资格的中国人。晚清政治的一大弊端是清政府丧失了治外法权,伍廷芳认为治外法权极为重要。1902年,英国承诺“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5](P4919)这是伍廷芳提倡修律的一大动因。另外,在修律过程中,伍廷芳经常提到诸如“仁”、“百姓生活”、“民命”等这类的言辞,体现出了其对传统儒学“仁政”、“以民为本”思想的继承和运用。他曾言“治国之道以仁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因之,他提出了“现行律例”“亟应先议删除者”为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5](P5325-5326)他还提倡“化民之道固在仁教,不在刑威也”。[5](P5326)而且,他在《关于军机处钞交御史刘彭年奏禁止刑讯有无窒碍摺》中明确表示其所提出的停止刑讯“不过申明旧例,略为变通。其实与西法无涉也。”[5](P5357-5358)因而,笔者认为,伍廷芳的改革动力与其说是来自于对西法的追求还不如说是来自于对中国内忧外患的深切关怀以及对国家独立、富强的追求。在《中华民国图治邹议》中,伍廷芳曾感慨“回忆前朝供职”,“季世遘乱,政纲失纽,屡有条陈,辄思补救,奈终见沮,十不一行,志敛心灰”。[11](P563)当然,如前所述,伍廷芳的儒学态度较为开放和灵活,没有太多的纲常伦理影响。因而,他能够吸收西方的法学原理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概言之,伍廷芳所吸收西方法学原理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陪审制”、“律师制”、“罪行法定”等,这些原则已经超越了纲常伦理的范围。
注释:
① 苏亦工先生认为“清末修律工作的实际展开是伍氏到任后推动的,且伍氏的作用居于主导地位而沈氏只发挥了次要的作用。”参考《重评清末法律改革与沈家本之关系》,《法律史论文集》,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张之洞有言“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张之洞著,李忠兴评注:《劝学篇》,第13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版。
[1] 丁贤俊,喻作凤.伍廷芳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 张之洞.李忠兴评注.劝学篇[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3] 龚书铎,黄兴涛.儒臣的应变与儒学的困境——张之洞与晚清儒学[J].清史研究,1999(3):74-84.
[4] 张昭军.从“经世致用”到“中体西用”—— 张之洞对传统儒学的调适和锢蔽[J].孔子研究,2004(4):98-111.
[5] 朱寿朋编,张静庐校点.光绪朝东华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4.
[6] 张之洞.张之洞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7] 赵尔巽等.清史稿·刑法志[Z]. 北京:中华书局,1998.
[8]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9] 吴剑杰.张之洞年谱长篇[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10]熊秋良.论伍廷芳的法律思想[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10): 134-140.
[11]张元洛,等.伍秩庸博士哀思录[M].北京:商务图书馆,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