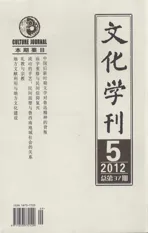韩昌黎与“天一阁”及其他
2012-03-20艾珺
艾 珺
看到这个题目,似乎会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相声“关公战秦琼”——如俗语所谓“八竿子打不着”也。
是的,韩昌黎,生于唐代宗三年(768),比天一阁楼主范钦(1505~1585)出世要早730多年,天一阁更是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范钦致仕后回到宁波的次年56岁之际。
“十万卷签题,缃帙斑斑,笑菉竹绛云之未博;三百年清秘,祥光昞昞,接东楼碧沚以非遥。”这就是全祖望视野中的与创建于十六世纪的意大利马拉特斯塔图书馆、美第奇家族图书馆并称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也是亚洲当今存世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烟波四面阁玲珑,第一登临是太冲。玉几金峨无恙在,买舟欲访甬句东。”这是清末民初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所记述的“天一阁”。叶昌炽注云:“《天一阁书目》所列范氏诸印有‘四明范氏书记’、‘甬东范氏家藏图书’、‘古司马氏’、‘万古同心之学’、‘东明山人’、‘东明草堂’、‘七十二峰一吾庐’、‘和鸣国家之盛’,司马印也。”说起来,正是范钦在“天一阁”使用的这枚藏书铭印“和鸣国家之盛”让我杜撰出这个题目。或许,也正是缘于范钦创建下“天一阁”,才将韩昌黎的言论凝缩为这样一句祈愿禳灾之“符咒”、“镇阁”之印。
明末清初,被后世誉为著名经学家、史学家兼思想家的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开篇即言:“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唯恐含辛茹苦集藏的书籍惨毁或散失,几乎是所有藏书楼主死不瞑目的心病。
藏书楼第一惧怕火灾,以防祸患为第一要务。“天一阁”之命名,取义于汉郑玄《易经注》中的“天一生水”之说,寓意即为以水克火。楼前辟有“天一池”,蓄水防火,可谓虚实结合。也有人说,是先建的用以防火的“天一池”,因池名阁,如《天一阁碑目记》:“阁之初建也,凿一池于其下,环植竹木,然尚未署名也。乃搜碑版,忽得吴道士‘龙虎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公所书,而有记于其阴。大喜,以为适与是阁凿池之意相合,因即移以名阁。”(《藏书纪事诗》之一三二)一如《东斋脞语》所言:“范氏立法尽善,其书不借人,不出阁,子孙有志者就阁读之,故无散佚之患。其阁四面皆水,读者不许夜登,不嗜烟草,故永无火厄。迄今三百年,虽十亡四五,然所存尚可观也。”无论怎么讲,藏书楼防火无不用心良苦。
楼主的另一大心病,便是唯恐身后子孙不肖致使藏书散失。范景中《藏书铭印记·澹生堂朱文方印》记述明末藏书楼“澹生堂”的藏书印云:‘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旷翁铭。’此印《东湖丛记》曾着录,三百年后澹生堂藏书再度显世,其名益着。观此印即令人忆及《藏书约》中寄语:‘然而聚散自是恒理,即余三十年来,聚而散,散而复聚,亦已再见轮回矣。今能期尔辈之有聚无散哉。要以尔辈目击尔翁一生精力,耽耽简编,肘敝目昏,虑衡心困。艰险不避,讥诃不辞,节缩饔飧,变易寒暑,时复典衣销带,犹所不顾,则尔辈又安忍不竭力以守哉!”“拜经楼”主陈书崖甚至还有一方藏书铭印曰“陈氏藏书子孙永保”。有的遗训甚至带有惩戒性的内容。王述庵藏书印即是:“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石备。购且藏,剧劳勚。愿后人,勤讲肄。敷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勿废置。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棰。述庵传诫。”范氏亦然。范氏立有“书不出阁,代不分书”、“藏书为子孙共有”的遗规,甚至具体规定严禁带书出阁,阁厨锁钥分房掌之,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得开锁,违者以不允许参加祭祖大典作为严惩。他把这些规则制成木牌张挂在各处,时时警示家人,甚至还刻治了藏书铭印“子子孙孙,永传宝之”。此外,为使藏书永不致在下一代两个儿子手里散失,他订立了个规则:将家财分作两份,一份是天一阁的全部藏书,一份是其他巨额的钱财。如后世清代大学问家全祖望的另一篇《天一阁藏书记》所感叹,“吾闻侍郞二子方析产时,以为书不可分,乃别岀万金,欲书者受书,否则受金。其次子欣然受金而去。今金已尽而书尚存,其优劣何如也”。如此一系列家规制度,实可谓既严密又富有操作性。
清代拜经楼主、文学家吴骞有道:“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此昔人诒厥之名言,是可为拜经楼藏书之雅则。”除上述两大威胁藏书楼的基本隐患外,再即盗抢和兵祸等社会动乱,尤其是可能致使百年心血一朝尽失的危害。衰世、乱世毁书,盛世刻书、藏书。作为学者,范氏十分明白,这是自己生前身后都难以预测也左右不了的事情。“毛氏藏书铭印:‘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所谓结念之殷,悬忧之切,托之子孙,不如祷之鬼神矣。”(《东湖丛记》)于是,便有了范氏的这方藏书铭印“和鸣国家之盛”,意在为藏书楼的平安祈盼永远的盛世之福。《铁琴铜剑楼书目》卷二十:“宋本《击壤集》,芙川藏书,卷三册首空页,有芙川以血书‘南无阿弥陀佛’六字,题其后云:‘乙巳十一月得之,爱不能释,以血书佛字于空页,惟愿流传永久,无水火蠹食之灾。’”显然,将“和鸣国家之盛”藏书铭印盖到藏书上的用意,不啻于血书代印“祷之鬼神”的“符印”功能。
然而,事情并非总是尽如人愿。原有藏书七万余卷的“天一阁”,虽未失之于范氏下一代之手,但从明末战乱开始,历经鸦片战争中英军占领宁波、1861年太平军进驻宁波,及至民初江洋大盗薛继渭与不法书商相勾结盗书等等众多劫难,藏书大批散失。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天一阁”全部藏书已经仅剩一万三千多部了。三百多年,散失了五万七千余部,占最初藏书的八成以上。看来,历代藏书楼的最大威胁,还是社会动乱之灾。
汉代大儒董仲舒云“诗无达诂”(《春秋繁露》卷三《精华》)。“作品一经发表问世或传播成为公共所有,除了翻译和研究作品以及作者本身需要尽可能地还原文本之外,其它需要的受众的解读和使用便是多元化的了。”这一点,古今中外同理。“和鸣国家之盛”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韩昌黎原文,是一篇意在劝慰自感际遇不平的好友孟郊往江南赴任溧阳县尉而作的赠序。范氏就藏书而言将其凝缩为祈愿禳灾之“符咒”、“镇阁”之“符印”,自有其道理,无可厚非。但温读韩昌黎原文,其给人的启迪和警世意义之深远,迄今仍值得回味。韩昌黎《送孟东野序》文虽不失委婉、含蓄,然颇有甚为精警之说,且抄示几行如下,共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
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前提是“和其声”,然后才有“使鸣国家之盛”,这是一个非常明晰的逻辑。《礼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音乐、谣谚源起如此,“舆诵”同理。“大鸣大放”时期,因其属于所谓“阳谋”就难免迸发怨愤,愤怒出诗人。无论何时,一当“万马齐喑究可哀”——即无奈谣谶四起遑论太平。《述异记》卷下载:始皇二十六年,童谣云:“阿房阿房亡始皇!”这是百姓对于暴君的诅咒。《后汉书·五行一》:献帝践祚之初,京都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其实这是对于权奸董卓的诅咒。每逢谣谶四起,必将世呈乱相,世呈乱相何谈太平?清代刘毓崧《古谣谚》序云,“言为心声,而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盖谣谚之兴,由于舆诵。为政者酌民言而同其好恶,则刍荛葑菲,均可备询,访于輶轩;昔者观民风者,既陈诗,亦陈谣谚”。“舆诵”者,古人又谓之“舆颂”、“清义”,是众人的议论,亦即今人所说的“舆论”。《晋书·郭璞传》:“方辟四门以亮采,访舆诵于群心。”所言即此。“谣谚之兴,由于舆诵”,古代的谣谶便属于更为直接的舆论性的蕴涵民意的天籁之声。疏导舆论通道,化谣谶而为百鸟齐鸣,百鸟齐鸣则龙凤呈祥,龙凤呈祥即“和鸣国家之盛”也。便捷的网络时代,尤其为舆论的传播拓宽了渠道,增强了时效。时下遴选官员,实行任前公示。这种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代。《梁书·武帝纪》记载了梁武帝萧衍于南朝齐和帝中兴二年(502)称帝之前以梁公的身份向齐和帝萧宝融上的一篇《立选簿表》里讲到:“前代选官,皆立选簿,应在贯鱼,自有铨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舆论,故得简通宾客,无事扫门。”
至此,以“韩昌黎与‘天一阁’”作为本篇的题目已可谓自有道理并非妄言矣。至于“及其他”这段由感而发的赘言,之于破题解读之用意,想是亦毋庸赘言矣。因为,临到收笔的末了“画蛇添足”似的添了一段随感而发的赘言,只好另在题目后面再“添足”个“及其他”就是。
至于本文对于诸如“天一阁”这类祈愿禳灾之“镇阁符印”性质的解读,似乎尚属首例。不过,确也是笔者的一得之见、一家之言,欢迎讨论。
(明代范钦朱文藏书铭印印“和鸣国家之盛”见本期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