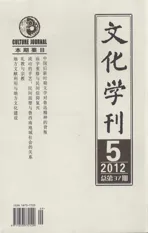儒学“致君行道”向“觉民行道”转变的内在理路——以“仁”的主体演变为主线
2012-03-20李双龙
李双龙
(喀什师范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儒学自产生起,就将“化民成俗”作为其重要的价值旨趣,而其途径主要经历了由“致君行道”向“觉民行道”的转变。在先秦至唐代漫长的儒学发展中,儒家知识分子更多地采取了“致君行道”的路径,寄希望于道德化身的圣君;宋明之后的时代,特别是阳明心学的兴起完成了理学的转向,采取了“觉民行道”的路径。这种路径的转向,是与儒家思想中“仁”的思想的发展有着密切关联的。
先秦时期“仁”的主体:理想中的圣人
先秦时期既是我国历史上社会政治极为混乱的一个时期,又是思想文化相当繁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许多思想派别出于挽救社会时弊的目的,发展起了各自的学说。儒学就是其中的一支。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少年学“礼”,企图以“礼”整合当时失序的社会现实,但此“礼”是西周时期形成的,秦晖教授认为西周时期是个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之上的“熟人”社会,也是个小共同体社会,因而是有着一定社会现实基础的,而随着斗转星移,疆域的扩大,血缘关系的淡薄,到了东周时期“熟人”社会逐渐演变成为“陌生人”的社会,所以,孔子时代“礼”的意义日益突显,但所能发挥的作用却与日俱减。这种对“礼”的遵从是以一种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为基础的,这就是原始儒学的“仁”的基本义,也即虽然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约束规范所发挥的作用在不断变化,但维系这种基本的关系的情感却始终未发生变化。“仁”是孔子及其儒学思想的基础。从文字学的角度而言,“仁”最初的基本含义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后逐渐引申为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所产生的情感,“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就是一种典型的知恩图报的情感。“仁者爱人”就是孔子对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理想要求,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合一的模式,这里的“仁”所反映的更多地是倾向于一种社会关系,“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既是对个体在社会中的要求,也是在家庭中的要求。反映在社会中就是社会理想,反映在道德方面就是道德理想。而一旦这种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的提倡者变为实施者或是与政治相接洽时,就会变为一种政治理想。孔子在侍奉鲁国权臣季氏时,极力劝说季氏家族行“仁”政,效“礼”法,在这种努力失败后,他只能抱着一种理想的政治抱负周游列国,因而发出“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的感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也只能是一厢情愿。此时的儒学在社会理想、道德理想及政治理想上只能停留在理论的层面。
孔子的“仁”学思想发展到孟子逐渐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个人层面的修身养性,一是政治层面的“仁政”思想,要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痛斥“独夫”“民贼”。个人层面的修身养性就是对个人“德”的要求,而政治层面就是“民为贵”的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是以个人的“德”为基础的“仁政”政治思想,此处”个人”当然是指国君。而孟子对“德”的要求既有人与生俱来的本质要求,也有后天的习得要求。与生俱来的就是“仁、义、礼、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辞让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非由外铄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告子上)。后天习得的要求就是理想人格的要求,即浩然之气的“大丈夫”精神境界。所以“孟子的‘仁政’学说,其核心是鼓吹君主的道德圣化,亦即君主道德决定论。君主道德圣化,就可以达到至尊至高的王位”。[1]孟子的社会理想与政治理想也是以其道德理想为基础的,而道德理想却寄希望于行“仁政”的君主身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 他曾以 “从者数百人”的规模率弟子游历宋、滕、魏、齐、梁等国,但均未受重用。在礼乐崩坏的失序状态中,要想取得统治的话语权不是靠思想的先进、文化的繁荣,事实可能正相反,往往是文化落后的国度击败文化繁荣的国度,正如曾经拥有文化繁荣的稷下学宫的齐国被处于中原边缘的秦国所吞并。所以,不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其政治理想与社会理想、道德理想理论上的一致性没能够取得现实的一致性,劝说君主接受自己的思想,达到“三代之治”的理想愿望也自然是落空的。从这一点而言,孔、孟所赖以寄托的“仁”的主体即圣君只是一种理想而已。如果说孔子、孟子没能审视社会现实,那么荀子作为战国末期大儒,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反对“独夫”也倡导儒学的理想社会,但他认为人之为为“伪”,“人之为”即人为的因素,认为人之性为恶,所以荀子发展了孔子思想中“礼”法思想,提出了“法义、法数、类”等概念,认为“人君者,隆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治之经,礼与刑”。所以,从孔子、孟子到荀子,先秦儒家学人都力图探讨一种能够救社风、正人心的思想,只不过,面对不同的社会现实,有着各自的侧重与倾向,但在人君作为道德的化身这一点上似乎却是一致的。
汉唐时期“仁”的主体:现实的圣人
汉代时,疆域的扩大、政治的稳定使统治阶层开始思考秦代灭亡的原因,他们认为战争与统治者大兴土木导致的民不聊生是秦灭亡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汉初儒者陆贾和贾谊,力倡“以民为本”的思想,对最高统治者指出了建立道德至上的社会、政治理想。陆贾说:“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 ”(《新语·道基》)在他看来,仁和义是圣人所以教化万民所必备的要素。但汉初最高统治者因出于社会政治的因素,未能对陆贾的思想加以重视。经过文帝、景帝的黄老之学的思想统治后,汉代社会特别是诸候与中央的矛盾日益突显。到武帝,在具备了推行儒学的时代背景下,董仲舒在“人性”的道德先验论基础上,提出“何谓‘仁’? 憯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董仲舒集·必仁且知第三十》)。而诸如憯怛、谨翕等都是指个人的情感表现,所以,就此而言,董仲舒虽然没能超出先秦孟子荀子对“仁”的感性认识的表达范畴,同时,他也承认“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人有先天的“性”的一面,也有后天的“情”的一面,君主也不例外,作为圣人的化身,上天的代表,教化民众的表率,就不能将个人的情感因素渗入到政治治理中。他进而糅合阴阳五行学说,提出了“天人感应”,将灾异称为是上天对民间的惩罚,作为对国君自我行为的警示,也是儒学理想人格政治化的另类表达,“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春秋繁露·基义第五十三》)。在先秦时期的儒学中专制权力的约束只能从个人的德性中寻找,一旦个人德性丧失,权力便是无止境的,春秋战国的无序就是明显的例证。董仲舒将约束的权力从个人的德性中分离了一部分,赋予“天”以临鉴的权力,希望国君“法天而行”。这正是儒者所孜孜以求的目标,将道德理想、社会理想进行政治化转向,最终完成道德理想、社会理想与政治理想的合一。所以董仲舒的“仁”学思想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君主在政治上不容置疑的权力,要求其“威势成政”;一是作为道德上理想人格的化身,要求对“德”的尊崇。就此而言,汉代“董仲舒的思路中出现了道统与政统合一的取向”。[2]“道统”代表着政治的理想,“治统”代表着政治的现实,二者的统一,使得“仁”的主体有了现实的依托。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因对君主行为的失望而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继而以盛世著称的唐代,却是“平庸的盛世”,其推崇的“道先,儒次之,末佛”的文教政策,将“天子”的理想人格落在了追求“佛性”的“长生不老”中。对精神世界的虚幻追求,使得唐代的社会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变得日益模糊。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世界中,韩愈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决心以“道”济天下。作为当时对外来文化——佛教有着相当造诣的知识分子,韩愈自然希望儒学能够战胜这种导致人心不古的外来文化,以“道”救治天下。但“道”之推行的前提是个人道德的完善。而完善的个人道德就是“性”,指仁、义、礼、智、信五种品质,所以他提出的“性三品说”融合了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并将此作为“道”的推行的基础。“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一切依据仁义的原则行事,就是‘道’……显示在民众中,就是士农工商的秩序……显示在等级上,就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的关系上。”[3]但这种力求从人之“心性”的内在因素改变世风日下的努力,也是立足于重建国家权威,重建社会秩序的视角,以期通过国君天子的心性修养来达到政治合理性的构建。汉唐时期,儒学在政治化之后,其思想更多地通过文教政策、法律予以体现,“仁”学思想也有了安身立命之处,儒者得以行道的努力也仍是通过寄希望于开明的君主。
宋明时期的“仁”的主体:“人人皆为圣人”
从理论角度而言,随着“仁”的主体的演变,儒者“致君行道”也逐渐向着“觉民行道”转变。余英时先生认为宋代是新学与道学同时出现的一个时期,二者又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就儒者理想层面的“内圣外王”而言,新学的代表人物王安石偏于“外王”,他极力进行政治革新运动,但司马光等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七·司马文正公》)。因此,这一运动受到了很大的阻力。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后期“新学”出现的一个动向就是“内圣”与“外王”并重,“内圣”就是道德性命之学,是构成“仁”的主要内涵。如果说宋初,“仁”与“政”是分离的,那么在中期的“新学”时期,“仁”与“政”逐渐走在了一起,无疑,王安石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通过极力劝说宋神宗,希望神宗象先圣先贤一样,以“道学”的理想境界,“外作器以通神明之德,内作德以正性命之精”[4],后得到宋神宗的赞许,革新运动由此得以推行。对理学发展有过重大贡献的“二程”,对于“君道”的推崇与提倡也是肯定的,程颐在注“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时提到:“乾道首出庶物而万汇亨,君道尊临天位而四海从。王者天体之道,则万国咸宁也。”(《周易程氏传·卷一》)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从宇宙与人间秩序的角度阐明了“理一”与“万殊”的关系,“若无太极,便不翻了天地,太极只是一个‘理’字”(《朱子语类·卷一》)。余英时先生认为朱熹所言“极”为太极,就是“君道”,是“理一”。而“万殊”在人间秩序的多样性,从内在理路而言,“理一”为本,“万殊”才不至于空落无序。至此,儒学在汉唐时期与政治结合的基础上,在宋明时期进一步以理论化的形式上升到由“君”而至“圣”而至“天”的高度,由先秦儒学发展而来的“致君行道”教化万民的路径也仍然延续着。
王阳明“龙场悟道”被认为是理学转向的标志,同时也意味着儒者“致君行道”路径的失败。王阳明曾试图按照朱熹的格致之学,格心之非,进而达到圣人境界,但现实的格竹过程却使他的身心备受折磨,由此开始怀疑圣人朱熹的说教理论。从现实层面而言,明正德元年,王阳明因“上封事”而“下诏狱”,并因此以“失身而枉道”为耻。正德三年,龙场之谪,王阳明在其间完成的《五经臆说》,所论及的更多的是“君道”、“臣道”,这也是作为一名儒者所孜孜以求者。但龙场之悟中,王阳明究竟悟到了什么?关于龙场之悟,学者已有过很多研究,但此处,从常理看,人之将死必有一番切身之感悟,这一感悟是对生活、对生命本真的感悟,故而“以身任天下”或“独善其身”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但“以身任天下”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之下显然是难以行得通,这大概也是龙场之悟的重要一悟,而“独善其身”则明显带有道家的“遁”世之嫌,与儒者身份是不相匹配的。正是在这种进又不得、退又不能的两难境地,王阳明作出了学理上的选择,“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年谱》)。 这样看来,《五经臆说》更有可能是侧重于对儒者价值取向的反思,对“理”与“心”的反思。程朱理学中具有普遍规范意义的“天理”、“人欲”,在理论层面转为个体的内在规范。“良知”成为王阳明所赖以寻求生命本真的最后归宿,“致良知”也就成为王阳明的行动取向,他也一再声称“良知”是他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
“良知”,“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理论起点,在阳明看来,心与理为一的根源就在于心本身来自理,这个心是渗入了“天”之“理”的心,也就是说 “理”由天赋予主体而转化为“心”。理是道德法则和规范,理在主体之中的存在状态就是“心之条理”。[5]所以,阳明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体之良知,也意味着传统儒学中“仁”内涵的扩大化,“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王文成公全书卷一》)。孝、弟(悌)、恻隐是先秦儒学中“仁”的主要内容,到阳明心学体系中将其融入“良知”,但阳明同时认为,这种以“仁”为主要内容的“良知”是与生俱来、人人所具有的,不分圣愚。清代焦循说:“良知者,良心之谓也。虽愚不肖、不能读书之人,有以感发之,无不动者。牧民者苟发其良心,不为盗贼,不相争讼,农安于耕,商安于贩,而后一二读书之士得尽其穷理格物之功。”(雕菰集卷八)这里所解释的便是“良知”所应有的、儒学所倡导的“仁”的具体表现。“仁”内容的扩大化所带来的是儒者在“外王”层面方式上的转变。同时“仁”的内涵扩大至人人皆有之良知,也就将传统儒学人性论中所认为的“等级”论化为“人人皆为圣人”的平等论,在思想理论层面打破了宋明理学所认为的只有圣人才拥有对“天理”的绝对权。在确定了这种“良知”的本体论地位后,阳明心学所努力之方向便转为“致良知”,即将良知予以推广,“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王阳明全集》第277页)事实上,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外王”倾向的重大转变,“阳明顿悟之后,对于朝政大体出之于缄默,再也没有流露出在政治上‘以身任天下’的意向”,[6]于是转向“觉民行道”。这一儒学价值取向的转向由阳明后学泰州学派推向了实处。
“觉民行道”的内涵:“百姓日用即道”
随着阳明心学的转向,在明代的政治文化中,期望“圣明之君”以行道的理想落空,倡导以“心性”为基础的“致君行道”理想的破灭,明代士人愈加感到由近乎理想主义的人格教化民众的路径难以达到社会的理想秩序。王艮在起初与阳明的接触中也试图继续“尧舜君民”,但阳明以“君子思不出其位”加以教导。最终,王艮接受了阳明的观点,作出了“觉民行道”的路径选择,提出“百姓日用之道”的本质论主张。
在王阳明的学说中,“百姓日用”与“圣人之道”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即“圣人之道”并非直接等同于“百姓日用条理”,更没有将百姓日用生活原则直接等同于圣人的生活原则。这一距离在王艮这里变得如此之近,他提出的“百姓日用条理,即是圣人条理处”,不仅将百姓之日常生活与圣人的神圣世界变得可能,而且进一步将圣人的神圣世界与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成为等同的现实。这样,在泰州学派这里,圣人之道首先就是百姓日用之道,圣人之生活就是百姓之生活,无论圣人还是百姓,自身的价值都要在日用中体现。
“百姓日用”的凸现在泰州学派的哲学思想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对百姓日用的追求意味着人开始走向对自身的生存境遇、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的自觉确认与自觉承担。百姓日用是人的一种存在性,它规定了人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王艮说:“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7]故而,圣人之生活与常人无异,圣人之为圣人,其标准也是是否合乎日用生活之道。同时“百姓日用”即“道”,“百姓日用”中处处体现“道”的存在,反映了个体与社会生活的一致性,因为“道”只有在个体存在的意义上才显现。人以什么样的方式认识自身,体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百姓日用即道”以肯定的方式认识到个体生活的现实性与有限性,这种现实性便是切身的日用常行,有限性便是受日用常行所限。正是在这种现实性与有限性中,个体憧憬着无限的本体,寻求自我与绝对、个体与社会结合起来的途径,以期在作为主体的自我与作为客体的世界之间找到一条合法的通道,在作为短暂生命体的自我与作为永恒存在的世界之间找到一种内在的联系,而从个体到社会之途径是否存在呢?泰州学派在丰富多彩的世界中寻找到了“日用常行”,在这日用常行中践行着“道”。不过,人从来就不仅仅是“道”的遵守者和机械的执行者,他是生活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复杂的社会存在物。尽管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却有自觉与不自觉的区别。罗汝芳说:“知有两样,童子日用捧茶是一个知,此则不虑而知,其知属之天也,觉得是知能捧茶是一个知,此则以虑而知,其知属人也。”[8]从这个层面看,“百姓日用即道”是要求个体对道德认知的自觉笃行。
结语
作为阳明学的继承者,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规定了自身“觉民行道”的本质属性,希望将“道”与“百姓日用”结合起来,这是宋明理学“致君行道”失败后的重大转向。无论是朱熹抑或是王阳明,初衷都是希望“人君正心”,在新君即位之初,继之以“开新”,有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并趋向理想的社会秩序。程颢的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各自有一个天理”在承认宇宙的普遍性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人间的秩序,张载的“生有先后,所以为天序;小大、高下相并而相形焉,是为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即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礼行”(《张载集》,19 页)类似于朱熹“天理”的“三纲五常”,而“存天理,灭人欲”是以普遍的形式所作出的要求,但其针对的对象如陈来先生所认为的却是天子以至于士大夫阶层,而士大夫与天子同为治天下的阶层。所以宋明理学中,天子的纯德是治天下的主要标准,“致君行道”就成为当时教化万民的主要途径。明代的政治文化催生了阳明心学,在内在理路上表现为由天“理”转向人之“良知”,如果说明阳的觉民行道之途还没有充分展开,那么其后学泰州学派却是“觉民行道”的自觉承担者。“就表现形式而论,晚明的儒学转向逐渐走出了两条路,一条路指向了对宋明儒学的悖反,一条路指向对宋明儒学的超越。”[9]显然泰州学派在特定的时空中指向了第二条路。“百姓日用即道”是从形而上的层面予以行的要求。“泰州学派反对为饰名夸善而工于戒严,并以出于内在良知为道德行为的特征……这一看法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将道德践履的主体性原则具体化了。”[10]这可以说是宋明以来儒学思想在教化实践中的最大转向,即使是王阳明也曾试图通过沿袭程朱的路径,通过发上谕、发榜文的形式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而由“致君行道”向“觉民行道”的转变意味着曾经一度的启蒙思想在中晚明时期的理学向心学的演变中得以催生。
[1]李晃生.儒家的社会理想与道德精神[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5.
[2][3]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308.126.
[4]王安石.周官新义·卷八.国学基本丛书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6.119.
[5]鲍世斌.明代王学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27.
[6]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185.
[7]王心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0·重刻心斋王先生语录[M].济南:齐鲁书社,1995.7.
[8]罗汝芳.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30·近溪子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7.6.
[9]蒋国保.儒学的民间化与世俗化-论泰州学派对阳明学的超越[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95.
[10]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