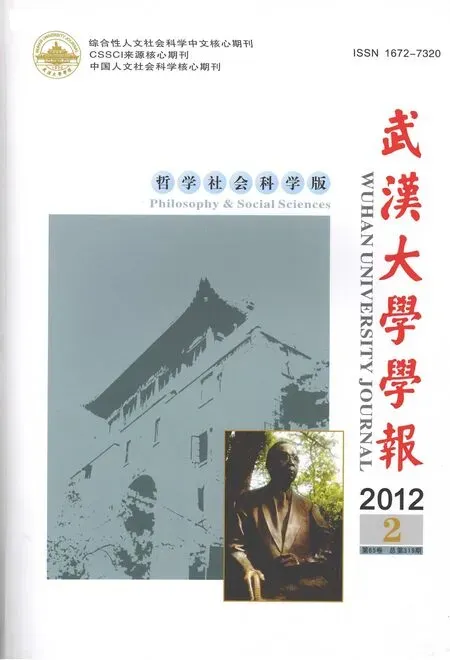国家义务论的宪政功能——论国家义务对现代理性国家的构建
2012-03-19蒋银华
蒋银华
众所周知,国家存在的终极指向是人权保障,国家保障人权之义务属应有之义。国家义务与人权概念互为条件,国家理性的根据有赖于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国家理性是一种从国家构成的本质角度来理解的认识,本文试图从构建现代理性国家角度论述国家义务的宪政功能。
一、国家理性的历史诠释
“国家理性”是西方近代国家兴起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思想因素。作为一个“斗争概念”,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同的“破”与“立”的作用。从“概念史”上看,“国家理性”概念是16世纪中叶在Giovanni della Case的著作中首次出现的。但据考证,“国家理性”这个概念在人文主义大主教Giovanni della Cas正式引入主流文化而传播开来之前,已在意大利民间方言里流行了数十年。另外,从概念史与观念史上看,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马基雅维里”这个名字与“国家理性”概念在16世纪末被等同了起来;从影响史看,马基雅维里是“国家理性”思想之明确而适当的开端①张旺山:《马基雅理革命:“国家理性”观念初探之一》,载陈秀容、江宜桦:《政治社群》,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4年,第77~79页。。
在哲学史上,“在理性中的统一”是政治的基本概念。在“Logos”中有理性,理性追求接触、联合、统一,人类彼此交谈,因而形成了政治社群。自Anaxagoras以来,兼具“根源”与“力量”二义:理性是有“力”的,并且理性也不单纯是“在人里面的一个东西”,它有时候会“闯进”人心中——从“外面”闯进来;后世所谓“超越”,大抵跟这种经验有关②陈秀容、江宜桦:《政治社群》,第96~97页。。而随着对国家理性理解的深入,弗里德里希提出,宪政的国家理性是令法治政府秩序化更为有效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持久的,其中最为根本的即是维护一个人确信的权利③C.J.Friedrich.Constitutional Reason of State.Providence:Brown University Press,1957.p.119.。他指出,任何事务都有其内在的理性,国家理性必须通过心灵来深层领悟④C.J.Friedrich.Constitutional Reason of State.Preface.。韦伯认为,国家理性并非工具理性,而是价值理性。
弗里德里希考察了近代西方有关国家理性的学说后认为,马基雅维里是近代真正从本质上研究国家理性的首位思想家。在弗里德里希看来,马基雅维里指出了关于国家学说中“强权即公理”的无效性,并试图为国家理性提供正当基础。马基雅维里非常关注国家存在的正义性,而且把政治正义置于国家安全和存在之上。他曾指出正义是区别国家(国王)与大盗的标准。马基雅维里开启了立宪政治的新的国家理性观,而且内含着法律统治的实质要素,他认为,政治生活由“必然的法律”所统治①C.J.Friedoich.Constitutional Reason of State,p.9.。因此说,国家理性具有了某种正当性的意义。
弗里德里希继而考察了存续主义思想,他指出,安全与存续是立宪政府所必须面临的问题②C.J.Friedoich.Constitutional Reason of State,pp.34~35.。按照弗里德里希对立宪主义者的考察,指出其对国家理性的根源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认为其主张自然法则是国家理性的根基,立宪则是关键。据此,弗里德里希主张,宪政是国家理性的根本,宪政原则是国家的安全与存续的根基。立宪的国家理性表现为自然权利诸原则,国家的存续源于公民权利的保障程度。因此,国家理性的正当性源于个人权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障。可以说,个人权利若是缺失,国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就是国家理性之所在③高全喜:《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何在》,载王焱:《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三联书店2003年,第9页。。在斯宾诺莎看来,他认为国家的理性是一种立宪的理性,政府的真正目的是保障民众的自由④C.J.Friedoich.Constitutional Reason of State,p.46.。不过,弗里德里希指出,上述思想对于国家理性和个人自由的正当性论述缺乏深厚的价值支撑。
如前可知,立宪主义是考察近代国家理性的立足点,从宪政维度分析国家理性正当性是把握问题的基点。弗里德里希指出,只有在宪政秩序中才可能实现这样一种正义,即依据每个人的自由与所有其他人的自由共存来定义的正义⑤王 焱:《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第88页。。
公民追寻的是正义,因此,如何协调道德与法律规则间的不适是立宪理性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宪政主义的国家理性是从立宪的政治和法律层面等方式予以解决。但是,其所依据的理性正当性最终仍要返归于个人权利的道德本质上。在弗里德里希看来,黑格尔的历史理性是立宪理性的敌人,他通过历史的辩证法来解决国家理性中的个人与整体的矛盾,使宪政主义变成空话,为极权主义开辟道路,在他的“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53页。论述中,可知这种立宪理性的最终破产。
弗里德里希将国家理性与宪政结合起来,他认为,立宪的国家理性是一种能更有效地指令政府依法行政的东西;并指出,麦迪逊要使人的尊严的核心体现在宪法中,那么,对于宪法秩序的存续而言,确保人的确信、信念、信仰至关重要,而确保人的生存和安全则成为同等重要的事情⑦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三联书店1997年,第110~111页。。弗里德里希主张,宪政是国家理性的归宿。他从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核心的政治观、以立宪教会国家为核心的政治观、以道德权利为核心的立宪主义政治观三方面考察了国家理性的变迁。这三个方面是平行进展与相互互动的,却潜伏着极权主义倾向。但无论如何,弗里德里希的审视却为我们深刻理解国家理性提供了深层基础⑧王 焱:《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第17页。。
二、国家理性的当代困境
一般说来,国家理性有这种原则,当国家安全和存续存在紧急情况时,国家的总体要求对于个人而言则成为当然的义务。但是,我们反思的问题是,国家这个有机体是否是绝对必须的呢?弗里德里希指出,我们必须深思将理性视为影响着事件未来过程的强硬力量这个问题。为此,他认为自由是关键价值,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正受到极权主义的严峻威胁⑨C.J.Friedoich.Constitutional Reason of State,p.9.。
梅尼克早年信仰第二帝国的统一理想和普鲁士传统,把国家政权当作是道德理想的体现,但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已经预感到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危害性,他察觉到国家理性中的“恶魔”性因素一旦失控,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梅尼克认为在史学史上,是浪漫主义摒弃了古典意义的理性,从而开辟了历史主义的道路⑩梅尼克:《德国的浩劫》,三联书店1991年,译序。。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梅尼克希望对强权与精神二者调和的向往,在1924年的《近代史中国家理性的观念》中,他设想着国家理性可以成为沟通政权和道德的桥梁。他提出,所谓国家理性是不是有此权力可以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经周详考察后,他主张:国家权力应该有一个基本的限度,即应该以保护公民的权利和福利为其限度。为此,他力图以道德理想来为政治权力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⑪梅尼克:《德国的浩劫》,译序。。
在极权主义者看来,个人权利对于国家理性已不再是无足轻重,维持现存的政治秩序成为“国家理性”的根据,个人则失去了存在的根基⑫弗里德里希:《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第5页。。弗里德里希以其自身体验到了国家理性两难困境:一方面,当国家的安全、存续等成为首要目标时,所有成员都应当为此尽责;另一方面,公民应当有其自身权利,若国家权力统辖着所有的个人意愿,个人就成为统治与利用的工具。如此漠视个人权利的国家理性,其正当性显然颇受怀疑。在弗氏看来,国家的理性根据有赖于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尊重,即便是在战争期间,也应如此。否则,自由宪政国家就不成其为自由宪政国家①王 焱:《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第5页。。
而马基雅维里则把政权的基础由神圣转到世俗,它向国家的内部去寻求国家的重心,把道德理想和价值判断完全驱逐出政治思维的领域之外。梅尼克在《德国的浩劫》中认为,希特勒纳粹党的法西斯专政是由于政权与精神文化、世界公民理想与民族国家利益互相冲突而未能一致的结果。梅尼克毕生追寻的是能在互相冲突着的思想之间找到调和,即在国家政权和个人价值、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历史传统和社会进步、德国精神和世界公民之间找寻最佳的平衡方案,执著致力于精神文化和政治权力之间健全而美好的平衡和统一②梅尼克:《德国的浩劫》,译序。。
然而,弗里德里希的论述则具有现实态度和价值关怀两种基调。他认为,国家的安全和存续是国家所要首先维护的前提,这个理由显然是国家理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国家的安全和存续是国家正当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这已经成为基本共识。但是,单纯的国家安全与存续绝对不是国家得以存在的最根本的正当理性。这关涉到国家的政治价值问题,对此,他认为,必须导入“立宪”机制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为此他提出,国家安全与存续的问题面对着立宪的秩序,面对着法治政府,当一种法律秩序的存续危在旦夕时,显然是不能为违背法律提供正当性辩护的③C.J.Friedrich.Constitutional Reason of State,p.14.。
由上可知,弗里德里希的论述是应令我们深思的。有学者认为,政治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权力建构的试金石,一个国家好与坏的判断标准应以权力的运用是否以正义为尺度;理性作为国家的正当性根基,体现着正义的国家理性才是真正的理性④王 焱:《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第6页。。而国家理性只在它是立宪的国家理性时才具有正当性,宪政能够有效地抗衡政治对人权的侵犯,但以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等理由侵犯人权时,这些理由则不具有理性的正当性,或至少这些理由自身不具有理性的正当性⑤王 焱:《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第7页。。宪政国家的终极理性是一个法律之下的普遍联盟。如果安全和生存问题能在宪政的架构之内得到解决,这个结论就是合乎逻辑的推论。它为未来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一种相对于一项绝对命令派生原则的制度形式。一旦自由正义的超验基础被否弃,这一点能否维持便成为另一个问题了⑥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第89页。。国家理性的当代困境值得我们深思。
三、国家义务对现代理性国家的构建
国家是什么?从宪政主义的国家理性而言,国家的有效性是有限的,是受到人权强有力拘束与制约的国家的权力体系⑦王 焱:《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第17页。。这些权力体系的合理性是由法律所规定的,立宪的理性使得国家安全和秩序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但是,国家本身并非目标,安全和存续本身亦非目的,惟有对这些总体目标确立宪法上的限制,才能避免极权主义的危险。所以这种宪政主义的国家理性,深含个人权利、道德权利、宗教使命的价值支撑。弗里德里希写道:“对于宪政秩序的安全和存续而言,保护最内在的自我的安全,要比保护任何边界和秘密更生死攸关。”⑧C.J.Friedoich.Constitutional Reason of State,p.119.。由此可见,个人权利、道德和信仰是立宪的国家理性之正当性之所在。
尽管欧克肖特崇尚的理性是技术理性,但他在考察了个人和个体性产生的过程后将人理解为受避免毁灭和维护自己的个性与所选择的追求的冲动支配的有机体。每个个人都有独立存在的自然权利:唯一的问题是他如何最大程度成功地追求他自己选择的行动方向,以及他与他那一类的“他人”的关系问题。这种对个体性以及最利于享有他的条件的追求,也反映在对适当的政府职能的理解和统治与被统治的合适样式中,二者都是中世纪遗产的嬗变⑨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欧克肖特认为,那些专心致志于探索个体性的暗示的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将个体性利益变为权利与义务的政府工具。为完成这个任务需要三个特征:首先,它必须是单一和至高无上的;其次,它必须是一个不受传统束缚的政府工具,必须是一个“主权”政府。第三,它必须是有力的——能维护秩序。在这个条件下,每一个臣民都确保了不受可能是他的伙伴,或政府本身强制的阻碍,不被公共压力所困扰,追求他选择的活动方向的权利。迁徙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个人和财产安全;选择自己的职业和处置自己劳动和货物的权利;等等,和在一切“法治”之上的,被一样应用于一切国民的法律统治的权利。这些适合于个体性的权利同样是每个国民的财产。每个权利意味着某种封建特权的废除⑩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第91~92页。。这些条件被看作是“公善”,这种政府是共同体的“公善”的建筑师和保卫者。政府的义务被理解为维护有利于个人利益的安排,这些安排就是将主体从共同忠诚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安排,它们构成了人类处境的一个条件①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第92页。。欧克肖特提出适合“大众人”愿望的政府样式即“大众”政府。“大众”政府实际上是代议制政府的一种变型。“法治是我们自由最大的单一条件”,法治政府是最适合自由社会的政府,法治是使用权力最经济的统治方法。而这一切均指向国家义务,均依赖国家义务的切实履行。欧克肖特认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是人民自己的事,但政府应当引导他们如何选择并实现理想的生活;同时,面对每个人自由选择信仰的问题,政府的职能只是在多元的信仰发生冲突时一视同仁地依法予以解决②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第145页。。这些规则、这个程序就是法律,国家义务、政府职能、公共权力应当法定化、程序化。
弗里德里希如此描述宪政论的人本主义精髓:人权从自然权利经由公民自由权向社会自由的发展被视为健全的政治秩序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权利可以通过宪法规定的条款来界定该政治社会所珍视的价值。因此,其具体而详细的阐述即使因社会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是这些阐释均包含共同的内核:承认人自身拥有其固有的尊严,并有权获得实现其生命潜能的机会。人权的着重点可以从自我保存转向自我表现进而至个人自我发展的各种形式。自主、参与以及创造普遍地受到重视,但是其排列顺序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不变的、绝对的。因此,在任由每个人独自追求其幸福、参政或通过与其同伴的自由联合为人的自我发展采取必要行动的程度方面,各政治社会是不同的③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第111页。。对欧克肖特来说,自由不是天赋的,也不是本有的,而是从历史经验中产生的。他认为,英国人享有的自由不是从政教分离中产生,也不是从法治、从议会制政府、从人身保护令中产生,而是从所有这些表示和代表的东西。也就是说,欧克肖特认为自由的根本即是分权,“它的自由的秘密就是它由众多组织在宪法范围内组成,从这部宪法最好的东西中产生出这个整体特有的分权。”④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第109页。而法治政府是最适合自由社会的政府,法治是使用权力最经济的统治方法,“法治是我们自由最大的单一条件。”⑤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第111页。
人权得到更加普遍的承认,这一事实是我们时代突出的特征之一⑥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第111页。。然而,所有现存国家都不能完全践行其对人权的承诺。这主要取决于是否能够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国际社会。它将会实现作为人类存在首要条件的自我保存这一基本权利,而且,免受战争威胁的自由将使政治关系变得缓和,并减少一向被作为侵犯人权以利于国家理性依据的紧急状态。为人权而战是没有终结的斗争,如果超验正义所要求对人的信念仍作为西方遗产的一部分而得到维护,它就会被推向前进⑦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第112页。。当公器私用,公共权力被用于追逐私利,不能有效保障人权时,则最终必然沦为一个外强中干的虚弱国家。弗里德里希将国家理性置于宪政的框架中加以审视,他认为,在国家之上还存在着绝对的价值,这一绝对价值就是立宪的国家理性。约翰·豪说:“宪政可以强国。”宪政的实施意味着依循现代社会的分殊化原则,通过对人权的宪法保障,通过构建国家义务体系,并予以法定化、程序化,且切实履行之,基于宪政基础上强大的理性国家方可得以构建。
既然“国家义务寄生于国家概念之中,国家义务与国家目的在同一时序上产生,国家义务与人权概念互为条件,国家义务论涵盖于国家正义论之中。”⑧蒋银华:《国家义务概念之萌芽与发端》,载《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7期,第30页。通过前文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国家义务之切实有效履行为构建现代理性国家奠立了正当性基础与可行性证立方案,国家义务论具有构建现代理性国家的型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