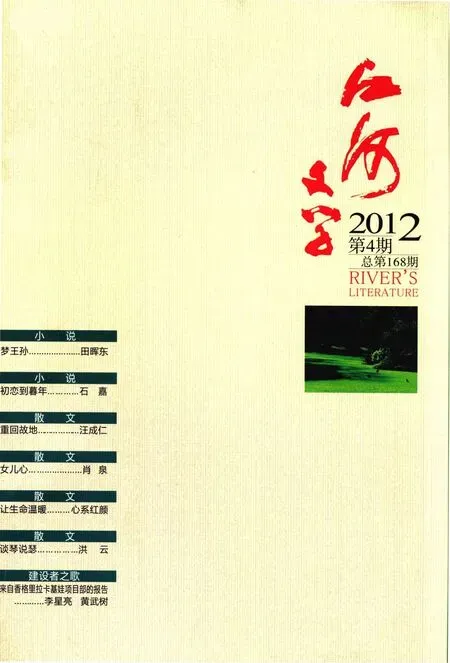重回故地
2012-03-16汪成仁
■汪成仁
丹江口是我的第二故乡。“花开红树乱莺啼”的季节,我来到了魂牵梦绕的丹江口水电站。弹指一挥就是四十年,想到第二天就要看到我曾参加过建设的大坝,晚上兴奋得彻夜难眠。去大坝的路上,因为大坝加高工程尚未竣工,我乘坐的轿车被拦在左岸副坝外面的一个岗哨,同伴劝我坝顶不要去了,但我说什么也要登上坝顶,大伙只好一起下车徒步前往,上副坝顶上的土石坡很陡没有台阶,我们就像“蜘蛛人”一样一点点往上攀爬,等爬到坝顶个个都已气喘吁吁。此时传来哐哐哐的机器声,走近一看,戴着印有“葛洲坝集团”安全帽的工人们头顶烈日,汗流浃背地操作着钻机,我们互相打招呼,一家人在此相见感到格外亲切。
站在坝顶高处,清风拂面、心旷神怡,湛蓝澄澈的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展现在眼前,二期工程大坝加高后,高程达176.6米,库容可达290亿立方米,不用多久丹江水将引入北京、天津,去滋润华北干旱的土地。到那时华北平原的人民喝上了引自汉江的玉液琼浆,将用怎样的方式来感谢汉江流域的父老乡亲和大坝的建设者呢。
沿着电站路徒步走到“憩息园”,只见江的南边是一座新建的汉江大桥,犹如一条彩虹飘在空中,江的北边就是巍巍大坝了,加高了的丹江口大坝在阳光映照下,显得更加雄伟壮观。见此情景,不由使我回忆起六十年代大坝浇筑的火热场面。当时大坝浇筑没有缆车,浇筑手段全靠门机和塔机,随着大坝的节节升高,这些数百吨重的庞然大物要随时拆除后重新安装,承担此项任务的是起重安装大队。起重安装大队有许多优秀工人,大多出身贫苦的农民家庭,没有读过书看不懂图纸,但都虚心好学,凭借实践和摸索,对这些大型起重机的拆装个个都是行家。为了加快大坝的浇筑进度,工人们在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攻克许多技术难关,采用许多土办法,把门塔机拆装时间缩短又缩短,为大坝浇筑争取了宝贵时间。这些优秀工人在丹江口电站建成后除少数留下外,大多数又风雨兼程地转战到葛洲坝。
在汤家沟,当年的皮带机早已不见踪影,但几根水泥立柱还挺立着,它记载了砂石厂普通女工们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从王家营到汤家沟有17条皮带机,全长1000余米,称作王汤皮带,你可千万别小看它的作用,它承担着大坝需要的全部砂石骨料的传送任务。值守皮带机运转的单位是砂石厂,多数是女工。默默无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在露天作业,那时还没有电子监控技术,工人们的一双眼睛犹如当今监控器的探头,目不转睛地监视着飞速运转的皮带,撒落在地上的料子就用铁锹一铲一铲铲回到皮带上。深夜上班实在太困时就靠在机旁听着隆隆的机器声打个盹。有人说皮带机工没技术“一推一拉、技术到家”,其实不然,责任可大啦,稍有闪失就会撕裂皮带,造成全系统停机瘫痪。女工张英值守237号皮带机时,有一次皮带跑偏,她使劲操作调整器,但走偏的皮带还是纠正不过来,她挺着大肚子用铁锹把柄死死挡住向外跑的皮带,幸亏有人及时来支援,避免了一场大的停机事故。工作辛苦不说,张英一个月34元的工资,上有老下有小,一年到头难沾油荤,整天饥肠辘辘,那时她身怀有孕,见到食堂炊事员挑来饭菜,闻到香喷喷的肉,可就是舍不得买,实在嘴馋了就掏2分钱向炊事员讨点肉汤拌在饭里。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女工们要比常人忍受更多的困苦,家里有嗷嗷待哺的孩子,可八小时上班栓得紧紧的一步也不能离开。下班回家急忙往嘴里扒几口饭又赶去班组“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大伙发言:“累不累想想红军过草地,苦不苦想想万恶的旧社会”。
在起重安装大队有一位钳工技术非常高超的葛师傅,浙江宁海人,乍看,他头发稀疏,面容清癯,身材瘦削,背还有点驼,饱经风霜的样子。1956年8月,他从上海第二技工学校毕业时,时逢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他响应国家号召到武汉重型机床厂当一名机修钳工。1959年8月,时任湖北省省长兼丹江口工程总指挥长的张体学,到武汉重型机床厂“钦点”6名技工支援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葛师傅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被分到丹江口水泥厂。凭着他扎实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技术,正要为水泥厂多生产水泥大显身手的时候,“四清”运动开始,一名学徒工借了一部扳车未还,这笔帐算到他头上,于是工资降一级,每月减少7元钱的收入,对于一个日子本来就过得紧巴巴的人来说尤如雪上加霜。提起葛师傅干工作,他老伴心疼的说:“我们老葛活了一辈子、干了两辈子的活,日子过得饭都吃不饱,干起活来却不要命”。有一次一台吊车行走机构的一个“盆齿”坏了,工地无配件,厂家也无货,也没有人敢接这个活,眼看吊车要停下来,一名机电专家请葛师傅“攻关”,机床用不上劲,葛师傅硬是用手工锉磨修好了这个报废的“盆齿”。吊车司机高兴地说真是铁杆磨成绣花针,要请葛师傅和他的学徒工吃顿饭,葛师傅抺抺额头上的汗水笑着说:“我是坏人,你不怕没有与我划清界线。”吊车司机说:“你苦活累活抢着干,我看不出你是坏人,你只管吃饱吃好。”他一上桌就连扒五碗饭。
葛师傅性格刚直,不趋炎附势,文革中又难逃厄运,几句批评领导的话被错误打成“现行反革命”,白天忙干活夜晚低着头挨批斗,大字报都挂在他的蚊帐上、脊背上,但他并不在乎这些,他说:“只要让我工作,怎么批斗都可以”。在检修保养东德6号门机的一年多时间里,机器里钻进钻出,他身上的工作服沾上的油污足足有一、二斤重。有人劝他:“人家对你如此不公平,你何苦不要命地干呢?”他还是那句话:“我是响应国家号召来丹江口的,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名老工人后来转战葛洲坝,并早已退休,他虽已七十六岁高龄,但精神矍铄,葛师傅说:“时常在梦中见到丹江口,我真的好想在有生之年再到丹江口看一眼。”葛师傅一生坎坷,但他对生活豁达乐观,他说“生活没有迈不过的槛,活着就要快乐生活每一天。”他有一只心爱的口琴,还是他早年上初中时买的,已陪伴他六十年,闲暇时吹几首歌曲荡气回肠,他最喜欢吹的歌曲是《歌唱祖国》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他最崇敬的人是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在“工人体育馆”晨练的人群中,碰巧遇见一位在葛洲坝退休的王工程师,探亲来丹江口,当年也曾参加丹江口水电站的建设,他的故事让我为之动容。他到丹江口的时间是1961年8月,从杭州电校毕业,那时他才19岁,风华正茂的年龄。当时工地上流传杭州来了一批年轻学生就指的是他们,一共有36人。男着西装,女穿裙子,一时间成为工地上议论的新鲜事。这些年轻人从美丽的西子湖畔来到这穷乡僻壤的山沟里,又遇三年自然灾害忍饥挨冻,不少人离开了丹江口。他从小家里贫穷,初中毕业后面临辍学,是政府送他读了一所食宿免费的水电学校,从此他将命运和祖国的江河紧紧联系在一起。艰苦环境磨炼了他的意志,1962年12月他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又担任团支部委员,由于勤奋和努力,很快他已能独立工作,成为队里的技术骨干。大坝施工进入高峰期时,1965年10月大队委派他和另外2人去新安江水电站接收、调运一台丰满门机,由于行程紧,途经杭州时仅在家里呆了二小时就向父母匆匆告别。门机运抵工地后电气部分由他技术总负责安装,由于完成任务出色受到工程局表扬,这一年他被评为工程局“五好职工”。王工程师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一天深夜一台门机因电气故障突然动不了,刚刚开仓的浇筑被迫停止,调度室点名要他去处理,他接到通知二话不说背起工具包从宿舍火速赶到现场,在排查故障时小腿被电气短路产生的电弧烧伤,脱下一层皮,他强忍着刺骨的疼痛,坚持排除故障,门机运转正常后才离开,到了医院被医生训斥了一顿:“烧得这么厉害,为什么不马上来看,得了破伤风还要不要命!”至今他小腿的皮肤仍留下大片的伤痕。人们常说叶落归根,王工程师本来可以回原籍杭州安度晚年,但他选择留在葛洲坝,他说:“水电工人四海为家,葛洲坝是我们亲手建起的美好家园,舍不得离开。”
在防渗墙的清基现场,为了抢在汛期到来之前浇筑,当时工程局组织各单位突击劳动,日夜三班清渣。工人们与洪水赛跑,为了尽快清完石渣,就尽量往吊罐内装,没想到吊罐提起突然坠落,夺走了一名工人的生命。
来到沿江大道江滩边,江面上依稀可见当年被洪水冲垮的几个桥墩,桥墩裸露在水面,仿佛在向人们诉说当年悬索施工大桥被冲垮惊心动魄的场景。1960年9月初汉江上游发生了28000立米每秒的特大洪水。洪水严重威胁正在施工的上下游围堰和河床坝体混凝土浇筑的安全,张体学省长亲自指挥这场抗洪抢险的战斗。9月6日那天,凶猛的洪水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疯狂地撞击着悬索大桥的桥墩,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声。5号和6号桥墩遭洪水冲击出现严重倾斜,桥面剧烈晃动,悬索施工大桥随时有垮塌的危险。此时此刻张体学省长紧急赶到现场,二话不说疾步上到悬索施工大桥上。大桥设计工程师看到张体学省长上到桥上,急忙上前阻拦道:“大桥随时会倒下,这里太危险,请你马上下桥。”张体学省长对他说:“你这个桥梁专家都不怕危险,难道我还怕什么危险?”大桥设计工程师说:“我上桥是为了抢拍一些资料,这是我的工作,我应该在桥上。您是一省之长,我要为您的安全负责。您要是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全省人民交代?”不管大桥设计工程师怎么劝,张体学就是不肯下桥。此时已是下午4点10分左右,滔滔洪水卷起高高的巨浪,凶猛地冲击着悬索施工大桥,发出了令人惊恐的轰鸣声。大桥设计工程师见桥面剧烈摇晃,感觉施工大桥就要倒掉。在这生死危急关头,来不及说什么了,就用尽全身的力气,猛地将张省长推到了桥头下。当工程师在桥上刚要转过身时,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悬索施工大桥被洪水冲垮了。工程师随着大桥一起倒在了洪水中,被无情的洪水卷走了。张体学省长被推下桥头后,被桥头下面的人接住了。当他还未站稳时,就看到大桥垮塌的惊魂一幕。随行的人员都说:“太险了,太险了!幸亏工程师用力一推,省长才从悬索桥上脱险。”在张体学省长的指挥下,十万建设者终于击退了猖狂的洪水,保住了上下游围堰,使河床坝体混凝土浇筑正常进行。
在沿江大道,只见梧桐、枫树挺立于道路两旁,江滩上鲜花竞放,争妍斗艳,杜鹃花、月季花、迎春花镶嵌在茵茵草坪和灌木之中,阵阵花香迎风飘来。江对岸的高山上大片的映山红,把刚刚发绿的山头涂得鲜红如火。人们不禁要问,丹江口的花儿为什么如此好看,想想当年筑坝的建设者们就会明白;丹江口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那是无数建设者的汗水浇灌的,那是为大坝建设献出生命的人用鲜血染红的。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丹江口是南水北调中线源头工程,葛洲坝集团承担了大坝加高工程,加高后的大坝将丹江口这座城市衬托得更加秀美多姿,如今的城区绿树成荫,道路宽敞,高楼鳞次栉比,几栋三十几层高的大厦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丹江大道当年的大礼堂已拆除新建成大型超市,展览馆已改建成工人体育馆,只是丹江电影院还是原来的样子。和过去相比如今电影院门庭冷落,曾记得63年3月放映电影《刘三姐》,电影院门口人头攒动,几个人争抢一张电影票,票被撕得粉碎。那个年代生活艰苦,一张电影票要五分钱,工人们省下饭钱看电影,可见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与渴望。今日的丹江口人文化娱乐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城郊的“净乐宫”游人如织,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古时的“净乐宫”原址在原均州老城,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至今有六百年历史。重建的“净乐宫”其建筑保持了历史原貌,大小石牌坊、御碑及石雕等八百多件文物是1967年丹江口水库蓄水前从原均州老城迁出保存下来的。迁移这些文物,当时起重安装大队立下了汗马功劳,石龟单件重近百吨,一共两件,没有大型移动吊车和平板拖车,采用土办法用托棍、绞车经水路、陆路慢慢地爬行、拖上船、拉上岸,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闻讯赶来目睹这一“石龟搬家”的壮观场面。
归期到了真叫人依依不舍,我默默地吟颂着艾青的著名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临行的这天早晨,我早早起床,拦住一辆人力三轮车,想坐着三轮车再好好看看丹江口城的面貌,于是我们从均州路口出发,往北走完丹江大道,再从沿江大道返回。边走边看大约二、三公里的路程走了半个多小时,我实在过意不去,掏出10元钱感谢这位三轮车工人,“不好意思耽误了你的时间”。可他执意不肯多收,只收了4元钱,他笑着对我说:“你老年纪大,大老远来这里不容易,我父亲也是当年大坝的建设者,我们都是丹江口人。”说罢他踩着三轮车离我而去,望着三轮车工人渐渐远去的背影,我不禁感叹!在我的记忆中,丹江口人淳朴勤劳善良,半个世纪过去了,丹江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丹江口人淳朴勤劳善良的本性一点都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