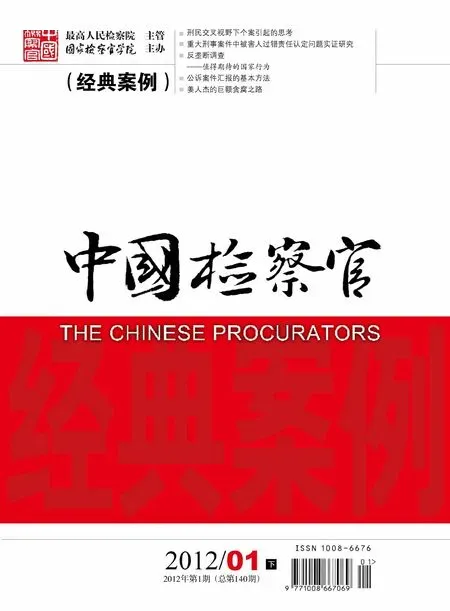间接故意杀人与过失致人死亡的界限分析
2012-01-29王剑波
文◎王剑波 王 浪
间接故意杀人与过失致人死亡的界限分析
文◎王剑波* 王 浪**
一、基本案情
2011年6月26日晚8时许,外来务工人员李某和张某下班时遇见同在本市打工的老乡赵某,赵某便邀请李某和张某到市郊兴隆酒店饮酒。在包间内,赵某提出自己有门路要与老乡李某和张某合伙挣钱,李某和张某便追问有什么门路挣钱,赵某称自己从厂子里搞出来了一批电缆,想请两位老乡帮忙找可靠的销售渠道。李某和张某听说后便不断追问电缆的存放地点,赵某坚持不说,李某和张某便对赵某进行谩骂和殴打。饭店服务人员看见后,便和饭店老板一起过来劝阻制止,赵某便乘机逃出了酒店,但李某和张某追出酒店并强行将赵某拉上白色松花江面包车带至市郊水库堤坝处。李某和张某将赵某拉下车,拳打脚踢继续逼问其电缆的存放地点,并威胁赵某如不交代就将其送交公安机关。赵某为摆脱李某和张某的追打,趁二人不注意跳入水库中,李某和张某便调转车头用车灯照射水面,并大声劝赵某上岸。十分钟后,李某和张某见赵某仍不肯返回岸堤,为消除赵某的顾虑促其上岸,二人遂开车离开堤坝。第二天,赵某的尸体在水库堤坝附近被发现,法医尸体检验报告证实,赵某全身体表无明显损伤,排除暴力致死,但肺水肿,结论为溺水死亡。
二、分歧意见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李某和张某的行为性质如何认定,意见分歧较大: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李某和张某对被害人赵某进行持续谩骂和殴打,迫使被害人跳水逃跑,进而使得被害人的生命安全处于危险状态之中,所以,二被告人负有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防止被害人被淹死这一危害后果发生的义务。然而,从客观上看,二被告人置被害人的安危于不顾,不履行因自己先前行为所产生的救助义务,独自驾车离开堤坝;从主观上看,二被告人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出现持的是一种放任的心理态度。因此,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不作为形式的(间接)故意杀人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李某和张某出于敲诈财物的心理不断威胁甚至殴打被害人赵某,致使被害人为摆脱纠缠不得已而跳入水库之中,二被告人随即采取措施对被害人实施了一定的劝阻行为,这表明二被告人对被害人死亡后果的发生是有所预见的。之后,二被告人又自以为是地认为被害人在其离开后就会返回岸上,因此独自驾车离去,最终却导致被害人溺水死亡结果的发生。由此可见,本案中二被告人既不是希望、也不是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被害人的死亡是违背二被告人意志的,即二被告人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持的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心态。因此,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李某和张某在酒店对被害人赵某进行殴打后,又将其强制带至水库堤坝继续殴打,逼问电缆的存放地点,并威胁如不交代就将其送交公安机关。可知,二被告人向被害人勒索财物的目的十分明显。在被害人为摆脱纠缠不得已而跳入水库之后,二被告人随即实施了一定的劝阻行为,并主动离开了现场,意欲让被害人消除顾虑,尽快脱离危险。由此可见,二被告人并没有杀人的故意,二被告人基于勒索财物的目的而纠缠、威胁甚至殴打被害人的行为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特征,应以敲诈勒索罪对二被告人定罪处罚。
第四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李某和张某强行将被害人赵某拉上白色松花江面包车,剥夺其人身自由并将其带至市郊水库堤坝处进行殴打的行为,完全符合非法拘禁罪的构成特征。之后,被害人为摆脱纠缠不得已而跳入水库之中,此时二被告人不仅没有进一步实施加害行为,还采取措施对被害人实施了一定的劝阻行为,十分钟后更是主动离去任由其自行选择出路。可见,二被告人对被害人溺水死亡的结果既不追求,也不放任,而是一种过失行为。由此,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罪。
第五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李某和张某无事生非,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随意谩骂和殴打被害人赵某,并强要被害人的财物。被害人为了摆脱二被告人的纠缠和殴打,不得已跳水逃跑,从而导致溺水而亡。由此可见,本案中二被告人的行为既侵犯了公共秩序,同时也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并造成了严重危害后果的发生,这完全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特征,应以寻衅滋事罪对二被告人定罪处罚。
三、评析意见
本文认为,被告人李某和张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进一步论证如下:
(一)被告人李某和张某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罪,是从1979年《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流氓罪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罪名,具体是指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根据现行《刑法》第293条的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的,成立本罪: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所谓“情节恶劣”,一般是指无事生非,打人取乐,并造成他人轻伤或其他不良后果的,等等。其“殴打”,既可以是向他人投掷石块、砖头等,也可以是拳脚相加。其二,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所谓情节恶劣,一般是指经常或者多次追逐、堵截他人的;追逐、拦截、辱骂老人、妇女、儿童的;以极端卑鄙下流的语言辱骂他人的;结伙追逐、拦截、辱骂他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等等。其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所谓情节严重的,一般指: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价值较大的公私财物的;经常或多次强拿硬要或多次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等等。其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由此可知,主观上的流氓动机与客观上的无事生非,是寻衅滋事罪的基本特征,也是寻衅滋事罪与其他犯罪的关键区别。[1]本案中,从客观方面来看,被告人李某和张某在公共场所持续谩骂和殴打被害人赵某的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行为特征;但是,从主观方面来看,被告人之所以殴打被害人,并非是出于流氓动机的无事生非,而是为了逼问其电缆的存放地点,并想进一步占为己有,这不符合衅滋事罪的主观特征。因此,综合本案分析,被告人李某和张某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二)被告人李某和张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
非法拘禁罪,是指故意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人李某和张某强行将被害人赵某拉上白色松花江面包车,并带至市郊水库堤坝处进行殴打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理由是:第一,非法拘禁罪是典型的继续犯,只要行为人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为目的,非法拘禁他人,不论时间长短,都成立既遂;但是,如果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时间过短,情节显著轻微,且没有造成多大危害后果的,一般不宜认定为本罪。本案中二被告人虽对被害人实施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但该行为时间不长,情节显著轻微,且没有造成多大的危害后果,这不宜认定为非法拘禁罪。第二,非法拘禁致人死亡,是非法拘禁罪的加重情节,一般是指在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过程中因过失造成被害人死亡或引起被害人自杀身亡。本案中二被告人在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的过程中,只是用拳脚对被害人进行了轻微的殴打,被害人的死亡并非被告人殴打所致,而是其在跳水逃跑过程中发生意外所致。可见,被害人的死亡与被告人实施的非法拘禁行为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此,综合本案分析,被告人李某和张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
(三)被告人李某和张某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40条对1997年《刑法》第274条的修正,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索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强索公私财物的行为。可见,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的,才构成犯罪。根据2000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一般认为,勒索的财物数额较大,情节严重,即使未遂也应定罪判刑;勒索数额不大,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宜认定为犯罪。本案中,被告人李某和张某在酒店对被害人赵某进行殴打后,又将其强制带至水库堤坝继续殴打,逼问电缆的存放地点,并威胁如不交代就将其送交公安机关。从表面上看,二被告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客观上也实施了威胁和要挟的行为,这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特征。但是,二被告人在被害人跳入水中之后就放弃了继续敲诈,而是主动离开了现场,以促使被害人尽快上岸。因此,二被告人的敲诈勒索行为情节显著轻微,不宜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四)被告人李某和张某的行为不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而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由于行为人的行为而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处于危险状态时,行为人负有采取有效措施排除危险或防止结果发生的特定义务。若行为人不履行这种义务以致发生危险或危害结果时,就是以不作为的形式实施的危害行为,行为人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从本案来看,二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殴打,迫使被害人跳水逃跑,进而使被害人的生命安全处于危险状态之中,二被告人因此有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防止被害人被淹死这一危害后果发生的义务。但是,二被告人置被害人的安危于不顾,不履行因自己先前行为产生的救助义务,而是想当然的认为被害人可以自己走上岸,以致被害人溺水而亡。因此,被害人的死亡与二被告人的不作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二被告人应当对被害人的死亡承担刑事责任。
那么,二被告人应对被害人的死亡负故意还是过失的刑事责任呢?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的相同之处在于:从主观上看,行为人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他人死亡的结果发生,并且都不是希望这种结果发生。从客观上看,都造成了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从主观上看,前者的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是持一种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态度,死亡结果的发生是违背行为人意志的,而且,行为人在预见到死亡结果可能发生的情况下,仍然实施其行为,是因为他认为凭借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如本人的能力、经验,当时的环境等)可以避免死亡结果的发生;后者的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是持一种放任的心理态度,死亡结果的发生并不违背行为人意志,而且,行为人在明知死亡结果可能发生的情况下,仍然实施其行为,是为了实现其他目的,行为人没有考虑凭借一定的主客观条件避免死亡结果的发生。从客观上看,前者的行为人通常会实施一些积极的行为以避免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后者的行为人则通常无此行为。[2]本案中,被告人李某和张某在被害人赵某跳水之后,未进一步实施加害行为,而是调转车头用车灯照射水面,劝被害人上岸。见被害人仍不肯返回时,二被告人为消除被害人的顾虑促其上岸,遂开车离开湖堤。由此可见,本案中二被告人既不是希望、也不是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被害人的死亡是违背二被告人意志的;同时,二被告人对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是有所预见的,但他们轻信被害人在其离开后就会返回岸上。所以,二被告人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持的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心态。
综上所述,被告人李某和张某的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的规定,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注释:
[1]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第812页。
[2]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72页。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100070]
**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检察院[57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