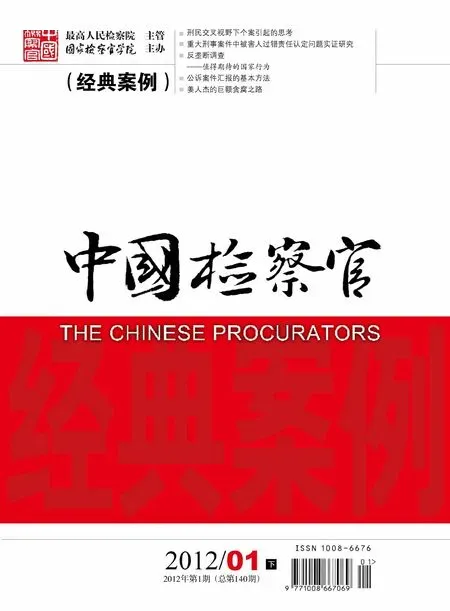论不作为犯罪之构成
2012-01-29温小燕
文◎温小燕
论不作为犯罪之构成
文◎温小燕*
本文案例启示:司机搭载受伤的人乘车,并在肇事者中途逃跑的情况下将伤者弃置路边,致其死亡的,由于在此期间排除了伤者被他人救助的可能性,因此构成法律上的先行行为,产生救助义务。同时,这种弃置行为之本质,可以等同于遗弃罪中的“遗弃”行为,应以遗弃罪来追究司机的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 2009年11月20日晚12时许,出租车驾驶员张某驾驶出租车至某市谢家村村口时,遇一中年男子王某扬招,张某即停车。王某将一大出血并已昏迷的老人搬上出租车后座,并告诉张某是自己撞伤了老人,要张某驱车前往市中心医院。当车行至市郊偏僻处,王某要求张某停车,自己要方便一下。张某停车后,王某下车逃逸。张某见情况不妙,便趁夜深无人之机,便将重伤老人弃置路边后驾车离去。次日,途经群众发现老人尸体并报案。经法医鉴定,该老人因失血过多导致休克而死亡。
一、分歧意见
对于这个案例,学界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即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与不构成犯罪。其各自的理由如下:
(一)构成故意杀人罪之理由
不作为犯罪的本质条件是负有作为义务以及具有作为的能力。在认为司机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学者看来,这二者都是满足的。
首先,司机张某负有救助老人的义务。认为司机张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学者,在张某具有作为义务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对于其义务之具体来源存在分歧,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作为义务来源于合同行为。司机张某与老人之间是一个承运合同的关系,《合同法》第301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旅客。因此,张某作为承运人,从老人上车的一刻开始,救助老人就成为其法律上必须承担的义务。
2.作为义务来源于先行行为。张某将受伤的老人载上车,使老人出于其所驾驶的车辆的空间范围之内,这一先行行为,无论其出于何种考虑,都已经与老人的生命安危之间建立了联系,因而就具有了救助老人的义务。
其次,司机张某具有救助老人的能力。法律不会强求不能履行义务的人去履行义务。但本案中,张某完全可以将老人送往医院,也可以拨打110求助或者呼叫出租车调度中心,这些方式都可能使老人免于死亡,也都没有超出司机的能力范围。
所以,司机张某有救助的义务,也有救助的能力,却没有实施救助,放任老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并最终导致其死亡,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二)不构成犯罪的理由
首先,司机张某不具有救助老人的义务。
1.张某并不因合同行为负有救助的义务。这里又分两种情况,一是王某带着受伤老人上车后,司机张某出于救死扶伤的品格,没有打计程表,他纯粹是为了见义勇为,这时他与受伤老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合同关系,因合同行为而产生的义务也就无从谈起了。二是司机张某出于小市民的考虑打了表,那么他与王某以及受伤老人之间就成立了一个运输合同,王某半途下车,终止了合同的旅行,置老人安危于不顾,此时合同已经终止,司机张某并没有继续履行的义务。况且《出租车运营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出租车驾驶员的义务有很多,譬如不能乱收费的义务、不能兜远路的义务等,但并没有规定遇到受伤的人一定要见义勇为、车上乘客受伤一定要送到医院。虽然《合同法》第301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旅客。但这限于旅客是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疾病、分娩、遇险等情况,而并不包括旅客上车之前就已经受伤,对上车前就已受伤的乘客必须实施救助早已超出了出租车驾驶员应有的义务范围。
2.张某并无先行行为引起之义务。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明文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将老人撞伤的是王某,王某的撞伤行为才是使之负有救助老人的义务的先行行为,而非司机张某的行为。救人的义务不能因为王某中途逃走而发生转移。张某拉载老人的行为,并不能导致其负有救助老人的义务。先行行为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并非所有在危害结果发生之前所实施的相关行为都是先行行为。司机张某如果将老人送往医院,我们可以称其为救死扶伤、见义勇为,其中止见义勇为的行为可能是不道德的,但认定其构成犯罪,而且是故意杀人罪这种极端严重的罪名,则难以让人接受。
其次,不能判定张某一定具有救助的能力。老人在上车时就已经大出血,即使司机张某继续将老人送往医院,也未必就能保证老人不因失血过多死亡。
二、不作为犯罪的基本法理分析
以上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各自都有其理论依据,但分歧也是很明显的。笔者认为,要正确认定张某行为的性质,就必须弄清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不作为犯罪、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以及作为的能力。
(一)不作为犯罪
不作为是相对于作为而言的。关于不作为概念的表述方式很多,有的表述成“不作为,就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行为的特定法律义务,能够履行而不履行的危害行为。”[1]有的表述成“不作为,是行为人消极不履行特定的应尽义务的行为。[2]而理论界通行的表述就是“应为能为而不为”。不作为犯罪可分为两类,一是真正不作为犯罪,即由刑法明文规定的只能由不作为构成的犯罪,譬如遗弃罪、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丢失枪支不报罪、拒不救援友邻部队罪等;二是不真正不作为犯罪,即行为人以不作为的形式实施的通常以作为形式实施的犯罪,大部分的作为犯罪都可能以不作为的形式构成。
不作为之所以能够成立犯罪,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不作为与作为具有内在的同质性,二者具有相当的危害性。对于真正不作为犯,刑法都规定了独立的罪名因此在认定时最重要的是判断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而不真正不作为犯罪,由于没有独立的罪名,其在刑法中的规定,都是以作为形式为模板,这就使得不作为犯罪的认定显得格外困难。对于不作为犯罪的认定,一般有其独特的判断方式,即先判断是否有作为的义务再判断是否有作为的能力。但这种判断方法也存在一定问题,特别是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罪,只判断是否具有作为的义务及作为的能力,有时并不能区分所构成的罪名。譬如,有救助的义务及能力但没有救助,并不能判断其到底是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还是不作为的故意伤害罪还是遗弃罪等等。所以,在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罪进行判断的时候,还要重点判断其与相对应的作为犯罪在行为上的同质性。“不作为的行为性只能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将不作为置于社会关系中考察才能予以说明,即其否定性的价值与“作为”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是等值的。”[3]
(二)不作为的义务来源
一般说来,作为义务有以下几种来源: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或者业务要求的义务、法律行为(譬如合同行为、自愿接受行为)引起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
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指由其它法律规定并由刑法加以认可的义务,这里的法律包括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等。如果只由其他法律规定,而未被刑法认可,则不能构成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此外,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还必须是具体的义务。
职务或者业务要求的义务是指一定的主体由于担任某项或者从事某种业务而依法被要求履行的一定作为义务。该类型的作为义务有的规定在法律法规中,也有的规定在具体行业的相关规章制度中。应当注意的是,行为人只有在具有职业或者业务身份的情况下,才具有相关的作为义务。
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是指法律行为如合同行为等,引起一个积极作为的义务。一般情况下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一定的义务,只产生违约的法律后果,并不会产生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只有在合同一方当事人因不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给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严重侵害的情况下,这一作为义务才能构成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
先行行为作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是由德国刑法学家斯鸠贝尔首倡的,1884年的德国判例首次确认了先行行为与法律、契约同样是作为义务的来源。[4]我国刑法界的通说认为先行行为只要足以产生某种危险,就可以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而不必要求先行行为具有违法的性质。
(三)行为与义务的对应
要成立不作为犯罪,必须具有特定的作为义务,但在违背了特定义务的前提下,构成何罪还需要具体分析。对于真正不作为犯罪,违背了特定的作为义务就构成相应的特定罪名,这种情况相对简单。比较复杂的是那些不真正不作为的犯罪,单纯通过其违反的义务,并不能直接判定构成何罪。譬如违反了救助义务的行为,由于刑法并没有“不救助罪”,所以,单单通过其违反了救助义务这一点,并不能判断其具体构成何罪。尤其不能在确定了行为人违反了义务的前提下,出现何种结果就定何种罪名。
对于不真正不作为犯罪,由于其行为必须与作为具有同质性,因此,在确定了行为人具有作为义务的前提下,还要对不作为行为本身的性质进行判断。真正不作为行为能够成立犯罪,是因为刑法设立了特定的罪名规定其构成犯罪。而不真正不作为行为能够成立本应由作为行为构成的犯罪,其实质在于其与作为行为质的相同性。同样是违反了救助的义务,如果这种不作为的性质等同于“杀人”,则成立故意杀人罪;如果等同于“伤害”,则构成故意伤害罪;如果等同于遗弃,则构成遗弃罪;如果其严重程度根本没达到刑法调整的范围,则不构成犯罪。所以,要判断不作为行为尤其是不真正不作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具体构成何种犯罪,应具体判断其是否与相应的作为行为具有同质性。
三、结合案例之具体判断
结合上述法理,本文案例中王某行为的具体性质可讨论如下:
1.张某是否负有作为的义务。不作为的义务来源有四种,如果王某具有义务,那他的义务来源只可能是其中的两种,即法律行为中的合同行为引起的义务或者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合同义务来源于《合同法》第301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旅客。但这限于旅客是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疾病、分娩、遇险等情况,而并不包括旅客上车之前就已经受伤,对上车前就已受伤的乘客必须实施救助已超出了出租车驾驶员应有的义务范围。而且,张某有无打表不能确定,也就不能肯定其行为属于合同行为还是助人为乐的行为。更何况,撞人的王某中途逃走,单方面终止了合同的履行,此时张某是否还有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也值得商榷。所以,认为张某的义务来源于合同行为并不恰当。笔者认为,张某的义务应该来源于先行行为,即将受伤老人拉上车的行为。因为张某一旦接受了受伤老人,并将其载于自己的出租车上,他就排他地支配了老人,排除了此期间老人被别人救助的可能性。张某将受伤昏迷的老人拉上车的先行行为,导致他具有将老人送去医院的义务,其没有将老人送到医院,就构成了对作为义务的违反。
2.张某构成何种罪名。如前所述,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罪的认定,必须满足不作为行为与其所对应的作为行为具有同质性。本案中,张某的不救助行为是否能够等同于故意杀人罪中的“杀”的行为呢?笔者看来,显然不能。如果造成老人大出血的人是张某,其故意的不救助行为等同于“杀”这似乎很能让人接受,但问题是,撞伤老人的是王某而不是张某,张某只是放弃救助,实质上等同于“抛弃”、“遗弃”的行为,而绝对无法等同于“杀”的行为,所以不能成立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正如日本学者指出:“仅仅为结果的发生提供一个因果契机而已的行为并不足以构成杀人罪的先行行为作为义务根据,这种场合只能构成遗弃罪。”[5]张某的行为类似于遗弃有赡养抚养关系的人而导致其死亡的行为,只不过赡养抚养义务属于法律的明文规定的义务,而这里的救助义务是由于先行行为而引起的义务。同时以遗弃罪来认定,也避免了定故意杀人罪明显过重而不认定为犯罪又明显放纵的不足,符合国民的法感情。
综上,张某将老人载于自己的出租车上的行为,排除了在此期间老人被他人救助的可能性,属于法律上所谓的先行行为,因而产生救助老人的义务。张某具有救助义务却将老人弃置路边,属于对作为义务的违反。但由于老人之危险状态并非由张某所造成,所以他的这种弃置行为之本质,并不能等同于故意杀人罪中“杀”的行为,不能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但这种弃置行为完全可以等同于遗弃罪中的“遗弃”行为,所以,张某的行为应当构成遗弃罪。
注释:
[1]刘宪权主编:《刑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2]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3]刘志伟主编:《刑法学新动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4][日]堀内捷三:《不作为犯论》,青林书院新社1978年版,第11页。
[5][日]藤木英雄:《刑法》,弘文堂 1978 年版,第201页。[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Ⅰ,有斐阁1972年版,第158页。
*华东政法大学[20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