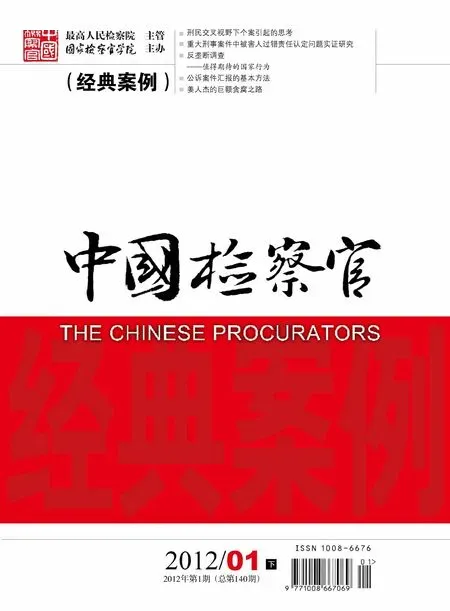刑民交叉视野下个案引起的思考
2012-01-29戴李强
文◎戴李强
刑民交叉视野下个案引起的思考
文◎戴李强*
本文案例启示:占有作为财产犯罪中的基本概念,其成立与否对认定案件性质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规范目的的不同,刑法占有与民法占有是有区别的,两者在占有的成立及种类上都有所不同,把握刑法占有与民法占有之间的区别,是实践中正确认定案件性质的前提。
[基本案情]2011年6月22日,黄某来到一家大型超市自动寄存柜旁,见钟某正在存包,暗中记下其所存包的特征。当钟某进入超市购物后,黄某利用一张作废的密码条,找到超市自助寄存柜值班保安张某,谎称其自助寄存柜打不开,要求张某将钟某寄存包的柜门打开。黄某准确说出柜内存放物品的种类和特征,张某打开自助寄存柜柜门进行物品核对,发现与黄某所叙一致,于是离开。黄某遂将钟某存放在该柜内的一个男式单肩挎包及包内物品、人民币6700元拿走。经鉴定,黄某取走物品共计价值人民币1.7万余元。[1]
根据行为人是否取得财产,一般可以将财产犯罪分为取得罪与毁弃罪。就本案黄某的行为来说,构成取得型财产犯罪不容质疑,问题的关键是黄某的行为到底是构成盗窃罪还是构成诈骗罪?赞成构成盗窃罪的认为,本案中超市与被害人钟某之间没有形成保管合同法律关系,超市及其保安人员履行的只是对超市柜台的整体管理,黄某侵犯的是寄存人钟某对柜内钱物的财产权利,因而黄某实施的是通过窃取的方式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应成立盗窃罪。赞成构成诈骗罪的认为,本案中,从钟某将财物寄存到超市的寄存柜内开始,虽然钟某是财物的所有权人,但是超市已经享有对寄存柜内财物的占有权,成立刑法上的占有,因而,黄某的行为不是对钟某财产权的侵犯而是对超市享有的占有权的侵犯,存在诈骗罪要求的“交付行为”,因而本案黄某应该成立诈骗罪。
笔者认为,就这一案件来说,要得出合理的结论,有以下几个问题需先予解决:其一,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限究竟该如何界定?其二,刑法意义上的占有与民法意义上的占有有何区别?其三,超市是否成立对寄存柜内财物的事实支配?
一、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限
通常来说,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占有的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多数情形下,盗窃罪中的犯罪人都是采用不为被害人知晓的方式取得对他人财物的占有,犯罪人取得财物的占有或者所有是违背被害人意志的。而与此不同的是,诈骗罪是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使被害人在陷入错误之后“自愿”作出对财产的处分从而取得财产,这种取得行为通常是不违背被害人意愿的。因而,一般情况下,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限比较明显。但是,当行为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采取诈骗的方式窃取他人财物的时候,到底是构成盗窃罪还是诈骗罪则往往难以认定。
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学界通常列举三个案例予以说明。一、掉包案。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柜台选购珍贵烟酒期间乘服务员不注意,将真烟酒换成自己携带的假烟酒并带走的行为。二、电话案。A打电话给在家休息的老人B:“你的女儿在前面马路上出车祸了,你赶快去。”B连门都没有锁就急忙赶到马路边,A趁机取走了B家的财物。三、西服案。洗衣店经理A发现B家的走廊上晾着西服,便欺骗本店的临时工C说:“B要洗西服,但是没有时间送来,你到B家去将走廊上晾的衣服取来。”C信以为真,将西服取来交给A,A将西服据为己有。
就以上三例来说,行为人的行为既有诈骗行为也有窃取的行为,认定行为人具体构成什么犯罪关键是把握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标准。[2]我们认为,诈骗罪通常表现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被害人 “自愿”交付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损失。与盗窃罪的客观行为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存在处分行为或者说交付行为。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正确地指出:“交付行为的有无,划定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限。被害人交付财物时,是诈骗罪而不是盗窃罪……”。[3]在以上三个案件中,掉包案和电话案中,被害人虽然都陷入了认识错误,但是,并没有基于认识错误而作出财产处分行为,因而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盗窃而不是诈骗。在西服案中,表面上有洗衣店临时工基于错误认识而作出的交付行为,但是,C并没有处分财产的权限和地位,案件中C仅仅是行为人实行犯罪的工具而已,行为人仍成立盗窃罪。在得出诈骗罪与盗窃罪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存在处分行为或者说交付行为之后,对前文列举案例的评析,关键就是看超市是否构成对财物的占有以及超市保安是否有处分财产的权限和地位?
二、刑法占有与民法占有的区别
就财产犯罪的具体认定来说,占有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占有是财产犯罪中的基本概念。通常认为,盗窃、诈骗、抢劫等罪在本质上都表现为两个行为过程:首先是破坏他人对财物的占有关系,其次是建立新的占有关系。用何种手段破坏原财物的占有关系往往揭示行为的犯罪性质,而是否建立新的财物占有关系通常反映行为的既遂与未遂。就破坏他人对财物的占有关系而言,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原财物占有关系的状态,主要解决财物到底有无占有以及由谁占有的问题;二是破坏原财物占有关系的手段。[4]一般情况下,通过破坏原财物关系状态的手段就能确定犯罪的性质,然而,当行为手段不典型或者多种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往往需要进一步分析行为前原财物的占有关系的状态。
占有作为一个法律概念首先来源于民法,其根源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现行各国民法上所确立的占有制度基本上是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相融合的产物。只是有的将占有认定为一种事实,而有的将占有认定为一种权利,从而形成不同的法律制度和条文规定。通常认为,日本民法的一大特色是将占有规定为一项权利,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民法更倾向于将占有规定为一种事实。如王利明教授就认为,占有是指占有人对物的事实上的支配和控制。这一对占有法律定位的区别在分析具体问题的时候不容忽视。[5]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法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民法上的占有,已经突破了事实占有的界限,实践中行为人更多地通过观念占有的方式来行使自己的占有。所谓的观念占有,是指财物虽然处于行为人物理控制的范围之外,但是根据社会上一般人的观点和习惯,可以推知由行为人支配时,该财物即属于行为人占有。如根据自然属性可以预料到会回到自己支配范围内的财物,例如饲养的家禽;从财物的性质、放置的区域等能够推定所有者,如放置在自己住宅很近的公用车道上的自行车;财物放在难以被别人发现而自己知道的场所,如行为人埋藏在野外的财物;由于战争等特殊事由使财物的占有状态发生变更等。[6]
就本文案例的解析而言,在此讨论民法上的占有,主旨还是在于更加清晰地认定刑法上的占有,并更好地对两者进行区分。而在讨论刑法占有与民法占有的关系之前,必须明确我国民法理论上对占有的定性。如果我国民法将占有规定为一项权利,那么,很有可能像日本那样,两者之间存在不小区别;相反,如果我国民法是将占有规定为一种事实,那么两者之间的区别应该相对较小。就目前的主流观点来说,我国民法学者并不主张将占有规定为一项权利,07年颁布的《物权法》已将占有规定为一项特殊的制度,即认为占有就是一种事实。因而,我们认为,就我国而言,刑法上的占有概念与民法上的占有概念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两者在占有主体、占有客体、占有内容的理解上是大体一致的。
当然,作为不同部门法语境下的概念,两者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两者在规制占有的目的上有区别。就民法来说,规定占有制度主要在于确定占有人的地位并以此明确占有人与他人的权利义务界限,而就刑法来说,其规定占有的目的主要在于确认财产被现实控制支配的事实,以达到维护财产秩序的目的。正是因为两者目的的不同,从而导致两者在占有的种类上有着不小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间接占有、占有改定、占有继承等场合。在这些场合下,刑法基于维护财产秩序的目的,主要对直接占有人的占有进行保护,而不去寻求保护法律上的真正权利人的利益,这显然不同于民法对占有的保护。
三、本案中超市已经构成刑法上的占有
(一)从刑法占有的定义来看,超市已经构成了刑法上的占有
德国刑法学者威尔策尔认为,占有的概念应该由三个要素组成:(1)物理的现实的要素,即事实上的支配;(2)规范的、社会的要素,即应该根据社会生活的原则判断事实的支配;(3)精神的要素,即占有的意思。前两种要素被称为客观的要素,后一种要素被称为主观的要素。[7]需要说明的是,就构成刑法上的占有而言,主观的要素在要求上通常比民法上的占有要求低,占有支配财物的意思并不限于对特定财物的具体的、特定的支配意思。“只要具有以将存在于自己支配的场所内的一般财物为对象的包括的、抽象的意思,通常就够了。”[8]就本案来说,从钟某将财物存入寄存柜内开始,财物已经处于超市器械的控制范围内,客观上超市已经对财物成立事实上的占有,同时,从占有意思上来说,超市从设立寄存柜开始,也明知在他人将财物存入寄存柜期间,财物丢损、灭失的责任应在超市,因而,在财物被寄存在超市期间,超市对财物有占有的意思。同时,由于超市顾客的不固定性,超市对柜内财物的占有可能只是抽象的、概括的占有,但这已经达到了刑法占有对占有意思的要求,可以构成占有。那种认为刑法上的占有意思应该是具体、特定的观点,通过否认具体、特定的占有意思的存在,而否认超市占有的成立,显然是不合理的。
(二)从刑法占有与民法占有的区别来看,超市成立对财物的占有
正如前文所论述,刑法占有与民法占有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两者追求的目的不同。民法上的占有制度主要在于确定占有人的地位并以此明确占有人与他人的权利义务界限;而刑法上的占有,只在于确认财产被现实控制支配的事实,以维护财产秩序。就本案来说,诚然,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认为,当顾客将财物存入寄存柜后,在民法上我们还是倾向于认定寄存人是财物的占有人,甚至是直接占有人,这是基于民法的主旨在于确认占有人地位以及其权利义务而作出的解释。然而,从刑法的角度来说,得出的结论并不相同。在这种情形下,刑法更加注重对超市直接占有行为的保护,对于寄存人基于所有权而享有的间接占有此时已经被刑法舍弃。正是基于刑法主要在于确认财产被现实控制的事实,我们认为本案中超市已经构成了对寄存柜内财物的占有。
(三)从社会的一般观念来说,本案中超市已经构成刑法上的占有
对法律的解释离不开社会民众的一般法情感,对刑法上占有概念的界定也是如此。通常来说,我们之所以将财物寄存在超市的寄存柜内,就是因为这样财物可以更加安全,退一步来说,如果在寄存期间真的丢失的话,超市会作出相应的赔偿。顺应这一思路,如果在顾客寄存财物后,超市连刑法上占有这种最低要求的职责都没有的话,那么顾客对在超市寄存期间丢失的财物又有怎样的依据来要求超市进行赔偿?就本案来说,如果我们认为超市不构成对寄存柜内财物的占有,那么在案发后,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向超市索赔?否定超市刑法上占有的成立,导致的后果将是作为顾客的不特定大众的财产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显然是与一般民众的法情感是相违背的。
在肯定了本案中超市对寄存财物的占有后,我们不难发现,整个的案情大致可以提炼为:黄某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进行欺骗——超市保安张某陷入认识错误——张某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黄某取得财物——超市因赔偿他人财物而遭受损失。结合前文关于诈骗罪与盗窃罪区别的论述,可以得出本案中黄某的行为应该构成诈骗罪。
注释:
[1]金林、罗永鑫:《欺骗超市保安开启寄存柜取走他人财物如何定性》,载《检察日报》2011年11月15日第3版。
[2]参见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12页。
[3]同上,第 12 页。
[4]参见沈志民:《论刑法上的占有及其认定》,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3期。
[5]同上。
[6]参见童伟华:《论日本刑法中的占有》,载《太平洋学报》2007年第1期。
[7]转引自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1页。
[8][日]大塚仁:《刑法概说》(各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页。
*安徽省安庆市人民检察院[24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