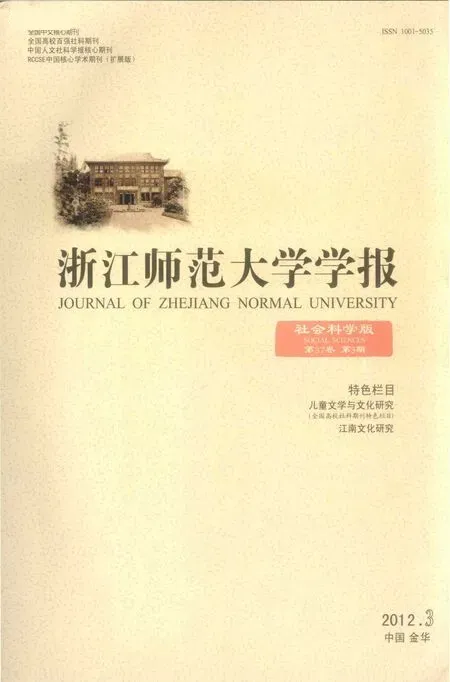对“语言学概论”课程性质与任务的思考
2012-01-29陈青松张先亮
陈青松, 张先亮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一、“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性质与现状
“语言学概论”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一般认为是语言学理论的入门课,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普通语言学概述。该课程介绍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从共性角度讲述语言的性质、结构、功能、运用、变异以及发展演变规律,[1]“是从理论上对全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进行研究的学问”。[2]“语言学概论”从1980年起正式列入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计划。[3]据国家教委社科司[1992110]号文件,“语言学概论”被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十门专业必修课之一。[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3745-92《学科分类与代码》,语言学(代码为740)与文学(代码为750)是并列的一级学科,作为概述普通语言学的“语言学概论”课程,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5]
那么,“语言学概论”的教学情况怎么样呢?根据该课程教师和研究者的印象式判断,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把“语言学概论”课程视为畏途,教师不知怎样教好,学生也不知如何学好。[6]在“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中,厌学厌教情绪普遍存在,[7]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对教学效果和教学评价的定量化分析可能更有说服力。外语界已有多位学者对语言理论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评价进行了较多的调查,如潘之欣、[8]吴格奇、[9]黄腾翔[10]等。根据潘之欣的调查,学生很喜欢语言学理论课程者为0,比较喜欢者为13.3%,感觉一般者为66.7%,不太喜欢者为13.3%,不喜欢者为6.7%。专门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概论”课程态度的调查在文献中非常少,罗耀华、柳春燕曾有意识地调查了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动机、学习目的、学习兴趣等方面的情况,结果显示:55%认为该课程较难,15%认为教材选编的内容过时、枯燥,30%认为难度适当;56%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学分,32%是为了考研,12%是由于对语言学感兴趣。[11]还有少量关于学生语言能力和语言学素养的调查,如何东萍进行了“中文专业语言类课教学与大学生语言能力培养研究”;[12]郜峰对部分中小学语文教师和部分普通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应届毕业生进行调查,发现他们的语言学理论修养普遍欠缺。[13]课程的教学效果也令人担忧,学生及格率低,对课程评价整体来讲不高。总而言之,课程现状与课程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至于如何改进“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学者和教师的尝试与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准确定位课程,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课程的“专业性”、“基础性”和“理论性”特点;[5,13]2.革新教学内容,增加新的语言学理论和语言研究方法的介绍;[7,14]3.改进教学理念及教学方法和手段,如运用开展讨论、实践调查等方式调动学生,使其主动参与课程,运用多媒体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一步抓住学生,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15-16]4.处理好“语言学概论”课程和其他相关课程(特别是“现代汉语”课)的关系。[7]
造成“语言学概论”课程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环境、教研思潮、师生的心理期待、课堂环境、师资和生源新情况等等,都可能对课程提出新的挑战。其中,教师和学生对课程性质和任务的认识偏差是造成课程教学问题的根本原因。
虽然我们把“基础理论课”的名目很顺口地挂在了“语言学概论”课程身上,但在实际教学中却往往会有所动摇而不能贯彻到底。如岑运强提出“教材应该努力作到‘四个面向’:面向学校、面向社会、面向应用、面向未来”,[4]虽说得很在理,但却已有轻微的实用主义倾向:面向这个那个,自然就会因这个那个而改变,改变既可能进步,也可能迷失;而许晋、李树新更是明确倡议要把“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为“培养新世纪高素质的以应用为主、略带研究特点的文科人才奠定基础”的课程;[17]黄育红认为“重视和加强语言学概论的实践教学对于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18]林秋茗认为“语言学教学应增强趣味性和实用性”;[19]梁驰华虽然承认“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普通语言学性质,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却提倡课程对语言学习起指导作用,并主张联系现实的语文生活,强化课程的语言教学指导作用。[20]
高举“理论性”大旗的学者也不在少数。曾毅平提出“应当进一步确立其专业基础理论课地位,注重培养学生语言理论方面的专业素养,发展学生认识和研究语言现象的能力”;[7]郜峰认为“语言学概论”课程应以理论性和研究性为基本属性,并把中学语文教师和中文本科毕业生语言理论素养的不足归因于相关高校教师对“语言学概论”课程性质的偏离,认为他们忽视了课程的“研究性”和“理论性”,侧重“应用性”方面的教学,停留在带着学生对语言现象作表面的浅层次的分析,对教材提到的学术理论也只作一般的介绍说明;[13]张先亮明确提出“语言学概论属于普通语言学,重在理论”;[5]聂志平认为“把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思维能力、语言教学能力,甚至论文写作能力,都压在语言学概论身上,无疑是没有认清语言学概论的课程性质,夸大了该课程的功能”,“这种认识,是很不利于语言学概论教学的”。[1]
因此,有必要对“语言学概论”课程的目标任务进行梳理,廓清相关的认识偏差。
二、课程的任务:传授两种基础知识,培养两种基本能力
作为语言学的入门课程,教育部公布的“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大纲规定:该课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观阐明人类语言的性质、结构、起源及发展等基本理论,通过教学,要求学生初步树立科学的语言观,掌握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具备运用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分析语言现象的能力。[5]但是,不同的教材和学者对于“语言学概论”课程的任务却有不同的认识和表述,侧重点也有一些差异。谢奇勇分两个角度进行了很好的概述。[14]我们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把该课程的目标和任务简要概括为:传授两种基本知识,培养两种基本能力。
“两种基本知识”是指“基本语言知识”和“基本语言学知识”。基本语言知识是指“人类语言的一些基本情况”、“人类语言的一些基本类型和关系”、“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些基本规律”、“人类语言一些基本结构的描述”、“语言的运用”等,[14]其中关于学习者母语的知识只是对已有知识的显性化。基本语言学知识是指“语言学的价值和意义”、“语言学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语言学的历史和主要理论流派”等。[14]这些语言学知识是构建人类语言知识的“元语言”,既包括我们用来解释语言规律的视角、概念、话语等元语言,又包括我们赖以分析并发现语言规律和言说语言规律的“方法论元语言”。[21]马学良、瞿霭堂就认为普通语言学是“传播语言学科的一般知识,也是语言科学研究和相关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基础”。[22]“语言知识”和“语言学知识”在更高层面上又是一致的,因为我们以为是“事实”的,其实已经是理论;我们对自己事物的“所知”,其实就是我们对它们的解释;我们的所有观察出来和被描述的“语言知识”,其实都是有意无意在特定语言学知识的指导下取得的,甚至本身就是语言学理论的构成部分。在“语言学概论”课程中,“语言学知识”和“语言知识”都不可偏废。
“两种基本能力”是指基本的“语言研究能力”和“语言鉴赏和运用能力”。这两种能力是学生通过学习基本的语言知识和基本的语言学知识以后实现的,是两种有关联的“能力”。语言研究能力是指能够对一些语言理论观点进行分析推导,能够对某种或某些语言的语言材料作一些基本的分析和归纳概括,如对语言要素、结构、功能的分析等。语言鉴赏和运用能力是指能够依据已学的语言学知识和已然明晰的语言知识,对言语样品进行评价,能够认识到言语样本在音律语气、遣词造句、合适得体、信息传达等方面的优点和缺点;或者能够有意识地运用合适的语言进行交际,更好地达到交际目的。
两种知识的传授和两种能力的培养都是“语言学概论”课程的任务,任何偏废都会导致课程的欠缺。李树新曾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说明什么是语言学概论。他说:如果将语言看作一座结构复杂的大厦,“语言学概论”就相当于为了解这座大厦的结构而举办的一个展览,它根据现在的研究成果将“语言大厦”的结构介绍和展示给大家,为大家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础。[23]显然,他对“语言学概论”课程的定位过于强调“语言知识”了。郜峰则把“提高学生的语言学理论修养水平”、“语言素质和语言能力”及“学术论文写作水平”作为课程的任务。[13]他过于强调语言研究和语言运用的能力,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刘云的看法相对谨慎,他认为“语言学概论”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了解语言学科的前沿成就和发展前景,具有较强的语言分析鉴赏能力,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24]但他却没有把能力的培养特别地突出出来。
三、对课程任务的认识偏差及产生偏差的原因
从教材和教学实际看,对该课程的性质和任务一直都存在这样那样的认识偏差和实践偏差,我们下面分四个方面来分析这些偏差。
(一)语言学知识方面的问题
在传授语言学知识方面,目前的教学实践特别是在教材内容上主要表现为五种偏差:1.过分强调语言学知识。过多或者过深地介绍语言理论体系和理论术语、概念,把语言学概论课程变成纯粹的理论游戏,甲派乙派张三说李四说,眼花缭乱刀来剑往。这种偏差在外语界的语言理论教材中多有体现;2.语言学知识单一化。1950-1980年代的语言学概论教材是在苏联教学大纲、苏联国定教本《语言学概论》(契科巴瓦编)和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的影响下编成的,这些教材套用“苏联模式”的倾向明显,着重介绍、解释、阐述的是斯大林语言学说,只是在语法、语音领域里,部分教材在结合汉语特点讨论相关理论问题时较隐蔽地接受了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25-26]这样的学术和教学传统影响深远:当代的“语言学概论”课程或者把语言学当语言哲学,在语言的符号性质、社会属性、有无阶级性等玄之又玄的问题上纠缠太多;或者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语言学之间划等号,大多数教材都程度不等地以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为主;3.语言学知识未能紧跟学术前沿。作为一门领先科学,语言学日新月异,教材里介绍的基本语言学理论必须是经过了时间考验的,但这并不能成为几十年不变或少变的遁词;4.语言研究方法方面的知识太少。只讲“鱼”而不授“渔”,忽视语言学知识的逻辑来源和历史过程;5.与相关课程特别是“现代汉语”的知识重复。现代汉语也是一门重要的语言学课程,论述现代汉语的语言学知识和论述其他语言的语言学知识肯定有相同的地方,两门课程内容重复是不可避免的,[5]但合理分工才能正确定位,这点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发表过看法;6.大幅度弱化语言学知识。大部分教材在“介绍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基本理论”内容的编排上比较弱,[4]这种倾向导致学生的理论素养得不到应有的培育。
(二)语言知识方面的问题
整体来看,语言学概论课程对语言知识的介绍较为零散且覆盖面较窄。在传授语言知识方面的偏差主要表现为:1.语种知识太少。语言学概论教师不可能对所有的人类语言都有了解,学生也不太可能学到很多的外族语言,但老师可以通过间接介绍来让学生了解语言的各种情况。一门课程学下来,学生如对人类语言的整体情况仍然缺乏基本的了解,这至少是人文素质下降的表现。部分教材对此已有所改进,如如邢福义、吴振国主编的《语言学概论》,教材后边有“世界语言谱系分类”附录;[27]李宇明主编的《语言学概论》,教材后边有“世界语言谱系分类表”、“中国语言的基本状况(民族语言)”和“中国语言的基本状况(汉语方言)”三个附录,对与课程相关的语种、方言知识进行了基本的简要介绍;[28]2.论证用的语言材料用例太单一。一般的语言学概论教材和课堂,用来说明相关概念和理论的语料多是汉语和英语的例子,几个外语用例在多部教材中反复出现,这虽有利于学生理解相关的理论观点,但却极大地降低了语言学理论的“普通”性质;3.因涉及语种材料少,用例语种来源单一,导致语言规律的概括有缺陷;4.对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等有效而方便的语言材料的利用还有待加强。
(三)语言研究能力方面的问题
主要表现为:1.只注意传授知识而不是有意识地引导和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这在教学方法手段的采用上尤为突出;2.条块分割,只注意呈现知识,忽视对语言学理论的内在逻辑性进行分析;3.重语法结构的分析,对语言其他部分的分析显得不够;4.强调语言材料的验证性分析,忽视对语言理论的分析推导。
(四)语言运用和鉴赏能力方面的问题
主要表现为:1.把“语言学”当作“学语言”或“学语言运用”,一切为提高语言学习效果和提高语言运用水平服务,用直接的应用目的来指导课程教学,忽视课程的基础性、理论性特点;2.各种与语言运用有关的介绍充斥教材和课堂,冲淡了主体内容;3.只重语言理论介绍,完全放弃语言运用知识(语用学)的介绍和运用能力的培育,这是另外一个极端。
上述问题已经引起了语言学概论教师和学者的注意,他们尝试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案,有的方案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认识上的偏差和实践上的偏废之所以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1.可能和我们的文化历史和学术传统有关。“经世致用”、“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语言的抽象理论的构建在国内学人的头脑中一直不占据主要地位,多数人在对异族语言的认识上更认为是堆砌材料而无助于学术,因此在语言学概论课程中便出现了强调实用、强调汉语语料的偏差;2.可能和语言学概论的教学历史有关。语言学知识的单一与建国初期政治、学术“一边倒”向苏联有关,这种学术惯性会使历史得以延续;3.和课程师资结构及知识结构有关。“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教师(至少早期的教师)大都由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的教师兼任或转任,他们对汉语理论和知识相对熟悉,用汉语用例分析语言理论驾轻就熟,但语言学的“普遍”性自然受到磨损。与此相对的是外语学院的“语言学理论”课程,因为该课程的教师多来自外语教学第一线,因此多吸收外国语言理论,多用外语的例子,反而很少吸收汉语研究的成果和例子,自然降低了课程的可懂度;4.和新时期新思潮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有关。实用主义思想的泛滥让学生对学习枯燥的基础理论知识不感兴趣,知识大爆炸和浅表化的学习潮流导致学生不愿意深入钻研理论,加上各个高校对基础性课程的重视也不够,因此,语言学概论这样不具备直接应用性的课程便饱受冷落。为了适应形势,很多教师只好硬是把理论课上成了实践课,把很多无关直接应用的纯理论的东西也硬拉上了应用的大船;5.和课程的学生构成有关。扩招后学生的整体素质比以前有所下降,对理论知识缺乏足够的理解能力;6.和教学方法及手段的采用有关。传统的“讲义+粉笔”与现代的“课件+鼠标”各有利弊,[1,5]刻意地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教师“架构”理论知识的魅力。因为存在各种影响课程目的和任务达成的因素,使得“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学生的学习状态和课程评价都不理想,这已经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担忧。
四、实现课程任务的原则
为了完成传授两种基本知识和培养两种基本能力的教学任务,在具体教学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语言学是科学,“语言学概论”课程内容虽然间接或部分地与实用有关,但该课程的本质目的是认识人自身。语言学不同于物理、历史等学科。如果没有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们就不会了解相对论的具体内容;如果没有学到抗日战争中衡阳保卫战的历史知识,我们即使人在衡阳也不知道远去的硝烟和方先觉的名字。语言学课程也和关系最近的文学类课程不同。如果没有学“文学概论”之类的课程,我们可能很熟悉电影中场景的切换与联接,但不会知道它的专业名字叫“蒙太奇”;可能我们看过王蒙的某些小说,但我们只有在文学概论课中才明了那种小说叫“意识流”小说。然而,语言学课程特别是有关母语的语言学课程,除了理论外,大多数实例介绍和规律总结都是我们预先就知道了的,学习的目的主要是梳理和解释。人类社会的主要认识任务有三个: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和认识人自身。对语言的认识,既包含对社会的认识,也包含对人自身的认识,但本质目的不是认识客体世界,而是认识人自身。
(二)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应该依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有所侧重和分解,并非每一堂课都要同时达成这些任务。如有关“语言性质”、“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学简史”之类的教学内容,主要通过精巧的理论构建和推导来让学生领会纯理论的魅力,以典型、奇妙、贴切的语言材料或社会事实来说明相关理论;而有关“语言的发展”部分,则可以一边讲授一些基本的理论知识,一边让学生调查语言新现象,让他们调查和对比语言、方言,从而学会语言分析的方法。特别是在“语言运用”部分,讲授语言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时,可以提供优秀的言语样本进行赏析,创设情景,让学生得体地使用语言,锻炼他们的语言鉴赏和运用能力。
(三)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可以采用多元立体的组合模式。课堂教学只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一部分,学生在课外的阅读自学、社会调查、研究讨论以及参加学术沙龙、论坛讲座等都是课堂教学的准备和延伸。“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总课时不多,一般在36-54课时之间,而该课程要完成的任务却很多。这些任务不可能全部在课堂上完成,因此只能借助于多元立体的教学组合模式,把部分任务分解到课前课后。赵贤德就曾经提到“教学内容科研化”、“教学形式趣味化”、“教学实践课外化”、“考核方式多样化”的观点,[16]这就是一种分解任务的思路。我们的整体思路和做法是:知识的传授贯穿课堂,能力的培养因势利导。在课堂上讲授基本的语言学知识和部分语言知识,并向学生示范如何查找和掌握研究文献、如何收集语言材料、如何调查语言现象与语言观念以及如何分析语言材料和调查结果等等,布置学生在课前、课后进行拓展阅读,收集语料和分析语料,并定时检查和评析学生的学习成果,以此锻炼学生的语言研究、语言鉴赏及语言运用的能力。
[1]聂志平.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问题探讨——以浙江师范大学为例[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5(2):77-81.
[2]岑运强.语言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前言.
[3]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J].语文建设,1999(2):49-53.
[4]岑运强.语言学概论教学再探——谈语概教材的编写[J].福建外语,1997(1):11-18.
[5]张先亮.关于“语言学概论”内容与方法的再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10(2):44-47.
[6]许云.“语言学概论”教与学管说[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藏语文教学与研究专辑):46-48.
[7]曾毅平.“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的若干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1):70-74.
[8]潘之欣.关于高校英语专业“语言学导论”类课程设置的调查[J].外语界,2002(1):47-55.
[9]吴格奇.“语言学导论”课程教学行动研究与教师知识体系的反思[J].国外外语教学,2005(2):32-37.
[10]黄腾翔.关于高校英语专业普通语言学课程的调查和反思[J].语文学刊,2011(6):133-134.
[11]罗耀华,柳春燕.《语言学概论》课程创新教学尝试[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9(2):57-61.
[12]何东萍.语言学概论课程改革之我见——“中文专业语言类课教学与大学生语言能力培养研究”课题报告之二[J].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93-96.
[13]郜峰.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原则初探[J].中国高教研究,2006(8):83-84.
[14]谢奇勇.关于“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内容几个问题的讨论[J].中国大学教学,2010(1):52-55.
[15]杜道流.“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5(5):112-113.
[16]赵贤德.“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途径[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0,31(6):9-11.
[17]许晋,李树新.高等院校《语言学概论》课程改革探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22(5):111-113.
[18]黄育红.语言学概论课程实践教学的“瓶颈”及对策探讨[J].教育探索,2010(10):54-55.
[19]林秋茗.“鱼”“渔”兼授:谈高校语言学课程教学原则[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2):36-40.
[20]梁驰华.高等师范院校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谫议——兼谈语言学概论与现代汉语的关系[J].高教论坛,2008(2):79-82.
[21]格雷马斯 A.J.结构语义学[M].蒋梓骅,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13-16.
[22]马学良,瞿霭堂.普通语言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前言.
[23]李树新.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改革与实践[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17(5):49-51.
[24]刘云.“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刍议[J].咸宁学院学报,2010,30(2):81-83.
[25]邵敬敏,方经民.中国理论语言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65.
[26]纪秀生.高师语言学概论教学新体系的构建[J].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7(2):71-73.
[27]邢福义,吴振国.语言学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64-371.
[28]李宇明.语言学概论: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53-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