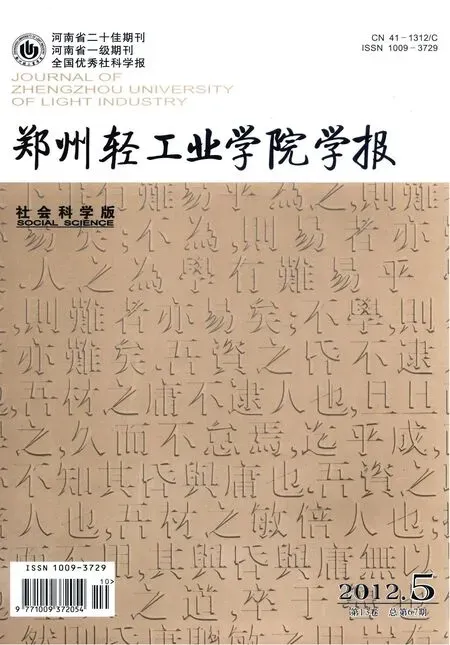政治性—主体性的革命话语与工人阶级的主体性生产——安东尼奥·奈格里对列宁思想的重塑
2012-01-28宋晓杰
宋晓杰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1933—)是意大利工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旗帜性人物。奈格里的早期政治理论始终建基于对劳动和劳动力的持续关注,彻底颠倒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坚持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中的客观主义幻象、决定论—目的论逻辑、回返式的辩证法逻辑以及革命的乌托邦残余等,并试图以危机而非平衡、对抗—分离而非对立—综合、主体性的历史动力而非客观性的自然趋势等范畴,来恢复政治性—主体性话语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逻辑优先权。在奈格里看来,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既不是从人道主义逐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线性目的论,也不表现为以1845年为临界点的科学和意识形态的“认识论断裂”——前者从根本上奠定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却以客观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意识形态体系遮蔽了政治性和革命性话语的历史连续性;后者则立足于历史的客观层面,以客观超拔的结构限制甚至消除了历史的主体向度。奈格里同样反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将积极的革命趋势和创构性的替代过程理解为抽象的人类本质的有机展开,因为它弱化了马克思充足性的主体性视域,过于纠缠在人与资本的密切关系之中,最终必然走向革命政治的乌托邦。[1]由此,奈格里明确把从社会学转向政治本体论的讨论逻辑界定为“从结构转向主体的路径”。一方面,它能够创建旨在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组织,使其自身成为革命性—主体性因素构成的主体结构,并使“建构群众的斗争、组织和革命生活的所有因素都位于其中”;另一方面,它又排除了形式主义或辩证形而上学的解决方案,通过“主体运行于自身之转型活动的复杂性的累积”,真正达及本体论领域。[2](P173)极端的主观主义者退回到“主人辩证法的‘普罗米修斯主义’”,试图以暴力的方式成为社会辩证法的主人;而沉醉于民粹和自发性崇拜的人则退回到“自发性美学的自我陶醉”,受制于重复性和虚伪性而过于尊重社会的辩证法。[2](P173)在此,结构与主体表现出十分微妙的关系,主体维度的过度膨胀或缺失均无法充分说明这个本体论路径的根本特征:充足的主体性力量必须建基于结构要素的重组,如此才能实现社会转型的革命筹划;然而结构只生产抵抗和革命的主体性因素,并不是作为根本前提的历史结构和社会形式。
从本质上看,奈格里的政治理论重在以充足的革命主体性话语,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范式、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的乌托邦气息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主体维度的过度弱化。本文拟通过对其核心逻辑取向的透视,深入分析奈格里重塑列宁思想的理论脉络,以揭示他政治地解读列宁并重构其当代形象的真实意图,进而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逻辑坐标来对之进行系统定位。
一、从认识论断裂到主体性断裂
在对列宁和马克思的理解方面,奈格里同阿尔都塞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逻辑路径。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假定马克思的思想前后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问题式,并拒绝二者之间相互通约的所有可能。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的方法论限制甚至取消主体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把它当做结构的功能承担者,并以结构间的断裂和转型来消解历史的连续性,以不同结构间的场所变换来重构自己的历史范畴。奈格里十分反对这种理解马克思的方式,他认为阿尔都塞抽空了马克思思想中关于力量主体的政治学分析,即工人阶级革命组织的筹划及其政治性—主体性的逻辑构架,并未揭示出结构断裂背后工人阶级主体性力量的充足性。
奈格里认为:“如果我们想要谈论马克思思想中的‘认识论断裂’,那么它只能开始于这一时刻:结构的定义不仅显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存在与工人阶级运动的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分析使自身从现存条件中解放出来,致力于把自身转化为一个规划,既定的生产力导致组织计划的产生。认识论的断裂是组织的诞生。”[3](P28)谈论马克思思想中的“认识论断裂”,首先意味着重新面对资本主义发展与工人阶级斗争之间的力量关系,并在确认后者本源地位的同时将这个理论分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连接在一起,以此去深入透视工人阶级新主体性模式的出现。事实上,“马克思思想的演进,远没有终止于‘没有主体的过程’,相反,它紧密地遵循革命主体的组织的现实性。政治经济批判的真实结果必然是这一主体性的根基。”[3](P28)由此,奈格里把“认识论断裂”转换成因革命主体性模式的出现而导致的“主体性断裂”,它积极地筹划自身革命组织和自由解放潜能。显然,从“认识论断裂”到“主体性断裂”的转换过程,是试图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中心结构的政治性—主体性转向,它再次确认了主体性和阶级斗争话语在奈格里政治理论中的中心地位。
二、从工人阶级的自发性到工人阶级的自主性
在自主主义的理论视域中和新的资本主义发展周期内,阶级斗争以客观的形式取得了主导地位,并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工人阶级不再单纯地表现为被剥削对象,它作为社会发展的本体力量和实现社会转型的直接有效的行动者,作为资本主义统治机制必须面对且以其为基础重构资本结构的力量主体,能够积极创造替代资本主义的另类社会。基于此,奈格里认为,列宁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思想资源,列宁主义的当代化视域同样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方式和革命形式等方面的重新规划,“列宁是我们为意大利无产阶级的政治构成所支付的代价。只有通过列宁主义才能谈论政治……它是阶级的共通语言:它能够引起困境,但是你只能借助它而和阶级(不与其他人)一起前行”[3](P13)。但他始终对列宁思想的双重性保持足够的清醒,并致力于将其理解为重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的理论基点。列宁的重要贡献在于他确认了这样的事实: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恰恰是工人阶级的最强大之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构成列宁理论视域的核心内容,奈格里对列宁思想的重组自然也围绕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和中心性展开,以彰显政治性—主体性话语的本体地位。
依照奈格里的理解,列宁思想的发展过程表现为从工人阶级的政治构成理论转向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理论。它主要包括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集中于1890—1900年,侧重分析工人阶级的政治构成;第二个时期集中在1900—1910年,侧重分析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理论;第三个时期集中在1910—1917年,侧重分析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摧毁。
第一个时期涉及的文本主要包括《什么是人民之友》《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奈格里指出,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理解模式过于专注于列宁的社会形态概念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试图以一种纯粹客观的社会结构取消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性维度。事实上,列宁通过社会形态的分析,不仅确认了工人阶级政治构成的基本特征,并且通过考察工人阶级真实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将其看做真正的革命主体。这构成了列宁思想的核心部分,“围绕工人阶级这个概念去澄清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阅读的独创性是合理的。工人阶级概念是在确定的社会形态概念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它作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过程的动力而日趋现实化”[3](P15)。奈格里在对列宁这个时期的著作其他文本的解读中更加强化了这一方式。他集中分析了列宁对工人阶级政治构成自发性特征的强调,充分认识到工人阶级自发的经济斗争的政治重要性。工人斗争和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工人阶级的斗争虽然不够成熟,但总能表达出一种极为充足的政治本能,这不仅消除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传统分化,使经济斗争具备了政治斗争的形式和内容,而且工人经济斗争的政治内容、工人斗争的自发性以及高度技术化、斗争强度和发达的政治意识,又为无产阶级更高程度的政治筹划提供了根本性的现实土壤,自然直接预示着更加强大的革命组织的出现。
第二个时期涉及的文本主要包括《怎么办》等,旨在超越工人斗争和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特征与单纯的经济斗争范围,试图直接在政治层面上确认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此时的政治斗争不再仅仅是经济斗争,而是在超越工人经济斗争和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的基础上,指向以政治领导和自主性政治组织为特征的基层组织理论:工人阶级的政党制度。这既提升了工人斗争和群众运动自发性的政治水平,又系统表达了基层激进政治运动中等级性和垂直性的政治关系与政治形式。列宁关于组织理论的这个历史推进,是以批判工人阶级的政治构成和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为基础的,它需要通过有意识的政治领导、组织和管理,外在地灌输和培育自身的阶级意识、政治革命意识及其内在统一性,以充分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目标。列宁主义的政党模式旨在通过等级制和组织化的方式,把工人自发的主体性提升为具备阶级统一性和持久战斗力的革命主体。
奈格里认为,革命主体的政治组织必须充分揭示出阶级自身的自由行动,并且可以保证积极的革命预想是可能的。列宁正是从社会形态入手深入讨论了工人阶级自发性的客观社会基础,进而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阶级构成的分析走向革命的组织理论。在此,列宁的分析视域虽然一直强调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和自发性,但它始终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列宁对主体性的强调始终与主体的劳动关系和具体的社会条件直接相关,主体只能“由其物质构成(斗争的物质性、工资的物质性和制度化设置的物质性)界定”[3](P18)。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受制于具体的生产方式,其阶级构成则决定了革命组织的相应模式。奈格里非常强调工人阶级的阶级构成对自身组织模式的规制性以及工人阶级的自我价值稳定过程[4]所体现的主体性和革命性的充足。他以工人阶级之阶级构成的历史转换为基础,强调基层的激进政治组织和无产阶级的自主性,并在工人阶级的主体模式、主导性的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革命的政治组织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模式中,逐步批判了以外在的政治调解、超拔的控制领导和自上而下的革命方式为特征的工人阶级的传统政党模式:布尔什维克式的先锋政党理论。
列宁的先锋政党模式只与“诸多系列的社会阶层的恢复和重新统一、劳动形式、生存形式、收入形式与斗争形式”连接在一起[3](P18),只是对劳动过程和生产方式组织形式的预先描绘,并且只与前革命时期俄国的工业生产方式相适应。这个时期俄国工业生产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劳动分工的严格化和劳动任务的专业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构成自然以专业工人或高度技术化工人为主要特征。在《规划者的危机:共产主义和革命组织》一文中,奈格里承认这种布尔什维克式政党概念的现实有效性,认为它以工厂生产为中心,在工人阶级之外代表工人阶级自身,集中表现为工人阶级的精英和专业的先锋组织自上而下地领导和组织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主体主动性的加速,迫切需要中心化和先锋的组织化定形;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使先锋组织从预先形成的自主层面和阶级自发性中解放出来”[5](P181)。正是在“社会工厂”的领域中,先锋组织才能够构建斗争的焦点,也正是围绕着这些焦点,才能以理性的方式动员和组织被剥削的群众进行斗争。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和领导者,先锋组织自上而下地组织和控制工人阶级斗争,“可以与新的群众组织建立起有效的关系,并能够聚集和推动总体运动朝向反叛的可能性”[5](P181)。
然而,列宁组织理论的重要之处正在于,它将“关于组织问题的讨论和实践,重新与当今阶级斗争真实的现实性相联系”[5](P112)。原来与俄国前革命时期的专业化的工业生产和专业工人相适应的专业的先锋政党,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工人主体性模式和生产方式。20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工人斗争和群众运动的自发性根本没有采取垂直的或等级的政治组织形式,反而在现实斗争和政治抵抗中采取自主的和平面化的组织方式,它们完全漠视任何的工人精英和所谓的官方工人运动,而采取一种完全不同于列宁政党理论的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模式。随着规模化生产和劳动力去技术化趋势的真正确立,资本已经抚平了工人内部以及工人先锋与群众之间的等级关系。特别是在“后福特制”模式中,劳动力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水平地扩散至整个社会领域,资本已经在一种去辖域化的平面空间中彻底实现了在整个社会中对劳动的控制,列宁在“后福特制”之前所区分出的经济斗争的具体性和政治斗争的一般性已经失效,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已经成为完全同一的东西。工人阶级的阶级构成也由专业工人向大众工人转变,外在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也已失去其客观的社会历史基础。
在随后的《反对工作的工人政党》一文中,奈格里进而以规模化的工业生产和大众工人的主体模式为基础,指认了一个大众先锋的组织形式。他区分了大众先锋组织的两个不同方面:一方面是工人力量的大众组织,作为工资和占有斗争的主体;另一方面是政党组织,作为反对资本命令的斗争主体。在传统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理论传统中,前者代表优先的战术领域,后者则作为无产阶级战略的独立承担者而存在。但在奈格里的区分中,情况刚好相反,前者代表战略和规划的方面,后者则指向战术的主体。奈格里致力于翻转布尔什维克先锋政党的中心地位,意在强调大众的主动性与工人的领导之间不可分割的总体关系,并以此来批判列宁主义的政党模式。“在列宁主义中,政党以工人阶级的政治构成为基础,担任解释者和代表的角色,其中阶级构成被迫自上而下地贯彻无产阶级战略联合的少数派。政党以工人阶级的技术构成和资本的构成为基础。前者使工人阶级以社会主义的形式,参与把工作强加到社会总体性活动中,后者则使工人阶级只是自上而下地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化为社会主义的权力管理。”“今天,这些前提都不再成立。相反,政党把自身呈现为对价值规律消失的资本主义管理的废除。……政党必须从内部自下而上,而非从外部自上而下地,揭示既定的阶级统一性和发生在无产阶级内部的重构。政党的反叛艺术是助产术的,它以相同强度但以相反方式,反对资本家非理性命令的重担。……政党通过攻击和破坏价值稳定的过程,把生产劳动的总体性撕离资本主义的命令。工人阶级的立场是把自身呈现在作为恢复利润障碍的客观性和自主性中,并在这个自主性中,它发现自身需求、共产主义和占有的世界。……这就是权力的制度形式隶属于工人阶级的过程如何实现的:政党不再拥有代表的功能,它摆脱了资本主义必然性的这一最后残余。”[5](P88-89)在此,专业的阶级先锋转变为大众先锋,后者位于阶级内部,拒绝任何形式的外在的政治领导和调解,而把工人阶级显示为未被任何外在机制调解的力量主体,工人阶级只能把力量授予自身。
值得注意的是,奈格里虽然充分强调了工人阶级的首要性和自主性与大众基层组织的主动性和革命性,但政党作为大众先锋的一个方面,仍然承担了揭示工人阶级统一性和自主性、反对资本主义命令的重要功能,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群众相分离。同时,革命主体的优先性也以工厂工人为中心,大众工人承担着阶级先锋的角色。在这个革命组织模式中,大众先锋表现出既内在又外在于工人阶级的矛盾倾向。
在后来的《控制与破坏》一文中,奈格里最终强调了工人阶级的自我价值稳定过程对政党的决定作用,并把政党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战术附属物。他认为,传统的政党模式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往往都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噩梦,在它们之中,制度化、改良主义和对无产阶级独立性的解构总是表现出直接相关的必要关系。在经典的政党理论中,无产阶级的欲望和需求总是附属于“被神秘化了的”筹划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并日益演变为个人化的权力崇拜,逐步枯竭了工人阶级自身的创造力。政党通过强加筹划的普遍性,要么表现为无能的调解代理人,要么表现为强大却自负的先锋。“当前国家形式的结构是这样的:制度上的政党出现使国家可以在对反抗方面的解构和政党出现的秩序化效果之间,提出一个有效的替代方案(敲诈)”[5](P275),传统的社会主义政党模式因其筹划的普遍性和自上而下的调解方式,不仅无法有效保证无产阶级自身的需求和欲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资本主义命令的同谋。无产阶级的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直接占有力量和财富,充分发展自身的激进欲望和需求,日益获得自身充足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政党不是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的“直接因素”,不是“固定在自我价值稳定的充足客观性中的直接的和激进的反权力”,而是“无产阶级力量的功能”和“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的保证者”,“但与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相分离,甚至某时与它相矛盾”。[5](P276-277)它在无产阶级的大众反权力的运动中起作用,但对无产阶级需求和欲望的生产和组织没有控制权,反而“自我价值稳定的政治学拥有对政党的支配权”,换言之,在无产阶级的自我价值稳定过程中,“权力被消解为力量网络,阶级的独立性通过个体革命运动的自主而得以建构。唯有分散的力量网络才能组织革命的民主;唯有分散的力量网络才能保证重构辩证法的开放,它把政党归结为一个革命军队,归结为一个对无产阶级意志坚定的执行者”[5](P278-279)。由此,政党只是作为无产阶级意志的代理人和无产阶级价值稳定过程之功能性的承担者而存在,并不直接构成其内在的固有部分和因素。
在对阶级构成、生产方式与政党职能的分析过程中,奈格里最终认识到无产阶级力量的自我利益、直接需求和欲望生产可以自行决定、组织和生产自己的斗争形式,并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权力调控和政治秩序。这清楚地显示出奈格里政治理论方法论的基本逻辑取向:在颠倒资本主义发展本体力量的基础上,以阶级斗争为逻辑中轴,重建政治性和主体性话语的本体论语境,并最终走进通向共产主义的欲望和革命的政治学。
第三个时期涉及的文本主要是《国家与革命》。列宁主张只有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才能真正彰显无产阶级的主体力量,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奈格里认为,列宁视域中的“国家”具有较为广泛的含义,它不只是镇压性的政治工具,也是超越社会的外在权力和强制力量,是阶级矛盾无法调和的产物;它既构成资本主义的权力形式,又竭力消除阶级斗争的张力,作为威慑的超验力量来调节社会矛盾。因此,国家除了作为资本主义的统治工具和超验权力之外,也通过司法宪政制度来实现劳动的宪政化和对社会劳动组织的潜在塑形,以借助于一系列司法宪政体系和政治秩序的外在调节(命令和暴力)和生产组织职能,实现对工人阶级斗争的调控和支配。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司法关系链条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剩余价值生产机制的另一潜在维度,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个独有的表现形式。
国家职能的这一双重特征使对国家的消除必须从总体的物质基础出发,彻底粉碎一切资本主义的命令关系、工作关系、司法关系和生产关系,而非单一地摧毁作为国家表层形式的权力机关。“共产主义斗争前后一致地成为反对工作、反对国家以及反对建构国家和劳动组织具体的极权主义关系形式的法律的斗争”[3](P28)。由此,奈格里甚至把列宁粉碎国家的分析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关于价值规律解体的讨论看做是一体两面的表达。他认为,列宁消除国家的观点是为了批判自上而下地实现革命的幻想,是为了批判国家自上而下地实现自身统治的权力乌托邦,是为了借助于从内部自下而上而非从外部自上而下的革命组织、大众实践和群众运动来创造新的替代性的社会秩序;列宁最终旨在确认一个新的自主的社会主体和无产阶级主体力量的充足性,后者能够自上而下地建构出替代资本主义社会或(超越资本主义工作体系的)后工作时代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构想,唯有激进的和革命的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
总体而言,奈格里在他所区分的三个时期中,将列宁的相关思想重构为革命主体性话语的历史推进过程:从具有工人阶级自发性和主体性的专业工人和专业先锋政党向具有工人阶级自主性和自我组织性的大众工人和大众先锋政党,再向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完全自足和自我价值稳定过程及作为其功能承担者和战术附属物的政党模式转变;从外在的自上而下的转向内在的自下而上的革命组织形式。奈格里以主体性为本体性视域,给予列宁思想以充足的当代化动力,此时的列宁已经被打上了鲜明的自主主义烙印,变成了始终操持主体性—政治性—革命性话语的“超越列宁的列宁”和政治的列宁形象。
三、从生命政治到革命主体性生产
奈格里非常重视列宁思想的当代化及其现实意义,他竭力使列宁的革命组织理论和革命实践适应于当前阶级斗争的客观情势,并试图以政治性—主体性话语把这种结合放置在他后来确认的后帝国主义时代的话语中。
在奈格里看来,西方的政治科学往往把“夺取权力”当做列宁思想的惟一主题,并且总是与粉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和消除国家直接联系在一起。然而,列宁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虽然他以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了政权,但国家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变得日益强大和邪恶。事实上,回到列宁的问题恰恰意味着“是否有可能采取这样的道路:它即刻颠覆事物的现存秩序,并创造出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世界,它摧毁西方形而上学的始基——无论是权威的原则还是社会剥削的工具——及其政治的等级制和对生产力的控制”[6](P298)。资本主义的权力理应同时包括国家控制和实现剥削的社会结构,二者并不只是表现为抽象的国家理性和政治理念,而是将资本结构渗透至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因此,列宁的共产主义斗争带有生命政治的特征,“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政治意志把自身归属于它所批判、建构和转换的生命方式”[6](P298)。奈格里直接祛除了西方政治科学试图把政治单纯地理解为国家理性的幻想,也批判了以等级制或政治决断来界定政治的方式,坚持认为政治绝对不能与社会和人类领域相分离。
列宁反对把政治当做对经济形式的反映,拒绝仅仅以政府形式来分析国家的方式。相反,一方面,他“调制、混合、充足和革命化理论的形式:总是成功出现的必然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意志,在它之中,身体和理性、生命和激情以及反叛和规划可以以生命政治主体的形式创构自身。这个主体是工人阶级及其先锋,后者构成无产阶级身体中的灵魂”;另一方面,他又把“群众的生命及其需求的总体表达看作身体(physical)和肉体(corporeal)的潜能。……这个共产主义政治本体论的进步无疑是神秘的,尽管它仍然真实存在,因为它通过它的生命政治方面,特别是以它所表达和欲求生产的自由的肉体充足性为方式,表现出共产主义思想卓越的现代性。只有在这里,在这个身体的唯物主义(它极力实现自身的自由)中,在生命的现实性(革命,只有革命才能使它复兴自身)中,我们才能发现真正的列宁。因而,列宁不是再现了对政治领域自主性的忏悔,而是为了一个身体的革命创造”。[6](P298-299)显然,从列宁思想的生命政治特征,重新转向对主体性生产机制的分析,始终指向完全政治化—主体化—革命化的列宁形象,已经远远超出了列宁理论视域的容纳范围。
究竟共产主义斗争的新身体是什么?它在当前社会条件中如何实现自身的转型?在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上,奈格里依然基于自主主义的理论传统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来专注于对“超越列宁的列宁”的揭示,这与他对待马克思的态度极其相似。他认为,早在1960年代早期这些问题便已经出现,因此对列宁思想的重新审视,不仅需要与生产条件、权力关系和主体模式的持续转型充分结合在一起,而且必须使列宁主义面对这些社会转型问题时保持自身充足的合理性。列宁思想的当代化必须直面资本主义生产类型和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以及新的社会历史主体的出现:生产劳动的本质在根本上变得非物质化,生产性合作也已完全社会化,“这便意味着工作现在与生命共存,就像合作与诸众(multitude)共存一样。因此,劳动在作为整体的社会中(而不再只是在工厂中)拓展其生产网络”,于是,“超越列宁的列宁”的领域,其关键问题已经转变为“什么样的掌握权力的主体性生产对于今天的非物质性的无产阶级是可能的?或者换言之,如果当前生产的背景由非物质劳动的社会合作来建构——我们可以把它界定为一般智力,我们如何能够建构这个颠覆性的‘一般智力’的身体,因为它将会是新革命肉体的存在得以产生以及主体性生产强大基础的起点和手段”[6](P300-301)。在此,奈格里重构列宁形象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列宁所规划的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组织和消灭国家的革命战略,唯有以一系列的社会转型为现实背景,以新革命主体性模式的生产和筹划为根本目的,唯有在充分认识这些新的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致力于寻求新的革命组织和解放规划才能获得充足的现实合理性。
显然,在列宁思想的当代化视域中,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生产构成了奈格里重塑路径的逻辑起点和理论终点。无论从工人阶级的自发性到工人阶级的自主性、从生命政治到主体性生产,工人阶级力量的自足性和本源性都取得了主导优势。于是,“重装上阵的列宁”(Lenin Reloaded)只能意味着“将列宁的思想带出它已经生存之中的现代性空间(主权工业模式),并把它的革命决断转变为一个新的内在于后现代诸众中的共产主义的和自主性的主体性生产。”[6](P307)
四、携带唯意志论气息的“政治的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柯林尼克斯从创建历史的社会理论中确认出两条线索,一条将历史的创建归结为社会结构,它与从个体视角和目的中抽取出来的客观关系相关,另一条则强调历史源于相互冲突的各色人群的动机和利益的重组。从本质来看,可将之归结为历史理论中结构与主体或行动者的对峙——前者强调纯粹客观层面历史结构自身与历史结构之间的自我生成、客观演进和现实转化过程,往往具有客观主义和某种决定论的色彩;后者则立足主体性维度,突出主体塑造历史的充足创构力量,又不可避免地携带唯意志论的主观主义色彩。在逻辑取向上,立足主体的历史理论与将阶级斗争视为历史运动的根本动力的“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十分接近。“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的生产能力设置了可能性的限制,或更具体而言,特有的剩余价值抽取模式构成打开社会结构的钥匙。它同时告诉我们,阶级斗争产生历史运动。这并没有使历史变成偶然的、意外的或不确定的。”[7]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虽然可以用来解释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但马克思在“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判断中同样确立了反观性的分析模式。这当然不是一种目的论,而是深刻揭示了这样的事实:使生产力转型的推动力不是原因,而是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转型的结果,阶级斗争构成历史运动的根本动力。由此,可将这个历史观归结为“唯意志论”的历史观或“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它旨在脱离客观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分析框架,侧重以阶级斗争为核心来揭示现实的历史变迁,使其脱离了客观历史情势的限制。[8]它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不同阶级斗争的发生、可能性后果、内在规律以及具体本质都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并不是极端夸大主体维度和阶级意志的唯心主义思潮。
奈格里重塑列宁思想的逻辑路径更符合上述理论传统。他以政治性—主体性的革命话语将列宁塑造为操持工人阶级主体性生产和共产主义革命话语的激进形象,从而使阶级对抗重返经济生活的中心,重构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只不过生产力代表着无产阶级对自由和财富的重新占有以及革命主体颠覆性的解放潜能与创造性的自由本性,生产关系则指向资本主义的命令体系对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的严整规划。他试图走出纯粹结构层面的客观历史分析,使阶级关系彻底摆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必然性模式,以此确立工人阶级力量的根本地位。柯林尼克斯指出,“政治的马克思主义”清除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会陷入“恶性循环”,将社会转型的动力归结为“敌对的阶级意志之间的冲突”,最终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一个“唯意志论的社会理论”,因而它只是一种赋予阶级剥削关系以首要性的唯物主义的“控制社会学”。[9]奈格里确实简化了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把历史发展化约为阶级对抗的产物,忽略制约阶级斗争产生、性质和结果的客观脉络,存在唯意志论嫌疑和相对主义的风险。
严格说来,奈格里不是纯粹的唯意志论者,他始终摇摆在唯物主义与唯意志论之间。在历史理论层面,他重建阶级斗争的中心地位旨在反对立足纯粹结构对历史进行客观主义和目的论的描述;在现实层面,他并没有取消历史结构对主体的制约作用,也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的现实土壤,抽象地谈论阶级构成的历史转换和列宁思想的当代视域。然而,主体的过度充足弱化了结构的前提作用,结构对他最重要的意义是为了营造通向无产阶级自主性和共产主义革命的现实条件,只是他走向革命主体的中介环节。
[1]宋晓杰.政治性—主体性的逻辑构架与阶级斗争的革命政治学[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1):55.
[2]Saree Makdisi,Cesare Casarino.Rebecca E Karl Marxism Beyond Marxism[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6.
[3]Timothy S Murphy,Abdul-Karim Mustapha.The Philosophy of Antonio Negri:Resistance in Practice[M].London:Pluto Press,2005.
[4]Paolo Virno,Michael Hardt.Radical Thought in Italy:a Potential Politics[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nesota Press,1996:264.
[5]Antonio Negri.Revolution Retrieved:Writings on Marx,Keynes,Capitalist Crisis and New Social Subjects(1967—1983)[M].London:Red Notes,1988.
[6]Sebastian Budgen,Stathis Kouvelakis,Slavoj Zizek.Lenin Reloaded:Toward a Politics of Truth[M].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7.
[7]Ellen Meiksins Wood.Marxism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J].New Left Review,1984(147):105.
[8]Aston,Trevor Henry,Philpin C H E.The Brenner Debate:Ag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115.
[9]Alex Callinicos.The limits of political Marxism[J].New Left Review,1990(184):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