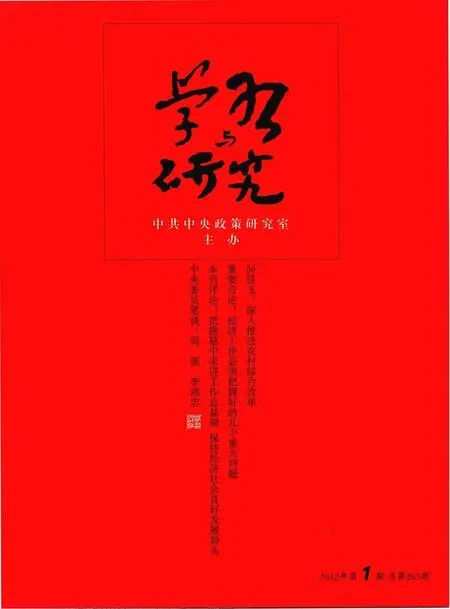论圣人崇拜——关于中国哲学精神之探索
2012-01-27朱义禄
朱义禄
(同济大学 文法学院,上海 200092)
说及中国哲学精神,至少要与下列三个条件相符:一是得千古如斯的流传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二是为历史上不同的哲学流派所公认,然后又在历史长河中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所赞同;三是不只是一种纯粹理论思维中的学说或观念,而是在下层民众上有着广泛的传播。符合这三条的,有人们较为熟悉的大同理想、阴阳学说、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等。本文对认为圣人崇拜亦可作为中国哲学中的本根性观念与情结。
一
圣人崇拜是有悠久的历史溯源的。圣原作聖,圣是聖的简写。从语义学上看,圣只是聪明人的意思。《说文解字》:“聖,通也,从耳呈声。”应劭《风俗通》云:“聖者、声也,通也。言其闻声知情,通于天地,条畅万物也。”聖的原始意义是“闻声知情”,就是从耳闻的具体事物而通晓天地万物。在《诗经》、《尚书》、《国语》中,有不少聖字,但只是聪明能干之意,尚无崇高无比之义。如《尚书·洪范》言“睿作聖”,即为显例。《左传》中的聖人,也指多知明德的人,无神圣莫测的意思。圣人神圣莫测,崇高无比的观念起始于孔子。孔子痛心疾首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他精心杜撰出一个“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把传说中的尧、舜塑造成为理想的圣人,把他们看成与天同样伟大和崇高。《论语·泰伯》中记载了孔子对尧舜的崇拜:“大哉尧之为君!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看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圣人是高不可攀的。
孔子不敢以圣人自居的,他的学生子贡“固天之纵圣”的说法,编造了一个上天使孔子成为圣人的神话,开启了把孔子圣化的先河。以孔子私淑弟子自居的孟子,力倡性恶论的荀子,无不奉孔子为圣人。“孔子,圣之时者也。”“彼大儒者,仲尼、子弓是也,因天下之和……非圣人莫能为。”从趋势上看,以孔子为圣人作为崇拜对象在孟、荀那里,就显出端倪了。
圣人从聪明变为崇高无比,是源于孔子的。往后圣人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崇拜的偶像,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成为儒、道、墨、法的共识。至少在先秦时期,圣人崇拜已成为不少哲学学派的共识。“儒家以仁义而而尊圣,道家以自然无为而崇圣,墨家以事功原则而希圣,法家以专制暴力而扬圣。出发点不同,但归宿却一致。”各家殊途同归,均对圣人抱着虔诚的崇拜态度。其根本原因是冀望出现一个圣人,来结束诸侯割据的局面,实现亘古未有的大一统。圣从普通的聪明人,进而易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圣人,是当时经济状况、政治期望与心众心理等综合因素的结晶。先秦诸子中的儒、道、墨、法,只是得时代风气之先罢了。拯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结束分裂的战争状态,诸子对圣人的历史性呼唤得到了回响。一统宇内的秦始皇自称“秦圣临国”,让先秦诸子的呐喊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圣人崇拜情结的母范,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定型了。
从学理上说,圣人就是理想人格。在一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制度中,出于现实的需要,人们的利益、要求、期望集中于某一个楷模身上,即为理想人格。理想人格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文化中人们最推崇的人格范型,这种人格范型最典型地体现了该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价值标准,也是该民族的哲学家精神的体现。由于理想人格是以美仑美奂的形态出现,对人们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理想人格往往同现实有一段差距,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因而理想人格具有追求性与超前性两大特征。
对圣人的憧憬与追求,一直是中国人的定势化的文化心态。明初理学家、白沙学派的创始人陈献章说:“夫士夫何学?学以变化气质,求至乎圣人而后已也。求至乎圣人而后已也,而奚陋自待哉?”他把这种求学心态归结为“希圣求圣”。颜李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塨,圣人崇拜的心态主宰了他的一生。做人的志向以“圣人”为榜样,学问的追求以“圣道”为目标:“我辈居官,立志为圣贤,出而效帝王,皆分内也。”“夫学而不以希圣希贤卓然千古为志,虽知无大错迕,仅仅乡党自好者耳。”在李塨的著作中,“圣人”、“圣道”、“圣门”、“圣教”、“圣绪”等带的“圣”字的词汇,随处可见。“立志为圣贤”是李塨一生憧憬的理想。李塨强调,不立下做圣人的志向,即使行为上没有什么大的差错,也只是与同流合污的“乡党”而已。
明末史学家计六奇记载了一个宋明理学的信徒“希圣”的真实状况。他叫刘之纶,四川宜宾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官至兵部待郎。“喜理学家言,大书其坐隅曰:‘必为圣人。’里人因呼为刘圣人。”这一传统心态在近代并未消失,康有为因开口闭口不离“圣人”二字,被乡亲们称为“圣人为”,而其一生从未放弃过置身于圣贤之列的念头。本世纪初,著名学者章士钊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之思想,动欲为圣贤、为王者、为天吏、作君、作师,不肯自降其身,仅求为社会之一分子,尽我一分子之义。”中国人“动欲为圣贤”的文化心态,是与先秦以降对圣贤人格崇拜的传统相关的。
二
圣人崇拜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哲学精神,与历代帝王期望圣人“弘我王化”而利用行政权力极力倡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威震六合的秦始皇,在几次巡行中把自己和圣人等同起来,如“皇帝躬圣,既平天下”、“大圣作始,建定法度”、“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石,显陈旧章。”“大圣”、“秦圣”,就是秦始皇,他认为自己是一统宇内的伟人,就以圣人自居。他是否意识到了自己是圣人观念历史演变的承担者这无关紧要,但先秦诸子的共同呐喊到他那里却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把“圣”与帝王直接联系起来,始作俑者是秦始皇。自他以后,历代帝王及王朝的事物无不冠以“圣”的字眼。如皇帝称为圣上,皇帝命令为圣旨,皇帝生日为圣旦,当代王朝称圣朝,德行才智超凡的宰相为圣相,皇帝母亲称为圣母,皇帝诏令称为圣谕广训……是要人们在圣人崇拜的心理定势下,无条件地服从现存的皇权统治。
尊孔崇圣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维护专制统治的秩序。生性风流的唐玄宗李隆基,他以为孔子能“弘我王化”的主张就说明了这一点。历史上第一位祭孔的皇帝是汉高祖,但仅是祭祀而已,没给孔子以什么殊荣。孔子首次受封是汉平帝时,孔子被追谥褒成宣尼公。孔子十三世孙孔霸做过汉元帝的老师,元帝即位后,被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孔霸上书求奉祭祀孔子,元帝下诏,令“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后代帝王尊孔祭孔,是汉代奠定了格局的。孔子之祭祀至唐玄宗时正规起来,孔子取代周公先圣的地位,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追谥孔子为文宣王。这是孔子首次封王。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玄宗李隆基在诏令中说:“弘我王化,在乎儒术”。李隆基的理由是,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象孔夫子那样,“能致天下太平,成天下之大经。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赐。”元代封孔子为大圣至成文宣王,并分别加封从祀诸儒,以孟子为亚圣,又加祀董仲舒,以及杨时、李桐、胡安国、蔡沈、真德秀等人,皆赠太师,从祀孔子。明清两代祭孔基本上如前代制。
为什么生前未曾走运的孔子,死后被奉为仪范百王、师表万世的至圣先师。因为帝王虽口含天宪,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只有为数不多的才称得上是有道明君。如吴孙皓、蜀刘禅、宋仁宗赵祯、清宣统帝溥仪等,则可谓昏庸型;如梁武帝萧衍、宋真宗赵恒、明世宗朱厚聪等,可谓迷狂型,佞佛信道,乃至弃朝政而只想炼丹求仙。也有难以归入这两类的,如贪财好货成瘾的明神宗朱翊钧,还有白痴一样的晋惠帝。有些帝王对自己的地位不感兴趣,如喜爱木工手艺的明熹宗朱由校,嗜好演戏常粉墨登台唐庄宗李存勖。昏庸无能、粗暴迷信的帝王在历史上是比较多见的。汉代的匡衡说:“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息之道。”显然,孔子已成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圣人了。帝王们抬出孔圣人的旗号,目的是为了说明自己统治是有权威性的。明清之际儒学大师李顒对此有很好的说明:“古今有治统,有道统,治统不可一日无人,道统亦不可一日无人,而道统与治统尝相为盛衰而终始。故治统开,道统始开;而道统盛,治统愈盛。道统之大成集于孔子。”把“治统”与“道统”纳入到圣人崇拜的框架中,这从“不可一日无人”的话中即可知晓。皇权以及与此相应的制度是“治统”,孔圣人之教诲就是“道统”。明代名臣吕坤说得更干脆:“亘古五帝三王不散之精,铸成一个孔子。”到了近代,李大钊提出,要把“孔子本身”与“历代帝王所雕塑之权威”作出甄别。“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且倡民权自由之大义,亦未可知”,而后者则成为“专制政治之灵魂”,得非“掊击”不可。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思想,在该社会里成为具有主宰地位的理念,那是题中应有之义。
三
圣人崇拜之所以能持久,有帝王出于“弘我王化”的“治统”与“道统”合一的因素,还有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阶层持久性的自觉认同。前者是以行政命令、权力支配下推行的外在强制,后者则出自内在的自觉,是发自心灵深处的。
视孔子为圣人而顶礼膜拜的,首先不得不提及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把孔子列入“世家”,是历史编纂学上的一种破格。不同其它列入“世家”的贵族,这是一个文化学术的传承所成的“世家”。在《孔子世家》结束时,司马迁的赞颂可谓深契孔子学术与人格的真谛:“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司马迁奉孔子为“至圣”,认为时光流逝而其影响从未消却过,众多的贤人、君王则“时则荣,没则已”。孔子整理古代典籍,教授弟子,不仅是文化史上的壮举,而且是重要的政治活动。孔子教出来的学生,不少人为将相,或为王者师,在当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司马迁的《史记》,是后世史书之祖,其对孔子学术与人格之尊崇,为后世大多数史学家所承继。从汉末到魏晋,为中国学术文化一大转折的时期。旷放睿思的玄学替代了定于一尊的儒学。一些玄学家畅谈义理多本自老庄,但谈圣人的境界仍以孔子为标准。南齐周顒曾直截地指出,“王何旧说皆云老不及圣”郭象承何晏、王弼的余绪,仍尊孔子为“至人”、“圣人”。可见玄学家虽大畅老庄义理,但在人格崇拜上仍以孔子为圣人的标准。《晋书·文苑传》记载了李充的一段话:“夫极灵智之妙、总会通之和者,莫尚乎圣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载之遗风,则非圣不立。然则圣人之在世,仕言则为训辞,莅事则为世轨,运通则兴时隆,理丧则兴世弊。”圣人是集了人世间智慧的大成,他的言论就是训辞,他的行为就是规范。这足以表明,就是在玄学的时代里,对圣人的崇拜一如以往。类似的材料很多,尤其是儒家学者的著作上,是充塞着对圣人崇拜言论的。
其次是一般的儒生,也即民间知识分子对孔子所作的崇拜。《庄子》一书中,经常可以见到称孔子为圣人的话。如《天运》中说:“孔子,此方之贤者也。”孔子不敢与圣人挂钩,而先秦诸子大多称孔子为圣人,虽各自理解的不尽相同。两汉对孔子崇拜之有力,与董仲舒、汉武帝之努力相关,然纬书对孔子的神化,也起了极大作用的。纬书作者已不可考,把他们视为一般的儒生还是可以的。唐君毅认为,纬书之产生是经生与方士的糅合,为“儒家与阴阳家方术之士思想之混合品,而表现汉代之民间之知识分子之宗教思想,而只假托诸孔子者。”纬书中关于孔子的描述,带有浓郁的神学色彩。纬书对孔子的神化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感生。据《春秋纬演孔图》记载,孔子是少女颜征在梦中与黑帝性交后生下的。感生这一观念,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由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的时期,多见于各氏族男性始祖的降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诗句即为明证。作为“素王”的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未处天子之位,自然也应当有这样的感生史。二是神异。具有神性的孔子,有异乎常人的特征。头象尼丘山,四周高中间低。身长十尺,大九围,坐着象龙,立着象牛。此外,孔子海口、牛唇、虎掌、龟背,舌头的纹理有七重等等。三是制法。《春秋纬演图》说:“孔子论经,有鸟化为书。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书上,化为黄玉,刻曰:‘孔提命,作应法,为赤制。’”孔子担负了上天给他的重大使命,代天立言,为后王制法。确切地说,是替火运的赤帝汉朝制法。由纬书可知,孔子已被汉代民间知识分子作了人格上的神化,俨然成为一个有意志的人格神。代天立言,为后王制法,孔子这一神圣化的形象,在汉代确立而世代延续了下来。
第三,各个时代中不同领域中的杰出人物,对孔子的膜拜也是不绝于史的。史学家司马迁、文学刘勰、诗人李白、皮日休则为内中的代表人物。后于孔子五百年的司马迁,尝以史学对孔子作人格上的憧憬,已如前述;后于后司马迁五百年的刘勰,意在用文学理论对孔子作人格上的崇拜。刘勰自幼深受佛教洗礼,出仕以后,也没有中止其佛教活动。但从《文心雕龙》全书内容看,又以尊孔崇经为主旨,其书以《原道》、《征圣》、《宗经》为头三篇,即可窥见其用心。最后一篇《序志》畅明其对孔子的崇拜,意在点明写作《文心雕龙》的目的、意图、方法和态度。在他看来,自有人类以来,再也没有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了。在梦中随孔子南行的刘勰,对孔子托梦于他感到无比的兴奋,他认为,对圣人的崇拜,最好的办法是给经书作注解。不过从经学的角度看,马融、郑玄在这方面发挥得已很精当,即使有什么深入的见解,也难以自成一家。因此,他试图从文学理论的视野来作一番努力,故“《文心》之作,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文心雕龙》之问世,其间深深蕴藏着刘勰对孔子的学术与人格的极度崇拜。自魏晋以降至宋元明清,文学家推崇孔子人格者代不乏其人。李白之诗颇多隐居、任侠、求仙之情调,也有嘲笑儒生的诗句,“鲁臾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孔子人格的尊奉,“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对孔子人格的崇拜,诗人率多与思想家有深契相印之处。生活在晚唐时期皮日休,是极具个性的诗人,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称,《皮子文薮》一书“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他的圣人崇拜情结不逊于李白:“伟哉!无子后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没,知天地而终。”在他的心目中,孔子要比尧、禹还要伟大:“帝之圣者曰之尧,王之圣者曰禹,师之圣者曰夫子。尧之德有时而穷,禹之功有时而穷,夫子之道久而弥芳,远而弥光。”尧的道德、禹的事功是有局限性的,而孔子之“道”越是弥久而光芒益显。也就是说,孔子对后世的垂范作用,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
四
历史上许多哲学家,他们的理论体系的构筑、永垂后世的名著,与圣人崇拜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一种是借孔子的权威来畅说自己的学说。最为突出的是康有为,被时人誉为“南海康圣人”的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中,把信而好古的孔子,改塑成讲民主、信进化的孔子,为戊戍变法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六经》之中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尧、舜、文王,都是孔子改制时所寄托古圣先贤;《六经》描绘的尧、舜、文王的盛德大业,都是孔子对民主制度的理想所在。
这样的引伸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满,湖南人苏舆看出了康有为托古改制中所弥散着的西方民主意识。他说,甲午战争年代以后,社会上“邪说横溢,人心浮动”的根源,“始肇于南海康有为,弟子启超张其师说,其言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说辅之。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申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仇恨与恐惧之心,跃然纸上。而赞成者经学家皮锡瑞有另一种说法:“中国人重君权,尊国制,猝言变革,人必骇怪,故必先言孔子改制,以为大圣人有此微言大义,然后能持其说。”借用圣人的言论与经书的命题、范畴,以著作的方式,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是当时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也是康有为借孔圣人之中口,以托古改制的手法,以达到维新变法目的的真实原因。
二是通过注释圣人的著作,来表达自己独创性的思想。玄学创始人王弼,在对《论语·述而》中“志于道”时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于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是道路不可体,故但志慕而已。”这是以道家之说去界说孔子的“道”。综观《论语》,“道”的含义是具体可知的。一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方法,二是治国安民之术,孔子以此作为人生奋斗的目标。王弼以为,“道”是贯通一切事物的,但又是人的知觉无法感触的。恍恍惚惚,只能心中欣慕而已。在先秦儒道是对立的学派,王弼为创立玄学的需要,把儒道合而为一。于是孔子的“道”被王弼赋予了老子本体论的意味,其内涵为老子的“自然无为”,孔子的“道”本义大相径庭。
三是以孔圣人之学(“圣道”)为学问的正宗所在,以此来区别正邪的标准。王夫之《张子正蒙注》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作此书是有感于张载的《正蒙》,“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救来兹之失”是说,宋明理学到了王阳明那里,已经是“诬圣之邪说”了。对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王夫之认为“宋自周子出,而始发明圣道之所由”,以为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与“圣道”相符。二程对周敦颐的学说有所发展,“二程子引而伸之”。到了二程的弟子游酢与谢良佐,已见到了佛教渗入之痕迹。到了明代则变本加厉了,先是白沙学派的创始人陈献章,禅学的味道已经是很明显的了,“遂显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集心学之大成的王阳明,王夫之以为是异端邪说,与“圣道”背道而驰。王夫之把理想中的学术,尊之为“圣学”。
四是以孔子的言论作为真理的标准。如吕坤所说:“师儒相辩于学,曰:孔子有言。则寂然不敢异同矣。”“异同”就是不同的意见。从人的认识能力来说,现实中的事情,是会反映到人的头脑里。但对同一事情人们会形成不同的看法,就产生了分岐。分岐是多样的,有细微差别,也可能是重大分歧。对同一认识对象,人们产生不同意见(“异同”)是正常的,不可能把人们的想法整齐划一起来。相反的是,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以愈益接近真理。儒生间相互辩论,有了不同的意见。有人举出了孔子的言论,大家寂然无声。“孔子有言”,成了真理的唯一标准。原因很简单,孔子的言论是达到了“极精极纯而至善”的地步:“予于《孟子》此章,脱去言诠,探他底蕴,所谓‘知言’者,不是知其他的言,只在孔子一人身上,知其言极精极纯而为至善也;只是将孔子之言,去尽知天下古今群圣群贤之言,皆不如孔子一人之言为至善也。”孟子说,“知言”是他的特长之一。其本意是说,他擅长对错误的言论进行分析,抓住它们的弱点,如对告子、杨朱、墨子等到人的批驳即是。阳明后学的罗汝芳,则附会到圣人崇拜上去了。孟子的“知言”,在罗汝芳看来,就是要明了孔子之言达到了“极精”、“极纯”、“至善”的地步,并且超越了古今普天下的圣贤。显然,这种超越时空的真理观。这样的概念到黄宗羲那里,有进一步的提升:“余以为为孔子之道,非一家之学也,非一世之学也,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孔子之道”不仅决定人间社会的伦常,而且还在天地万物及其运动中显出其主宰的价值来。“孔子之道”被黄宗羲抽象上升,是决定天地万物运动不息的精神实体了。
五
19世纪末,严复对国人主权意识的极度淡薄,与对圣人的顶礼膜拜,有过深刻的揭示:“中国人之斤斤与外人相持,亦均以新法有碍孔教为辞,若欲以国殉之者。旅顺、威海、胶州之割,关税、厘金、铁路、矿产之约,举国不甚措意,偶有言及者,如秦人道越人之肥瘠。独至春间,独逸营兵狼籍即墨孔庙之事,乃大哗愤。士夫固然,商贾之徒,亦颇洶洶。”严复所说的外国士兵践踏即墨孔庙事,是在1898年。是年,俄国强租旅顺与大连,而英国看中威海卫。湾,英、法等国公司,在山西、河南、云南等省,获得矿产开采权。也在这一年,德国强租胶州湾。严复这一刹那间的真实记载,凝固下了国人对圣人崇拜观念的执著。民众国土的割让、主权的丧失可以漠然视之,而于孔庙的保护则备为关注。
这段材料给人们以三点启示。一是“动欲为圣贤”的国民文化心态,是先秦以降国人圣人崇拜传统的沿袭。时间跨度达二千多年,不因封建王朝更迭而变化,也不因社会形态变换而消失。二是弥漫于社会各阶层之中,范围相当广泛,上有革命领袖,中有著名学者、士大夫,下则为商贾与一般民众。自知识分子到商人,对国土被强行租借、主权拱手于他人的事实持冷淡的态度,而于孔庙被外人践踏表现出如此的愤急之情?反思的结果就是第三个启示,即圣人崇拜千古如斯地沁入中华民族的心田之中。不同于西方人总是把理想寄托在上帝身上,中国人总是把希望寄托于圣人那里。有了圣人,就不再需要上帝了。在西方,人人皆可为上帝之子;在中国,则人人都可为圣人。上帝高高站在凡人之上,而“希圣”之后还是一个凡人。所以王阳明有“满街都是圣人”的论断:“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都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从王艮与王阳明的对话中,不难知晓,一个民族的哲学精神一旦形成,决不是僵死的的沉积物,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发源处愈远,它就愈益显得澎湃汹涌。这就是“动欲为圣贤”的国民文化心态的原委所在。
到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中。人们对于精通某种技艺或学问,而达到出类拔萃水平的能工巧匠、学者,喜欢冠以“圣”或“圣手”的尊称。如杏林中则称医道精明者为“医圣”,东汉末年的张仲景获此桂冠。“书圣”王羲之、“诗圣”杜甫、“药圣”李时珍,都是家喻户晓的。《水浒传》中萧让能模仿不同流派、风格的书法,几可以假乱真,誉之为“圣手书生”。20世纪80年代末,被时人誉为补白大师郑逸梅说:“‘圣’为儒家无上之称,而近人以圣者,如康有为就有康圣人之称号。又方地山善制联,人誉之为联圣。邓春谢之画石,艺苑推之为石圣。夏宜滋有卢同、陆羽癖,自制梅花、水仙、茉莉等花茶,清芬溢座,而茶中绝无梅花、水仙、茉莉等花,人称茶圣。又程砚秋得罗瘦公之捧场而名扬梨园,及罗瘦公捐馆,身后萧条,砚秋经纪其丧,人以伶圣许之。”除“康圣人”是从政治意义上界说之外,“联圣”、“石圣”、“茶圣”、“伶圣”等,均是由于擅长某一技艺而出类拔萃之故,荣膺“圣”这一无上之称号的。方地山擅长写对联,世人赞为联圣;邓春澍工画石,被艺苑推为石圣;夏宜滋精通茶道,自制的花茶清芬溢座,而茶中决无梅花、水仙、茉莉等花,人们称为茶圣。程砚秋能跻身于四大名旦之列,是与罗瘿公为其赎身之助与编剧之扶分不开的。但罗瘿公死后萧条,程砚秋不仅买墓地成其丧事,而且坚持定期祭祀,后人以伶圣称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三百六十行中杰出的人物或能工巧匠,都可以冠以“圣”的头衔。葛洪《抱朴子·辨问》中所说:“世人以人所尤长,众所不及者,便谓之圣。”从孔子至今,中华民族出现了许多圣人。只要不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刻意打扮成圣人的,他们的言行、思想、著作与技艺,内中必定有很多弥足珍贵的东西,值得今天继承和发扬。回眸历史,中华民族已经向世界贡献了很多的“圣手”。我相信随着中国在各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中华民族必将为涌现出更多的“圣手”。
不妨离开古代以儒学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文化环境,把眼光转到现代。1937年9月,延安陕西公学举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事隔四年,1941年10月,诗人柳亚子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赋诗时,写下了“鲁迅先生今圣人,毛公赞语定千春”的句子,可知毛泽东对鲁迅的赞语,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知道的人是很多的。20世纪80年代,聂卫平在几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屡克日本超一流棋手,人皆以“棋圣”称之。至今已近二十年,举国上下,未见有异议者。综上所述,对圣人崇拜挥之不去的情结,深深地扎在了炎黄子孙的心灵中。
本文只是对圣人崇拜,作为中国哲学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了论证。因为圣人崇拜具有普遍性意义上的传承性,为统治阶级、不同的社会阶层乃至于底层的民众所认可。至于圣人崇拜的种种学说及其对中国文化、政治、哲学、教育等领域的具体影响,本文难以详论。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