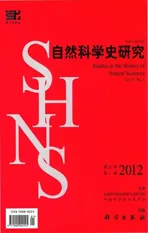明清之际定气注历之转变
2012-01-27王广超
王广超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中国古代历法为阴阳合历,即把朔望月和基于太阳年而划分的节气结合起来考虑历日安排。自汉代至清代,历日安排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变。第一次发生在隋唐之际:之前采用“平朔平气”法①所谓平气、平朔,指朔望月与节气时长固定,取大月为30日,小月29日,大小月交叉安排,平均起来一个月大概29.5日。可以通过连排大小月的方法使计算值逼近实际值。节气也是固定的,将回归年长度等分二十四份,每一份为一个节气。如东汉四分历,朔望月为,而节气长度为。这样,每积累32~个阴历月出现一次无中气月,为使中气相对固定于某月,此月置闰。每经过一次闰月后,下月中气会落在月初(偶有落在初二日),以后每个月中气日期逐步向前推进,历经上旬、中旬、下旬,最后在下一次闰月前的月份内落在月尾。这是由于每次更换一个中气比上一次多积累一个闰分造成的。,唐初改平朔为定朔,根据月亮实际运行周期推算朔望月。唐代至明末以定朔、平气注历②所谓定朔,是根据日、月同经的实际时刻确定某月的初日。由于月亮沿白道不均匀运动,按实际同经时刻确定朔日会导致在历谱中出现几个月连大或连小的情况。这在隋唐之际曾引起很大的争议,一度废止定朔法注历。后来李淳风提出“进朔法”,使四大三小情况不再发生,定朔法再度被采用。使用定朔平气注历对传统无中气置闰规则影响不大,其原因在于前后两个中气交气时刻距离约近30天半,而一个最大的“实朔望月”也不超过30天,故此非闰月这个月,均含有一个中气。而又由于月亮在天球上的视运动迟速不匀,直接反映在近点月上,在近地点两侧轨道半周范围内运行快,远地点半周运行慢,这种迟速以日为单位,经27日,所产生的积累量,在一个平近点月中自行抵消。故此,仍然积累32~33个历法月造成一个无中气月。关于隋唐之际定朔争议可参见陈美东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345~346页)。。第二次在明清之际:改平气为定气注历,即根据日躔行度安排节气。实际上,早在北齐(550~577)时,张子信即已发现“日行在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这一规律。自隋代刘焯(544~610)的《皇极历》之后,各历多列有包含一年之中太阳不均匀视运动的日躔表。而在定朔、交食的计算中,唐初历法即已应用定气作为太阳改正,但是注历依然采用平气。①如唐初行用的《麟德甲子元历》云:“凡推日月度及推发敛,皆依定气推之,若注历,依恒气日”。参见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184页)。陈展云在《旧历改用定气后在置闰上出现的问题》一文中详细地分析了清历采用定气法后在置闰方法上的转变,指出:采用“定气”注历,会出现两种无中气的情况,一种为“跨限”所致,一种为“累月”所致,清历对跨限所致的无中气之月不置闰,仅当累至一定月份后出现的无中气月才置闰。[1]可见,采用定气注历会使置闰计算变得复杂。从编算历日的目的是为敬授民时这一角度来说,采用平气注历更为可行,而定气注历并无必要。于是,就产生了如下的问题:何以传教士天文学家要改平气注历为定气注历?定气注历又何以最终得到朝廷的认可?黄一农在《从汤若望所编民历试析清初中欧文化的冲突与妥协》一文中列举了清初所编民历与传统历法的几项不同,其中包括定气注历[2]。此文的讨论仅限于清初时段,且着力于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中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在历日安排上所做的变革与妥协,对节气注历这一转变的历史脉络及其影响未作深入分析。本文试图从明清之际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出发,分析当时节气注历转变的始末及清初历算家对此转变的反应,希望从节气注历的转变方面理解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传入对岁次历书的影响。
1 明末改历中的定气注历
“定气”注历要追溯到明末改历。明代历法自明初确立后,一直没有改进。钦天监官员基本上根据现成的立成表推算天象,不太关注历理的探究,致使明末历法严重失准。一些不满历法现状的士人,建议朝廷改历。而当时正值传教士来华传教屡受挫折之际,他们最终确定了通过改历而获得朝廷认可从而实现传教目的的策略。崇祯二年(1629)五月发生一次日食,传统历法再次失准,而徐光启(1562~1633)等按照西法的推算得以应验,证明西法优于中法。于是礼部奏请开局修历,乃以徐光启督修历法,是年11月6日成立历局,开始翻译西法。历局的主要工作包括制器、测验、演算、翻译、制历等,自崇祯二年迄七年(1629~1634),先后进呈历书5次,共计137卷。其中的前三批是徐光启生前就已完成、并大都亲作润色审改的,而后二批是徐氏生前已作安排或已开展工作,继由李天经(1579~1659)完成的。其中的《日躔历指》和《日躔表》与节气推步相关。②本文使用了《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和《故宫珍本丛刊》两个版本的《西洋新法历书》,《通汇》版中收入的奏疏较全,而未收入日躔表,《故宫珍本丛刊》有日躔表部分。
新法根据日行位置计算节气,以冬至点为起点将黄道均分为十二份,每一份为一宫,规定:太阳交宫时刻为中气,交宫中点为节气。节气时刻的计算大体分为三步:先求天正冬至时刻,然后求本年节气日率,进而以节气日率逐一加天正冬至日干支及时刻,求出每一个节气的干支及时刻。而天正冬至时刻和节气日率的计算均以入宫和入宫中点为依据。从其推步技术来看,新法节气时刻的推算比传统大统历法更为科学,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1)传统历法日躔盈缩限固定在冬至点,而新法则认为盈缩限即远地点是移动的,并将这一变量纳入到了加减差的计算之中①《日躔表》收有《太阳平行永表》,其中有太阳远地点变动数据,远地点随时间逐渐偏离冬至点,一年移动45分。;(2)与传统历法相比,新法节气推步加入了地半径差、蒙气差修正。([3],60~67页)
在历书翻译即将完成之际,李天经将监局官生推算的甲戌、乙亥日躔细行表与其他编译历书一并进呈,并指出其中的节气推算与大统旧法不同([4],728页)。实际上,李天经在“崇祯七年闰八月十八日题本”中就已指出旧法推算崇祯八年八月秋分有误,认为旧法不明太阳盈缩加减之理,因此导致冬、夏二至的推算有几刻的差误,而推算其他的节气则有一、二日之差。([4],718~719页)
不过,就节气问题,真正引起崇祯帝注意的是关于崇祯九年(1636)雨水日期时刻的推算。李天经在崇祯八年四月进呈的“丙子年(崇祯九年)新历”中的雨水节气时刻与旧法所推相差两日。([4],757页)此一变动引起一些维护旧法的士人的批驳,崇祯帝命李天经详细奏禀。在奏疏中李氏论道:
盖论节气有二法:一为平节气,一为定节气。平节气者,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五为岁实,而以二十四平分之计日定率,每得一十五日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秒五十微为一节气。故从岁前冬至起算,必越六十日八十七刻有奇而始历雨水。旧法所推十五日子正二刻者此也,日度之节气也。定节气者,以三百六十为周天度,而亦以二十四平分之,因天立差,每得一十五度为一节气。故从岁前冬至起算,考定太阳所躔宿次止,须五十九日二十刻有奇而已满六十度,新法所推十三日卯初二刻零八分雨水者此也,天度之节气也。([4],757页)
可见,“日度”与“天度”这些概念成为李天经重新界定节气合理性的概念工具,传统平节气依日度而定,计日定率,而新法则依天度而定,因天立差。由于太阳之行有盈缩,日日不等,故此李氏主张不应拘泥气策以平分岁实,而应根据日行位置计算节气。
李天经主要以新法“合天”为理由论证定气注历的合理性,春、秋分的推算是他论证的突破点。传统岁次历书中,昼夜长度一般分注于重要节气之下②《崇祯十二年岁次己卯大统历》冬至日历注如下:“(十一月)二十八日辛巳冬至,十一月中,日出辰初初刻,日入申正四刻,昼四十一刻,夜五十九刻。”见《大明崇祯十二年岁次己卯大统历》(国家图书馆古籍影印室编:《明代大统历日汇编》,第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58页)。。由于旧法采用平气算历,而依据所算太阳实际位置计算昼夜漏刻,故此往往在春分前二日、秋分后二日注昼夜平分五十刻③如《崇祯十二年岁次己卯大统历》春分日为(二月)十九日丁未,却在十六日甲辰注“昼五十刻,夜五十刻”。页40;(八月)二十四日己酉秋分,却在二十七日壬子注“昼五十刻,夜五十刻”。见《大明崇祯十二年岁次己卯大统历》(国家图书馆古籍影印室编:《明代大统历日汇编》,第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52页)。。李氏提出这一安排存在矛盾。不但如此,李天经还组织实际测算春、秋分太阳高度为新法辩护,进而将新法推算春秋分之合理性推广到其他节气。([4],757~758页)
其实,对新法来说,改平气为定气注历势必会影响传统的置闰规则,而这是维护传统历法的士人难以接受的。如新旧法在推算崇祯十四年的节气以及九月十四日丁亥日食两方面存在差异,钦天监监正张守登等会同监局官生登台测候日食,证明测候与新法推算一一吻合。但关于节气及置闰问题,张守登说道:
谨按郭守敬之法所推太阳行度,春分亦开在本年二月初十日,正值昼夜平分之日。职等公随礼部提督黄家瑞并在局官生测得赤道平分亦与新法相同,历法所注可考也。惟于十二日为春分者,按大统立法冬至日行盈积八十八日有奇,当春分前三日交在赤道,实行一象限而适平。夏至日行缩,积九十三日有奇,当秋分后三日交在赤道,实行一象限而复平正。气盈朔虚积余生闰之法,所以与新法不同。若以太阳十五度为一气,则无积余之数,无积余凭何生闰。新法所谓庚辰岁闰四月正坐此也。臣等再四虚心考正,不敢偏执,犹不敢不求至当以仰副圣明。([4],842页)
11月中旬,上车湾郑姓渔民等三人在江豚活动区域布下了过河网,他们趁着凌晨1点左右巡护交接班的时间,卸下了机船的发动机,悄悄地往下游陶市方向驶去,准备收网。“这是江豚的活动区域,很有可能伤及江豚,马上把网交出来!”周家喜巡查时发现了这条船,看清是老熟人郑某某后,大声喊话。
可见,张守登提出郭守敬法并非不知日行之盈缩,按其日行盈缩法推春分与新法相同;只是旧法用平气注历,故此实际日行往往春分前三日、秋分后三日适交在赤道。在张守登看来,之所以用平气,是为能够产生闰余,从而进行置闰,而新法以十五度为一气,无闰余,故不能置闰。了解中国古代历法发展史的都知道,置闰的目的是为消除闰余,使十二中气与阴历月相对应,张守登此论有本末倒置之嫌。
事实上,采用定气也会产生闰余,而为使中气相对固定,也需要置闰。在“十五年新历”疏中,李天经就次年十月与十二月是否置闰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从中可见新法置闰规则:
臣谨按本局所推新法诸历,悉依天度起算,其节气交宫与夫伏见行度等项,皆在天真正之实行度也。所有置闰之法,首论合朔后先,次论月无中气。除十三年臣局依天度所推本年四月有闰,已蒙圣明洞鉴。新法合天,众心允服矣。兹臣恭进十五年新历,而十月与十二月中气适交次月合朔时刻之前,所以两月间虽无中气,而又不该有闰。盖新法置闰,专以合朔为主。若中气适在合朔时刻前者,是中气尚属前月之晦,则无闰。若在合朔日时后者,则前月当有闰,而无疑也。今臣等预察得崇祯十六年正月后有闰,因正月后止有惊蛰一节,而春分中气在次月合朔之后,是十六年当闰正月,而无疑矣。([4],847页)
文中提到的“前月之晦”,指的是前月朔望月之晦,而非历法月末日。因为历法一般以合朔所在日为初一日,而历法月只截取整日数,和它同月相应的朔望月的尾数会转入下月初一日。李天经主张推算闰月应以日月实际行度而非历法月为准。这就是李氏所谓的新法“悉依天度起算”。上文论述了新旧法推闰的区别:传统历法采取定朔平气法注历,置闰取“无中气置闰”法,即积累32到33个月后出现无中气月,此月置闰;而按照新法定气安排历日,会出现两种无中气的情况,一种是跨限所致无中气,另外为累月所致无中气,按李天经所述,前者不置闰,而后者置闰。
可以看出,采用定气注历会使历日推算变得更为复杂。事实上,从编算历日的目的是为敬授民时这一角度来说,传统的以平气注历而用定气计算日月食更为可行,定气注历并无必要。传教士天文学家之所以改用定气法注历主要出于传教的考虑。因为若采用新法定气注历,计算难度无疑会增加许多,原钦天监官员将不能胜任,故此需要长期地借助传教士天文学家编算历法,这将有利于传教工作。
但是,新法正统化的历程并不顺利。自修历之始,历局就陷入与保守派士人的纷争之中。尤其在李天经接替徐光启掌管历局以后,历局与东局之间的纷争尤为激烈。而在东局解散后,钦天监官员与历局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5]正因此,在译书完结近四年后,于崇祯十一年(1638),皇帝下诏,“仍行大统历,如交食经纬、晦朔弦望,因年远有差者,旁求参考新法与回回科并存。”([6],543页)这可以说是自李天经掌管历局事务以来为西法争取合法地位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突破。但诏书中未提及节气时刻参考新法,由此推断,节气推算仍是维护旧法的官员与传教士天文学家之间的一个主要的分歧。另外一个重要的进展发生在崇祯十五年(1642)十二月,皇帝下旨“另立新法一科,专门教习,严加申斥,俟测验大定,徐商更改”。([4],846页)可见,此时崇祯帝已下定决心启用新法。最终,于崇祯十六年八月,崇祯帝下诏,改西法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但不久国变,新法未在崇祯朝施行。
新法之所以最终得到崇祯帝认可,除李天经等宣扬的新法“合天”这一表面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使用传统方法步算的钦天监官生在历算方面的无能。这种无能不仅体现在计算日月食的失准方面,还体现在论证平气注历的合理性方面。如上文提到的张守登有关置闰的论证就是例证。正是因此,他们只能按照传教士天文学家设置的种种规则测验中西法的优劣。相比较之下,清初历算家对新法定气注历的批判更加恰当,详见下文。
2 清初中西历争中的定气注历
顺治元年(1644)五月,顺治帝入主北京。前钦天监官员将加紧推算的新朝顺治二年历本进呈给朝廷,摄政王多尔衮询问他们依据何法推算,答称照旧法。多尔衮说旧法舛误颇多,悉闻新设历局中,西士汤若望之法颇合天象,允宜用此新法,于是传汤若望来朝。汤若望将他们所推新法历本进呈,多尔衮于是命将新旧法历本互与磨勘。汤若望指出旧法历本大谬七条,而监官于新法历本则无谬可指,只是说“臣等所学之法俱系前贤所传,不忍舍列代成典,改就外国新法。”随后,亲王传旨:“西洋新法,推算精密,见今造历,准悉依此法,着汤若望、龙华民等测验天象,随时奏闻。”([7],279页)
于是,汤若望率同历局供事官生殚竭心力,于顺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完成新历的推算,十九日装演完成,二十日恭进新法民历式样。在二十日奏疏中,汤若望着重强调新法依据太阳入宫度数推算节气,可据此推算不同地区太阳出入方位及昼夜时刻等项。最终,新历样本得到顺治帝的肯定。支持旧法的钦天监官员在新历行将就绪之际,进行了最后的努力,与汤若望赴礼部“共对历法新旧之异”。在将对手所撰大统历书详加推敲后,汤若望于七月二十五日上疏列举依旧法推算历书中五处自相矛盾之处。其中的前四项即围绕节气推算展开。([4],868~869页)随后八月份发生的一次日食为新法最终获得颁行客观上帮了很大的忙,依据新法推算与实测再次密合,皇帝下旨行用新法。([7],280页)“顺治二年岁次时宪历”即依据新法推算,颁行天下。
新法之所以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得以正统化,笔者认为有如下三个原因:首先,当时正处在政权更迭时期,新统治者的异族身份相比之下更容易采用外国新法;第二,不容忽视的是新法在明末改历过程中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影响,正是因此才有多尔衮在原钦天监官员进呈历本时询问汤若望之法;第三,明末汤若望等传教士天文学家培养了一批精通新法的历算人才,正是这些人在短短的两个月中帮汤若望推算出历样,而他们后来在钦天监中被委以重任。当然,汤若望首先需要做的是裁汰原钦天监历官。这一意图通过顺治元年八月二十二日礼部对监、局天文官生的考试得以实现。[8]
进而,汤若望将自己培养的亲信安插进钦天监。十二月初九日,内院命重整后的钦天监速将其编制的职衔造册送呈。([4],897页)顺治二年二月,内院参考汤若望送呈的职衔名册,议定钦天监编制。该监最高主管官员为修正历法掌管印务一员,下领监正、监副、主簿各一员,并设历科、天文科、漏刻科三个单位,原回回科含所属官生尽遭裁汰。([4],902页)笔者将《治历缘起》中参与修历的监局官生和由屈春海整理的《清初钦天监时宪科职官年表》[9]对比发现,除汤若望掌管钦天监事务外,深谙新法的朱光大、刘有庆分别提升为管理历法以及监副的职位,原历局官生宋可成、宋发、李祖白、焦应旭、掌承、朱光显委以时宪科博士之职。
《顺治二年岁次乙酉时宪历》依新法推算,其中出现了一些与传统历书迥异的历日安排。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己酉)夏至,七月三日(壬子)为处暑。在此二月之间,夹两个月,只有一个中气,其中一个月为闰月。从其编排看,选含大暑气的月份为闰月,清末历算家汪曰桢对此进行过分析,认为“盖大暑加时在合朔加时之前,则中气尚属前月。”([10],186页)实际上,这正是李天经所谓的“新法尤视合朔后先”的一个例子。另外,由于依据日行宫度确定节气,而太阳在冬至点附近运行较快,致使在冬至附近容易出现一个朔望月内三个节气的情况。实际上,依新法推算的顺治三年十一月就出现了大雪、冬至、小寒等三节气。①据查,顺治三年十一月一日,大雪;十五日,冬至;三十日,小寒。参见《大清顺治三年岁次丙戍时宪历》(国家图书馆善本库顺治三年藏本)。还有,顺治十八年十一月份含冬至、小寒、大寒等三节气,致使阴历月与中气对应混乱。对此,汤若望于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初一日进十八年民历式样奏疏中进一步强调定气是天上真节气,与旧法平节气不同 。([4],964 页)
传教士天文学家改行新历、排挤钦天监旧臣的做法招致维护传统士人的强烈反弹。当时对西法抨击最为猛烈、影响最大的当属杨光先(1597~1669)。他对西方天文学较为系统的抨击见于他所著《摘谬十论》,其中定气注历为书中抨击的重点,第二、三、四摘与此有关。第二摘为“一月有三节气之新”,指责上文提到的顺治三年和十八年十一月按新法推算出现大雪、冬至、小寒等三节气,这在杨光先看来是不可宽恕的错误,认为自开天辟地至今未有此法也。三摘为“二至二分长短之新”,指责新法春分至秋分比秋分至春分所行日数多八日。四摘“夏至太阳行迟之新”,指责新法规定夏至日行迟。([11],921~922页)实际上,杨光先是当时维护传统士人的一个代表,其对于新法定气注历的批驳则折射出维护传统的士人对现行历法的看法。最终,在康熙初年,藉汤若望“选择之误”,将传教士势力逐出钦天监,李祖白(?~1665)等五名中国籍传教士天文学家遭处斩,汤若望被革职,幸遇天变大赦而获释。于康熙五年(1666)七月在北京病故。[12]自康熙四年至八年,岁次时宪历的推算由杨光先和吴明烜负责,先后根据大统历和回历推算。
“历狱”后京城中还有几位精通天算的耶稣会士,其中南怀仁的水平最高。南怀仁为比利时传教士,于顺治十七年奉召从陕西入京,纂修历法。([7],288页)他曾潜心研究杨光先所布的西法“十谬”,经条分缕析后,以“言必有凭,法必有验”的态度完成《不得已辨》一书。[13]针对杨光先对有关节气推算的指责,南怀仁指出:节气是依据太阳过宫度分决定的,每行三十度为一节气。之所以顺治三年十一月有三节气,是由于冬至前后日行疾,而此月恰逢大月。与此相应,夏至日行迟。故此,春分至秋分所经日数比秋分至春分日数多。南怀仁认为,杨光先等没有认识到日行的日数与度数之别,致使旧法所定节气与天行所差甚远。([14],16页)
康熙帝亲政后,曾数次申斥钦天监官员推算天象不准。后来,得知京城中还有几位善于历算的耶稣会士,于是派内阁大臣前去询问他们能否指出当时钦天监所算历书的疏漏之处。当时,南怀仁指出,历书最大的错误就是规定下一年(康熙八年)为13个月。([15],58页)事后,内阁大臣将南怀仁所指历法中错误一一呈禀给皇帝。次日,以南怀仁为首的几位传教士奉召进宫,与钦天监官员当面对峙,最终决定以圭表测算日影决定胜负。在三次赌测日影的竞赛中,南怀仁胜利,赢得了康熙帝的信任。[16]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二十六日,皇帝命将吴明烜所造的康熙八年《七政历》及《民历》各一本交与南怀仁,命其指出其中的差错。十二月,南怀仁奉旨将查对历本的结果上奏,所指旧法错误多集中于节气注历方面。([17],50~51页)
事后,康熙命图海等大臣赴观象台测验南怀仁、吴明烜所算历日,呈报结果是吴明烜测验逐款皆错,南怀仁测验即已相符,将康熙九年一应历日交与南怀仁推算,吴明烜交吏部议处。康熙八年二月初七,杨光先因历日差错不能修理且左袒吴明烜而遭革职。而吴明烜则很幸运地以监副的身份留在钦天监供事。([17],52~58页)
康熙八年三月,南怀仁授钦天监监副职衔,监理历务。指责先前钦天监官员按古法推算康熙八年历置闰出错。南怀仁指出,置闰当在九年二月。皇帝于是命礼部详查此事,钦天监官员多支持南怀仁,后来下诏“罢康熙八年闰,移置康熙九年二月,其节气、占侯系从南怀仁之言”。([18],391页)自此,定气注历得以长期行用。
当时,钦天监中有些人并不认可新法。据《三鱼堂日记》记载,陆陇其(1630~1692)曾于康熙十四年(1675)闰五月初二日会见漏刻科蔡九旌,蔡氏言“铜壶滴漏,交食节气,始设平日,不常设。……历主古法,不甚服西人。”([19],491页)可见,蔡氏对新法定气注历并不以为然。当然,对新法更为精到的批判来自于当时的历算家。
3 清初历算家对定气注历的反应
入清以来,《天学初函》、《崇祯历书》等天文学书籍广泛流传①据《三鱼堂日记》记载,陆陇其曾向传教士利类思请教有关西方天算问题,利类思推荐陆氏阅读新法历书,这些书并不难得到,因“书板皆在天主堂,得数金便可全印”,后陆陇其果然买了日躔表二本,乃西洋历书中之一种。参见文献[19],487、491页。可见,当时购买新法历书并非难事。,民间出现了一些精于天算的历算家。清初历算家中,尤以王锡阐(1628~1682)、梅文鼎(1633~1721)的影响最大,对清初“时宪历”改平气为定气注历持反对态度。
王锡阐是明末遗民,明亡后曾先后投水、绝食以求殉国,拒不仕清。在其天文著作《晓庵新法》中,以崇祯元年(1628)年为“历元”,以南京为“里差之元”。他对西法总体评价是:“谓西历善矣,然以为测侯精详可也,以为深知法意未可也。安其误而不辨未可也。”进而举出五处西法不知法意之处,其中的第一、第四、第五与定气注历有关。王锡阐认为中历的确存在岁差数强、盈缩过多的问题,但即便如此还不至于差过两日,而《历指》对中法春秋分差过两日指责纯粹是不明中法的意思。([20],433页)另外,在王锡阐看来,西法也存在内在矛盾:
而西法唯主经度。经度者,东西度也。以经度求黄赤距差,绝非平行。二分左右经度之一距差,几及其半,二至左右经度之一距差,仅以秒计。故但主日辰,则平气已足,若主天度则需兼论距纬。如四立为分至之中,中西皆然。今以距四十五度为立春定气,此时日距赤道尚十六度有奇,则所谓中者,经度之中,非距纬之中也。距纬之中在距至五十九度以上。设止用经度,亦祇可谓天度之平气,于日行南北未有当也。([20],595 页)
王锡阐的反驳可谓点出了关键。确实,西法定气依据十二宫计算,而十二宫则依据黄道经度划分。但实际测算太阳位置时,却以测量太阳的视高度为根据,由此推求太阳视赤纬,进而根据黄赤距差求出太阳黄经。但黄赤距差随黄经的变化并不均匀,故此经度的中点并不一定对应距纬的中点。因而,王锡阐说“故但主日辰,则平气已足,若主天度则需兼论距纬。”但西法并没有考虑后者,故此也并非完全按其所说根据天度计算节气。
不但如此,王锡阐指出,采用定气注历会导致闰月安排的错乱,出现一月有两中气或一岁有两个可闰之月的情况,并举出顺治十八年《时宪历》因安排闰月出现的一系列问题。([20],433~434页)当年历书算定七月应置闰,致使秋分中气落在八月初一日,也就是所谓的归余之后气尚在晦。另外,由于十一月份含冬至、小寒、大寒三节气,导致了本该在十二月份的大寒中气安排在十一月份。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以新法推算的雨水中气应在十二月二十九日,下一日才会出现朔日,但是,这样的话就会将作为首春中气的雨水安排在腊月末尾,钦天监历官不得已才退朔一日,将雨水安排在正月初一日。王锡阐认为这是钦天监官员的无奈之举,暴露了他们不明中法之意的缺陷。②其中的历日安排参考自郑鹤声的《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292~293页)。
总之,王锡阐认为定气注历并非西法的优越所在,西法强在“书器尤备,测候加精”。在他看来,最初徐光启翻译西法的初衷是不错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翻译有绪,然后令甄明大统,深知法意者,参详考定其意。”只是徐光启的继任者在翻译之余并未兼顾会通之法。([20],593~594页)
梅文鼎比王锡阐年幼五岁,开始历算研究正是杨光先挑起历争前后。由于是从中法入手研究历算,在早年的研究工作中表现出一定的崇中抑西的倾向。后来,在接触到《崇祯历书》后,通过认真研究,转向以西法为主。[21]关于中西历法的关系,梅氏曾有从“权舆”说向“西学中源”说的一个转变[22],而转变的契机正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月康熙对梅文鼎的召见,晚年做《历学疑问补》,宣扬西学中源说。
梅文鼎深受王锡阐的影响,学术取向上与王有很多相似之处,对节气注历的看法即是一例。在《历学疑问补》中,梅文鼎谈到对“定气注历”的看法。首先,梅氏指出中国传统历算家并非不知定气,只是以恒气注历,以定气算日月交食,并指出翻译西法的人没有详加考证,就称旧法春秋二分并差两日,这纯粹是诬陷古人的做法。那么,中法何以不用定气而用恒气注历呢,梅文鼎认为古人主要是出于置闰的考虑,对此论道:
问授时既知有定气,何为不以注历,曰:古者注历只用恒气,为置闰地也。……惟以恒气注历,则置闰之理易明,何则?恒气之日数皆平分,故其每月之内各有一节气、一中气,此两气策之日,合之共三十日四十三刻奇,以较每月常数三十日多四十三刻奇,谓之气盈。又太阴自合朔至第二合朔实止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奇,以较每月三十日又少四十六刻奇,谓之朔虚,合气盈朔虚计之共余九十刻奇,谓之月闰,乃每月朔策与两气策相较之差也。此月闰至三十三个月间,其余分必满月策而生闰月矣。闰月之法,其前月中气必在其晦,后月中气必在其朔,则闰月只有一节气,而无中气,然后名之为闰月。斯乃自然而然,天造地设无可疑惑者也。([23],11页)
然而,在梅文鼎看来,用定气会造成节气之日数多寡不齐,故此会出现一月内三节气,或在非闰月内只有一节气的情况,这就会导致“置闰之理不明,民乃惑矣”的结果。([23],11页)
可见,梅文鼎的论调与王锡阐基本相似,认为中法并非不知定气,只是出于置闰的考虑不以之注历,而强行采用定气则会产生闰月安排混乱的结果。与王锡阐仅指责传教士天文学家“不知法意”不同,梅文鼎对节气注历提出一个折中的建议,即仍以恒气注历,而用根据新法计算的定气分注于节气日之下,这样就可以使置闰之理明了无误,而定气之用也并存不废。([23],13页)
后来,钦天监依据新法推算嘉庆十八年八月当置闰,如果这样的话,当年冬至在十月内,就会出现南郊大祀不在仲冬之月,而次年的春分、惊蛰也将较早出现等一系列不合常理的问题。于是,嘉庆帝命钦天监再三详细通查。最终,钦天监历官根据康熙十九年、五十七年闰月安排之成例改嘉庆十八年闰八月置十九年闰二月。([24],512~513页)
4 结论
定气注历可以说是中国古历在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传入影响下的一个重要的变故。无可否认,从现代天文学意义上说,定气注历确实比平气更“科学”。但是,中国古代历法毕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其最终目的不是发现天体运行规律,而是依天体运行之规律敬授民时。就此来说,改定气注历其实并无必要。传教士天文学家改定气注历主要是出于传教的考虑。清初历算家王锡阐、梅文鼎从历法为敬授民时这一角度批判新法定气注历,认为此为“不知法意”之举。本文关注的问题是:何以“不合法意”的定气注历在明清之际得以颁行。当然,定气注历的科学性是重要的因素。李天经通过实际测验、理论推演等方式论证定气注历符合天度。而清初历争中,定气注历的合理性更是通过圭表测影得以彰显。如果“合天”是改定气注历的必要原因,而当时所处的变革局面则为定气注历提供了可能性。相较旧朝廷,满族统治的新朝廷更易接受新法。最终,新法定气注历在清代得以长期行用。
致 谢承蒙两位审稿专家对论文初稿提出宝贵意见,韩琦研究员指出文中的一些疏漏和不当之处,业师孙小淳研究员和国家天文台李勇研究员分别对论文提出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1 陈展云.旧历改用定气后在置闰上出现的问题[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5(1):22~28.
2 黄一农.从汤若望所编民历试析清初中欧文化的冲突与妥协[J].清华学报,1996,新26(2):189~220.
3 徐光启,等.西洋新法历书[M].汤若望,修订.第4册//故宫博物院.故宫珍本丛刊.第386册.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
4 徐光启,等(纂修).西洋新法历书[M].汤若望(修订)//薄树人(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学卷.第8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3.
5 石云里.崇祯改历过程中的中西之争[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3):62~70.
6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 黄伯禄.正教奉褒[M]//韩琦,吴旻.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
8 黄一农.汤若望与清初西历之正统化[M]//吴嘉丽,叶鸿灑(主编).新编中国科技史.下册.台北:银禾文化事业公司,1990.465~490.
9 屈春海.清代钦天监暨时宪科职官年表[J].中国科技史料,1997,18(3):45~71.
10 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M]//续修四库全书.104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1 杨光先.不得已[M]//薄树人(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学卷.第6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3.
12 黄一农.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J].清华学报,1991,新21(2):247~280.
13 黄一农.康熙朝涉及“历狱”的天主教中文著述考[J].书目季刊,1991,25(1):12~27.
14 南怀仁.不得已辨[M].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线装书库藏.
15 Golvers N.The Astronomia 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M].Nettetal:Steyler Verlag,1993.
16 王广超.明清之际圭表测影考[J].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31(4):447~457.
17 南怀仁.熙朝定案[M]//韩琦,吴旻.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
18 清实录[M].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19 陆陇其.三鱼堂日记[M]//续修四库全书.第55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0 王锡阐.晓庵遗书[M]//薄树人(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学卷.第6册.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8.
21 严敦杰.梅文鼎的数学和天文学工作[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8(2):99~107.
22 王扬宗.康熙、梅文鼎和“西学中源”说[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3):77~84.
23 梅文鼎.历学疑问补[M].卷2//兼济堂纂刻梅氏勿庵先生历算全书.魏荔彤,辑.第12册.清雍正元年(1723).
24 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M].第8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