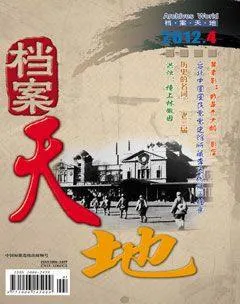撞上林徽因
2012-01-01洪烛
档案天地 2012年4期
我国著名的历史人物——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曾着力研究过北京周围的古代建筑,并合著《平郊建筑杂录》一书,他们简直为北京地区的古代建筑,唱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赞美诗。在他们的理解中,那些饱经沧桑的亭台楼阁、寺庙塔院也有其灵魂,为昔日的繁华吟咏着缠绵悱恻的挽歌,而且是神秘的历史最可信赖的证物。
正是基于这份刻骨铭心的爱,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提出了把北京改造成新中国首都的建议:第一,北京市应当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第二,必须阻止工业发展。因为它将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和住房短缺;第三,严格保持紫禁城;第四,在老城墙里面的建筑物要限制在两层到三层;在城西建造一个沿南北轴向的政府行政中心。只可惜除了保留紫禁城这一条得到采纳外,其他的都被政府否廖。彭真市长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南望对梁思成说:“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梁思成大吃一惊。他不敢想象,那个烟囱林立的北京城,那对于他太陌生了,也太遗憾了。
其后,北京城的面貌便开始了自明清以来最大的演变。古城墙全被拆毁,除了保留南面的前门和北面的德胜门以及东南角楼,其余的城门楼子也都被夷为平地……梁思成在他一生的最后20年里,一直遗憾地关注着这一切。在当时的北京,他恐怕算最心疼的一个人了。尤其城墙的拆毁,对于他肯定比拔牙还要痛苦,但他也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
梁思成一直认为,建筑是一本石头的史书,忠实地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不能否认历史,更不能切断历史;只是在当时破旧立新、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中,他的声音太弱小了,很快就被推土机、起重机的喧嚣给淹没了,但这弱小的声音也是很宝贵的,历史会感激他的。真难得他能保持局外人般的清醒,也许不是清醒,而是出于对北京城似乎狂热的爱。
梁思成在“文革”期间曾遭受揪斗,据说,他当时胸前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白字写着打了一个大大的“黑字”:“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为此,他踉踉跄跄地游行。但他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建筑学家,最终还获得了姗姗来迟的肯定。他的老友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结尾时记载:“梁思成于1972年1月9日逝世,终年七十岁。十四年后,在本来该是他八十五岁生日之际,清华大学举行了对他一生事迹的纪念会。一大批同事、学生、家属和朋友,以及一些官员参加了会。面对差不多七百名参加者,约有四十人致词颂扬他的人格和成就。”
梁思成出身名门,他是梁启超之子。但他又是北京之子——北京忠实的儿子。他虽然对中西建筑文化了如指掌,并且曾经留学美国,但他在北京,一直喜欢住在老式的四合院里。靠近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三号的一座四合院,就是他和林徽因20世纪30年代的旧居。
林徽因原是“新月派”诗人,后受夫君影响在建筑学方面也有造诣。她参加过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以及国徽的设计。1948年,女学生林洙是梁家的小客人,林徽因经常给她讲北京城的规划,谈建筑,培养了她对建筑的兴趣。林洙一直记得,林徽因特意向她看了哪些北京的古建筑,最喜欢哪几处,她回答最喜欢天坛和太庙,因为天坛经过长长的神道,到达仰视晴空的洁白的圜丘,真正给人以通向天堂的感觉;太庙门内的大片古松是那么宁静肃穆……
说来也巧,林徽因病逝七年后,林洙成为梁思成晚年生活的最后伴侣。她一直认为:“林(徽因)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生活的领路人。”
林徽因是1955年离开梁思成也离开这个世界的。用美国学者史景迁的话说:在寒风凛冽的北京,在最后一堵庞大城墙颓然倒塌之时死去的。
史景迁为《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写了“前言”:“我还看到,思成和徽因一道,乘火车,坐卡车,甚至驾骡车跋涉于人迹罕至的泥泞之中,直至最终,我们一同攀缘在中国历史大厦的梁架之间,感受着我们手指间那精巧的木工和触手即得的奇迹,以及一种可能已经永远不可复得的艺术的精徽。”对于梁思成与林徽因而言,古代建筑不仅是历史大厦的梁柱,也是艺术的祭坛。
印度诗人泰戈尔曾于1924年访华,估计留下过不少照片,刊登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的大小报纸上。其中一幅是他4月23日抵达北京后拍摄的,画面呈众星捧月之势:以白发、白胡须的老诗人为中心,其余人物分别是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及其父林长民……他们的身后是密集的树丛与花盆。仅仅依靠这模糊的背景,无法确切地辨别摄于什么地点。是故宫、西山,还是北大校园?似乎都有可能,总之是在北京吧。
出于礼貌,还是别有深意?徐志摩站在泰戈尔左首的最边上,中间隔着一袭旗袍、身材婀娜的林徽因,这三位诗人并肩联袂形成的完美格局,如同老树、鲜花与青藤,交相辉映。在泰戈尔的另一侧,站立着未来的优秀建筑学家梁思成等人。
徐志摩是泰戈尔在华访问的全程陪同,最先于4月12日,抵上海的码头,迎接来自印度的老诗人。这老少两代诗人之间不仅毫无代沟,而且一见之下,即引为知己,成为20世纪诗坛上著名的“忘年交”。在来北京之前,徐志摩还引导泰戈尔去杭州看西湖,在一艘桨声悠扬的舳舨上通宵达旦地赏月、吟诗、谈心。志摩甚至向老诗人吐露了自己对一位叫林徽因的北京姑娘的暗恋,以至泰戈尔见到林徽因本人后,都忍不住想扮演中国神话里的月老,替心有灵犀的一对青年男女牵起红线。泰戈尔倚老卖老,很仗义地替志摩去做徽因的“思想工作”,可惜,一番好心最终并未促成好事:少女的情怀像深潭般矜持,没有答应。
这段感情虽是徐志摩单方面的,已足以感染作为旁观者的泰戈尔了,他相信自己面对的是中国的一位“情圣”。年轻的诗人即使在单相思,也依然喷涌出照亮夜空的岩浆与烈焰,这燃烧的激情,本身就是无字的诗篇。泰戈尔甚至比林徽因更快地读懂了这份意思。
而林徽因未尝没有读懂,并非心如止水,只不过作为传统女性,她不得不要求自己尽可能保持冷静:徐志摩是有过婚史的男人,他的浪漫令女人们着迷,他的多情又令女人们畏惧……
其实早在两年前,徐志摩就亲口向林徽因求过婚,并表示愿与元配夫人张幼仪离婚。“这些年,徽因和她伤心透顶的母亲住在一起,使她想起离婚就恼火。在这起离婚事件中,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弃,而她自己却要去代替她的位置。”
这是善良的林徽因无法做到的事情,甚至比让她爱上一个人更难。即使徐志摩真是所向无敌的“情圣”,也闯不过林徽因这道关的,毕竟,这是一道林徽因自身同样无法闯过的关:她有着先天性的禁忌与顾虑。林徽因选择了那张与泰戈尔合影里的另一个人: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她后来果然成了梁启超的儿媳,而且,1928年正式举办婚礼。
徐志摩还是于1922年3月离婚了。梁启超作为其恩师,闻讯后特意写了封信加以谴责,劝诫徐志摩不要“追求幻梦中的极乐世界”,不要“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徐志摩给恩师复信:“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我灵魂的伴侣。要是我找到了她,那是我的运气;要是我找不到她,那是命该如此。”
其实,泰戈尔代徐志摩求情时,林徽因已“名花有主”,因而,老诗人的努力也是徒劳的。泰戈尔只能一声无可奈何的长叹罢了。他特意为林徽因赋诗道:“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这首诗或这个故事,使徐志摩显得更浪漫了,使林徽因显得更纯洁了,使泰戈尔显得更伟大了。
很快,徐志摩死了,这对林徽因是一次巨大的打击:永远地失去了一个高山流水的知音。她没有像伯牙那样摔琴。从此,很少写诗了。林徽因在给徐志摩写的悼词中说:“朋友,你不要过于看轻这种间接的生存,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着你的存在,而增加了生的意识的。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和兴趣相同的努力者,你不在他们中间的事实,将要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