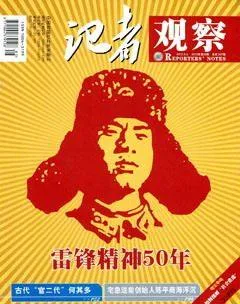“诚信为本”的市场悖论
2012-01-01
记者观察 2012年5期
在中国传统商业历史的管理遗产中,最值得骄傲和推崇的可能要算“诚信为本”了——几乎人人都说,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组织的成功,是来自于恪守“诚信为本”的原则。
无论是晋商、徽商、宁波帮、潮州会,还是传统老字号全聚德、同仁堂、张小泉等商铺,都异口同声地宣称:遵守“以义制利、诚信为本”的商业原则是其辉煌商业成就的独门暗器。商业评论家们也加入到了鼓动中:财源滚滚的商业制胜之道,是来源于“诚信”的竞争能力。即使是客户、消费者也告诉我们:愿意购买或消费商业产品的理由,是因为商家的“价格不二、童叟无欺”。这一切使我们不得不相信: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组织的成功,来自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原则;而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组织的成功史,就是一部“诚信”竞争史。
然而,中国传统“诚信为本”的商业原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遵守规则、公开公平”的市场信用原则,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两回事。中国传统“诚信”是一种人格信任,而非制度信任,君臣恩义、父子孝义、朋友侠义,都大于社会的规则、正义。“诚信”所遵循的是基于熟人之问的“私德”,而非基于社会规则制度的“公德”,它不能支撑现代商业市场公平公开的信用规则。
被深度误解的“诚信为本”商业古训
当百年西方管理已经使用计划、战略、效率等词语描述企业的方向与竞争能力时,百年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组织却一直坚信并宣称:只要遵循“诚信为本”的原则,利润就会滚滚而来。
3cc737345b1d8086e0c71de03407c9218d7985e83c1c2021217ea4eb0f82c489 虽然中国传统商人一直高声宣称必须“诚信为本”,然而“诚信为本”却是一个概念模糊不清的口号。来自传统商人两条铁打的生意规矩,一个是诚信,一个是不欺。显然,这是以同样的模糊性来解释模糊性。而另一些解释,譬如诚信就是“言必信、行必果”“人无信不立,事无信不成”,则体现了中国传统逻辑思维能力的弱化,一些概念常常处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中。
在晋商中,广泛流传着一个“诚信故事”:当年一位货主在晋商店铺中寄存了一批货物,货主因种种原因而导致多年未取——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法律合同条款而言,此事如果就此结束,既不存在欺诈问题,也不存在诚信的问题——显然晋商认为这是“不诚信”的行为,他们的做法是千方百计、历尽辛苦地寻找到了这位货主的后代,直到若干年后,终于找到了这批货物主人的儿子,并把这批货物亲手交给了他。直到这时,才是中国传统商人所认为的“诚信”的实现、完成。
中国传统商业的“诚信为本”原则,并非是遵循纯粹意义上的商业契约原则,而是遵守人际关系交往中的社会道德原则;更准确的说,中国传统商人所恪守的“诚信为本”,并非是描述商人与客户之间的法律“契约关系”,而是上升到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显然,对于中国传统商人、商帮来说,仅仅遵守市场交易商业原则的底线,并非是他们眼里的“诚信”,只有而且必须超越这个商业底线,进入到道德原则领域来衡量诚信,才算是中国传统商人眼里“诚信为本”的本意。
在人类社会的各种交往活动中,存在着“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两种基本的信任方式,一般来说,在交易性的商业交际活动领域中,所遵循的是契约、合同、规则等“制度信任”原则;而在非交易性的人际交往活动领域中,譬如家庭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等,则是遵循人品、道德、情感等“人格信任”原则。虽然“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但是二者之间却不能在不同领域随意性地取代或替换。在商业交易领域,如果以朋友义气取代制度规则,就可能引发商业纠纷的恶果,而在人际关系的非交易领域,如果父子兄弟间以契约合同维系义务关系,同样是可笑的做法。
借用梁启超先生“公德”与“私德”的区分法,中国传统商业所恪守的“诚信为本”原则,所遵循的是人格信任的“私德”,而并非社会秩序的“公德”。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文明下的乡土社会,每个人几乎都是熟人,都有程度不同的私人关系,因此,“熟人网络”关系成为了事实上的传统商业圈。在这样的“熟人商业圈”里,情感投入、信守道义、和气生财,成为了最重要的商业原则。虽然中国传统的“人格信任”,看起来是那么的温暖、感人、充满人情味,但却混淆了一个重大的、基本的商业原则,即商业活动的基础必须建立在遵守市场信用基本原则上,而不是建立在私人感情的道德基础上。
我们今天对于中国传统商业“诚信为本”的深度误解,正是在于没有将“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区分开来;没有将“相信熟人”与“相信陌生人”区分开来;没有将“遵守私德”与“遵守公德”区分开来。而是将它们混为一谈,以至于我们将传统“诚信为本”的古训,误解为是今天的遵守制度、信守规则的市场信用原则。当中国传统商业“诚信为本”古老商则,是以人际交往的人格、人品、情感信任方式或原则,替代了商业性的法律、制度、规则、交易方式或原则,这就给今天的企业管理造成了一个巨大障碍和麻烦,即传统“诚信为本”原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平、公开、透明的现代企业信用体系,不但是背道而驰的,甚至是在破坏市场公平制度原则。
传统诚信是“熟人网络”的游戏规则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流,而非商业经济为主流的社会,农业时代的竞争往往是围绕土地、财富和权力展开的。不入流的商人、商业始终处在社会的边缘状态。虽然中国传统社会里依旧充满了激烈的商业竞争,但这种商业竞争是非理性、非制度化的竞争,竞争主体的不平等性、竞争秩序的紊乱性、竞争结果的非建设性,导致了官商勾结、权利寻租的泛滥,商业机会主义的丛生。
在这种表面上看似混乱、无序、非理性的商业竞争中,隐藏着一种商业竞争的秩序、标准或原则,那就是“成为熟人”——客户之所以会放心大胆地进行交易,是因为对方是信得过的熟人;官员之所以敢收礼为商人办事,也是因为对方是无话不谈的可信赖的朋友。在这样的“熟人网络”里,冷冰冰的、法律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并不会给中国传统商人带来滚滚利润;而只有投入极大的情感因素,真心真诚地结交朋友,最终达到高度的“人格信任”,才会因此而声誉鹊起,财源滚滚。
在传统商业“熟人网络”中,欺骗的制止并不是来自道德化的说教,而是来自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本身的强大制裁性。过去山西有名的票号,对于借钱不还者的做法是:自绑其身,到票号门前,大喊三声“我是借钱不还者”,即可免除债务;这是现代人所无法理解的规则,但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做了,那么,他就将在本乡本土无立足之地,成为一个寸步难行的废人。
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法律保障和统一的商业竞争规则,因此“信任熟人”成为了几乎唯一可信任的标准。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商人们所说的“朋友就是财富”“做事就是做人”“先做人、后做事”的管理逻辑。熟人网络中“人格信任”式的诚信,是中国传统社会普遍的做人行为准则,而并非是专为商人或商业活动而设置。中国传统社会所遵循的“做人”诚信原则,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司马迁在《史记》中带给我们一个经典的“尾生抱柱”的诚信故事:有一个人叫尾生,与某女子约会于某桥下,但该女子未按时赴约;当时大雨如注,河水上涨,已经淹没了桥柱,但尾生不愿意失信于女子,宁愿抱着桥柱而被淹死,也不愿意离去。显然,晋商“历经多年磨难寻找货主后人”的诚信故事,与“尾生抱柱”的诚信故事,二者如出一辙。
在中国,信任度不是依赖法律,而是依赖血缘关系,所以,凡是家族兴旺的地方,很容易出现商帮、匪帮,而家族的凝聚力,又使得商帮充满了强大的组织能力,从而获得了多种可能的商机或利润来源,传统商人、商业需要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商业与市场”的关系。虽然晋商“历尽磨难寻找货主后代”被认为是诚信行为,但从现代企业管理角度来看,是难以理解的不讲成本、不讲效率的“愚蠢”行为。但是中国传统商人、商帮,确实因此而名声鹊起。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交往规模的不断扩大,熟人群体开始减少或解散,越来越多的“陌生人”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如果以“私德”替代“公德”,其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是可想而知的。
“诚信为本”中隐藏着“蔑视规则”的病毒
一个现象是:为什么宣称拥有“诚信为本”传统的中国商业,却在今天出现了严重的诚信缺失现象?而西方管理信守自私的“为己惠人”,却反而获得了我们所期待的商业诚信?
仅仅用西方企业市场历史的长久或是中国传统“诚信”文明的断裂,无法解释和揭示这种现象的真相,尤其是认为今天中国市场假冒伪劣泛滥成灾的现象,是因为传统“诚信”文明的断裂丢失所致的看法,更为恶劣。如果这个解释或看法成立,那么建立良好市场诚信环境的途径,就成为了呼唤传统“诚信为本”回归的道德行动,可是今天中国市场信用严重缺失的混乱局面,其主要根源正是传统的信任“熟人”、不信任“制度”,遵守个人“私德”、不遵守社会“公德”的所谓“诚信为本”的恶果。
中国传统“诚信为本”商业古训中,隐藏着“蔑视规则”的病毒。中国传统商业“诚信”的真相,是使用“人格信任”替代了“制度信任”。“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本不矛盾对立,即使现代企业管理仍然需要人格上的信任。但是中国传统商业之所以用“人格信任”替代、甚至是凌驾于“制度信任”之上,原因是“诚信”受制于“礼”,而信守于“义”。当遵守亲情、友情、熟人的承诺,比遵守法律、规则的承诺更重要时,“蔑视规则”也就成了一种必然。在商业世界中,漠视规则必然付出代价,20年来中国企业所经历的商业信用问题,从所谓的“三角债”问题、银行的巨额坏账到法院判决执行难、假冒伪劣泛滥成灾等等商业痼疾,本质上都是现代商业信用缺失所致,没有任何一方是胜利者或受益者,每一家坑蒙拐骗的企业,即是信用丢失的始作俑者,最终又是信用丢失的受害者。
“信用”已经成为了中国商业的稀缺资源,而在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地域环境里,是难以建立起大型的企业组织,企业间也难以进行有效的、低成本的合作。我们必须意识到,现代社会已经由“熟人世界”转变为了“陌生人世界”。面对越来越广泛的跨地域交往,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传统的信任熟人的“人格信任”不再有效,取而代之的是制度、规则的信任,依赖制度或规则信任,正是现代企业市场信用体系的内涵,即公正透明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才是今天信用的本意。
现代企业利润获取的来源和强弱,依赖于制度化的市场信用体系,信任度的半径越大,企业越可能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以及更多的商业利益;反之,越是依赖于传统的人格信任,企业活动的空间也就越狭小,建立起大型企业组织的希望越是渺茫;因此,建立中国现代企业信用体系,并不是呼唤传统诚信的回归,而是需要培育“企业公民”意识——现代社会的企业信用体系,要求企业要对于规则保持敬畏,需要摆脱传统诚信“人格信任”的阴影,学会并习惯于“制度信任”,这一点,对于渴望走出国门、实现国际化的中国企业来说,尤其重